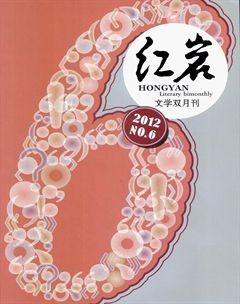無法撫慰
2012-05-08 03:40:12賀彬
紅巖
2012年6期
賀彬
1
1979年夏天,我堂姐從200公里以外她插隊的水縣,返回康城南岸區長江兵工廠自家門前的那棵大桑樹下時,她忽然發現,當年同自己一起奔赴廣闊天地的那些男女同學們,都有些迫不及待地結婚成家了。
那些十七八歲就離家下鄉的孩子們,在經歷了十來年的消磨和幻滅以后,重新涌回城里來,忽然就感到了蒼老。那蒼老催促著他們,找尋婚姻,搶占每一個工作機會,而我的堂姐,在這一場返城的浪潮中,卻成了最后的遲到者。
說起來,我姐在他們那一班同學里,其實更早地就接近于一個老人了。她繼承了我們家族少白頭的基因,剛去往水縣的山中時,右邊前額上就冒出了令人驚心的白發。加上她熱愛讀書,從長江廠搬來的那口舊木箱里,總是源源不斷冒出不知從哪里弄來的小說名著,除了《艷陽天》和《金光大道》外,還有《茶花女》、《基度山伯爵》這樣的搶手貨,甚至還有一本特別稀有的《紅樓夢》上冊。他們的那個生產隊長知道了這些,在用很有深意的眼光觀察了她一陣后,就將她任命為村小的民辦教師。她無意間成了那個20來人的知青點里的特權人物,不再需要下地掙工分,而是固定享受每天一毛五的津貼,有時候還有學生家長悄悄送來的雞蛋,咸菜,白面饅頭等等。我姐一向是有些懵懂的人,她安然享用著這一切,卻忽略了民辦教師的身份,讓她一次又一次地失去了招工回城的機會。
1978年的冬天,水縣那些剩余下來的知青們,私底下串連,然后相約到縣城里去搞了一次起義。……
登錄APP查看全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