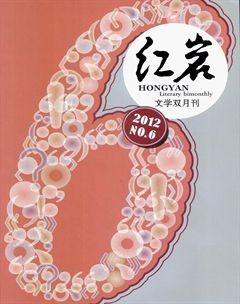滴答
2012-05-08 03:40:12王富中
紅巖
2012年6期
索先生的女兒
索先生把車開到懸崖邊,停下來的時候,太陽剛好昏黃地掛在河面,浪起了緊鎖的皺紋。
“你決定了?”我沒有看他。
“決定了!”索先生還有一絲焦慮,他按著喇叭一直不放。
“和小梅商量好了?”我側身過去,打開放錄機,我們百聽不厭的一首《滴答》。吉他聲敲打著懸崖邊上的馬兒生,那個叫做侃侃的歌手正唱著“小雨它拍打著浪花”。馬兒生長得極其茂盛,風一吹,毛絮揚得到處都是。
“還沒和她說。”索先生側頭過來看我,“不過,我想,她不會反對的。”
“這樣大的事……”我雖然為他急,但盡量平緩。
“決定了,就這樣!”索先生的喉結咕隆咕隆地轉了幾下,好像吞下了大量醞釀起來的口水。他打開車門,走下去,撿起石頭,砸向懸崖下面的河,把太陽砸碎了。他無所謂地聳聳肩,拽住馬兒生,折斷頂端的毛絮,一根一根地像箭,射入下面的懸崖。
把車倒在了泥濘的土路上,我們繼續向前開。沿途都是新翻的土豆地,新冒出來的嫩芽格外翠綠,糞便的氣味里夾雜著存放時間偏久的尿臊,這些都是上好的農肥。我敢肯定泥土里面有蠕動的蚯蚓,正覓食的螞蟻,和緩慢移動著身體的蝸牛。索先生還是有些心神不定,他對即將迎接的事情,還沒有做好最徹底的準備。我看得出來。我把《滴答》音量調大了些,侃侃的圓潤聲被車窗灌進來的風,搶了一些調子。“滴答滴答滴答/整理好心情再出發”,索先生也跟著哼起來,他從來都走調。
我們在幾間青瓦房圍起來的院子里停下來。一個六七歲的小男孩坐在門前的石凳上,看見我們下車,立馬擋住了門,他不允許我們進去,拿了一根細木棍趕著,嘴里還吆喝著什么,把我們當做了偷吃草的羊群,或者性格倔強的小牛犢。
登錄APP查看全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