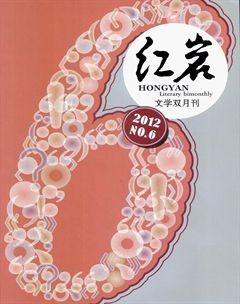喇叭花
2012-05-08 03:40:12姚念兵
紅巖
2012年6期
路是沒有錯的。
前些日耳聞,某人死在路上。累死的?凍死的?餓死的?病死的……沒準是孤獨死的。死者沒有親屬,應該在此地沒有,潦草埋了,不知姓甚名誰,也無從得知死因。死人是不說話的。
年紀?七八十吧。看著夠老的。
這些,都是高家緒告訴我的。他在殯儀館工作,燒人,他沒有算過,燒了五六年,沒有一百也該有八十吧。他穿著洗得發白的藍大褂,扣子掉了大半,迎風離去,像個鼓滿氣的球,走得艱難。
風是西北風,冬天里最難對付的那種。外出的人最怕遇到這種風,還夾雜細沙,別想睜眼睛。我趕著馬車,去澇溝趕集。車上裝滿大白菜,集上三胖餐館等著大白菜擺席。三胖的確很胖,腿短粗,肚子幾乎墜到地面。不過手很長,差點兒過膝。就是差那么一點兒,沒能成為王侯將相,倒成了大廚。他年輕時當過兵,打過仗,立過功,差點當上排長。后來和駐地女青年搞對象,提前復員回原籍。
都是白兔奶糖惹的禍。三胖一提到往日就會說這句話。我總會想起名叫《都是月亮惹的禍》的歌子。要是沒有那包奶糖,那姑娘也不會和我親嘴,一個糖一個,半夜還沒親完。教導員發現了,我的前途也完了。
西北風里,一對新人穿得喜慶,笑容燦爛地被擁進三胖餐館。卸了車,我進去偷把喜糖,三胖趁沒有旁人,照我懷里塞包煙。一出餐館,馬拖著空車迎上來。我坐上車,撕開錫箔紙,抽一支點上,馬輕快地走起來。它知道回去的路,不用我操心。
這匹馬有個好聽的名字,順耳。是母馬,但買來三年中,我還沒見過它發情。
登錄APP查看全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