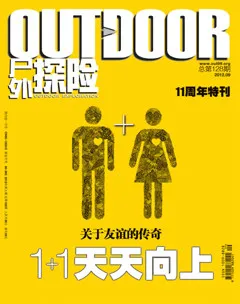索南達杰,不孤獨的駐守







盯著牛屁股和羊屁股,永遠翻不了身
1992年,青海治多縣年輕教師扎多和朋友在中學的改革失敗,憤而離職。恰逢治多縣成立西部工作委員會以開發可可西里,縣委副書記杰桑·索南達杰兼任西部工委書記,正招聘工作人員。扎多去找他的老師和同鄉索南達杰。
扎多三人來到縣委見索南達杰。這位38歲的新任縣委副書記對三位年輕教師非常客氣,盡管他們曾是他的門生。“請坐請坐。”他熱情地招呼。
“我們想跟你走。” 扎多說。
“為什么呢?你們有那么好的工作。”索南達杰問。
三人講述學校的遭遇,罵校長膽小無能,出爾反爾。索南達杰的臉色漸漸沉下來,扎多以為索南達杰為他們義憤填膺,于是繼續滔滔不絕地斥責,“我們和他勢不兩立!”
不等他講完,索南達杰變了臉,手指伸出,指著三人大罵:“沒出息!憑這些話,我不要你們!好像都是別人的錯,還背地里說人壞話!”
三人張口結舌,無言以對。
索南達杰頓了頓,語氣和緩一點說:“可可西里是無人區,到那里比索加牧民的生活還要艱苦,而且有生命危險。其實縣委可以點名要人,但那里太苦了,我要拉人走,他和家里人會怪我,所以希望大家自愿。你們要充分考慮一下。”
最后索南達杰在三十多位報名者中選了扎多一人。此后一年半,扎多跟隨索南達杰12次進出可可西里,直到索南達杰犧牲。
1985年10月17日,暴雪襲擊青藏高原腹地,災情最嚴重的索加鄉,26萬頭牛羊中,22萬頭凍餓而死。人們一生積聚的財富,被雪花一夜之間化為泡影。這場雪災刺激了索南達杰,他主動要求擔任索加鄉黨委書記,從1987年開始一干六年。
索南達杰曾告訴扎多,他一生所做“最偉大的事”是對上不交稅,對牧民不征稅。他不是傻瓜,知道這樣做可能免官坐牢,但牧民損失慘重,他實在不忍雪上加霜—實際上20年后,索加牧民的牲畜都沒恢復到1985年的水平。他曾想挑出境況好一點的人家來交稅,但牧民們都很艱難,矮子里拔不出將軍來。他往上級做工作,但上級不免稅,他只有一條路:抗稅。所以索加在交稅方面倒數第一,年年如此,他敢做敢當,處之泰然。
但他在任時,沒有索加人感激他,因為他冷峻寡言,從不示恩,人們不知道他為家鄉做了什么。只要他下鄉,聽說索書記來了,全村人誠惶誠恐接待他,在他面前甚至連話都不敢說。他對牧民并不噓寒問暖,做表面文章。在他任職六年間,獨霸一方,為索加人爭得許多利益,但他不謀私利,有一股凜然氣概,令人敬畏。有一個故事說,縣里開會,鄉黨委書記索南達杰遲到了,他身穿大衣,進得門來,會議桌前的所有人不自覺地站起迎接他,包括縣委書記。
但不管他怎樣努力,索加仍然貧窮落后。牧業是這個荒涼高原的主業,卻輕易被一夜大雪摧毀,這一陰影時時籠罩著他。他后來對扎多說:“索加盯著牛屁股和羊屁股,永遠翻不了身。”
20世紀80年代中期,可可西里發現了金礦,出現淘金熱。這個五萬多平方公里、與寧夏自治區面積一樣大的可可西里在行政上屬索加鄉,那里的礦產資源令索南達杰興奮起來,也許可可西里能救索加?
1991年,索南達杰給玉樹州委書記史國樞寫報告,提出玉樹州的五個西部鄉,海拔最高,氣候最惡劣,交通最不便,應該成立西部工作委員會,做出適合當地情況的發展規劃。史國樞將他的報告轉發全州,隨后在三個縣各成立了西部工委。索南達杰升任治多縣委副書記,兼任西部工委書記。他最初的目標是可可西里的金礦。
這里不是無人區,而是無法區
可可西里環境嚴酷,氣候惡劣,人類無法長期居住。站在這里,遠望蒼蒼茫茫,惟見雪山荒原,間或有高寒草原和高寒草甸,天地間一片蕭索。他們進入可可西里,才知道這是什么鬼地方:年平均氣溫攝氏零下4℃,最冷的地方年均攝氏零下10℃,氣溫最低時攝氏零下46℃。扎多跟索南達杰進入可可西里,大部分時候沒有帳篷,就睡在卡車車廂或吉普車里,每次睡下去,全身凍得麻木,聽著冷風呼嘯,擔心第二天凍僵的身體還能不能化開。
第一次進可可西里的路上,索南達杰讀著一本《工業礦產手冊》, “你要不學知識的話,就變成野牦牛了。”他對扎多說。
他們進入可可西里,一路見到許多被殺的藏羚羊:有的只剩骨架,有的骨肉完整,卻被剝了皮,血肉模糊。
此時可可西里盜金已近瘋狂,大量金農涌進可可西里非法采挖。有些淘金者夏季淘金,冬天打獵。后來知道藏羚羊的毛可以賣錢,于是盜獵者驟多。藏羚羊是藏北高原上的旗艦物種,但處于滅絕邊緣。野生動物學家喬治?夏勒博士估算:20世紀初,生活在青藏高原上的藏羚羊超過一百萬只,而到90年代中期,只有約七萬只。沙圖什貿易是藏羚羊日益減少的關鍵原因。“沙圖什”意為“毛絨之王”,指藏羚羊的絨毛,由它制成的披肩代表著稀有和奢華。偷獵者駕駛吉普車追蹤藏羚羊,在夜間包圍它們,用燈光照射使羚羊視覺消失,然后用槍大批屠殺。
索南達杰曾嘆道:“這里不是無人區,而是無法區。”
從可可西里回來,索南達杰空前焦急,很快成立了“野生動物保護辦公室”,后又成立“高山草場保護辦公室”。人們被他搞糊涂了—西部工委成立的目的是開發可可西里,現在怎么成了“保護野生動物”?
索南達杰雖沒有受過佛教教育,但藏族根深蒂固的傳統文化,比如眾生平等、不殺生、保護自然等觀念,已令他開始關心藏羚羊等野生動物的命運。索南達杰手提包里的書籍,由《工業礦產手冊》變成復印的散頁《瀕危動物名錄》。扎多搞不懂索書記在想些什么。從《工業礦產手冊》到《瀕危動物名錄》,不知不覺間,索南達杰對可可西里的認識發生巨大變化,可是他孤獨寂寞,沒人可以與他對話。他得不到多少支持,甚至吉普車的汽油也是靠西部工委三個人的工資墊付。但他一句怨言也沒有,從來不說別人的壞話,扎多這才明白,當他找索南達杰報名時,索南達杰為什么那么痛恨他埋怨校長。只有一次,在數次向上打報告得不到回音后,索南達杰嘆口氣:“在中國辦事,不死幾個人是辦不成的。”
最后一次巡山
1994年1月初,他們最后一次進可可西里。索南達杰這次十分鄭重謹慎,跟縣長借了一把七七式手槍,跟公安局借了沖鋒槍和一把生銹打不響的五四式手槍。
這次出行兵強馬壯,除了索南達杰、靳炎祖和扎多,還有向導韓偉林、借調的司機才扎西等。1月8日夜里11點45分,他們從格爾木出發。動身前,索南達杰給夫人才仁發了電報:“元月9日離格赴可,索。”沒有寫歸期。
最初幾天,他們抓獲了不少盜獵者,繳獲了二十多支槍和幾千發子彈。索南達杰把槍栓卸下來,將槍支和槍栓、彈夾分開,塞到吉普車的座椅底下。
15日,一行人頂風冒雪來到可可西里最西北角的泉水河河谷,這里是青海、西藏和新疆三省區交界處。他們在河床上發現了許多車轍,扎多興奮地說:“這是一幫大家伙。”
這一天雪大風狂,大家早上沒吃飯,好幾個輪胎又爆掉,人們情緒低落。索南達杰一直臉色陰沉,心情很差,沒人敢招惹他。下午六點多鐘時雪停了,索南達杰和扎多乘吉普車順車轍往前直追,將兩輛卡車甩到后面。追到一處河谷,這里彎彎曲曲,是個避風處,索南達杰讓司機停車,嚴肅地對扎多說:“你下車,等后面的車趕上來,告訴他們在這里扎營,等我回來。”
扎多依言下車,看索南達杰的吉普車遠去。白雪皚皚,山谷寂寂,天地間很安靜,他的心突然狂跳起來:“如果索書記碰到那幫大家伙,他單槍匹馬,還不被收拾了?”
他急跑到半山腰往遠處眺望,吉普車不見了,只有雪地中的車轍曲曲折折隱入山后。
兩輛卡車趕上來,扎多告訴靳炎祖,索書記命令在此扎營。“但我覺得索書記有危險,我們是不是追上他?”他問。
靳炎祖猶豫著說:“既然索書記讓我們扎營,還是在這等他回來吧。”
靳炎祖是扎多念治多中學時的老師。在只有三個正式干部的西部工委,索南達杰是他領導,靳炎祖是他老師,因此扎多總是服從者。但今天扎多做出反常舉動,他跳上另一輛卡車,“快,快!”他沖司機叫。東風卡車猛地躥出去,“轟轟”的巨響回蕩在河谷。
“東風”追出好久仍不見索南達杰的影子,天漸漸黑了,汽車減速順河谷前行,忽然前方燈光一閃,一個黑影沖過來。扎多一驚:盜獵者?急令司機停車,挺起腰,將槍握緊。
來人很快沖到近前,車燈照耀下,卻是索南達杰。扎多跳下車。索南達杰以為來的是盜獵者,見是扎多,怔了一下,收起槍,跨上一步,手指扎多的頭,聲色俱厲:“誰叫你來的!”
“天這么黑了,我怕你有麻煩……”扎多道。
“誰是縣委書記?你,還是我?”索南達杰氣狠狠地叫,“這是戰場,只有一個領導!”
扎多打個冷戰。索南達杰比他高出一大截,氣勢洶洶站在面前,如同一座黑塔。扎多小聲說:“我帶車過來,是想……”
“你帶車?你說了算嗎?你是領導嗎?誰任命的?”索南達杰句句如刀。
扎多嘀咕說:“我以為你會有危險……”
“‘我以為,我以為’,你以為你是誰?你讀過幾本書?”索南達杰噴出的怒火幾乎要將扎多燒焦。
可可西里的寒風呼嘯著,刮起雪花打在臉上,扎多苦苦熬著,可索南達杰狂怒未止,扎多站在他面前,心里冤屈苦澀,悲憤難言。可可西里很苦,他這個受過許多苦的孤兒都無法忍受,每次離開老婆孩子,心中又害怕又悲傷,生怕再也見不到她們,但一有退縮之念就罵自己膽小鬼。可如此受苦,換來的是什么?他對索南達杰忠心耿耿,盡管后悔來可可西里,卻從未下決心離開他,今天也是為了他的安全,沒想到又被欺辱。“我越待你好,你越欺負我!”扎多灰心絕望,心里反生出一股力量:“你罵吧,我這一次出去可可西里,絕不再回來!”
扎多打定了主意,心神穩下來,反而淡定許多,不再辯解。兩人坐進吉普車里,索南達杰坐副駕駛位上,扎多默默鉆入后排,不料索南達杰不解恨,扭過頭來繼續痛罵。
“好好好,你罵吧,”扎多心想,“我再跟你,我不是人!大不了再回去當牧民,沒什么了不起的!”他由害怕、傷心、絕望,漸漸轉為憤怒。
快到宿營地時,索南達杰忽又轉身,將手指著扎多的鼻子,憤怒和劇烈的胃痛令他的手顫抖著。扎多痛定思痛后,傷心像冰融為水,汩汩流出來。他甚至聽不清索南達杰罵的什么,只覺得自己太傻。有人警告過他,跟著索南達杰沒有好下場,可自己仍然那么堅定地跟隨他。
車慢慢行駛,車窗外一彎新月升起,照著白雪覆蓋的可可西里,天地一片銀輝。車行至宿營處停下,扎多滿腔怨氣,操起鋼釬去河邊打冰燒茶。靳炎祖走到索南達杰面前,也許想給索南達杰消消氣,說:“我告訴過扎多不要再走了,他根本不聽話嘛。”扎多再也忍耐不住,回頭大喊一聲:“你閉嘴!”
“你說什么!”索南達杰勃然大怒,如一頭獅子般沖過來,右手將扎多手里的鋼釬搶去,左手“砰”一下推到扎多身上。扎多沖上去,一把將索南達杰推得“噔噔噔”倒退幾步。他像野牦牛一樣豁出去了,甚至想到了腰上的藏刀。“你憑什么?我也是單位的干部,不是你兒子,你算老幾?!” 他圓睜雙眼,惡狠狠地沖上司叫。索南達杰愣一愣,喊:“你個小娃子,你要是長到我這么高,我嚼都不嚼就吃了你!”扎多的怒火傾瀉而出:“我怎么就不如你?我不當官就不是人嗎?我也是男子漢!你能干什么,我就能干什么!你要是動手,我今天就跟你拼了!來來來,今天就是兩個男子漢來拼一拼!”索南達杰看著他,呆在當地。
扎多意猶未盡,用藏人中最惡毒的話罵索南達杰:“吃你父親的肉!”索南達杰忽然像小孩子一樣低下聲音說:“你跟我過不去不要緊,為什么要罵我父親?咱倆是一個村子,我靠得住的,不就是你一個人嘛,當年我從多少人里把你挑來的?”“沒人愿跟你,你不就是看我孤兒好欺負嘛!”扎多叫道。索南達杰說:“我把最好的槍給你……”
“別說什么槍不槍,”扎多喊,“明天我他媽的不拿了!”“你還這么說!為了你們的安全,這是我一個個求來的,子彈也是我一顆顆求來的,這些你都看到了……” 索南達杰說。
“我沒看見!”扎多喊。
索南達杰徹底軟下來,低聲說:“這兩年來,我在這里邁一步,你也邁一步,我們在可可西里的每個腳印,我們受過的苦,只有你我知道,我老婆也不知道嘛。”
“我不知道!你少來這一套!”扎多喊,“你不就是利用我嗎?我他媽的再也不干了!再也不受你欺負了!”終于痛快了的扎多越來越有勁。
索南達杰氣得胸膛起伏,怔怔地說不出話,忽然大喊一聲:“你走!”
“好,我走!”扎多大叫一聲,手持手電筒轉身便往黑暗中走,他知道自己單身一人走,不是餓死就是凍死,但在狂怒中哪還顧得上那么多。索南達杰在身后喊:“那電筒是西部工委的財產!”
扎多聞言,將電筒舉過頭頂,奮力砸到地上,電筒立即稀爛。他抬腳便走,一抹額頭,滿手的汗水。在攝氏零下40℃的冬夜,他全身火燙,恨不得索南達杰過來動手,他扎多會往死里打!雖然他比索南達杰弱小得多,但憤怒激起的勇氣,讓他敢以死相拼。
人們沖上來拉住扎多,靳炎祖也來勸:“我剛才只是隨便說一句嘛。”扎多有點不好意思,也知道自己往外走是死路一條,只好鉆進帳篷。他吵完后脾氣消了一點,卻也不想補救了,反正是撕破臉了,破罐子破摔吧。
索南達杰坐在帳篷里,用一條氈子將全身裹得緊緊的,縮成一團,臉上冷冷的滿是傷心絕望。靳炎祖給他倒杯熱茶,問:“要不明天休整一下,修修輪胎?”
“別問我,”索南達杰說,“我不是領導了,我管不了了!”
他掏出一大把藥片,一般人吃四片,他是一次十六片,一把一把地咀嚼,如牦牛吃草一般。他不喝水,也不吃飯,如同一個風燭殘年的老人,而不是那個40歲兇巴巴的壯漢。
索南達杰一夜輾轉反側,扎多卻睡得酣暢,他早上醒來突然覺得不好意思:“索南達杰來可可西里不是為私利,是為了家鄉,我和他是家鄉人,他又是我的老師,他又病又累,就是打我一通出出氣又有什么了不起?我為什么沉不住氣?”
索南達杰起床后自己收拾被褥,裝到口袋里。那是重活,平時是扎多幫他做的,在海拔5000米的地方,爬上卡車,將東西遞上去扔下來,就是扎多這樣的小伙子也勉力支撐,需要時不時停下歇一陣。看索南達杰喘著粗氣艱難地收拾行李,扎多一下子想通了:這么可憐的人,我何苦再添他煩惱?
索南達杰坐在氈子上,不喝水,不說話,只是捂著肚子扭頭看著地下。扎多知道他的病有多嚴重,親眼見他在可可西里痛得死去活來。扎多偷眼看他,越看越難過,終于鼓足勇氣走過去說:“索老師,我昨天錯了,對不起。”
索南達杰將頭扭向一邊說:“算了,別來這套了,我們兩個這輩子就這樣了,以后你走你的陽關道。”
扎多蹲在他面前,低著頭,手摳著地下的土,眼淚一串串滴下來,打濕了地下。索南達杰抬起頭,眼望遠處說:“別這樣了,你昨天說得很清楚了,我們各走各的路。”
扎多不知道說什么,“吧嗒吧嗒”掉著眼淚。索南達杰忽然端起杯子喝了口水,好像一下有了精神,喊:“韓師傅,今天修修輪胎吧,我們休整一下。” 扎多知道他不生氣了。
人們聽他開始說話,無不大慰。恰在此時,轟轟的馬達聲傳來,還沒回過神來,一輛吉普車已沖到跟前。人們手忙腳亂操起槍大喊:“停車!”吉普車遲疑了一下,猛地加足馬力沖過去。
人們舉起槍沖吉普車輪子“啪啪”射擊,索南達杰跳上自己的吉普車,大喊一聲:“注意后面!”吉普車“轟”地一聲追了下去。
扎多拿著槍沖來路緊跑幾步,果見有煙塵滾滾而來,是一輛卡車。那卡車司機來到近前,見面前五六個漢子黑洞洞的槍口對著自己,戛然停車。人們將車里的幾個人拉下來綁起,上車一看,滿車血淋淋的羚羊皮。
索南達杰押著逃跑的盜獵者回來。這一仗抓獲盜獵者八人。扎多存了警惕之心,跑到河對岸,那里看得更遠,見又有煙塵一路而來,“啊,又來了!”他大叫。
一輛卡車開過來,見有人用槍指著他們,立即放慢速度,人們以為要停車了,可車開到跟前突加油門,橫沖而過。人們一邊躲避一邊噼里啪啦開槍,水箱打破,玻璃“嘩啦啦”打碎,輪胎也被擊中,汽車一頭栽在路邊,汽油嘩嘩地流出來。扎多想,電影上打中油箱總會起火,看來并非如此。司機一側的駕駛室門上有三個彈孔,人們把司機拖出來,他“哎喲哎喲”地叫著,原來大腿中了一槍。
又是一車血淋淋的羚羊皮。
扎多把司機拖進帳篷,發現傷口青青的,并沒流血,正想怎么包扎,遠處又沖來一輛吉普車。索南達杰將皮大衣扔到地上,手拿小口徑步槍沖上去將車截下。過了一會兒他覺得冷了,對扎多說:“把我衣服拿來。”扎多奔跑著去拿大衣,心里很高興:索南達杰又理他了!
這一仗又抓獲12人,繳獲一支火槍、一支改裝半自動步槍、九支小口徑步槍和3000發子彈。
司機才扎西悄悄對扎多說:“韓偉林打了很多子彈,應該節省著用啊,不知道還要遇到多少人呢。”韓偉林手持沖鋒槍,一射一梭子彈,其他人只是一槍槍地打。扎多想到駕駛室門上的三個槍眼,一個念頭一晃而過:“原來是他打傷了司機。”盜獵者全部拿下,大家歡呼雀躍。索南達杰悄悄問扎多:“司機腿上那一槍是誰打的?”扎多說:“可能是韓偉林吧,聽說他沖車打了一梭子。”
索南達杰沉吟一下,肯定地說:“是我打的。他們討厭得很,我就對著門上打了三槍。”
扎多怔一下,心想:“他是不是要搶功?”
索南達杰悄悄說:“你回到治多千萬別說是他打的。他是老百姓,是我們拉來當向導的,如果這些人報復他,他就沒法混了。我們是政府人員,沒事。”
扎多呆在當地。槍聲甫歇,索南達杰居然想得那么深遠。
英雄之死
那些盜獵者中,一個受槍傷,還有個得高原肺水腫,不停咳嗽,看樣子快要不行了,情況緊急,必須立即送傷員出去治療。扎多建議索南達杰帶傷員先走,其他人押犯人殿后。索南達杰沉吟不決,最后說:“扎多帶兩個傷病員先走,到格爾木醫院,我和其他同志押犯人。”
如果索南達杰先走,那么永遠留在這里的就不是他,而可能是扎多了。
索南達杰把那支最好的七七式手槍給扎多,說:“你試給我看!”扎多裝彈演試。索南達杰又細細教他怎樣用保險,要他不要怕手冷,必須二十四小時持槍。他低低而堅決地說:“萬一他們有什么動靜,不管三七二十一,干掉!天塌下來我撐著!”
扎多覺得索南達杰過于緊張了,他后來才知道,對于形勢的險惡,索南達杰比他清楚得多。
索南達杰細細叮囑:如果迷路了,要認準北極星;要是陰天,就看地上的冰塊,哪邊化得多一點就是南方;如果發現一叢草,哪邊草密一點也是南方。“如果真的迷路,他們就是不打死你,你自己也活不下來,要是走錯了二三十公里,汽油不夠用,也回不來了。不要看車印,那也許是自己的。記住,所有的山和河都是東西走向。”
索南達杰從口袋里把所有的子彈掏出來,他的藥片和子彈混在一起。扎多從他掌心挑出子彈。索南達杰拍拍他的肩說:“一定要活著出去!”
索南達杰安排扎多坐后排的右邊,肺水腫病人坐副駕駛位,傷員坐扎多左邊,這樣扎多可以持槍監視兩人。他對肺水腫病人厲聲道:“你好好跟著扎多走,如果動了他一根毫毛,我下半輩子不當書記了,專門抄你的老窩!”
扎多的車慢慢駛離營地,回頭看,索南達杰還站在那里看著他。經過昨天的爭吵之后,在他們相處的最后一天,他與索南達杰才有那種他所盼望的兄弟情誼。
1月17日早上,索南達杰帶車隊出發,前方是租來的卡車,后面是西部工委的北京吉普,中間夾著幾輛盜獵者的車。風雪交加中折騰一天只走很少的路,天黑后便宿在大雪峰上。索南達杰讓卡車車廂上的盜獵者下來,坐在駕駛室里,否則會凍死。他自己駕車出去尋路。
盜獵者中后來被抓住的人供認,他們夜里悄悄商量,想把索南達杰吉普車下面的機油帽擰掉,這樣第二天開不多久機油漏掉,索南達杰困住,他們乘機逃跑。可晚上一直沒機會下手,索南達杰手持沖鋒槍守夜,一夜沒睡。盜獵者于是密謀了另一方案—把西部工委的人抓住,再趕上扎多的車,搶走傷員。
這一夜奇寒難忍,索南達杰走到靳炎祖和韓偉林跟前問:“有沒有凍壞腳?”給他們脫下鞋來替他們揉腳,生怕二人入睡后凍傷。如是者一夜三次。
第二天走了大約四五十公里,來到太陽湖附近的馬蘭山,此處地面犬牙交錯,北京吉普顛簸嚴重,索南達杰已經三天沒吃飯,幾天沒睡覺,身體極度虛弱,受不了顛簸,于是坐到老馬的卡車上。卡車比吉普車平穩一些。西部工委的北京吉普里只韓偉林和靳炎祖兩人,以及所有的資料、筆記、地圖、行李和幾十條槍。
行至太陽湖西岸時,索南達杰所乘卡車兩個左輪爆胎,索南達杰對韓和靳說,加速前進攔住車隊,讓他們燒水做飯,“幾天沒吃飯了,一會兒我們過來喝個熱茶。”
靳和韓領命而去。晚上8點,他們在太陽湖南岸趕上大車隊,讓租來的車去接索南達杰,其他所有的吉普車和大車排成“一”字形,他們則將西部工委的吉普車停在車隊的對面。“好好好!”盜獵者連連答應。
韓偉林坐在駕駛位上,下體裹著大衣,冷得要命。太陽要落山了,可可西里能將人輕易凍死。靳炎祖好久沒見那些人下車燒水,對韓說:“我去看看。”他把沖鋒槍放座位上,挎著一把手槍徑直走向中間的吉普車。“你們怎么不燒水?”他問。
一人下車說:“水燒著呢,局長,外面太冷了,進來坐。”他們都喊政府的人“局長”,也不知哪來的規矩。一人在吉普車里拿噴燈噴著火,火上是一個鐵杯子,里面的水快冒汽了。
靳炎祖好幾天沒喝水吃飯,那杯熱水具有巨大的誘惑力,于是他徑直上了后座。副駕駛位上一人急轉回身,一把抓住他頭發,旁邊的人抓住他胳膊,外面的人打開門,將他三下兩下拉出去,正想掙扎時,一個鐵棒砸在腰上,將他打翻在地。
韓偉林正在車上昏睡,什么也沒看見。一個盜獵者走過來招呼:“我們茶燒好了,你把碗拿過來。”韓偉林比靳炎祖警惕,說:“不要了,我不喝茶,”他又補了一句,“再說我也沒有碗。”“沒關系,我們有,給你端過來。”
那人一手端著碗開水,一手托著碗炒面過來。韓偉林把沖鋒槍放副駕駛座上,打開車門,兩手去接水和炒面,眼看要接到時,那人手一松,兩只碗掉在地上,韓偉林“啊喲”一聲,那人順勢抓住他的雙手往外急扯,韓偉林腿上裹著大衣,無法借力,“撲通”摔倒在地。一盜獵者從另一邊打開門,拿起沖鋒槍,七八個人圍上來毒打,打昏過去,醒來再打,很快身上血肉模糊。
盜獵者將兩人扔到西部工委的吉普車里,韓偉林被反綁在駕駛座上,嘴里塞了床單。靳彥祖被反綁在后排座上,頭被狐皮帽套上,擋住了眼睛。韓偉林雖不能動,但眼睛看得清清楚楚:
他眼看盜獵者拿出吉普車里的幾十支槍,裝上子彈。眼看他們人手一槍,排兵布陣。眼看他們將車發動,一輛輛車排成弧形,形成半包圍圈,面對索南達杰來的方向。眼看車燈熄滅,可可西里陷入沉默和黑暗,像死亡一樣令人窒息。
眼看遠處車燈閃亮,索南達杰來了!他的車在車陣前50米停下,過了幾秒鐘,索南達杰下車,像是有所警惕地慢慢走過來。
眼看盜獵者們慌亂起來,舉起槍,槍口對準他。
索南達杰下車前,他的司機聽到他自言自語:“可能出事了。”索南達杰拔出那支生銹的五四式手槍,“太大意了。”他說,然后走上前去。
一個盜獵者從對面走過來,好像與他打招呼,走到跟前,那人突然一個虎撲將索南達杰抱起,兩人撕打起來。只見索南達杰一下將其摔在地下,抬手一槍,那人再也不動。生銹的手槍居然打響了!
槍聲“叭叭叭叭”響起,一排排子彈射向他。所有車燈打開,照著索南達杰。他手持手槍沖那一片車燈射擊,就像舞臺上的孤膽英雄,又像一只藏羚羊,在燈光照射下失去視覺,任人槍殺。突然,索南達杰似乎中彈了,一條腿跪下,艱難爬起繞到車后。人看不見了,但槍聲持續,韓偉林和靳炎祖不斷聽到“嘩啦”、“砰砰”的聲音,那是子彈擊中汽車。后來方知,索南達杰憑一支舊槍打爛了大部分車燈。
槍不響了,可可西里靜悄悄的,一片死寂。
過了好久,一個盜獵者沖索南達杰的卡車司機喊:“把車開走,要不吃肉喝湯一塊干!”
那司機“轟轟”地將車開走。燈光下,只見索南達杰匍匐于地,右手持槍,左手拉槍栓,怒目圓睜,一動不動,猶如一尊冰雕。
沒人敢過去。即便死了,他也令人膽寒。
杰桑·索南達杰
(1954年?1994年),曾擔任青海省玉樹藏族自治州治多縣縣委副書記,于1992年創立治多縣西部工作委員會(西部工委 ),開展可可西里地區生態保育的工作。1994年1月18日,在與盜獵者的搏斗中身亡。1996年5月,中國國家環保局、林業部授予索南達杰“環保衛士”的稱號。
哈希·扎西多杰
跟隨杰桑·索南達杰從事以藏羚羊為主題的野生動物保護工作。1998年5月創辦了青藏高原第一個民間環保組織“青藏高原環長江源經濟促進會”。2002年加入三江源生態環境保護協會,現任協會常務秘書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