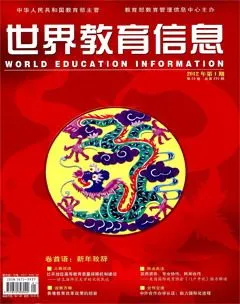追問“錢學森之問”



一、創(chuàng)新焦慮
“去年(2005年7月29日)看望錢學森時,他提出現(xiàn)在中國沒有完全發(fā)展起來,一個重要原因是沒有一所大學能夠按照培養(yǎng)科學技術發(fā)明創(chuàng)造人才的模式去辦學,沒有自己獨特的、創(chuàng)新的東西,老是‘冒’不出杰出人才。”
國務院總理溫家寶2006年如是說道,進而感慨萬千:
“我理解,錢老說的杰出人才,絕不是一般人才,而是大師級人才。學生在增多,學校規(guī)模也在擴大,但是如何培養(yǎng)更多的杰出人才?這是我非常焦慮的一個問題。”
在《父親拉著我的手》中,錢學森之子錢永剛對父親的深切懷念流諸筆端:“他晚年雖然臥床了,但他的頭腦不僅沒有‘臥床’,更加關注那些影響國家前途的大事,尤其是中國的教育。他多次和我談到這個話題。他認為中國的學校沒有形成培養(yǎng)創(chuàng)造性人才的機制。”
這便是“錢學森之問”。其實,此問并非錢學森原創(chuàng),之所以冠名,只因錢學森被奉為新中國自主創(chuàng)新的化身。“錢學森之問”敘述的無疑是一個古老民族集體性的創(chuàng)新焦慮。
二、精神遺產(chǎn)
2011年10月6日,大眾汽車集團特邀正在德國訪學的筆者作為主嘉賓出席在其總部舉行的一場沙龍,主題即為“錢學森之問”。如此設計,緣于德國學術期刊《教育領導》2011年刊發(fā)筆者的一篇論文,也算是西方輿論界對錢學森百年的一種紀念。
12月11日百年祭當天,坐落在上海交通大學徐匯校區(qū)的錢學森圖書館正式啟用。赭紅色幕墻映襯下的那臉可掬的笑容,如溫煦的冬日陽光,撫摸著這座海納百川的大都會。
出生于上海的錢學森于1929年以總分第三名考入鐵道部交通大學上海本部(今上海交通大學),1934年參加清華大學航空機架專業(yè)庚款公費留美生考試,被時任清華大學理學院院長葉企孫(“兩彈一星”23位元勛中有10位出自其門下)破格錄取。西安交通大學(由上世紀50年代中期上海交通大學內(nèi)遷部分組建而成)與清華大學2007年和2009年相繼開辦“錢學森實驗班”和“錢學森力學班”,旨在培養(yǎng)創(chuàng)新型人才,實至名歸。此舉似乎也意在重鑄昔日“百人一院士”之輝煌:錢學森耳提面命的中國科學技術大學近代力學系第一第二屆(1958級和1959級)學生共約500名,其中竟涌現(xiàn)5位院士。
顯然,上述高校的努力既非錢學森畢生孜孜以求的“大成智慧學”之踐行,“大成智慧學”亦非打開“錢學森之問”的金鑰匙。否則,錢學森在彌留之際何以仍對“錢學森之問”萬般糾結(jié)?否則,“錢學森之問”何以成為錢學森饋贈國人的一大精神遺產(chǎn)?
三、兩大高潮
錢學森晚年曾羅列自幼對他影響至深的17位老師,其中除了父母、博士導師與三位偉人(毛澤東、周恩來、聶榮臻),7人出自他求學6年的北京師范大學附中,有國文的、藝術的、數(shù)學的、生物的、化學的,當然還有時任附中主任(校長)林礪儒(建國后出任北京師范大學校長、教育部副部長)。錢學森之所以成為全才型大師,正因為這6個春秋通識教育的歷練,而附中的通識教育全然建構(gòu)于“誠·愛·勤·勇”(附中校訓)所彰顯的非認知性素養(yǎng)之基石上。1955年10月29日,突破美國封鎖線抵京翌日,功成名就的錢學森便心急如焚地趕回這所闊別20余年之久的母校。這一連串舉動恰恰是對“誠·愛·勤·勇”的完美詮釋。
“我對師大附中很有感情。在我一生的道路上,有兩個高潮,一個是在師大附中,一個是在美國讀研究生的時候。六年師大附中的學習生活對我的教育很深,對我的一生,對我的知識和人生觀起了很大作用。”
人生兩大高潮,刻骨銘心,上海交通大學的四年寒窗(實為五年,其中一年因突發(fā)傷寒而被迫休學)竟然不在列。作為機械工程系成績最優(yōu)畢業(yè)生,時任校長黎照寰特向錢學森頒發(fā)獎狀,以彰其“潛心研攻,學有專長”。至今,上海交通大學校園里還盛傳當年佳話:水力學考試和熱工實驗報告雙滿分。1989年2月,在為交通大學1934級畢業(yè)55周年紀念刊撰文時,錢學森盛贊母校“在當時的大學本科教學已是世界先進水平”。
至于上海交通大學失寵于錢學森,恰恰由于賦予該校的那輪“東方MIT(麻省理工學院)”光環(huán)。刻意仿效MIT辦學模式、一味復制MIT課程設置,與世界一流大學無縫接軌的慘痛代價便是特色的喪失。
而對北京師范大學附中,錢學森卻流露拳拳眷戀之情,這既出自他對林礪儒所嘗試的中國教育現(xiàn)代化之敬意,也體現(xiàn)他對林礪儒在附中主任就職演說中所倡導的“全人格教育”之推崇,更可被視作為一種他對“全人格教育”所蘊含的基礎教育基礎性之闡釋。
四、基教為本
輿論界時下流傳這么一種說法,即中國的基礎教育嫁接美國高等教育,可謂珠聯(lián)璧合。然而,高中畢業(yè)生赴美留學的浪潮日益洶涌澎湃,曠世奇才卻未曾橫空出世。盡管如此,中國的基礎教育仍留給人們無盡的想象:以懸梁刺股的精神來夯實知識。而這種想象已被翔實的數(shù)據(jù)證實。2009年展開的第四屆國際中學生評估(PISA)顯示,上海15歲學生在全球65個發(fā)達與新興經(jīng)濟體中獨占鰲頭,閱讀、科學、數(shù)學三大素養(yǎng)均雄踞榜首,且絕大多數(shù)上海學子能達到勝任力最高等級,而美國學生僅分別排名第17、第23和第31位。國際國內(nèi)專家于是異口同聲贊道,上海的基礎教育是在高端層面實現(xiàn)均衡化,即優(yōu)質(zhì)教育資源的普及化。這個結(jié)論著實難以令人置信,僅僅是陷于瘋狂且越發(fā)變本加厲的擇校現(xiàn)象便可把它駁得體無完膚。此外,民眾的直覺訴說著另一種質(zhì)疑:能力在多大程度上具有可測性,測試是否會導致學校教育偏向認知而放逐非認知性要素?測試結(jié)果能否成為學子人生道路的導向?
當然,全球第一,此佳績無可辯駁,問題在于,以多大的代價來換取此等輝煌。可以斷言,這個代價遠非筆者為《北京大學教育評論》撰文中所指出的“淚水+汗水”,而是創(chuàng)新人才的扼殺與創(chuàng)新精神的閹割,由此葬送基礎教育基礎性。
就在趕赴大眾集團總部當日清晨,筆者驚悉,“蘋果之父”斯蒂夫·喬布斯英年早逝。喬布斯與其說是天才,不如說是創(chuàng)新的象征。于是,喬布斯之死——創(chuàng)新——錢學森之問,便構(gòu)成沙龍的主旋律。
與錢學森輝煌的教育人生相比,喬布斯甚為坎坷,首推中斷學業(yè)(入學僅半年便退學)。而與喬布斯平分數(shù)字化世界的比爾·蓋茨(微軟創(chuàng)始人)和馬克·扎克伯格(臉譜創(chuàng)始人)同樣孤注一擲。就在2011年達沃斯論壇上,奧巴馬的前首席經(jīng)濟顧問、白宮國家經(jīng)濟委員會前主席、世界銀行前首席經(jīng)濟學家、克林頓內(nèi)閣的聯(lián)邦財政部長勞倫斯·亨利·薩默斯(Lawrence Henry Summers)津津樂道地說,過去25年來改變世界的是比爾·蓋茨和馬克·扎克伯格這兩位哈佛肄業(yè)生。而薩默斯的另一重身份是哈佛大學前校長。顯然,哈佛的偉績并非對杰出人才的孵化,而是對優(yōu)秀少年的吸引;造就世界IT這三位霸主的并非大學,而是基礎教育及其與家庭、社會的互補。
五、少兒啼血
誠然,對中國當今高等教育的痼疾切不可熟視無睹,但中國創(chuàng)新人才枯竭之禍根卻深扎于對未成年人的各級各類教育。從娃娃抓起,贏在起點,結(jié)果往往要么夭折于起跑,要么敗退于中途,要么乏力于沖刺。2011年寒假前夕,一首詩歌《媽媽,我壓力好大》因引發(fā)家長的酸楚與共鳴在互聯(lián)網(wǎng)上被瘋狂轉(zhuǎn)發(fā)。作者是南京一名小學五年級女孩,她如此傾述衷腸:
一分一秒一嘀嗒/外面的鳥兒早已飛回家/無論是寒冬還是酷暑/我都在家/我在家/不是擺弄芭比娃娃/也不是上游戲網(wǎng)站4388/而是拿起筆在奧數(shù)題上比比畫畫/啊/壓力好大/我真討厭黑板上5678/什么時候我能給自己放一個假/一株草和一朵花/我都希望去探索它/啊/壓力好大/我真希望和小伙伴玩娃娃家/你當爸爸我當媽媽/照顧寶寶直到他長大/時光一天一天被學習打發(fā)/學習的內(nèi)容難度也越來越大/媽媽,我想告訴你/長大的我不會沒有出息/不要讓大自然和我沒有關系/給我放個假,好嗎/媽媽,我的壓力真的好大
面對少兒如此啼血,任何對基礎教育的修補或診療均難以化解民眾心中的“錢學森之問”,任何對中國學校制度的美好想象均與家長的切身體驗背道而馳,任何貌似對“錢學森之問”的解答最終在孩子成長現(xiàn)實前面淪為反身詰問。
“錢學森之問”其實并沒有那么詭奇而玄奧,只是以弦外之音在拷問,中國娃娃怎么了;創(chuàng)新其實并沒有那么深不可測高不可攀遙不可及,只是渴求那一片本屬成長應有之義的自由;教育改革其實并沒有那么風起云涌雷鳴電閃刀光劍影槍林彈雨,只是把“錢學森之問”格式化為捫心自問。
六、監(jiān)測之器
走進錢學森圖書館大廳,一座現(xiàn)代雕塑“升騰的智慧”撲面而來:4 015頁模擬手稿,寓意錢學森從1955年回國到1966年“兩彈”成功之間的4 015個日日夜夜;9.8米高度,表意錢學森人生旅途的98個春夏秋冬。
尚若錢學森在天有靈,這樣的圖騰并非他所愿,只因他從未自詡為天才。
就在錢學森入學附中的第一個寒假,1924年1月17日,魯迅應校友會之邀來校作題為《未有天才之前》的講演。“天才并不是自生自長在深林荒野里的怪物,是由可以使天才生長的民眾產(chǎn)生,長育出來的,所以沒有這種民眾,就沒有天才……我想,天才大半是天賦的;獨有這培養(yǎng)天才的泥土,似乎大家都可以做。做土的功效,比要求天才還切近;否則,縱有成千成百的天才,也因為沒有泥土,不能發(fā)達,要像一碟子綠豆芽。”魯迅發(fā)自肺腑之言時時縈繞在錢學森耳畔心間。錢學森曾沐浴在一方泥土的滋潤之中,也畢生甘做一抷土,但至終無以開辟一片廣袤的沃土以構(gòu)建創(chuàng)新型國家。
于是,在這座以自己名字命名的圖書館,錢學森切切期待的或許是另一種表征性符號——一個碩大而震撼的問號,問的是:錢學森何以成為錢學森?此問可對應經(jīng)典“康德四問”中的第四問,即人何以為人或成人;而且,這是“康德四問”中唯一游走在人類學與教育學層面上的問題。猶如“康德四問”,“錢學森之問”也因無解性而被賦予永恒的生命力。
擁有永恒的生命力固然瑰麗絢爛,但畢竟過于縹緲迷離。當下,“錢學森之問”如若作為教育監(jiān)測之器,時刻拷問教育之點滴,錢學森百年祭便也算作一種創(chuàng)新。?箏
(作者簡介:俞可,上海師范大學中德教育研究與協(xié)作中心總干事、留德哲學博士、德國多特蒙德理工大學學校發(fā)展研究所客座教授、全國高等教育學研究會學術委員會秘書長)
編輯:覃云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