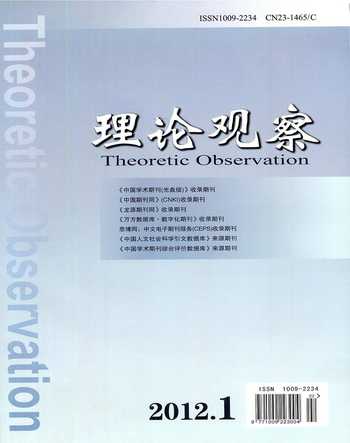創建學習型社會的新視野暨實踐
董婷 李敢
[摘要]自“創建學習型社會”寫入了中國共產黨的黨代套報告后,在科學發展觀指導下實現經濟發展、社會和諧、人民幸福相統一使成為黨工作的一個宗旨。經由對“幸福廣東”建設中受到高度重視的“幸福書”之“斯蒂格利茨一森一菲圖西委員會報告”有關幸福社會建設的解讀,文章認為,建設“幸福社會”理念與實踐可以有效促進社會各界對“幸福”的認識和理解,以及思想的統一與民意的凝聚。是學習型政黨推動學習型社會建設實踐中的一個示范。
[關鍵詞]學習型社會;幸福;社會建設
[中圖分類號]C913[文獻標識碼]A[文章編號]1009-2234(2012)01-0052-02
一、“幸福書”與“斯蒂格利茨—森—菲圖西委員會報告”的背景簡介
為深入推進“加快轉型升級、建設幸福廣東”的發展規劃,2011年春,廣東省委向全省力薦兩本“幸福書”,其一即為“對我們生活的誤測:為什么GDP增長不等于社會進步”。該書裁剪于2009年的“斯蒂格利茨—森—菲圖西委員會報告”。該報告又名“經濟績效與社會進步委員會報告”“(Report bv the Commission on me Measurement of EconomicPerformance and Social Progress”)。報告中提及的“委員會”指的是以該報告三名作者姓氏命名的“斯蒂格利茨—森—菲圖西委員會”,簡稱“斯蒂格利茨委員會”。報告作者中的作者為諾貝爾經濟學獲得者,即阿瑪蒂亞·森(印)是諾貝爾經濟學獎1998年獲得者,約瑟夫?E?斯蒂格利茨(美)是諾貝爾經濟學獎2001年獲得者。“斯蒂格利茨—森—菲圖西委員會報告”主要論述在經濟社會發展領域,除了傳統GDP之外。如何創建一個新的標準體系,其目標在于建設一個幸福社會。
二、“幸福書”原本的基本內容與主旨
“斯蒂格利茨—森—菲圖西委員會報告”的基本內容與主旨在于倡導各國政府發展模式應當逐步實現從既有聚焦于“生產導向”的測量過渡到聚焦于“幸福導向”(未來福祉)的社會進步測量。報告認為,對幸福的界定應是一個多維的取向,至少在原則上,測量幸福應同時考慮以下8個關鍵維度,這8個維度在實質上塑造影響著人們的幸福水平提升,但是其中不少方面卻為既有的收入測量體系所輕視。報告還就如何測量幸福提出了12條建議,涵蓋了“幸福的多維建制、幸福測量中主客觀維度的同等重要性、環境壓力的物理指標、可持續發展測量的務實路徑”等內容。有關建議的具體內涵如下:
建議1:物質幸福的評估不宜夸大
生活中,適用于對市場生產進行測度的GDP常常被用以對民眾福祉的衡量,此二者的混用可能會衍生出有關民眾幸福度量的誤導性指標,并誘導出錯誤的決策。實際情形為,物質幸福(其主要代表物為物質生活水準的GDP)只是與家庭實際收入、國民凈收入以及實際消費的關系更為密切,即當收入降低時,生產可能會擴張,反之亦然。
建議2:家庭視角應予以重視
家庭視角要考慮家庭收支在部門之間的轉移問題(如納稅與付息等)。以及家庭戶可以分享到的受政府補貼的非貨幣服務(比如衛生保健和教育等)的數量與質量。因此,經由對家庭收入和消費的測度。可以更好了解公民物質生活水準(物質幸福)的現狀與趨勢。
建議3和4:對收入、消費和財富的統合考察
收入與消費指標對于生活水準的評估非常關鍵,但其必需與財富指標一道使用。譬如,一戶在消費品上增加開支的家庭可能增加了當前幸福度,但卻犧牲了未來的幸福。在進行幸福測度時。這類行為應納人家庭資產盈虧表中予以考慮。同樣,這種關聯也適用于其他經濟部門和整體經濟。在這個事關可持續性的測量過程中。對財富的度量是中心環節。至于這方面的未來應用。當考慮到財富的諸種資本儲備形式,例如自然資本與物質資本、社會資本與人力資本等。如建議3所言,盡管平均收入(消費和財富)是非常有意義的統計數據,但它們還不能較為全面地反映生活水準。在這方面,消費(收人、財富)的中位數應該比其平均數能夠更好地測量個體或家庭的情況。理想的操作是,這些信息不應被孤立地看待,而應聯系起來看待,即對一個家庭戶富裕程度的了解要綜合涉及物質生活水準多維度信息。如收入、消費和財富等。
建議5:將收入測量納進非市場活動
在實際生活中,家庭為自身也提供了不少服務,這些服務都是經濟活動的重要方面,但它們尚沒有為官方收入和生產標準所承認。在許多發展中國國家,家庭自產產品在國民經濟中依然扮有重要角色,評估這些國家的家庭消費水平,需要對這種家產產品予以必要的關注。一旦非市場活動得以重視,閑暇問題也就出現了,也就是說,假如以更少時間可以獲得原先同質同量的商品與服務,即意味著人們的生活水準獲得了提升。
建議6:生活質量取決于人們的客觀條件和可行能力
對幸福(生活質量)測度所采取的措施應有利于健康、教育、個人活動以及環境狀況的改善,尤其要就社會關系、政治發言權的測度發展出穩健可靠的措施并予以貫徹,而其中的不安全狀況則可以經由生活滿意度去表達。對生活質量的評價不應只是依據人們的自我報告,還要包括對人們“功能性活動”(functlonings)測度的認知,因為人的有價值的生活是由一系列“功能性活動”構成的,這些活動“包括吃衣食住行、讀書、看電視、社會參與(投票選舉、在公共媒體上發表言論觀點,以及上教堂做禮拜等等”,他們可以被列為一個清單。這其中,真正重要的是人們的“可行能力”(capabilities),即人們可以擁有的機會集(opportunity set)以及在此機會集內人們的自由選擇度和人們對生活的評價。2同時。也要看到。對于任何生活質量測度而言,相關功能性活動和可行能力的選擇都是一種價值判斷,而不只是一種技術操作。對這些特征的測量,不僅僅需要客觀數據,也需要主觀數據。
建議7和8:全部生活質量指標均應均衡評估不平等狀況
對各國在不同發展時期或者發展階段生活質量的任何評估,都應對個中國的不平等境況加以關注。首先,能否提出這類問題很關鍵,即生活質量某個領域的發展是如何影響其他領域發展的,且不同領域的發展與收入相關性究竟怎樣。其次,為了解在生活質量諸多領域均處于弱勢的人們的需求及其規模之間的交互作用,在具體領域的政策設計方面,應對生活質量不同層面所受到的影響予以綜合考慮。
建議9和10:主客觀幸福的測度都很重要,可以嘗試建立不同指數
盡管對生活質量的評估需要多元化的指標,但仍需要建立起某一概括性綜合標準。統計部門應把人們的生活評估、快樂體驗及其本身的調查的進行優先次序整合,因為收集有意義而可靠的主客觀幸福的數據是可能的。同時,在政府統計體系能夠提供必要數據的前提下,也可以設定某些類似標準予以補充,比如基于人們陳述和偏好的“等效一收入”(equivalent-income)標準。為了獲得對人們生活更加全
面的評價。以上每個方面都需要獨立測量。主觀幸福度量值不僅可以提供對生活質量本身的一種測度,也可以提供對幸福限定性影響因素(收入及其它物質條件之外)的理解。盡管這方面還有許多懸而未決的問題,但這些主觀測度能夠為生活質量測度提供重要信息則是毫無無疑問的。也正因為如此。在那些小規模和非官方調查中所使用的價值檢驗類問題也可以囊括于官方更大規模的調查統計之中。
建議11和12:評估可持續性。需要清晰的指標工具
對可持續性的測度與評定是報告的一個核心關注點。可持續發展環境因素的測度應是具有獨立性的跟進。這就需要研制出一組精選的測量指標,特別是需要一種可以測量對環境破壞達到危險水平程度的清晰指標。綜上所述,可以發現,在12條幸福社會建設的建議中,1-5條主要是論述發展模式當逐步實現從生產到幸福的轉向:第6-10條則主要是論及主客觀數據對于幸福測度的同等重要性;第11和12條主要是論及可持續性測度的實用路徑。
三、幸福社會建設的一個案例:“幸福廣東”建設
在國內的“新四化”(工業化、城鎮化、市場化和國際化)背景之下,對廣東而言,可以發現,“幸福廣東”理念的提出是廣東更上一層樓發展的必然訴求,是在科學發展觀指導之下。以“殺出一條血路”的氣魄。源自恩格斯“歷史合力”思想的合力理論(theory of conitznctures)新視野,是改革促創新、改革促發展邏輯的進一步演繹。以“幸福廣東”打造“給力廣東”可以為廣東未來的發展注入活力。此舉可以向外界傳達,除了經濟的進步,社會進步也將是廣東特征,即廣東不僅僅是GDP大省,還將是GNH(Gross National Happiness國民幸福總值)大省。而研究、制定并努力付諸實施(致力于“幸福廣東”建設)的“幸福政策”則不僅可以構成政府執行力新的挑戰與動力,還可用作為一種新的政策評估標準和未來政府績效考核標準的組成部分,可以涵蓋經濟增長、政府責任的甄善、公民權利的甄善以及文化發展、環境保護等諸多方面。有鑒于此,相應而言,“幸福廣東”理念的提出是廣東政府施政理念的一大突破,意味著多年以來作為全國GDP“龍頭”的廣東省,其施政方針正從對GDP推崇向關注民眾幸福傾斜。是廣東落實科學發展觀的又一力作,是廣東政府對善治的努力追求。
四、從“幸福書”看“幸福社會”建設中的公共政策意蘊
在一定程度上,依據世界上對GDP指標體系的一致性反思,可以預測“幸福廣東”社會建設將不僅僅局限于廣東一省,因為廣東往往是中國改革開放事業試點省份,歷來是中國改革開放事業中的“試驗田”與“排頭兵”,其間蘊含著中國政府已經開始真正正視其新的政策需求,體現了未來公共政策選擇、制定與評估的可能性轉向。這將是一個巨大的發展轉向,一個從對物GDP過度追捧發展到提升民眾福祉的轉向。或正如斯蒂格利茨委員會報告所言,對幸福社會建設的探討將在全球范圍內引發一場從“生產導向”到“幸福導向”的公共政策轉向,在一定那個程度上,這種轉向可以有效彌補既有模式只注重物質利益而忽視人的價值、權利與動機的發展傾向。有利于社會的和諧與包容共享。可以說,在一定意義上,“幸福社會”建設理念探討與實踐的本身具備學習型社會學習的關鍵特征,是一個更為積極地反思已有發展問題、追求新的發展模式的過程,是一個社會化、組織化的學習過程。是“以學習求發展”的一個范例,3是學習型政黨推動學習型社會建設的一個示范。
[參考文獻]
[1][美]斯蒂格利茨,等,對我們生活的誤測:為什么GDP增長不等于社會進步[M],阮江平,王海昉,譯,北京:新華出版社。2011
[2][印]阿馬蒂亞·森,以自由看待發展[M],任賾,于真,譯,北京:人民大學出版社,2002:8—19
[3]連玉明,學習型社會[M],北京:中國時代經濟出版社,2004:3—9
[責任編輯:馮延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