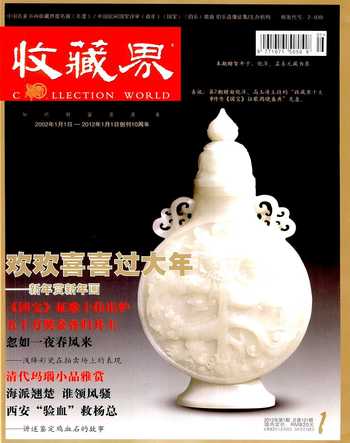不教詩思落紅塵
王軍


如今的瓷器只要沾上淺絳就身價倍增,所謂的官窯名家更是天價。前些時期到異地一古玩店,老板拿出一光緒后期釉彩花鳥壺,滿口不離淺絳彩名家、御窯廠名家,索價也高,余無語。誠然,淺絳彩的最大魅力就在于文人的參與,現在很多人稱淺絳是文人瓷,殊不知不是所有用淺絳彩在瓷上作畫的都可稱文人瓷。我想,真正優秀的淺絳作品應是體現中國文化韻味的作品。什么是中國文化的韻味,我想應該就是那筆不到之處。郎世寧的花鳥色彩絢爛,造型極其準確優美,但總覺得比不上惲南田的花鳥有味,中國畫的神就恰恰在此—不僅要畫得生動,如活的一樣,還要傳達一種境界,一種詩味,一種淡淡的平靜中的哀愁。
那么,我們欣賞淺絳恐怕要有所界定,造型優美、蘊含內斂地表現文人情思的淺絳彩瓷作品才能稱之為文人瓷畫,才是值得玩味的。
中國書畫的特點是詩書畫印融為一體。書是指畫中的題詩,往往是點睛之筆,畫中的韻味經詩一點,了然于胸,恍然大悟,這就是一種感受審美愉悅的過程。所以欣賞文人瓷畫,恐需看題詩以揣摩畫意,比較畫意詩意的契合、高下等。當然題詩也有高下,程門作品的詩多為自作,即使襲古卻不泥古,常能別開生面,此是少維、品卿難及之處。至于那些什么“鳥語花香”、“富貴白頭”等題句,顯然是真正的文人畫中不屑為的俗句(當然有的是文人瓷畫家們應酬之題就另當別論了)。
近日,雅昌網論壇近代協理員“曙光初照演兵場”展示一山水筆筒,山水華滋淡雅,畫中一老者拄杖立于溪澗旁,雅逸十足、閑逸十足。題畫有兩處:一為題贈款,由此處知是贈予一高級軍官;另一處為一首畫師自作的絕句:“十年提劍論猶壯,五夜抽毫奏捷忙。今日官街閑坐鎮,題封常寫謝恩章。”整個詩的詩眼就在一“閑”字,一種事業有成、功成名就之后的閑逸。一畫兩題妙合無垠。
多年前曾于本地文物商店購得一件程松石溫酒器底(圖1-a),當時購之,除了因為器物上的花鳥畫得不錯外,還有欣賞其“詩思不教落紅塵”(圖1-b)題詩的原因。其實這句是故為倒裝之句,應為“不教詩思落紅塵”。文人的獨傲就在這句詩中展現得淋漓,詩思豈能落俗塵!松石引此句既是自傲也是自勉,畫花鳥、山水、草蟲又豈能落俗套。程松石此作作于1891年。無獨有偶,近日見2006年廣州保利夏季拍賣會上拍的一幅居廉丁亥(1887年)作的《蛙蟬圖》立軸,上有題識:“午苑風和本來真,落下何曾久寄人。為殿百花開獨晚,不教詩思落紅塵。丁亥春月陽山樵子居廉。”松石與其同時期的畫家居廉同賞此句,是一種巧合?恐怕更是一種同時代文人間流行的風尚詩句吧!
在許多淺絳畫師中,我覺得程氏父子的藝術修養極高。很遺憾個人無財力擁得程門的作品,只收了兩件程言的殘器與一件程盈的扇面。其中就有一件殘筒,是梁基永先生的舊藏,它的題句是程言的原創:“青山一入尋無路,鳥響煙生水滿溪。”中國古代繪畫尤其喜歡追求畫外之意、畫外之音,所謂形好畫、聲難圖。宋代著名詩人梅堯臣《魯山山行》詩中“人家在何許,云外一聲雞”句常常被畫人題入畫中,但幾乎不見哪位畫師在畫中直接呈現雞的形象。藝術貴在含蓄,程言的這件殘筒同樣未在堤柳之上繪上鳴叫的春鳥,只是在滿漲的溪水上著一渡船,但是船上的那位紅衣渡客側身的動作仿佛在傾聽那隱在山澗云霧背后的鳥鳴聲,使我們感受到春水高漲時漫山云霧、鳥鳴盈耳的美妙意境。
程友石的這件一品鍋(圖2)敝人把玩數年,愛不釋手,上有題詩:“一枝春欲寄,千里路何長。”此詩句為程友石原創,意蘊豐富。“一枝春欲寄”句化自《贈范曄》:“折花逢驛使,寄與隴頭人。江南無所有,聊寄一枝春。”作者是南北朝時的陸凱,據傳這首詩是他率兵南征度梅嶺時所作。他登上梅嶺,正值嶺梅怒放,立馬于梅花叢中,回首北望,想起了隴頭好友范曄,又正好碰上北去的驛使,就出現了折梅賦詩贈友人的一幕。《贈范曄》寥寥二十字,簡樸中道出了真摯的友情,平淡中顯出了高雅的意境。自此“一枝春”作為梅花的代名詞,向人們預示著美好的春天即將來臨,祝愿人們的美好祈望定能實現。程友石的這件一品鍋是送給一位叫“仰高”的長輩的。友石在此化用古句卻不完全抄襲古意,而是賦予更為豐富的意蘊:陸詩中“聊”字意為“姑且”,暗寓與友人的關系之深,非泛泛之交,物小而情誼重。程句用一“何”字,有兩種理解,可理解為“多么”, 表達無奈、悵惘的情感,我是多么想“寄”此情,然怎奈山高路遠,不得矣!也可理解為“有什么”,表達豁達、開放的心胸,即使千里又有什么長的呢,物小(一支春梅),路長,均擋不住我的欲寄的“深情”。從此可見程友石的才情,學古之中自有變化。試想仰高老先生收到此物后,定感慨萬千!
我的收藏以淺絳文房器物為主,特別鐘愛這件署名小竺的六方水盂(圖3)。水盂正面繪一依石芭蕉,兩側題句:“白云初晴,幽鳥相逐,眠琴綠陰,上有飛瀑”。這兩句出自司空圖的《二十四詩品》“典雅”一品,這四句后面兩句大家更熟悉些:“落花無言,人淡如菊。”背面繪一幅月映風竹圖,此圖為有本之作,是模仿揚州八怪之一的鄭板橋的作品。小竺據著名淺絳收藏家晨欣先生考證是歙縣人,又叫明香館主人。這件小竺的作品題句與繪畫均體現中國美學中虛靜空靈的特點,月夜之竹、依石的芭蕉不都是無言安靜之景物嗎?然而無言不是無知,大道無言,淡而不木乃是中國哲學、美學追求的最高境界。
無需再舉例贅言,總之,文人瓷畫一定是值得涵詠而充滿意蘊的瓷畫,不一定非得詩書畫印俱全,但一定是高標獨立的,一定有不落紅塵俗世的“詩思”。最后引馬未都先生的話結束拙文:“收藏不能做‘保管員,要解讀出藏品背后的文化內涵,這樣你才能對得起古人給我們留下的這些文化遺存,而同時這些文化遺存也是我們在當今浮躁社會快樂存活的精神依存之一”。(責編:雨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