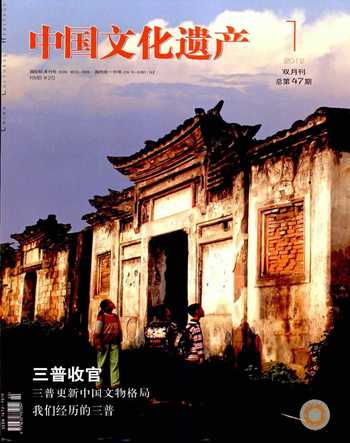北大上學記
羅琨

1958年,我在北京第一女子中學畢業,考取了北京大學歷史系,發放錄取通知的前一天,我們還在參加中學組織的街道工廠勞動和街道掃盲工作,到接到通知的那一刻,才剪斷系聯母校的臍帶,準備開始新的生活。
考取了第一志愿去北大讀書,當然高興,因為北大是我熟知的學校,上小學的時候,我家住在西老胡同,每天都要經過北大理學院的大門,穿過一個窄窄的胡同——“大學夾道”,才能到達我們的東高房小學。聽說反饑餓,反內戰學生運動的時候,特務就曾蹲守在附近監視學生,而我們六年級班主任楊春蔭老師,則常在小酒館和北大學生一起吃酒、聊天。那時父親在北大文科研究所工作,我也曾隨著父親去過五四操場和北大紅樓。
我還知道北大的前身是京師大學堂,1907~1911年我的外祖父曾在那里任教務提調,專辦學務;1909年我的祖父也從學部調任京師大學堂農科監督,籌建農科。1919年正在北大德文系讀書的一位舅舅因參加五四運動的游行示威,曾被關在午門內;1922年另一位舅舅則在北大研究所國學門讀研。而就在1958年前后,一位姑母家的表姐在北大讀地質地理系,且為侯仁之先生的副博士研究生,另一位姑母家的表兄正在北大讀化學系,后來專攻尖端科學。我的同班同學也有不少考上北大、清華,所以我覺得自己考取北大是一件太平常的事了。
接到錄取通知后,母親送我一把梳子、一把雨傘,這是上學要用的東西,此外沒有特別鼓勵、叮嚀的話,更沒有像現在高考后的“慶祝”活動,當時我上有年邁的外祖父母、祖母,“空巢”病弱的姑母,下有四個年幼的妹妹弟弟,夠他們忙的。直到很多年后,我才知道1957年姐姐考上北京農業大學,父母很高興,告訴他農大的前身就是祖父羅振玉創建的京師大學堂農科。所以我想這時父母更多是感到欣慰,因為他們曾有過約言:“伏生有女傳經史,莫羨鄰家占夢熊”。
就這樣,我懷著一顆平常心,一個人背著行李坐公交車去北大報到了。
一
北大五年的學習生活,節奏都是很快的,剛剛報到安置好,第二天就分配到圖書館善本室去抄資料,同去的還有兩位歷史班的同學,他們比我早一天報到,也早一天參加了這項工作,這是我第一次踏進北大圖書館,第一次知道進善本室是不能用鋼筆的。
不久,就開始報名分專業,那正是“考古專門化”改為“考古專業”的第一年,我們58級在大一就分專業,我毫不猶疑地立即報了名。因為我們的時代重理輕文,在我讀高中時,北大地質地理系讀書的那位表姐,多次來探望舅父舅母,談起學習生活,尤其是野外實習,我十分羨慕,心向往之。但我不可能學地質,因為自幼體質差,初中得了肺結核,高中還免修體育,學地質是完全不可能的,于是轉向了考古。
我從小喜歡亂翻書報,高中時知道了蘇聯發掘了花拉子模城,又讀了一本蘇聯小說《成吉思汗》,講到花拉子模城的毀滅,開始對田野考古及通過考古,發掘、復原被歲月淹沒歷史的工作很著迷。回首往事,我常想就像《成吉思汗》里贏弱的小圖干一樣,他的影子被縫到了托缽僧的斗篷上,從此決定了他一生的道路。我也是從那時起,就把自己的影子和考古學縫到一起了。而且后來因為身體不好,系總支書記吳為能找我談話,希望我轉到歷史專業,但我還是毫不猶疑地謝絕了組織的好意,堅持留在考古專業。
學考古父母當然是支持的。不過高考、選專業填志愿,都是我們自己做主,甚至沒有和父母、老師商量,當時高考填六個志愿,我沒有填滿,好像只填了四個,包括北大歷史系和圖書館學系。現在想來,父母確實希望我們姊妹能繼承家學,但是繼承家學不一定要局限于祖父和父親專長的學問,選擇有互補性的專業會更為有利,而最重要的是要有“興趣”,即對所選事業的熱愛,才能有自覺性和主動性,才能在攀登中不畏艱辛。
我在北大正是1958~1963年,正值反右過后一個個政治運動的小高潮和三年經濟困難時期,但當時北大還是重視教學的,這五年的記憶就是勞動、運動,抓教學質量。
勞動,我們參加過首鋼的大煉鋼鐵;農村的搶種搶收,北大的建校勞動,我們參加過修建北大的石砌圍墻,聽說呂遵諤先生是砌虎皮墻的高手,而虎皮石是我們肩挑、手搬,穿過半個校園運去的;參加過“一百號工地”(北大分校)遷墳、修路……勞動的高潮延續到經濟困難時期,還遭遇食堂管理員貪污,生活條件可想而知。在校外勞動,有時下工要摘野菜帶回食堂,從而認識了馬齒莧等一些野菜。還有一次勞動,每日午餐都是饅頭、熬大蔥根(蔥須)、蒸鍋水(代替湯),我一直不解有這么多蔥根,蔥都到哪里去了。不過在當時,和市民比,大學生的糧食定量還比較高,和廣大農村的同齡人相比,我們更屬于“幸運兒”。
運動,主要是各種政治學習、批判,常常開會到很晚。搞運動更要學習、討論、準備發言,生活節奏很快。
每當一個運動高潮過去,抓教學質量就被提上日程,除了在文史樓和各個教室樓間奔波上課,就是奔波找自習的場所,2 7齋寢室兩張雙層床,一個小方四屜桌把房間裝得滿滿的,只能留一人自習,多數人都去找閱覽室。記得冬天的清晨,六點多時天還沒有大亮,大飯廳外的路上,就會有不少影影綽綽的移動的人影,其中不乏打一大碗玉米面粥,邊走邊吃,奔向閱覽室的學生,晚了文史樓閱覽室就沒有座位了。一二節有課,就不去閱覽室,27齋后面、五四操場旁,一個小土山的桑樹下是我讀外語的地方,當時北大沒有那么多人,五四操場也鮮見有人活動。后來還發現了繞過五四操場,有一個理科用的閱覽室,寬敞、舒適,而且人少,晚上我常去那里自習。
1960年代前后北大的生活條件,當然不能和后來相比下鄉、下廠、各種勞動等,雖然繁重,為過去所不曾經歷,也由此病過幾場,但使我了解了象牙塔以外的生活。磨礪也是一種人生的財富,其它活動多了,學習時間少了,使我懂得了珍惜,而學習考古專業課,就像是追隨托缽僧去探索一個陌生的新世界,對我有無窮的吸引力。
燕園的生活還有一段難忘的經歷,就是參加“大搞科研”,好像是1960年寒假,學校再度掀起大搞科研,班上大部分同學參加編寫《北京史》(或者叫《北京文物志》?),首先是下去調查,回來編寫、討論提綱,重點在于如何“突出紅線”,記得張永山講他去焦莊戶調查地道和抗日戰爭的地道戰。我作為剛修過石器時代的考古班的學生,被分配到世界史教研室,參加編寫世界史講義的課題。在批判“科研大躍進”的過程中,曾談到“由低年級為高年級寫講義,不啻為笑話”,確實,科研工作不適宜采取“大躍進”的形式,作為一個低年級的學生在所謂“老中青三結合”的科研班子里也起不了作用,但在我卻是一段難忘的經歷。
那是一個寒冷的冬天,不知什么原因,寢室沒有暖氣,在27齋,清晨醒來總會不由自主地摸摸床邊的暖氣管,卻總是冰涼的;打回一壺開水放在地上,待到拿起用水時,總有壺底沾上的水已凍結在地上的感覺。38齋也是一樣,聽說一些男同學要戴著帽子睡覺……但邁進世界史教研室就像進入一個溫暖的大家庭,齊思和先生十分風趣又平易近人,一些青年教師就像孩子一樣圍繞在他們周圍,記得一次一位青年教師剛剛起身想出去一下,抬頭一望,忽然低語“齊先生要講故事了”,趕快又坐下。而我,總是默默地坐在角落里、饒有興趣地觀察并傾聽他們的一切。當然,還有工作,在我,主要是學習,我讀了當時出版不久的多卷本《世界通史》第一卷后,帶著問題找到了嚴文明先生,先生給我開了一個書單,告訴我了解這些問題要看哪些書,第一次給我指出科研工作的門徑。
大學生活也有很多有趣的事,同班有十位女同學,大學五年室友都是同專業的,除了外出實習、勞動,今敦煌研究院院長樊錦詩在我下鋪幾乎是住了五年。同室三年多的是57級畢業分到考古所的曹延尊、劉一曼。初進北大就同室,前后住了一年多的是李東琬、許愛仙。57級畢業以后,我們又和59級的林秀貞住于一室。這些室友們都很有事業心,很用功,和他們相處都很融洽,他們至今大都不枉一生,取得很多成果。
記得到北大報到后的第一個周末,同為家在北京的我和李東琬都決定不回家,因為縈繞心間的是馬雅可夫斯基的詩句:“十八歲/對于人生/只有一次/年輕人/一定能代表所有的孩子/向年長一代戰斗者說/我們要改變大地的生活”。十八歲,我們成年了,該獨立了,但這第一次的離家難免思家心切、無法成眠。夜晚,我們對坐在桌前,望著外面大雨滂沱,沖刷著寢室的窗戶,一只大壁虎緊緊扒在窗外玻璃上,我第一次如此清晰地觀察到它的肚皮和四肢。在那些日子,也曾抓過碧綠的很大的尖頭蚱蜢,栓在墨水瓶上,作為“寵物”,伴我們讀書。
記得分專業不久,57級曹延尊、劉一曼剛從周口店發掘工地回來,帶回來發現的鹿牙和鬣狗糞化石,得知我們是考古班的新同學,在上交系里之前,特地取出讓我們開開眼。我第一次面對他們帶回的“圣物”,輕輕撫摸這些遠古世界的見證。轉眼四年過去,五七級就要畢業了,1962年是他們在校的最后一個新年,除夕之夜,曹廷尊、劉一曼、樊錦詩和我在二十七齋的寢室里暢談畢業后的工作,憧憬未來,直到午夜臨近,才匆匆跑到大飯廳參加聚會,元旦鐘聲響了,四雙手緊緊的握在一起,相約十年后再會。在我們年輕的心中,十年是十分漫長的,我們能做很多的事,會有很多體驗可談。然而直到2005年中秋,才踐行了重聚約言,這本應是一次愉快的聚首,四十年,為了青年時代的理想我們都盡了力,并且在生活和工作中找到了自己的位置,四十年,我們都經歷了很多苦辣酸甜,但是只有三個人走過來了,曹延尊英年早逝,想起他的未竟之業和當時尚不解喪母之痛的幼子,在莫高窟前、在中秋之夜清冷的月光下,禁不住無語凝噎。
二
我們五八級分專業早,參加田野考古較多,尤其是“認識實習”為其他各屆考古班所不設,在田野工作中,我們的實習包括了從測量、開方、挖土到用小鏟清理發掘、繪圖、刷陶片、拼合、簡單地修補、畫圖、整理,對學生是很好的鍛煉。
1959年認識實習,參加陜西華縣發掘,先在遺址區,所在探方方長是56級的勞伯敏,記得挖的第一個灰坑,靠坑壁有一個堅硬的二層臺;后來發掘一座地穴式的房子,中間一個柱洞,李仰松先生兩次來看我的房子,第一次告訴我,把柱洞清理出來,第二次檢查清理結果。這是一座用一根柱子撐起遮擋風雨棚頂的橢圓形房子,堅硬平整的居住面上,留下一個陶灶,一堆螺螄殼,房子的主人是怎樣的人,當陶灶點燃的時候,又發生過怎樣的故事,曾引起我長久的遐想。
后來我們班分配遺址區和墓葬區的兩組調換工作地點,以便對兩種遺跡的發掘都有感性認識。我則被分配到修補室,幫助工作并學習修補技術,我的師傅是考古隊請來的一位當地教師——紫娃,手很巧,在這里我看到、學到不少修補、復原的技巧。
在華縣,除了參加田野考古,當時的蘇聯留學生劉克甫給我們講授摩爾根《古代社會》。課堂在室外,他讓我們“席地而坐”,圍成一個半圓,就開課了。糾纏起起拗口的親屬稱謂,別有一番樂趣。
發掘工作結束,我們參加了麥收。華縣生活使我們見識到八百里秦川的富庶,麥收時生產隊提供的午餐是半斤一個的粘谷面窩頭,也是一種難得的美味。麥收后去華陰參觀了考古所的一個發掘點,又背著從華縣帶的饅頭登華山,在山上據說是慈禧太后避難住過的地方住了一夜。下山去西安參觀。由于數日連續緊張、勞累,到了西安半坡博物館我就發起了高燒,曾在西安工作過的同學張岱海陪我去了醫院,直到數日后,同學們參觀結束,才能起床和他們一起回京。雖然由于生病,錯過參觀西安雁塔、碑林的機會,但西安之行使我第一次知道唐長安規模宏大,后世帝都如北京故宮無法與之相比。
1960年,懷柔發掘是搶救性質的發掘,于2月28日開工,領隊是北京文物工作隊的郭仁先生,我的方長是56級的楊育彬。我們住在懷柔飯店,當時懷柔縣城只有兩條街,飯店用水比較困難,吃飯時只能在院子里的水龍頭下簡單沖沖,難免把殘留在手上的的骨頭渣、棺材灰和手上的饅頭一起吃下。
這是我第一次發掘漢墓,很開眼界,第一次知道了用探鏟可以準確找到墓葬四界。這批墓葬保存不錯,有漆器,可惜在當時條件下無法保存。這次發掘雖然天寒地凍,條件也比較差,但我的方長喜歡唱歌,而且唱得很好,一面以半蹲半跪的姿勢剔骨架,一面陶醉于墓坑中的歌聲,真是一種難忘的經歷。這次發掘結束,我們還在當地大廟里辦了一個展覽。
1961年,雪山發掘是正式的生產實習。以前發掘都有高年級帶領,這次是獨立工作,鄒衡先生要求嚴格,記得有一位同學用大鏟“斂平”技巧掌握得不夠好,鄒先生看到,把大家召集起來,讓他把探方地面斂平,然后指出他的錯誤,再斂平,直到正確了才讓大家解散。還有的同學,在斂平耕土層時發現底部拖拉機留下的痕跡,以為是遺跡不敢往下做了,鄒先生也大聲、詳細地指出其錯誤。這樣雖然少數同學自尊心有點受傷,但多數同學受到教益,所以大家都很尊重先生。當然,先生不僅嚴厲,也很關心學生的方方面面,當時我和張永山在一個方,曾發現一座圓形房子,地坪堅硬,還有一灶坑,該次發掘房子少見,先生看見很高興,立即給發掘者和房子合了一個影。后來我看到先生在《手鏟釋天書》中講,主持洛陽王灣發掘,工作進展順利,不僅“對成仰韶、龍山完整陶器共達500余件”,還有
“6位男女同學,居然對成了終生伴侶”,從而感到“有說不出的欣喜”,我才明白那也是先生對我們未來的美好祝愿。
“民以食為天”,“人們首先必須吃喝穿住,然后才能從事政治、科學、藝術、宗教”,雪山發掘正是困難時期,當地村民(包括我們請的民工)基本是以紅薯充饑。考古隊師生雖然都有基本的糧食定量,但副食糖、油,還有動物蛋白和脂肪都很匱乏,田野工作是體力勞動,老師們除了指導我們發掘,還要到周圍地區踏勘、調查,更是辛苦。吃飯問題有時不能不受到關注,記得一次我們都吃完了飯,鄒先生才調查回來,當他從廚房出來,一手拿著調查找到的鬲足,一手拿著饅頭,滿臉充溢著笑意,我們都覺得,這是一位有事業心的學者最幸福的時刻。
1962年,畢業前的專題實習我參加的是山西組,共五人,包括張永山、曹定云、徐治亞、祁惠芬和我,指導老師是蘇秉琦先生。在山西侯馬,具體指導的是工作站王克林先生(北大考古專業52級),由王先生帶我們踏勘、考察周邊遺址,介紹要我們整理的遺存出土情況等等。分工我和徐治亞整理一批小墓,首先是繪制全部隨葬陶器圖,然后編寫發掘報告。張永山整理的是銅器墓,還制作了一些拓片。
蘇秉琦先生是在我們整理工作告一段落時才去的,檢查我們的器物排隊,型式劃分是否得當等。記得是張永山去潼關接先生過黃河,再陪同到侯馬。當時在侯馬有不少先生的學生在那里工作、實習,先生的到來對我們來說,就像過節一樣,學生們紛紛匯報工作、請教問題,除了暢談學問外,先生還請大家吃了羊湯。正值三年經濟困難時期,真是一種難忘的美味,有人笑談,吃得都快要“張口可見”了。
三
回首此生專業的選擇和學生時代,我確實是很幸運的,第一件幸事就是我出生在一個父母非常明智的家庭,他們很重視身教,而且不僅愛子女,更懂得如何愛、如何教育,如何在潛移默化中引導子女開創自己的道路。記得六七歲時,閑談中母親問我們姊妹倆喜歡什么(后來讀了《論語·公冶長》“子曰‘盍各言爾志”,才知道這是一種教育方式),姐姐說了以后,我脫口而出“我也是”,母親馬上講“不要拾人牙慧”,雖然當時不免有些委屈,這卻使我受用一生。1984年我第一次參加“全國商史學術研討會”,提交論文《殷墟卜辭中的高祖和商人的傳說時代》,得到胡厚宣先生的鼓勵,說此文“發前人所未發”;也曾有編輯來函約稿,認為我關于先秦史、甲骨文研究的一些論文“給我國文明起源研究提供了獨特的視覺和成果”,如果說我在這方面能有一點成績,只不過是記住了母親的話:“不要拾人牙慧”。
更為幸運的是我讀北大是在1958~1963年間,在這里我們受到磨礪,懂得了珍惜,更適應了快節奏的生活。在校期間雖然運動多、勞動多,讀書的時間打了折扣,但同時很注意抓教學,大學教育的專業訓練基本沒有缺失,尤其是系領導說,“都是勞動,考古班與其上工廠農村,不如去考古工地”,于是我們獲得更多田野考古實踐的機會。這段經歷,對于畢業后轉入史學領域的工作者尤為珍貴。記得1980年代或稍晚,一次學術討論會中間,參觀二里頭遺址,當時對于二里頭文化的性質以及夏商分界斷在哪兩期之間,有多種看法,爭論難分難解。在鄒衡先生旁邊看陶片的一位歷史所先秦室主任說:如果能讓我把一個灰坑從頭做到底,就能解決這個問題。我在旁提醒他說,各種不同意見的論者,可都是有多年實踐經驗的考古學家。鄒衡先生抬頭嚴肅地看了我們一眼,訂正我說:“豈止是多年”。我想學歷史的若有多一點的田野工作實踐和見識,就不會有這樣簡單地看問題,歷史學和考古學者也能夠更好合作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