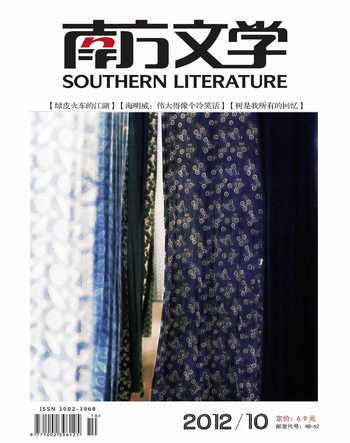愛神眷顧阿翔
嘉賓主持
【謝湘南】詩人,有詩集《零點的搬運工》《過敏史》出版,就職于《南方都市報》,現居深圳。
本月詩人
【阿翔】生于1970年。1986年寫作至今。曾在《大家》《花城》《山花》《今天》等雜志發表作品,著有《木火車》《少年詩》等詩集。曾獲《草原》2007年度文學獎,第六屆深圳青年文學獎,第二中國詩劇場貢獻獎。參與編輯民刊《詩篇》。現居深圳。
在我遇到的詩人中,阿翔是最特別的一位。他是我見到的唯一的全職詩人,除了寫詩、編詩、天南地北地與一眾詩人鬼混,他幾乎不干別的事,生活的所有軌跡都在圍繞詩歌運轉;他是一個真正的網絡詩人,如果一天不上網,他會像吸食鴉片的人斷了煙一樣——空落、焦躁、不安、痛苦——互聯網是他通向廣闊人群的窗口,是他的發聲器。
他因為年幼時失聰,從而也喪失了通過說話與人溝通交流的能力(很長一段時間里,詩歌是他人生唯一的通道),但神奇的是,因為愛情,現在的他找回了部分聽力,他逐漸地能說出話了。這真是一個奇跡,詩歌與愛情(通過詩歌與互聯網獲得)拯救了詩人阿翔,讓他的生活煥發出美好。
阿翔是安徽當涂人,那是個什么地方,我其實沒有概念。但我猜想,在上世紀八、九十年代,它與內地灰蒙蒙的小縣城,并無二致。阿翔在該城的一個軋花廠工作了十二年,打棉包、抬重物、做油漆活……那是他作為一個全職詩人之前,所歷經的生活暗流。那是2004年之前的事了。但作為沒落的工人階級中的一員,他打上了那個時代深深的烙印,“打過架,斗過毆,酗過酒”,甚至絕望時想要了結自己,唯有詩歌,像一盞明燈,對他的生活構成照耀與指引。后來工廠倒閉了,阿翔作為一個流浪詩人的形象才煥發出來,盡管是生活壓力所迫,但只有揮手告別,走出那灰暗的縣城,詩人阿翔才開始迎來他人生的開闊。
2004年之后,阿翔待過的城市有合肥、北京、南寧、廣州、十堰、茂名、南京……從2008年開始,阿翔在深圳暫居下來。也就是在深圳,阿翔才找到真正的幸福與生活的安寧,盡管租住在城中村的農民房,盡管生活不寬裕,但因為有愛情的滋養,阿翔成了我們當中笑得最燦爛的一個。
阿翔與他的妻子羊羊幾乎形影不離。每當圈中人聚會朗誦詩歌時,阿翔會用他獨特的爆米花般的語言,先爆炸一遍,然后羊羊用她充滿母愛的聲音,復讀一遍。他們互為“復讀機”,互為彼此的影像在深圳生活著。這些年,阿翔在羊羊的幫助下,已逐漸能“字正腔圓”地說話,這讓我們感到神奇,當他突然清晰地說出一個詞語,準確地說出一個句子,不需要我們費勁地去猜想時,我覺得,這是比寫詩更美妙的事。
阿翔寫過一本詩集《小謠曲》獻給他的羊羊——樹叢大而黑/轅馬不安寧/嘴唇有野蜜/至少你的守候沒有白晝/至少你的月亮沒有淪陷——她在鏡子里解開衣服/不說話/有時厭倦了/就在我手上咬一口……
從這些詩句中,我看到一個粗獷男人溫存的內心。當然,他們也從不放過在朋友面前秀恩愛的機會。有一次羊羊過生日,她收到了所有身邊或認識或不認識的朋友的祝福短信,而這是阿翔為了給羊羊一個驚喜,精心策劃的一場愛心轟炸。
阿翔喜歡喝酒,可以說無酒不歡,他可以把酒與詩人生活等同起來。每次聚會,他都可以旁若無人地喝到嗨。如果有人跟他對飲,他會迅速地把自己喝醉,面色通紅地倒下便睡。一兩個小時后,他會自己醒來,尚酒席仍未散去的話,他會接著喝。如果他仍未酒醒,而恰好此時羊羊也不在現場,他會被朋友們扶著送上一輛的士,消失在深圳的夜色中。
阿翔的詩
古詩
閱讀古詩就是起死回生。
他無所謂,索性坐在沙發上,對白夜視而不見。
它曾經是彌漫香氣的草藥,一下子回到郊外草莽,懂得欣賞的人近乎無幾。
虛構地鐵里的蚱蜢,這里,古詩多于星辰,人的命運各不相同。
破敗的旅店,“在露骨風情之下,你就得忍受市儈的臭味相投。”
有時美是危險的;有時顏面要去掉積攢太多的天賦。
他一直這樣以為,不受縛于遺囑的限度,說出即孤獨。
沒有秘密的人不靠譜,像假面舞會,差一點發出尖音。
現場的隱喻讓他扭過臉去,從不單方面試著去理解。
別擔心,古詩使他身后終究有蹤跡。
為了平衡,他偷偷培養著慢性胃病。
明月詩
在異鄉,那么遠的路程超過以往,成片的樹葉緊貼著光斑
散發出脫離世事的味道。鄰家晃動的人影在一里之外
不可高聲談論,或者,對生活保留一定的忍耐
這符合你的身份,當然,也許不是,是陳舊的審美讓人念及享受。
這樣寫,并非僅僅是天上的明月,具體到地上的河灣,浮云蕩漾過去
事實是,你看到的裸露,一陣陣泛白,隔著鐵和環境
然后被定義為轉移注意力,不能在原地停留。
有限的教誨,我不確定是否領悟,在這個時辰,軌道震動聲
使我反復尋找節奏,難以釋懷。因此
你獲得光亮的重量,是帶有泥沙性質,又仿佛幻象
我知道,用一首詩表現新的美學,才能確定距離的意義
我會懂得很多。多好啊,虛無如同挽留,那是另一個
主題,并不產生歧義。這一切,對于你,在荒蕪的林中
身軀懷著飽滿,同時隱藏著遼闊的秘密。
新贊美詩
她不能冥思苦想。不能在漫長的夏季
過早暴露,星期五黑得不像話,連傷害也是黑色的
身上的大雨操縱她的美。她曾經糾纏
雙性的身份,練習
健忘癥,以及對健忘癥的適應
多么不可能的安眠,“夢里的水滴還在滴答作響”
有時發現樹木:那失傳更久的舞蹈
比飛鳥還輕盈,以至于觸摸到一層不真實
的外皮(如果真有的話);有時她感到
無能為力,地理上的故鄉無緣無故地
變得星稀蟲喑,那些無關的耳朵
不會過來傾聽。如果專注些,就會注意到
手指上纏繞的毛線,周圍的空氣
是毛茸茸的,而眼前的速畫像不可理喻,但她不會
輕易說出。事實上,她所失去的可以組成
新國家,像一流的子宮
包括特有氣味、視野和情感,由此
她無邊無際。然后轉到了小教堂的歷史感
然后是祈禱,對傳記影片從片頭
到劇終視若無物
在雨中索性收起雨傘,“啊!這嘆息,這短暫
這上帝親吻的閃電!”
白皮書詩
無數雨水淹沒我的閱讀,進而急促,
一點點劇場的荒涼,光艷消失,
那么多人相互阻隔,目睹年華已逝,影響你的一切,
有時,你會想一些問題,
這里就有一個,譬如冷氣融入新鮮空氣,
由于經驗不足,感冒隨時發生,
之后一蹶不振。還未被經歷過,用白皮書掩蓋“域名不存在”,
無法訪問,最終歸于我自身難保,
對負重累累進行清算,只識得酒中趣味,
慣于秘密旅行,你就會明白這一不爭事實。
“你終于沉淀了下來”,這意味著我無可掙脫,
“沉到了最底層。”傳說中的引文,
可以在黑暗中側耳聆聽,當然我不用沉湎于夜色,
像你說的僅僅是安靜的位置,
漂浮一首詩的古舊韻律,“你將永久盤踞”。
鐵軌深不可測,唯有你能夠檢視嗓音,
在世界的姹紫嫣紅祈禱,
癌癥不可放在這里擴散……
并以此證明樹木有呼吸的幽香,我看到你的童年,
泥濘的腳印,或許,是尋找云朵上的“一滴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