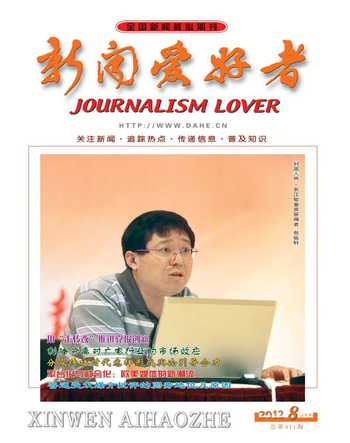“輿論政治”:《國風報》與晚清憲政文化的實踐
從戊戌變法以后,憲政就一直是國內外報刊熱衷探討的問題。改良派人士在日本創辦的《清議報》和《新民叢報》不僅將西方的立憲制度條分縷析地介紹給國內讀者,同時還將憲政文化作為一種國民常識進行普及和宣傳。盡管革命派創辦的《民報》對君主立憲進行了激烈的批判,但對于以憲法實施為政治合法性的基礎這一點并沒有太多的異議。辛亥革命的結束無疑也結束了清政府立憲實踐的可能,但改良派人士在憲政文化建設中的努力并非毫無“遺產”可言,至少在一些報刊的議政方式上已經將“輿論政治”變成了憲政文化的直接表現形式,這不僅在新聞史上意義深遠,也給現代政治文化提供了更多的可能性。
《國風報》于1910年2月創刊于上海,作為一份旬刊,它出版至1911年7月停刊。在這份由何國楨編輯發行的刊物中,早已在輿論界有著赫赫名聲的梁啟超(使用筆名滄江)是其主筆。它也是《新民叢報》停刊之后,改良派人士最主要的輿論陣地。在《國風報》刊行出版之時,正是清政府推行預備立憲如火如荼之時,宣統帝固然還無力主政,一班耆舊老臣和封疆大吏也各有盤算。于是,圍繞國會問題、鐵路舉債問題和民變處理等問題,《國風報》以每期8萬余字的篇幅連篇累牘地發表相關言論,起到了轉移一時輿論的作用,創刊后便行銷十七省及南洋、澳洲、美國、加拿大等地。
“輿論政治”與憲政文化
在《國風報》的敘例中,論者便稱“夫立憲政治者,質言之則輿論政治而已”[1],在長輿的《立憲政治與輿論》一文中進一步發揮,稱“專制政體之下,固無輿論發生之余地也。立憲時代則不然,一切庶政無不取決于輿論”[2]。立憲政治是歐洲資產階級革命的一個成果,它所確立的三權分立模式是在于一種權力的內在制衡,以及遵循一種普遍法來治理國家。清政府在最后十年其實已努力在政治體制上做出一些改變,為了維持穩定以及皇族的利益,預備立憲已經提上議事日程。但辛亥革命客觀上也使宣統五年的立憲沒有出現,另外在立憲過程中簡單地將從前的官僚機構改變成為新設的咨議局等做法也違背了程序正義,這也是其后各種歷史敘述將其看成“騙局”的根源。
從1896年的《時務報》開始,康有為和梁啟超等人所宣傳的政治改良其實有過一些變化和曲折。在戊戌變法前后所宣傳的改良主要是一種“自改良”,主要是對具體制度環節的改變。而在《新民叢報》與《民報》的論戰過程中,維新派人士在擁戴君主的同時,其實已經不斷地介紹西方君主立憲制的成功經驗,并經常以日本明治新政作為師法的對象。在革命派和維新派論戰的開始階段,雙方的焦點主要在于改變政治的手段以及滿族的統治是否合法的問題。但在清政府開始通過積極姿態應對危機時,革命派報刊對各種政治改革均抱有懷疑和否定的態度,在報刊言論上也多以揭露內幕為己任,對于相關制度的介紹和宣傳遠不及《國風報》等立憲報刊深入和透徹。
由于歷史的后設性,《外交報》、《中國新報》以及《國風報》經常被看做努力維護滿清統治的利益,而很少被認真看待它們在憲政文化實踐中的貢獻。只要衡量一下這些報刊的言說,它們對立憲政治的設計其實非常清楚。他們將國會問題當做最先決的前提,然后再由國會進行政黨的構造和重建,在內閣組成之后,具體的政治治理將接受廣泛輿論的監督,投票表決也將因此而具備真實的效果。
探討國會的開設與否是當時政論報刊中的熱點,以《國風報》為代表的報刊強調國會的積極意義,并期待其迅速召開。孫洪伊等人也因此上《國會代表請愿書》,條陳迅速召開國會的必要性。而以《新世紀》為代表的無政府主義報刊則對國會的存在持全然否定的態度,認為政治是人民自決,不需要組織任何形式的政府。在《河南》、《云南》等留日學生雜志上,看到的更多是國會的負面效果,呂志伊的《國會問題之真相》里極言“以今日之提倡立憲、要求國會者,皆欲利用國民者也”[3]。
對于留日學生雜志上提出的這些問題,《國風報》自然也關注籌組國會的實際情況。一旦發現皇族內閣的雛形,該報便毫不留情地進行批評,并幾次三番地組織請愿活動,這似乎不能簡單看做是“資產階級立憲派敵視群眾,敵視革命,對群眾暴力革命的恐懼遠遠超過對清政府的不滿”[4]。這些預演對于清政府固然沒有取得良好效果,但對于后來的袁世凱政府卻產生了不小的壓力。至少作為中華民國的總統,袁世凱不可能不考慮輿論對于國會的期望。而與國會相聯系的政黨雖然沒有對垂暮的晚清起到作用,但在袁世凱當政時期已經明顯能起到一些制約作用,這不能不說是憲政實踐逐步產生效應的結果。雖然《國風報》沒有迎來三權分立的立憲政治,但卻收獲了輿論左右政局的可能性。
輿論與國民啟蒙
在《國風報》所提出的“輿論政治”中,有兩個不同的面向:一是對政府的監督和批評,使之行之有效;二是引導社會思潮,對普通國民進行啟蒙和政治教育。輿論的勢力之大,已經是晚清報界人士的共識,而他們最擔心的問題也是國民受到不當言論引導走上偏激之途。當時各地發生的民變固然沒有太多輿論的介入,但報界人士不斷告誡政府,一旦民眾受到輿論的鼓動產生對政府的不滿,則會引起災難性的后果。因此,在《論政府阻撓國會之非》一文中,滄江(梁啟超)將國會與國民課本放在一起,“籌備案中有編輯簡易識字課本、編輯國民必讀課本、創設簡易塾等條,最為可笑,吾前曾言之。夫國家教育之本意,非驅一國之民悉從事于政治也,故普通教育重焉。所謂政治教育者不一端,而官私大學之教授,報紙之論列,政黨之指導,其最要也”[5]。梁啟超辨析了普通教育與政治教育的區別,認為在國民教育中常出現泛政治化的錯誤做法,而忽略了循序漸進的步驟。理想的國民教育應該是一種自我的啟蒙,而啟蒙的結果是能夠自如地參與到國家政治事務中,而具備基本政治常識的要領無非是大學的教授、報紙的宣傳以及政黨制度的不斷深入。對于接受過普通教育,但沒有進入大學學習或者不屬于政黨成員的人來說,報刊輿論無疑是強化其政治參與性的最便捷途徑。
晚清的國民啟蒙問題一直是研究近現代史必須面對的問題,通過眾多學者的辛勤研究,思想家個人的啟蒙理路已經呈現無遺。但對于一般民眾的啟蒙問題,則往往只是著眼于基本素質提高的層面,對于白話文運動和下層啟蒙運動的研究都可做如是觀。但其實,在鼓動一時之風氣的精英與等著亦步亦趨的下層民眾之間,肯定還會存在一些中層人士,他們受過相當的文化教育,但對于世界大勢或者政治觀念并無深入了解,他們有固定的閱讀時間,也有參與政治的必要資本。這些人有可能成為地方咨議局的成員,也有可能成為憲政民主的直接實踐者。他們接受的政治訓練可能并不專業,而對政治事務的實踐往往要乞助于先有的“案例”,而這些往往是報刊信息與政論碰撞的結晶。
探討國民文化的復雜性不在于掌握當時究竟有多少缺乏基本文化素質的國民,而在于一些思想界精英虛構了國民的文化形象,也簡單化了知識精英與欠修養國民的對立。保存國粹與批判儒學在某種程度上是內在一致的,都是虛擬了一種理想的國民文化境界,然后希望所有的國民都按照同樣的路徑去發展,而放棄了可能有的其他選擇權。在國粹派或新文化人士視野下的國民,都是知識未定的青年,對他們的啟蒙是方向和價值,而不是選擇和同情。而借助輿論引導的國民,則會給予他不同的選擇權,他可以沒有固定的價值觀念,但一定會清楚自己的權益,成為一個具有現代政治意識的國民。
晚清的立憲政治沒有成功,但憲政文化卻給中國的政治文化帶來了一些較為新鮮的維度,而《國風報》憑借輿論啟蒙國民的思路也是彼時國民文化中的一個新思路。從《申報》開始,中國出現了不少商業報紙,它們構建的新聞文化不見得完全是呼應西方的市民社會,構筑起來的空間具備一定的公共性,但其討論的策略決定了它對政治問題的隔靴搔癢。而《新青年》等構筑的文化空間則將文化建設當成了建國方略,目標懸之過高,常會成為各種主義和信念交戰的場所,與普通國民的政治權益相關度較低。而清末民初的一批立憲派報紙,尤其像《國風報》,既能探討重大的政治問題,也為略有常識的國民提供了解政治的各種參考,尤其是了解到自身的權益。這對于現代國民文化的塑造有著重要意義,也對“輿論政治”的真正形成提供了可能。
參考文獻:
[1]《國風報》,第一期.《辛亥革命前十年間時論選集》,北京:三聯書店,1977年版,第586頁.
[2]《國風報》.第十三期.《辛亥革命前十年間時論選集》,三聯書店,1977年版,第624頁.
[3]《云南》.第十六期.《辛亥革命前十年間時論選集》,北京:三聯書店,1977年版,第456頁.
[4]《辛亥革命前十年間時論選集》.序言,北京:三聯書店,1977年版,第8頁.
[5]《國風報》.第十七期.《辛亥革命前十年間時論選集》,北京:三聯書店,1977年版,第641頁.
(作者為北京聯合大學應用文理學院新聞與傳播系副教授,博士)
編校:趙 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