非211,直接申請澳洲全獎
2012-04-29 00:44:03
大學生
2012年19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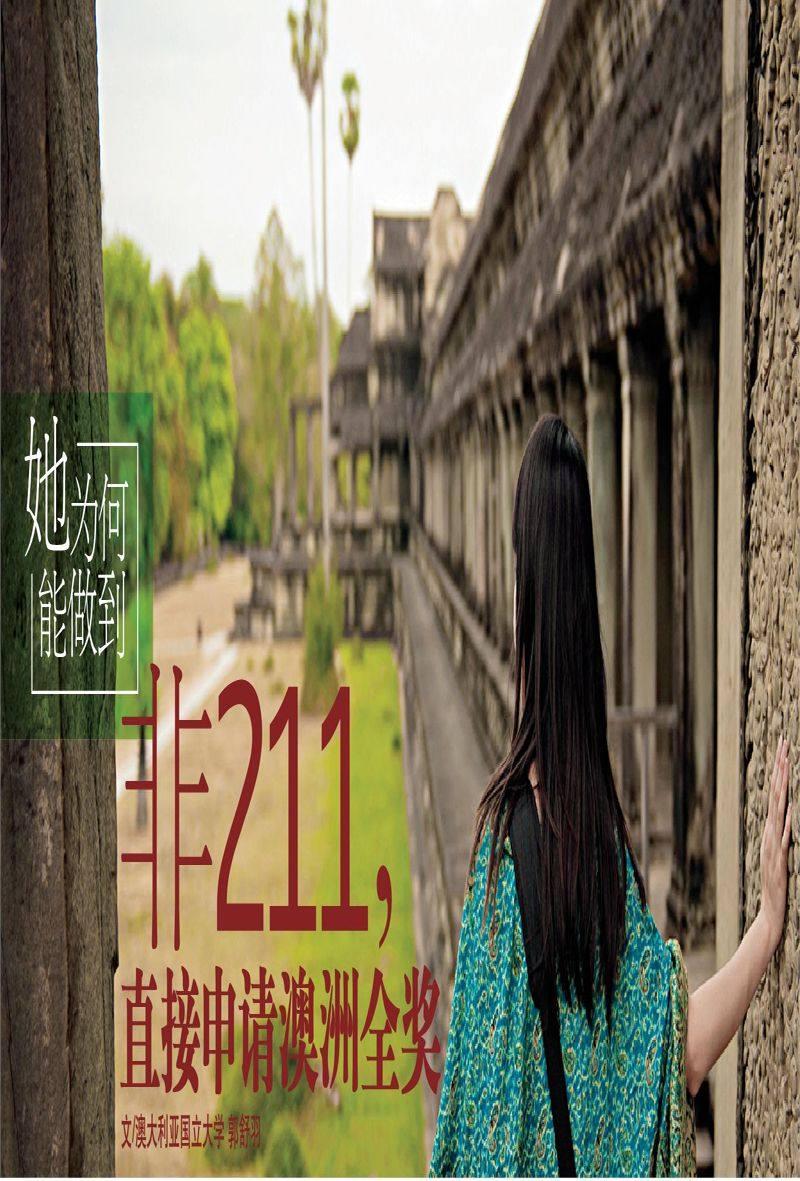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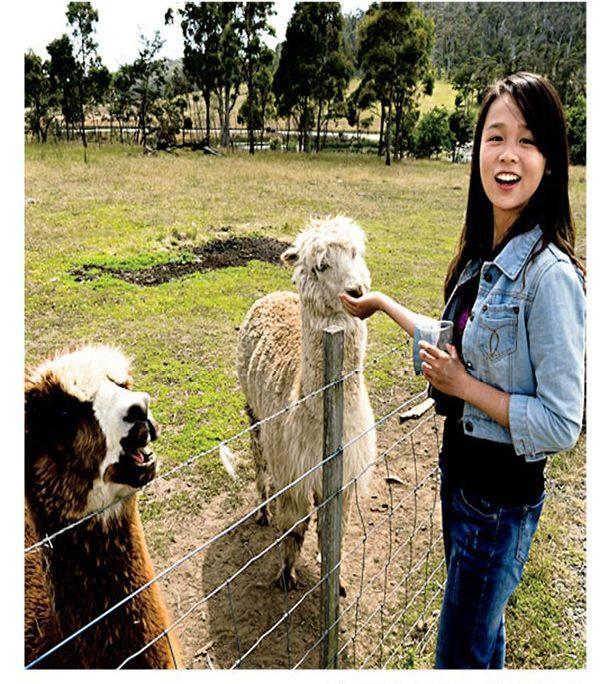

2008年大三結束的夏天是我生命中的轉折。
5·12汶川大地震后的一周,我開始臨床實習。此前,我是南方醫科大學的乖學生,每天學習到深夜,因為受到嚴格的科研訓練,以為自己的世界觀理性而嚴整。大一第一次面對尸體,我只將其看作單純的物質殘骸或標本,并不感到恐懼,也嗅不到死亡氣息。考試前,與同學們在有著刺鼻福爾馬林氣味的解剖樓里復習到深夜,也從未擔心過鬼魂。
直接面對鮮血與病痛,我卻無所適從。
第一次上手術臺,面對一個9歲的小女孩柳兒。她因為反復發作胃潰瘍,造成幽門梗阻,要做胃大部分切除手術。手術前的談話和身體檢查都不太順利,柳兒已預知要發生的一切,因為恐懼哭泣。麻醉后,她陷入深沉的睡眠。電刀劃開一道深長的切口,主刀醫生下了一張判決書:“她的疾患會在19歲時惡化成胃癌,無法遏制。”
地震和現實中的生老病死相交疊,現代醫學的光環慢慢褪去,人類并不如想象中強大,無法了解自身,掌控命運。從那一天起,我“嚴整”的世界觀被撕開一道缺口。開始不易察覺。但是,我知道它就在那里。
那個夏天,我決定第一次長途旅行。
在哈巴雪山郁結坍塌
我不曾料到旅行生涯會有一個驚艷的起點——一座高5396米的雪山。
也是在那個夏天,我認識了Vicky,覺得他是一個傳奇。那個夏季,他帶著“極限營地”進駐廣州,募集第一批隊員,目標是香格里拉的哈巴雪山。Vicky那時只有25歲,卻走過很多地方,自由自在地旅行,冒險,帶領懵懵懂懂的都市人進入野外并以此謀生。……
登錄APP查看全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