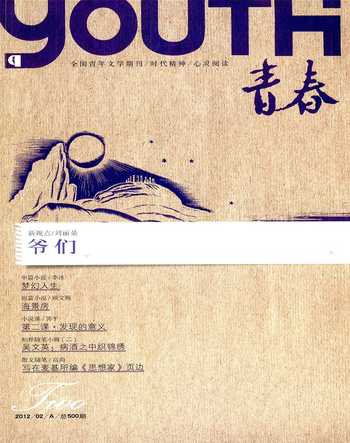爺們
謹(jǐn)以本文獻(xiàn)給我們最愛的馬雁,文中的兩首詩(shī)分別引自馬雁的詩(shī)《我們乘坐過(guò)山車飛向未來(lái)》、《痛苦不會(huì)摧毀痛苦的可能性》
我第一次看見B少爺是在電視上。那是一個(gè)教育頻道的訪談?lì)惞?jié)目,兩位女嘉賓坐在一張長(zhǎng)得竟有條凳風(fēng)格的桌子兩側(cè),時(shí)而巧笑倩兮,時(shí)而美目流盼,可惜都交付與不解風(fēng)情的桌子觀賞。在這悠長(zhǎng)悠長(zhǎng)的桌子中間,端坐著油頭粉面的B少爺,竭力伸長(zhǎng)他那鵝頸般的脖子,時(shí)而向左,時(shí)而向右,問著那些明顯缺乏娛樂性的問題。當(dāng)女嘉賓的回答略顯漫長(zhǎng)時(shí),為了令電視屏幕看起來(lái)不是靜止的,B少爺不得不把頭轉(zhuǎn)過(guò)來(lái),看著左女嘉賓,又很快地把頭擰過(guò)去,看著右女嘉賓。她們的回答顯得沒完沒了,B少爺不得不加快腦袋的轉(zhuǎn)速,以至于我看了一會(huì)兒,就不得不因頭暈換臺(tái)了。
那兩年,B少爺在國(guó)內(nèi)很活躍,在四處的圈子中留下了他的足跡和艷史。所以當(dāng)B少爺最終出現(xiàn)在我面前時(shí),關(guān)于他的事情我已經(jīng)聽說(shuō)得差不多了:美國(guó)教授,海上才子,容顏不老,風(fēng)流成性。我們見面的地點(diǎn)是一家全國(guó)連鎖的咖啡店,叫做島上咖啡,同B少爺一起出現(xiàn)的詩(shī)人S老爺頗有一些癡處,例如:寫詩(shī),他只尊杜甫;會(huì)朋友,他只去島上。我曾在北京八大城區(qū)的一切島上同他見過(guò)面,當(dāng)然最經(jīng)常去的是P大附近的那家。P大附近的島上咖啡是S老爺悶了常來(lái)坐坐的地點(diǎn),為了解悶,他每次會(huì)喊上一兩個(gè)愛好文學(xué)的男女青年前來(lái)陪他聊天。那二年,不知道為什么,S老爺喜歡的青年聊友是我和Q。所以那天B少爺出現(xiàn)的時(shí)候,Q也是在的。
Q坐在我的對(duì)面,B少爺坐在他的旁邊,S老爺坐在我這邊。我終于見識(shí)到B少爺?shù)恼嫒萘耍幻嫒籼一ǎ酆锼瑴啿幌窠咏鍙垺D翘焖窈⒆右粯油嬷男孪鄼C(jī),那是一個(gè)很傻的SONY,根本沒有鏡頭可言,可是后來(lái)我知道,B少爺個(gè)人攝影展上那些具有抒情抽象派風(fēng)格、亦真亦幻的照片都是用這樣的相機(jī)拍出來(lái)的。那天,看見我的第一個(gè)瞬間,他便按下了他的快門。接著他又拍下了幾百?gòu)堈掌涗浟嗣恳粋€(gè)“咖啡館清談”主題的雷同瞬間。
——且慢。讓我們潛入他的電腦,仔細(xì)地看他拍下的這些照片吧。第一張,S老爺像金剛一樣占據(jù)了大半個(gè)沙發(fā),把我擠在一隅,坐得筆直,像一根狗尾巴草。我的目光是對(duì)著鏡頭的;第二張,是我的特寫,我的目光是對(duì)著鏡頭的,第三張,S老爺陷入頹廢,吞云吐霧,我的目光對(duì)著S老爺,在畫面中留下一個(gè)不顯眼的側(cè)面……
那天晚上我始終沒有用正眼看過(guò)一次Q,這個(gè)問題,后來(lái)B少爺觀察照片的時(shí)候也發(fā)現(xiàn)到了。事實(shí)上,他就是因?yàn)楦杏X到蹊蹺才去認(rèn)真觀察照片的。他的觀察得到了一定的結(jié)論,后來(lái)他興高采烈地對(duì)Q公布了他的發(fā)現(xiàn)。他說(shuō)他看破了Q和我之間的玄機(jī)。B少爺?shù)脑挘蟾攀遣粫?huì)錯(cuò)的,因?yàn)锽少爺是對(duì)談戀愛很有經(jīng)驗(yàn)的人。
接下來(lái)的故事,主角是我和Q,給它們一個(gè)標(biāo)題,叫做《戀愛故事》吧。既然是戀愛故事,那么不說(shuō)也罷,因?yàn)樗械膽賽酃适露贾皇谴笸‘悺偃藗內(nèi)娜飧惺艿模悄且稽c(diǎn)點(diǎn)“小異”;讀別人的人生時(shí),人人看見的就都是“大同”。就讓那一點(diǎn)“小異”隨風(fēng)而散吧!
略去十萬(wàn)字的兩年之后,我和Q同學(xué)的婚期在即。恰好B少爺回來(lái)了。那二年,B少爺在國(guó)內(nèi)營(yíng)謀了一下,終于還是回美國(guó)去了。美國(guó)教授與中國(guó)教授之間的區(qū)別,不僅是“刀”和“元”的區(qū)別。但他又實(shí)在舍不得祖國(guó),這里有無(wú)數(shù)的花姑娘,各種熟悉和各種奇異,舉辦著無(wú)數(shù)場(chǎng)詩(shī)歌朗誦會(huì)、學(xué)術(shù)研討會(huì)和混吃混喝、游山玩水的筆會(huì)。凡是這種事情都是沒什么正經(jīng)可言的,那正是為B少爺喜愛的逍遙。所以他趁著暑假溜回來(lái)了,暫住在Q家里。
白天的時(shí)候B少爺時(shí)常是出去的,去向不明,過(guò)程不明,會(huì)見何人不明,結(jié)果倒是很明確,那就是回來(lái)。他睡得很晚,起得很早,興高采烈,精力充沛,到家之后肯和我們打撲克,一直打到盡興,從不推三阻四。當(dāng)然,B少爺出門一定是去干正經(jīng)事了,就算有什么不正經(jīng),我們又何必亂猜。有時(shí)B少爺跟我們唱起歌劇,后來(lái)幾乎天天唱,在打撲克的間隙,或者邊打撲克邊唱。他的牌打得一般,但是牌風(fēng)很好,哪怕被Q指責(zé)出錯(cuò)了牌,也只是笑嘻嘻地聽著;歌劇呢,唱得比他做主持人有娛樂性多了,他出身音樂世家,偏做了文學(xué)的玩票。還有,我終于知道了B少爺迷人豐姿的出處,某個(gè)早晨他依舊一大早出去,到了中午回來(lái),皮箱里裝滿了動(dòng)物園批發(fā)的廉價(jià)衣物。他把箱子打開,每天穿一件新的,或是10元的T恤,或是20元的襯衫。那些地?cái)傌洿┰谒纳砩希巳硕家詾槭敲绹?guó)買的。——說(shuō)實(shí)話,動(dòng)物園是個(gè)很有品位的地方,戲仿的對(duì)象經(jīng)常是TOMMY這樣的品牌。
有B少爺在的日子很是歡樂。
偶爾我們也三人同游,那一定是有什么公共性的事件,或是某個(gè)熟人的飯局,或是某個(gè)活動(dòng)的開幕。有一天我們大約凌晨回來(lái),Q醉得不成樣子,不知道為什么,我們仨一同鉆入了距離家還有50米處的小花園,Q面對(duì)松樹垂頭而坐,身體重得像石頭。一刻鐘過(guò)去了,又一刻鐘過(guò)去了,我還是搬不動(dòng)這塊石頭,每隔5分鐘,B少爺過(guò)來(lái)看他一次,又笑嘻嘻地走開,然后傳來(lái)他那響遏行云的歌劇。
那是Q嗜酒的末期,那時(shí)B少爺也是酒中之仙,盡管他已經(jīng)不年輕。大概這樣的人在一起,總歸是要醉幾場(chǎng)。后來(lái)有一次,我們又三人同游了,這次是去P大,跟P大的人會(huì)面。吃飯的地點(diǎn)選在北宮門的西貝莜面村,我的師兄雅莊和龍章都來(lái)了,大家已經(jīng)熱聊了一陣,又來(lái)了一個(gè)人,是K大爺。——大爺?shù)臓斈疃暎皇禽p聲。他姓K,名叫大爺,是個(gè)白面的江南人,穿一身很有來(lái)頭的衣服,在時(shí)尚界工作。初見K大爺?shù)囊粋€(gè)小時(shí)內(nèi),他是個(gè)無(wú)趣的家伙,坐在桌邊,一本正經(jīng),談著比如“如何給雜志融資”之類的無(wú)聊話題。他看上去很像一個(gè)雜志的主編,所以后來(lái)他一直有工作,一直做主編,做垮了好幾個(gè)雜志,都是因?yàn)樗茏屪约嚎瓷先ズ芟竦木壒省:髞?lái)我想。
第一頓吃完后,我們這支隊(duì)伍(Q,B少爺,K大爺和龍章,只有雅莊回家了)來(lái)到P大西門的街邊露天烤翅店,飯局于是才正式開始,而酒和劇談是這頓飯的主角。作為文人的小聚,文學(xué)自然會(huì)是情不自禁的話題。K大爺?shù)莫b獰面目于是開始顯露,叫喊著某某是SB,另一個(gè)某某也是SB。但K大爺沒有說(shuō)明任何理由。龍章在同他爭(zhēng)論,說(shuō)某某不是SB,某某是哥們。K大爺仍然堅(jiān)持道:某某是SB。他們的車轱轆話說(shuō)到第四遍時(shí),已經(jīng)是黃昏,天光依然很明亮,我們圍繞著一張簡(jiǎn)陋的白色塑料飯桌,話題此起彼伏。是B少爺?shù)谝粋€(gè)發(fā)現(xiàn)旁邊座位上的女生的,那大概是個(gè)美麗的女生,旁邊還攜帶著一位研究生形狀的男士。B少爺喊那女生過(guò)來(lái),坐到我們這桌來(lái),那女生說(shuō),一會(huì)兒,過(guò)一會(huì)兒。Q于是也喊那女生來(lái),K大爺也喊。那女生繼續(xù)說(shuō):過(guò)一會(huì)兒。男的也跟著說(shuō):一會(huì)兒再去。就這樣幾個(gè)回合,那女生終于帶著她的男伴坐過(guò)來(lái)了。
他們剛坐過(guò)來(lái),就下了一霎兒的黃昏雨。風(fēng)忽然起來(lái)了,雨嘩啦嘩啦地下,大顆大顆地落在身上。飯館老板娘扛來(lái)一張遮陽(yáng)傘,插在塑料桌子中間的那個(gè)眼里,我們于是都坐得往前湊了湊,雨仍在下著,淋濕了我們的后背。誰(shuí)也沒有說(shuō)話,只有噼里啪啦的雨聲包圍我們,所以并沒有顯出沉默,我們的耳邊煞是熱鬧。每個(gè)人都在凝神聽這雨聲,過(guò)了幾分鐘,Q感慨道:“浪漫!”
這也是此時(shí)此刻我的想法。
雨很快就停住不下了,天黑下來(lái),風(fēng)吹得我們后背的衣裳也漸漸干了。這一群人于是有了較為松散的布局。那個(gè)男伴已經(jīng)介紹了自己的來(lái)頭,說(shuō)他是附近Q大的研究生,說(shuō)那女孩是他的一個(gè)朋友,從重慶過(guò)來(lái)看他。他的話沒有人認(rèn)真聽,但人們都聽到了其中比較重要的部分,大家的心思都在那個(gè)女孩身上。女孩沒有跟她的男伴坐在一起,而是坐在K大爺和B少爺中間。B少爺從他的座位上站起來(lái),大聲唱起了歌劇,同時(shí)散發(fā)著名片,那上面印有美國(guó)教授的頭銜,和他的一切私人信息,包括手機(jī),住宅電話,郵件地址,和家庭住址。
“無(wú)聊,真是無(wú)聊啊。”龍章單獨(dú)坐在一旁,遠(yuǎn)遠(yuǎn)地看著酒意上頭的B少爺和K大爺一邊高談闊論,一邊分別依偎著那個(gè)女孩,奇怪的是,她的男伴始終在旁邊帶著謙虛的笑意看著這一切。
女孩已經(jīng)喝高,情緒漸漸放開,有他們喜愛的豪放。男人們提到她的男伴,說(shuō)是她的男朋友,她說(shuō),他是有老婆的。她再三指責(zé)她的男伴,看來(lái)對(duì)他積怨甚深,但眼前的這幾個(gè),又是什么好東西呢?就連Q,也不肯放過(guò)這個(gè)貧嘴的機(jī)會(huì):
“姑娘,你真美,要不是我女朋友在,我就撲上去了。”
“唉大哥,我真羨慕你,姐姐,我真羨慕你們倆。你們是多么好的一對(duì)兒。有這么好的感情。”姑娘用喝多了的大舌頭說(shuō)道。
這時(shí)Q被啤酒醍醐灌頂,接著,我站起來(lái)對(duì)那女孩說(shuō):“你說(shuō)你都二十八歲了,你那么老,還喊我姐姐。”
“不是,小妹,我真羨慕你們倆。”醉中的重慶女孩語(yǔ)無(wú)倫次地說(shuō)。
這一瓶啤酒的快意激起了Q反抗的精神,他繼續(xù)對(duì)重慶女孩說(shuō):“你真美,太漂亮了,我愛你,你比我的女朋友漂亮多了。”
如果這一場(chǎng)胡鬧不歡而散,那么它就不叫胡鬧了,這些非凡的人物也便不能稱其為“非凡”。歡宴仍在繼續(xù),長(zhǎng)夜那么長(zhǎng),人生那么短,不胡鬧何以銷此永夜?夜深時(shí)歡樂到達(dá)巔峰,過(guò)量的啤酒使人們魚貫地奔赴廁所,而當(dāng)Q摟著我走到廁所門口時(shí),發(fā)現(xiàn)B少爺正守在廁所門口高唱歌劇,而重慶女孩在里面反叉著門。后來(lái)B少爺尾隨重慶女孩重新回到座中,Q則尾隨著B少爺,K大爺一邊放肆地跟重慶女孩開著玩笑,一邊回轉(zhuǎn)頭來(lái)低聲對(duì)我們說(shuō):“這個(gè)女人目光輕佻,渾身亂動(dòng)。”
龍章自言自語(yǔ)道:“無(wú)聊啊,真是無(wú)聊。”
夜幕中,我看到他站起來(lái)走掉了,沒有同任何一人打招呼。臨近黎明時(shí)重慶女孩也趁亂跑走了,還有她的男伴。幾個(gè)人曾經(jīng)試圖追趕,但沒有追上,K大爺只好去追早起晨練的某個(gè)人的狗,Q去追K大爺,追著追著他們打起來(lái)了。我們只是看見,Q和K大爺一邊打架,一邊退回到我們的桌子邊。K大爺后來(lái)坐出租車走了,我們仨也打了一輛出租車回家去,Q的精力還沒有消散,完全沒有,我也是,于是我倆又痛痛快快打了一架,我徒手把Q的T恤撕爛,還拿了幾個(gè)大頂,做了幾個(gè)前后空翻。
“Q,你怎么可以當(dāng)著雁窠調(diào)戲那女孩,我是絕對(duì)不敢的,我哪怕倒下來(lái)立刻死了,也絕對(duì)不敢當(dāng)著清歌說(shuō)你說(shuō)的那些話!”這是后來(lái)當(dāng)我不在的時(shí)候,B少爺教育Q時(shí)說(shuō)的。
B少爺?shù)睦掀徘甯枋莻€(gè)小歌星,K大爺?shù)睦掀琶钗枋俏璧秆輪T,兩位都是國(guó)色,從她們沉魚落雁的容貌,可以看出她們的丈夫達(dá)到了好色的極致。不像Q,不小心落了找文學(xué)女青年的俗套。這年八月,文學(xué)男青年Q要和文學(xué)女青年我結(jié)婚了,還有三天要舉辦婚禮的時(shí)候,B匆匆飛回了美國(guó),Q想留他參加婚禮,但他沒有時(shí)間了,為了表達(dá)對(duì)我們婚姻的祝福、對(duì)我們尚武精神的激賞,他在小商品市場(chǎng)花一件襯衫的價(jià)錢買了套刀叉之類的西洋餐具送給我們做禮物。
我們的婚禮舉辦在一家前身是皇家糧倉(cāng)的開闊建筑,以沉著的赭紅為布置的底色,亮晶晶的玻璃杯里盛滿猩紅色的美酒。侍者穿著深藍(lán)色的長(zhǎng)袍,穿梭在自助餐供餐臺(tái)和一個(gè)個(gè)以細(xì)細(xì)的水簾分割開、彼此可以望見的小房間中。來(lái)的無(wú)非是各路豪杰,包括K大爺在內(nèi)。有抱負(fù)的文人捋著他的幾根胡須,看著水晶宮一樣的婚禮現(xiàn)場(chǎng),富有深意地說(shuō):“怎么有些韓熙載夜宴圖的味道?”
當(dāng)晚,許多人涌入我家,大家仍不想走,人們高談闊論。X被K大爺指著鼻子數(shù)落一頓之后,發(fā)誓今生再也不理K大爺了;而K大爺數(shù)落X的,是跟Y有關(guān)的一些事,跟X根本沒有淡關(guān)系。只是,他的盛氣凌人,令X感覺受了污辱。有K大爺?shù)牡胤娇偸欠滞庑鷩蹋藗儽M可能地提高他們的音量,好使他們被人聽到。聲浪一浪高過(guò)一浪,夾雜著時(shí)而爆發(fā)的大笑。在聲浪的迫擊下,我走出客廳,巡視各個(gè)房間,尋找到來(lái)的女客。就在客廳旁邊的小房間里我看見妙舞撐不住睡了。這是暑氣剛剛有些消退的八月,其實(shí)還熱得很,妙舞不知從哪里扯了一床大被子蓋在身上,蓋得嚴(yán)嚴(yán)實(shí)實(shí),安安靜靜地瞑目而眠。她睡得很香,甚至發(fā)出了輕輕的鼾聲,像個(gè)天使一般無(wú)思無(wú)慮,容光煥發(fā)。我有些擔(dān)心,怕她會(huì)熱得出汗,同時(shí)怕外面震耳欲聾的喧囂吵到她。但妙舞看起來(lái)很好,她的樣子是那么甜美,就像一株忘憂草。我輕輕地走出房間,把門關(guān)上了。
K大爺正在客廳里發(fā)表關(guān)于妙舞的演講,可惜妙舞沒有聽到。事實(shí)上,K大爺無(wú)時(shí)無(wú)刻不在稱贊妙舞,他的老婆,他的女神,他靈魂的女主人。K大爺說(shuō),妙舞根本不愛好文學(xué),對(duì)文學(xué)毫無(wú)興趣,但是那年,妙舞正當(dāng)妙齡,家里人安排她嫁給一個(gè)溫州鞋商,結(jié)婚的前三天遇見了他,便決定跟他走。“她竟然會(huì)跟我走!這個(gè)一生中從來(lái)沒有跟她的家里人說(shuō)過(guò)一個(gè)不字的乖乖女,這個(gè)純真無(wú)瑕,不諳世事的少女!她為什么要跟我走?我?我這個(gè)人,一無(wú)所有!我連一間可以棲居的房子,連一毛錢存款都沒有!所以,我要歌頌妙舞,歌頌我的老婆,偉大的女性!”
Q在跟我結(jié)婚之后,升級(jí)成為Q老爺。這個(gè)封號(hào)是我的女朋友們作主加封的,用以表彰Q老爺在家庭中衣來(lái)伸手、飯來(lái)張口的功勛。話說(shuō)都什么時(shí)代了,作為一位文學(xué)女青年,難道不要追求男女平等嗎?看官,你有所不知,鍋碗刀叉、油醬鹽醋這些神器,是Q老爺使不來(lái)的,在他一生中從未單獨(dú)對(duì)付過(guò)它們。作為與他心意相通的朋友,我怎么舍得讓那些盆盆罐罐去欺負(fù)他呢?男女不平權(quán)的起源并非是他們用鐵鏈子把我們鎖起來(lái),而是我們的愛。
某個(gè)融融夏日,正是B少爺歸來(lái)的季節(jié)。黃昏時(shí)分,B少爺和Q老爺一起不見了蹤影。他們說(shuō)要去見K大爺。我在家中等候著他們,等著、等著睡著了,他們?cè)缟喜呕貋?lái)。
這樣一個(gè)沒有老婆的夜晚,他們干什么去了呢?他們依舊去了偶遇重慶女孩的地點(diǎn),既非緬懷遺跡,又沒有繼續(xù)漁色,我想他們是無(wú)所事事。他們依舊清談到深夜,然后三個(gè)人到P大校園里面游蕩。他們走到了未名湖畔,K大爺談起剛才同他們一起吃飯的人,其中有一個(gè)人是狗監(jiān),——一個(gè)文學(xué)刊物的編輯,許多年來(lái),他是K大爺唯一的編輯,只有狗監(jiān)在他那個(gè)頗有名望的期刊上發(fā)K大爺?shù)男≌f(shuō),別的人都不肯。K大爺?shù)奈膶W(xué)才華有目共睹,他是Q老爺在小說(shuō)方面唯一佩服的人,2002年他出版了一部長(zhǎng)篇小說(shuō),長(zhǎng)達(dá)50萬(wàn)字,才華橫溢犀利優(yōu)美,把南方生活的方方面面寫成一副清明上河圖似的風(fēng)俗畫,其中有部分的色情描寫,令出版商認(rèn)為有可能獲利。這件事的最終結(jié)局是銷售的慘敗,就好像K大爺從來(lái)沒有寫過(guò)這么一部小說(shuō)一樣。如今K大爺又有一部50萬(wàn)字的長(zhǎng)篇小說(shuō)脫稿,此外他還有若干振聾發(fā)聵的中短篇,然而,肯發(fā)他的小說(shuō)的編輯只有狗監(jiān)。
“你看到了嗎?狗監(jiān)。狗監(jiān)今天的那個(gè)樣子。”
K大爺接著告訴他們,多年來(lái),狗監(jiān)一直把自己居功為K大爺?shù)亩髦鳎路餕大爺?shù)男≌f(shuō)得以發(fā)表,全都是因?yàn)樗蝗酥Γ鶮大爺?shù)奈膶W(xué)才華沒有關(guān)系。
“狗監(jiān)的確是狗的嘴臉。”B少爺和Q老爺都贊同道。
“是的,狗的嘴臉!”K大爺說(shuō),心痛無(wú)比地想著狗監(jiān)洋洋得意的態(tài)度,“很多年了,他一直這樣。過(guò)去我認(rèn)為,他總算是欣賞我的,可是現(xiàn)在,我要同他絕交。”
K大爺拿出電話,打給狗監(jiān)。已經(jīng)是半夜兩三點(diǎn)了,狗監(jiān)被從床上震醒,莫名其妙地聽著電話。K大爺十分欣慰狗監(jiān)沒有關(guān)機(jī),他用最暴力的語(yǔ)言對(duì)狗監(jiān)說(shuō)了絕交的話,聲稱十年的友誼就此結(jié)束,讓他帶著他那本破雜志沉入深淵中吧!
打完這個(gè)電話,K大爺心花怒放。三個(gè)人面對(duì)著靜靜的湖水,K大爺說(shuō),他還要再打一個(gè)電話。他再次掏出手機(jī),在通訊錄里翻找,找到了一個(gè)叫做“小怪物”的女孩。
“出來(lái)吧,我們?cè)赑大校園,過(guò)來(lái)和我們喝酒。現(xiàn)在就來(lái),打車過(guò)來(lái)。我在這里等你。”
“你……有病吧?”小怪物說(shuō)。
“現(xiàn)在就來(lái),打車來(lái),我在這里……”
他沒有講完電話,便被掛了。三個(gè)男人又繼續(xù)向校園深處亂走,無(wú)所事事,逍遙快活,一點(diǎn)也不想回家。就這樣他們迎來(lái)了黎明,迎來(lái)了第一個(gè)出門晨練的人,是一個(gè)老大爺。老大爺在清爽的晨風(fēng)中呼吸了一口新鮮空氣,正準(zhǔn)備散步,迎面碰見了酒意熏熏的K大爺,問他道:“大爺,你會(huì)打太極拳嗎?”
“什么!”老大爺有些惱怒。
K大爺站在他面前,把自己擺成太極拳。
老大爺悻悻然地看了一會(huì)兒他的獨(dú)角戲,走掉了。
后來(lái)我們想過(guò)勤奮而有超邁才華的K大爺為何不得意的問題,這大概是因?yàn)樗^(guò)狷介。很多平庸的小說(shuō)家都默默地獲得了以他們的平庸才能所能獲得的最大的聲名,甚至遠(yuǎn)超過(guò)他們所應(yīng)獲得的,K大爺卻許多年不再發(fā)一篇小說(shuō)。就這樣我們?cè)谀炒挝膶W(xué)活動(dòng)中又見到了K大爺。他仍然清秀整潔,挎著時(shí)髦的帆布包。Q老爺提醒我說(shuō):“看他的鞋!”我趕緊從他的鞋上逃開目光,回應(yīng)道,“早就看到了。”K大爺穿著一雙雪白底色、大紅圖案的鞋,顏色和式樣一樣夸張,正如K大爺咄咄逼人的風(fēng)格。活動(dòng)結(jié)束后,我們和許多人一起走在鼓樓大街上,兩旁盡是小店,馬路邊突然出現(xiàn)一只白鵝,不知從哪家飯館逃席出來(lái)。鵝是很有詩(shī)意的動(dòng)物,古人認(rèn)為“鵝性最傲”,這從它們伸長(zhǎng)的脖子、彷徨不顧的神情可以看出,同時(shí)它們還是卓越的舞蹈家。Q老爺和K大爺前去惹它,鵝一邊生氣,一邊自顧自地走著,而Q老爺和K大爺擋著它的去路,還和它一起跳舞。后來(lái)這兩個(gè)人被鵝追趕,一群詩(shī)人們都笑了。
因?yàn)榕抡`了地鐵,或者耽誤明早的上班,許多人都回去了,只剩下K大爺、Q老爺和我,他們二人意猶未盡,想繼續(xù)找個(gè)地方坐坐。K大爺輕車熟路,很快來(lái)到了一家露天燒烤攤,店主和小二都和他認(rèn)識(shí),看來(lái)他經(jīng)常在這條大街上彷徨無(wú)措。大家坐下來(lái),喊了烤串和啤酒,興高采烈,手舞足蹈,離去的人的車子正好經(jīng)過(guò)我們,看到三個(gè)人在街頭歡樂的情景。
“雅莊的詩(shī)怎么樣?”
Q老爺問K大爺。K大爺說(shuō):“雅莊!雅莊是狗屎!什么雅莊?”一邊說(shuō)著,一邊把雅莊剛剛送給他的詩(shī)集放在小板凳上,坐在上面。
“你不能這樣說(shuō)。”
“我這么說(shuō),是因?yàn)檠徘f的確是狗屎。他不是嗎?他不是狗屎,那他又是什么呢?”
“你是個(gè)SB。”Q老爺說(shuō)。
“我可能是的。”K大爺說(shuō),“但雅莊一定是狗屎!”
“你這個(gè)SB!你媽的。”Q老爺用最原始的方式對(duì)準(zhǔn)K大爺破口大罵,排山倒海,K大爺有些愕然,我從來(lái)沒見過(guò)K大爺這樣,我所見過(guò)的只有怪物一樣的K大爺,從未見過(guò)他這樣輕聲地說(shuō)著話,竭力謀求著轉(zhuǎn)圜,想讓Q老爺平靜一點(diǎn),并在風(fēng)中縮起肩膀,好像受了傷。
“我們走。”Q老爺帶著我去攔出租車。
“不要走。”K大爺說(shuō)。“我還叫了別的人,一會(huì)兒他們就來(lái)了。”
出租車已經(jīng)叫到了。
“不要走。”K大爺說(shuō)。
我們坐進(jìn)出租車呼嘯而去,留下K大爺一個(gè)人坐在街邊的小板凳上。我問Q老爺說(shuō),我們是不是太過(guò)分了。我們離開前的十分鐘內(nèi),一直是Q老爺在咆哮,而K大爺只是聽著。
“我受不了他那樣說(shuō)雅莊,還拿雅莊的詩(shī)集墊屁股。”
“他不是故意的吧?”我說(shuō)。
“他一定是故意的。”
我默然了,因?yàn)槲蚁肫餕大爺曾經(jīng)說(shuō)過(guò),在他的家鄉(xiāng),那個(gè)江南古城,生活著的都是一些非常刻毒的人士,他們就算要離開你的屋子,也會(huì)逡巡不走,一直到成功放一個(gè)屁留在那里,才會(huì)立刻走掉。
但是后來(lái)我們一步一步見證了K大爺?shù)尼绕稹K目襻淖源螅麑?duì)他人的蔑視,他不顧一切的大喊大叫,都不適合文學(xué)界而適合戲劇界。就這樣,K大爺成為一名先鋒戲劇的導(dǎo)演。
K大爺?shù)牡谝粓?chǎng)戲劇完全賣不出去,上座基本靠贈(zèng)票,所以我們也趕到了現(xiàn)場(chǎng)。我們進(jìn)入戲院,坐下觀賞。整場(chǎng)戲沒有啟用一個(gè)專業(yè)演員,大概是因?yàn)镵大爺請(qǐng)不起。詩(shī)人無(wú)錯(cuò)扮演主角,這大概是浪蕩子無(wú)錯(cuò)這一生唯一一次舞臺(tái)經(jīng)驗(yàn),但是,他演得很好。沒有人比無(wú)錯(cuò)更能詮釋這個(gè)角色:一個(gè)幽居的、神經(jīng)質(zhì)的、絲毫不帶人間煙火氣的變態(tài)物種,因過(guò)分沉溺哲學(xué)而對(duì)這個(gè)世界深深地懷疑。另外兩個(gè)人物拿著水槍、棍子和各種道具,配合著主人公的臺(tái)詞,在扮演配角、推動(dòng)情節(jié)發(fā)展的同時(shí),給這個(gè)戲劇制造了日常性的荒誕。但無(wú)錯(cuò)的臺(tái)詞是這個(gè)戲的主體,無(wú)錯(cuò)的大段獨(dú)白,錯(cuò)亂、顛倒而強(qiáng)烈,那是無(wú)視外物、洞燭內(nèi)心的錯(cuò)亂,和具有強(qiáng)烈戲劇性、幽曲入微的顛倒。
密集的臺(tái)詞每一句都擊中人心,在劇場(chǎng),在滿是人的劇場(chǎng),在演員無(wú)錯(cuò)和我之間,存在一種一對(duì)一的傳達(dá)。這是個(gè)喧囂的年代,然而K大爺?shù)膭?chǎng)充滿安靜的力量。
安靜如何成為一種力量?設(shè)想一下,在海嘯當(dāng)中,使在整個(gè)星球中扭動(dòng)的漩渦瞬間凝靜下來(lái),使大海變得像星空一樣安靜,然而巨浪被凝結(jié)在原地,哪怕只有一秒鐘,這就是了。
所以后來(lái)我們參加了有各路群魔參與的戲后集會(huì),他們都是一些顛三倒四的中年人,包括無(wú)錯(cuò)在內(nèi),某種程度上他像極了他所詮釋的那個(gè)人物;還有一位年輕的詩(shī)人,還不能像中年人一樣,完全地、放開地、不顧一切地沉浸在他的詩(shī)酒生涯中,沒有準(zhǔn)備好街死街埋、路死路埋,這樣反而活不成,幾年之后,我聽說(shuō)了他上吊自殺的消息;還有幾個(gè)女人,她們不是、大概也不會(huì)成為任何人的妻子。從那天晚上起,我們就很少見到K大爺了。
然而甜熟的B少爺永遠(yuǎn)是為我們大肆歡迎的座上客。
B少爺?shù)诹位貒?guó)的最后一夜是在我家里度過(guò)的。非常湊巧,我的女友紅藥也來(lái)看我。紅藥穿著寶藍(lán)色吊帶連衣裙,胸口乍泄若許春光,顧盼生姿,談笑風(fēng)生,觸處生春,但她不像重慶姑娘那樣天真懵懂,敢在人群中如此耀眼的女生,一定是位有經(jīng)驗(yàn)的人士。
我時(shí)常覺得紅藥有些乏味,雖然她具有驚人的美貌,然而在美國(guó)教授B少爺眼中,就是另外一回事了。那一晚我們從外面吃飯回來(lái),在客廳中聊天,紅藥這一生中,見到的最有學(xué)問的人,我想也就是B少爺了,但紅藥看上去并不尊敬B少爺,她目光如炬,老于世故,很快知道可以放肆地調(diào)侃他,而不會(huì)遭到任何抵抗。這是一場(chǎng)傳說(shuō)中的交際花和花花公子的初會(huì),在我家客廳,我倆搬兩個(gè)板凳便可以坐下來(lái)看一場(chǎng)《日出》。
“原來(lái)就是你!”紅藥嗟嘆道,“P大西門的那件事我早就聽說(shuō)了,想不到今天才和你見面!我過(guò)去想,不知道有文化的流氓長(zhǎng)得什么樣?今天見到你,你哪里像個(gè)美國(guó)教授,哪里像快五十的老頭?你是不是一直冒著B少爺?shù)拿中序_,其實(shí)是個(gè)二十五歲的小白臉?”
“你以為有文化的流氓該如何?”我說(shuō),“有文化的流氓,看上去都不像流氓,像好人;像B少爺,決計(jì)不是流氓!”
“哈哈哈哈!”紅藥縱聲大笑。
“要說(shuō)流氓,那天那個(gè)重慶姑娘的男伴才是,他明明結(jié)了婚,還把人家從重慶喊來(lái),又不肯負(fù)責(zé)。那天他對(duì)我們說(shuō)是Q大的研究生,但后來(lái)聽說(shuō),他就是P大某老師的博士。”
“是嗎?你怎么沒有告訴過(guò)我?”Q老爺驚道,“那么他怎會(huì)不認(rèn)識(shí)龍章?”
“是的,他認(rèn)識(shí),只是裝不認(rèn)識(shí)。”我說(shuō)。
“那個(gè)人,”B少爺想起了一事,“后來(lái)給我寫過(guò)信。”
“就說(shuō)你!不應(yīng)當(dāng)亂發(fā)你的名片!人家不過(guò)是一個(gè)破博士,還知道撒謊保護(hù)自己。他竟然給你寫信!他說(shuō)什么了?”我問。
“我忘記了。”B少爺說(shuō)。
“是不是說(shuō),你要是不幫我發(fā)表這篇論文,我就把那晚的事情說(shuō)出去?”Q老爺大笑道。
我們都知道B少爺要趕明天一早的飛機(jī),5點(diǎn)鐘就要走,但不知從何時(shí)起,B少爺決定不睡了。這讓我覺得頗有些對(duì)不住B少爺,不該讓他窺見我家橋頭種著的紅藥,一早上坐飛機(jī),他一定很疲倦,但B少爺不覺得。他坐在客廳中間,興致勃勃地聽著紅藥說(shuō)每一句話。
好吧,把紅藥拋在一邊,讓我們談?wù)勆毓獍伞I毓庠谝粋€(gè)寒涼的初秋來(lái)到了我家,腳上穿著一雙拖鞋,沒有穿襪子。我出門買菜,順便買了兩雙鞋子,一雙綠色的,一雙紅色的。韶光喜歡那雙樸素的紅色的,穿上了,我拿了她的拖鞋到洗手間洗洗干凈,晾在陽(yáng)臺(tái)上。后來(lái)韶光還睡了一覺,睡醒后,她說(shuō)要走,去看K大爺?shù)脑拕 N艺f(shuō),我去送你。Q老爺說(shuō),正好,順便看看K大爺?shù)脑拕 N艺f(shuō),我不要看,我只是去送韶光。
韶光穿著樸素的鞋子,樸素的外套,我也把新買的那雙綠色的鞋子穿在腳上。我們一起去坐地鐵,我?guī)吡艘粭l非常繁瑣的路,可能是最遠(yuǎn)的路,是因?yàn)槲矣幸稽c(diǎn)走神,忘記了哪條路最近。5號(hào)線人很擁擠,韶光緊緊地挨著我站著,一言不發(fā)。我們其實(shí)不熟。我只是情不自禁要愛她,又知道徒勞。我們一起下了地鐵,韶光接了一個(gè)電話,然后把電話遞給我。
“你的電話。”
我聽見Q老爺在那頭大聲地說(shuō):“你怎么又沒帶手機(jī)?你既然去了,就去看看K大爺?shù)脑拕 !?/p>
“我不要去!”
“既然都去了,就去看看吧!”
“我不想去!”
我們一同走出了地鐵,韶光的手機(jī)又響了,Q老爺堅(jiān)持讓我看K大爺?shù)脑拕 ?/p>
我和韶光迎面碰上了那個(gè)一同來(lái)看話劇的男人,原來(lái)是見過(guò)的,曾有一度他是韶光的男友,后來(lái)聽說(shuō)好像不是了。我們一起去吃了麥當(dāng)勞,然后另找個(gè)地方坐下來(lái)喝奶茶,等待話劇開演。男人問:“你也要看話劇嗎?”
“是的。”
“以前看過(guò)K大爺?shù)脑拕∶矗俊?/p>
“看過(guò)。”
“認(rèn)識(shí)K大爺么?”
“認(rèn)識(shí)。”
“那他認(rèn)識(shí)你么?”
“認(rèn)識(shí)。”
大家無(wú)話了。我想他忘記了曾經(jīng)見過(guò)我。上一次見面是在詩(shī)歌節(jié)的宴會(huì)上,我淡妝靚服,如今卻穿著家常買菜的衣服。喝完了奶茶,我們慢慢走到劇場(chǎng)去,途中經(jīng)過(guò)一家潮店,男人進(jìn)去選購(gòu)衣物,我和韶光坐在門口的馬路牙子上等他。
“啊,格子襯衫!”韶光說(shuō),“格子襯衫好樸素,就像上個(gè)世紀(jì)。”
“是啊是啊,好樸素。”我說(shuō)。
“我回去要買一件來(lái)穿。”
“買一件。”我說(shuō)。
“看,又一個(gè)潮女過(guò)來(lái)了。這條街上潮人好多。”
“潮人!”我說(shuō)。
“他們都不夠潮。”韶光說(shuō),“以后我只穿格子襯衫。他們土極了,不知道往土里打扮自己。”
“土極了!”我說(shuō)。我想起許多年前,韶光是校園中的一段傳奇,她買各種大花圖案的棉布做床簾,等掛膩了的時(shí)候,就把它們摘下來(lái)縫成裙子穿上。
潮人出來(lái)了,高興地把他買到的東西給我們看,那是一條耐克的小圍巾,他說(shuō),只花了一百八十多塊錢。于是我們一起走入了劇場(chǎng),戲劇還沒有開始,我們占據(jù)了樓梯間,坐在樓梯上,韶光打開她的電腦,給我們看她新寫的詩(shī):
我們乘坐過(guò)山車飛向未來(lái),
他和我的手里各捏著一張票,
那是飛向未來(lái)的小舢板,
起伏的波浪是我無(wú)畏的想象力。
乘坐我的想象力,他們盡情蹂躪
這些無(wú)辜的女孩和男孩,
……
話劇要開始了,我們走入了劇場(chǎng)。這個(gè)戲講了一個(gè)淫蕩的女人的故事,極為沉悶。這不是因?yàn)镵大爺功成名就,水平倒退,這是K大爺?shù)谋旧唬氖澜缬^締造了這一場(chǎng)無(wú)聊的演出,蕩婦還是他早期的小說(shuō)中出現(xiàn)的那一個(gè),他傾盡他男人的想象灌注了一個(gè)蕩婦,于是,他對(duì)世界的態(tài)度便凝縮成這么一個(gè)蕩婦:他看不起她,不要她,但對(duì)她的鄙視永遠(yuǎn)是他戲劇和小說(shuō)的主題。
又過(guò)了若干個(gè)月,已經(jīng)到了深冬,銘心刻骨的冬天,以寒冷加深著我們對(duì)它的感受,試圖永遠(yuǎn)地留在我們的記憶中。我在凌晨突然醒來(lái),是因?yàn)槁牭搅诉甸T聲。
“篤,篤。”
當(dāng)我被驚醒時(shí),這兩下清晰的叩門聲仿佛還在耳畔,余音裊裊。是誰(shuí)呢?是否有人敲門?我凝神細(xì)聽,卻再也聽不到叩門聲了,電梯不知道為什么啟動(dòng)著,傳來(lái)清晰可辨的噪音,大概是晨起的人出去買早點(diǎn)。
我繃緊了躺在床上,毛骨悚然。過(guò)了很久,才強(qiáng)迫自己睡著了。我以為第二天會(huì)有什么奇異的事情發(fā)生,但是沒有。然而,到了第三天的時(shí)候,傳來(lái)韶光去世的消息。
我戰(zhàn)栗著質(zhì)問被這個(gè)消息擊中、傻傻地站在那里的Q老爺:“你為什么不讀韶光的詩(shī)?”
“什么?”
“你以為韶光的詩(shī)不合乎你的詩(shī)歌觀,所以你從來(lái)不提。你從來(lái)沒有真正關(guān)心過(guò)韶光,比如說(shuō),那天我不想看K大爺話劇,如果不看話劇,我就是在送韶光,可是你讓我看了一場(chǎng)話劇,一場(chǎng)惡劣透頂、無(wú)聊至極的話劇,所以我那天送韶光,就不純粹了,我無(wú)法讓韶光感受到我是在全心全意地送她……”
“我怎么能想到會(huì)這樣啊!”Q老爺聲淚俱下,哀慟萬(wàn)分,顧不上搭理我的無(wú)理取鬧,他幾乎沒帶任何行李,跳著來(lái)到了大街上,打了一輛出租車,奔赴機(jī)場(chǎng)去了,想要見韶光最后一面。他在車上眼淚滂沱,幾乎看不清這個(gè)世界。他丟三落四,慌慌張張,痛心疾首,悔恨交集。而當(dāng)他來(lái)到韶光香消玉殞的城市時(shí),韶光已經(jīng)下葬了。
痛苦不會(huì)摧毀痛苦的可能性,生命
不會(huì)消失自我的幻覺術(shù)。在一生的
時(shí)間里,穿越過(guò)巖石縫隙里的貝類
是潛藏的隱微的音樂,那是宏大的
樂隊(duì)在奏響……
而這天夜里我又做了一個(gè)夢(mèng)。我夢(mèng)見了韶光。她來(lái)找我,我們一起走在P大的校園中,輕描淡寫地談?wù)撝切┥镭P(guān)的話題,一邊談?wù)摚贿呥€會(huì)離題談到校園里的帥哥。在夢(mèng)中,我接受了韶光的解釋,有一些釋然了。
醒來(lái)時(shí)我想這個(gè)夢(mèng)非同尋常,這是韶光托夢(mèng)給我,她是懂我的心意的。盡管我們沒有真正交談過(guò),但她記得回來(lái)看我,把我當(dāng)朋友。在MSN上把這件事情告訴Q老爺?shù)耐瑫r(shí),我也告訴了B少爺,在他們頂天立地、呼風(fēng)喚雨的人生中,還從來(lái)不曾經(jīng)歷過(guò)這樣一個(gè)美人的去世,這樣一個(gè)既不屬于他們、又不愛他們,而他們深深迷戀、震動(dòng)他們靈魂的美人。
責(zé)任編輯⊙育邦
作者簡(jiǎn)介:
劉麗朵,女,1979年生,小說(shuō)家,詩(shī)人。北京大學(xué)中文系在讀博士。出版有小說(shuō)集《鎮(zhèn)與大城》(2005年),禪學(xué)讀本《生死請(qǐng)柬》(2006年),長(zhǎng)篇小說(shuō)《誰(shuí)能與共》(2009年)。小說(shuō)作品收錄于《小說(shuō)北大》等選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