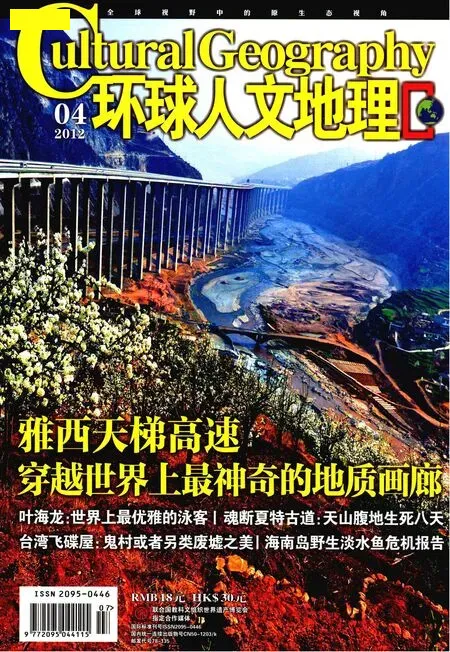西安人慢節奏和一根筋
秦巴子



正所謂一方水土養一方人,隨著年久日深的點滴浸潤,生活在同一座城市里的人身上,往往會帶有這座城市獨特的味道和印跡,讓人在人群中一眼就能分辨出那人是北京人,還是上海人,或者西安人……而西安人就在關中水土、文化的千年滋養下,越發特立獨行、與眾不同。
西安味道,就是把文化揉到生活里的一碗面
記得有一次在從機場開往城里的大巴上,筆者突然聽到后座傳來兩個江浙口音的交談,頗有意思。其中一個說,“很奇怪,每次到西安,都有一種莫名的敬畏與怯怯。”“畢竟是幾千年的帝都嘛,雖然衰落了,但氣象還在,有氣場的。”“是的呀,你說它土,它骨子里還是有洋氣的,說它小,但氣象卻很大,上海是很洋氣的,卻總是讓我感覺有些逼仄;北京是很大的,有時候卻覺得有點大而無當;西安讓人說不清楚,卻有敬畏。”“是個有味道的城市。”
那西安究竟是個什么味道?幾乎可以不假思索,很多人都會立即回答:文化味道!對,西安的味道就是文化味道。
沒錯,這個城市,的確是太有文化了。從地面到地下,從城里到城外,隨便撥拉撥拉,就有幾百幾千年的來歷,既給人無限的想象,也讓人不敢造次。而生活在這座城市里的人們,自然也被醺出了濃濃的文化味道。來自北京的年輕作家春樹,說她從西安人的表情和言語方式里,能夠感覺到一種大的從容與自在,她很敏銳地認為,那是從這個城市的文化底蘊中帶出來的。
然而,簡單地只說它是個很有文化的城市,其實還不足以說明它鮮活的部分。它確實太有文化了,但這是一種和生活揉在一起的文化。就像是揉了很久也醒了很久,既筋道有力又綿軟可口的一碗獨特的西安的面條一樣,所謂的“西安味道”,就是這樣一碗把文化揉到了生活里的面,而這,也正是我所認識的西安味道的神髓之所在。
無論是城墻根的自樂班,回民巷的好吃貨,還是書院門的字和文,八仙庵的淘之樂……你會發現,西安味道,不僅在建筑與文化符號里,在歷史與人文傳承里,更在西安人的日常生活中。
如果一句話能界定,那又不是西安人了
在西安,你見到的男人,大多很像兵馬俑;你見到的女人,大多很像鄰家小妹和大嫂。但你見到的這些人,其實大多又不是真正的西安人。
西安有多少種人?很難說。
藍田猿人、半坡氏族后裔、兵馬俑,這些都是西安祖先;但是幾千年以來,西安更有胡人、女真人、蒙古人、金人、西夏人,而這些都是異族。在唐代,長安的地位大概相當于今天美國的紐約吧,因此不少來到西安的外國人也會在西安住下來。進入現代,更有河南人、東北人、上海人、四川人、浙江人……大量進入西安,他們在這個特殊的城市里匯聚融合生息繁衍,所以“西安人”的含意也就隨之大了起來。
但無論怎么大,有一點卻是共通的,那就是西安人的開闊、從容、自在、平實,不卑不亢、不驚不乍、不張揚、不矜持、不慕權貴、不輕貧賤,在世事變幻中自有一種特別淡定的安閑。如果說,所謂厚土,就是能養人的土地;所謂文化,就是能養心的氣息。那么,毫無疑問,西安人就是被厚土與文化養出來的:關中自古富庶,土地肥厚,農耕文化發達,西安人做得出全世界最豐富的面食,面食的精髓即在于揉和——以揉的方式使其致密而和,西安人的筋道、力道與味道,大致可以在豐富多樣的面食中體現出來,綿中帶力、硬中含柔,樸拙中有倔強,平實處有波瀾。
“一碗面條一瓣蒜,一碟辣子似神仙”——你以為他單調,他其實腹有詩書,氣自華。從古城墻下面,或者環城公園里,數不清的秦腔自樂班里吹拉彈唱的老人中,隨便拉出一個來問,都能上下古今給你說出三朝五世的人文。此外,西安人也是極喜歡閑的,但他們不似成都人那樣喜歡閑在麻將聲聲里,相反,西安人的閑中自有一種古風與情懷。譬如秦腔,在外人聽來如吼,但其中的剛烈與蒼涼,婉轉與深情,非經西安的浸潤而不知其味。
大概是十年前吧,那時候我上班的地方在雁塔路南頭,就是現在的北廣場旁邊,上班中間,我會花20分鐘繞著大雁塔走一圈。有一次我正和詩人伊沙繞塔而行,接到了外地朋友的電話,當我告訴他,我們正在做工間操——繞著大雁塔散步時,對方吃驚的聲音中更多的卻是艷羨。然而,讓外地人聽了會羨慕得驚聲尖叫的,卻不過是我們稀松平常的日常生活而已。
三千年古城,十三朝古都,它的氣場與氣韻,已經浸潤到人的氣息之中。在西安,你能看到的是滿城的地上地下的文物與文化,你先有了敬畏,但西安人日常就是生活在里面的,你所敬畏的他已經視若平常,他無須張狂不必張揚,就已經是一個大氣場了。
不過,西安雖古,卻并不泥古自閉。眾多的大學與科研機構散布在城市的東南西北,在文化的厚重與現代科技的交織下,使西安人的開闊與開放中自有一種放達。縱通古今文化,橫亙現代文明,西安人自在其中,于是以不爭、以泰然,觀世象、處世事,似無為而有為。
總之,西安人是什么人?男人譬如藝謀,女人神似閻妮。但如果一句話或者一個概念就能夠界定,那又不是西安人了。
倔強與豁達,西安人的生命觀
西安是一個慢節奏的城市,慢的集中表現當然是人慢。在大街上,很少看到京、滬、廣、深那樣快步走路的人,若有人催促,西安人會回你一句:急啥嘛,急著干啥去呀。但這種慢,在很大程度上是一種從容,內心從容,所以腳步從容;慢也是一種閑適,心閑所以路寬,不必擠來擠去的爭個先后和高下;慢同時也是一種曠達,是人生世事寵辱高低經見的多了,而后了然于內心的一種禪境。
當然慢也含著散漫,所以西安人往往也不太守時。約定的時候到了人還不到,你電話去催,他說快了快了,我已經看到你家的樓了,其實,他也許才剛剛出門,離你家還六七八站地兒。急啥嘛,世間萬事,到了西安人這里,除了房子著火女人生娃,都不必著急。
西安人不急,但卻是犟的。西安人倔強,執著,頑強,一根筋兒,“認準的道兒就要一直走到黑”,而且還“不到黃河心不死”,“不撞南墻不回頭”。除此之外,西安人做事認真,而且不屑于多說,瞧不上京油子、衛嘴子和南方人的小算計小精明;西安人也憨厚,愛使蠻勁,他相信蠻到底就會有結果,他們相信即使是一個錯誤,堅持到十年二十年就會成正確的了。
不管怎么說,西安人自信自己是能干成大事的人。而他們對“大事”的理解,又與所謂的“成就”有所區別:西安人說的“大事”,那意思更多的時候是把人活大了——“活大了”指的是人的氣象,不是你有多少錢你有多大名。大錢大名在西安人看來,也不過就是碗里多些肉而已,多也好少也好,區別不大。所以,西安人的歌里就是這么唱的:“他大舅他二舅都是他舅,高桌子低板凳都是木頭,金疙瘩銀疙瘩還嫌不夠,天在上地在下你娃嫑牛,太陽圓月亮彎都在天上。”也許,正是這樣的生命觀,才讓西安人的執著倔強里還額外多了份豁達。
西安人的豁達,其實是一種得自開闊的文化傳承的集體無意識式的看穿與通透,他不善于跟你講道理,他講的道理有時候是混沌的;他不與人爭搶,是他早已經看到了幾座山之外的天地,他知道多少山之外還有平川,所以你爭搶的時候,他寬厚地一笑,有點無奈,有點狡黠,有點意味深長,還有點憨厚。
詩人伊沙有一首寫西安人的詩,道盡了其中味道。其中有幾句是這樣的“你是不是看上那個小白臉了啪一耳光/你要是看上他了你就跟我說啪一耳光/你要是看上他了你就跟他走啪一耳光/哭啥呢哭啥呢我好好跟你說話呢啪一耳光/他要是敢欺負你你就來跟我說啪一耳光/是不是占了咱便宜現在又不要咱了啪一耳光……”所以,如果遇到一個西安人這樣教訓你,那他其實是愛你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