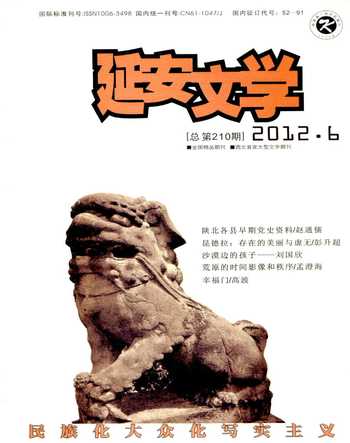識物十二章(選六)
范劍鳴
萬物各從其類,
在心靈的枝條長成碩果。
——題記
歌 聲
一只鶇鳥驟然起唱
它的歌聲
讓荒坡上糾結的荊莽,散漫的茅草
頓時獲得生命的尊嚴
萬物改變了秩序
瞬間承認了新的中心
我孤獨的身影
也突然有了代表人類的理由
一只鶇鳥戛然而止
它的歌喉,如此熱烈,蓬勃
造就一條通往神祇的新途
這歌聲,縱是春風十里吐露華章
縱是澗水千回,高處日出,低處月落
也不可媲美
當我默默走開
重新走向荒坡邊的火車站
卻無法把它帶給如舊的人潮
無法說出:生命的原理另有所在
琴 瑟
向低音致敬。向低音之外
更廣大的沉默致敬
三弦。六弦。五十弦。聲音的界線
纖指們涉過的河流。要多少崇山峻嶺
才能成就她們的浪花奔騰
低八度。再低八度
就是盲歌手周云蓬的
墨鏡和謠曲。就是一匹黑駿馬
在燈紅酒綠慣壞的耳朵里,踉蹌嘶鳴
高八度。再高八度。就是殘雷和崩霆
是譚嗣同晚清的肝膽和血
就是一棵大樹,接受閃電的裁決
——呵,在不為承認的時代
寧為焦桐,不作棟梁
曲終人散數峰青。我曾是一個弦上之音
但喑啞是音樂的歸宿,而孤獨
是琴身的命運。仰望星空
多少星辰一聲未發……
風 箏
好風是神的呼吸。青云
是夢里花開
攀爬一生,只為安慰天地間
那根松松緊緊的線
安慰那小折疊凳上的久坐
和白發下的望眼——
忽然就過了奔跑的年段
想著棲落,允許斂翅
接受室內墻壁上的一枚釘子
打斷地平線的牽掛,和藍天的惦念
一顆蒼老的心,從此順從風雨
歲月已證實:肉身無法飛翔
只有把內心的塊壘掏空
把往事的線軸繞大
在廣場,在河濱,在草地
起起落落,都合乎意愿
夜 幕
大街上,酒徒收拾好往事和歌喉
喑啞的影子被月光接住
更遠處,星辰在群峰之上
對寂寥的燈火發出最后的邀請
夜已闌。風吹前塵,吹霜
吹鐵軌上的笛孔,吹歸去來的足音
思想者仍在櫥窗寄寓
改換隊形,呼吁“養吾浩然之氣”
子時已過,喜炮傳來喬遷者的宣言
報警器如犬吠于深巷
靈臺上,愛的神像悄悄撤回
又悄悄擺上……哦,臥聽所得
我可以說出更多,我不敢說出更多
長久以來,一些事物總是在暗中滋養
而我無以回報。現在,就讓我報以黎明
報以歲月之初蛋糕一樣的光華
報以生之欣幸
花 徑
落英打下來。螞蟻的觸角上
微風遇到不可言說的美
花枝的呼吸,讓小草
擁有向上的力量
多么歡迎單純的腳步
無愛,無欲,無思
受縛于造化,又超脫了自然
仿佛蚯蚓的履痕,那樣酥輕,低溫
從虛線到實線,模仿星宿的軌跡——
這正是我的希望:被人工改變的地表
沒有哪一個物種是主角
或者,誰都成為了主角
包括隱伏地表之下
那根莖和土層里潛行的時節
包括,我內心躍動的
一個人類童年的影子
墓 地
遺傳和消逝,仿佛大地與天空
如此對立,又如此統一
這是兩只惟一掌握時光奧秘的
神靈之手——我多次聽到
如此平靜的描述:接納死亡的土地
永遠比生存的現場更博大
正如有轉化為無
實轉化為虛
一切智慧和經驗,在這里
轉化為情感和青草
有一刻,我從親情和家族中
超拔自己,立即發現陰陽兩界
是如此失衡:我們面向空無
訴說豐富的內心,自始至終忘卻
墓地是寬容的盲人和啞巴
多年以來,我們的到來和離開
并沒有增加冥界的一點分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