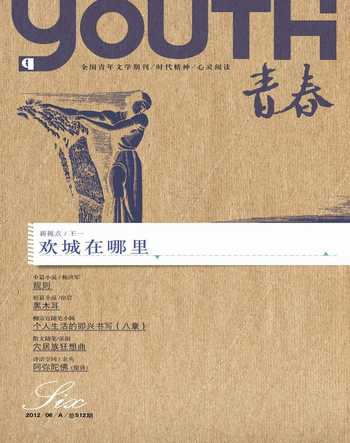穴居族狂想曲
張閎
深挖洞
一天,老師對我們說:今天不用上課了,大家回家取工具,挖防空洞。老師還教導說,這是為了響應偉大領袖毛主席的“深挖洞,廣積糧,不稱霸”的號召,云云,而我們早已無心聽取老師的教導。單是不上課這一件,就足以讓我們喜出望外,更何況是讓我們去挖地洞。我們的腦海里浮現出來的是電影《地道戰》中的那些激動人心的畫面。挖洞,我們算不上行家里手,但這卻是我們夢寐以求的事。平時無緣無故去刨洞,難免要遭罵,現在終于可以正大光明地干了。所以,只等動員令一結束,便各各飛奔回家。
挖洞,僅僅是戰備動員的一部分。然而,戰爭恰恰是我們所企盼的。簡單的挖洞勞動能夠成為戰爭前的預演,這對于我們這些十歲左右的男孩來說,實在是一件令人興奮的事情。我們根本沒有打算真的躲到洞里去。事實上,戰爭對我們又有何威脅呢?我們并沒有任何危險意識。我們對于核武器的了解,僅僅是那一朵著名的蘑菇云而已。核武器跟我們有什么關系呢?我們那里窮山惡水,十幾個縣加起來的資產,恐怕還抵不上一顆原子彈的價格。在當時,我們非但沒有見過飛機大炮坦克軍艦,連卡車和拖拉機都很少見到,即便是偶爾路過的自行車,我們也要在后面追逐許久。但這一切都沒有妨礙我們對于戰爭的熱情。遺憾的是,除了在一些打仗的圖畫書和電影中,或本公社一小股民兵不定期的軍事訓練之外,可以說沒有任何事情關涉軍事。這一點,讓我們頗感沮喪。跟在民兵屁股后面到靶場撿子彈殼,并且挨民兵小頭目喝叱的屈辱日子,我們已經受夠了。在這種情況下,我們只希望戰爭來得更快一些,更猛烈一些,讓所有的大炮都向我開火。
可是,號召是偉大的,行動是渺小的。挖防空洞的地點,無非是學校附近的小山坡或田埂。我們當時人小,挖不動,一個小組幾天下來,也只是在田埂上挖出一個狗洞般大小的坑,僅夠一人蹲在里面。我們輪流蹲過一遍之后,就對其失去了興趣。最初的熱情過去了,老師也不再提響應號召的事了,學校恢復正常上課。想象中的地道戰,再一次地被課間的肉搏戰所替代。那些被遺棄的小土洞,漸漸被荒草所覆蓋,為那些膽小的穴居動物提供了良好的安全庇護。一些較大的坑洞,則被農民們加以擴大,作為他們的蓄糞池或貯存紅薯的地窖,這或許勉強可以解釋為對“廣積糧”號召的響應。
許多年之后,我在城里見到了真正的防空洞。那是一個龐大的地下迷宮,昏暗而幽深,仿佛沒有盡頭,走進去便有一股陰冷潮濕的氣息撲面而來。而且,這里不只是一個單純的洞穴,而是一個完整的地下世界。
迷戀地洞并非男童們特有的怪癖。現代心理學認為,穴居經驗是人類的原始經驗。在那些古老的洞穴里,人類度過了自己的童年,積累了最初的生存經驗。內與外、溫暖與寒冷、安全與危險、光明與黑暗乃至現實與夢幻,這些構成人類基本存在感的經驗,都可以追溯到穴居時代。在尚未完全開化的男童身上,往往更多地殘存著這種本能的記憶。
洞穴是溫潤和安全的,如同母體子宮,為早期人類提供了安全保護。在精神分析學家看來,這一點正是少年人迷戀洞穴的無意識動機。這種原始經驗,是人類自我意識的開端。另一方面,洞穴又是黑暗和封閉的,是焦慮、壓抑和昏昧的空間。克服洞穴,從穴居狀態走出來,是人類文明史上的一次重大的事變。柏拉圖借用“洞穴”意象來隱喻人類的存在狀況。他設想的洞穴通過一個長長的通道與外部世界相連,陽光照不進洞內。一群囚徒背對著出口,面向遠處的墻壁。他們的四肢被套上了枷鎖,并且他們的頭頸也被固定住,無法轉動,因此看不到他人,實際上也看不到自己身體的任何部分,而只能夠看到面前的墻壁。但他們身后有一把明火,影子被火光投射到囚徒面前的墻壁上,外部世界的嘈雜聲也在囚徒們的耳朵回響。人類就是這樣一群囚徒,唯一能夠感覺或經驗到的實在,無非是這些影子和回聲。當阿爾塔米拉洞窟里的人類先祖,在洞壁上畫下那些受傷的野牛和猛犸的時候,他們在無意中將洞外世界映射到洞內,在黑暗的洞壁上再現洞外的生存狀況。
“地下”和“洞穴”,是文藝作品經常表現的對象。在許多文藝作品中,地下世界經常作為人的自我意識中的非理性部分的一種隱喻。地下的世界是一個悖謬的空間,既是一個安全的處所,又是一個危機四伏的世界。地下空間可以看作是人的無意識經驗的貯存地。地下,它是土地的內部,是萬物之源。它是生命的根基,同時又是生命的歸宿。它可以看作人類被壓抑的欲望和焦慮的象征。
維克多·雨果的小說《悲慘世界》寫道巴黎的下水道,它是巴黎這個天堂般的城市的欲望下水道,是老鼠、爬蟲和罪犯出沒的地方,這個空間意味著陰暗、潮濕、骯臟等令人不適的生理經驗,同時也意味著邪淫、罪孽和死亡等倫理上的負面價值。但雨果也看到了地下世界所蘊藏的原始正義和革命激情,他將巴黎的下水道稱之為“城市的良心”。與此相對照的,則是地面上的社會的虛偽、殘暴和不公。從雨果開始,文藝家對于地下世界的興趣越來越濃厚。從大仲馬的《巴黎的莫希干人》到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地下室手記》,從歌劇《歌劇院的幽靈》到好萊塢電影《蝙蝠俠》、《V字仇殺隊》,地洞、地下室、下水道、地鐵等種種地下空間和通道,構成了展示人性深處倫理沖突和政治激情的舞臺。
“深挖洞”的全民動員,如今看來甚為荒唐,但卻泄露了人類意識中的某種特殊的心理狀態。然而,在二十世紀七十年代的中國,穴居狀態是一個國家性的征候群。在那個年代,整個國家感染了一種“穴居妄想癥”。一個幽閉的地下狀態,神秘、封閉、潛藏、不公開和缺乏安全感,正是那個時代的政治和社會生活的特征。
衰老的獨裁者對洞穴有一種特別的愛好。安全感的缺乏,促使他向洞穴尋找安全庇護,唯有蟄居于洞穴方能安心。而對于可能在某個隱秘的深處的蟄伏的潛在的敵人,都必須設法將其引誘出來并予以殲滅。弗蘭茨·卡夫卡曾經在他偉大的小說《地洞》中描寫過這種精神征候。一匹大型穴居嚙齒動物,一直在挖洞,把自己的居所建成了一個無比龐大復雜的地下迷宮。它是地下世界的獨裁者。這個地洞既是居所,又是通道,還是防務設施,一個完整的地下城市。它感到四面都是敵人,時時擔心敵人的攻擊,因此,它把內部防務安排的無懈可擊,但它還是沒有安全感。它的敵人來自其內心,來自其內心無時不有的敵意。它的敵人就是它自己。
同時,也唯有將所有的人都幽禁于地下,自己方能充當太陽,成為唯一的光源。南斯拉夫導演庫斯圖里卡的電影《地下》,講述這樣一個故事:二戰期間,南斯拉夫一批反法西斯戰士被迫轉入地下。他們蟄伏于一位同志家的地下室里。那位同志在地面上掩護他們。地面上的狀況由那位同志所提供。地面的同志一直在制造戰爭假象,讓他們長期處于戰爭狀態,并讓他們在地下生產軍火,自己從中牟利。地上已經是和平年代,人們認為當年的地下抵抗運動中的戰士已經犧牲。人們將他們視作反法西斯的烈士。地面上的同志在進行莊嚴的政治表演,地下的戰士在積累著仇恨和戰斗的激情。地上和地下,兩個分裂的世界。地下世界具有超穩定的空間形態,其時間也是凝固的。當那些抵抗戰士再一次來到地上世界時,時間已經是波黑內戰時期。而他們的思維仍處于二戰時期。波黑內戰中表現出來的強烈的敵意、仇恨和歇斯底里,正是這種“穴居征候群”的重要表征。
擺脫黑暗,來到理性的陽光下,面對一個清明的世界,可以說是人類理性的第一次啟蒙。而從“深挖洞”的文革時期走出來,這個民族的自我意識也正在重新覺醒,成為回歸理性時代的開端。
學雷鋒
1970年代讀小學的人的整個少年時代,都是伴隨著學習各種各樣的英雄模范人物而度過的。其中,“學雷鋒”是這些學習活動中最經常和最持久的。每個學期,甚至是隨時隨地,老師都會一再重申向雷鋒叔叔學習的要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