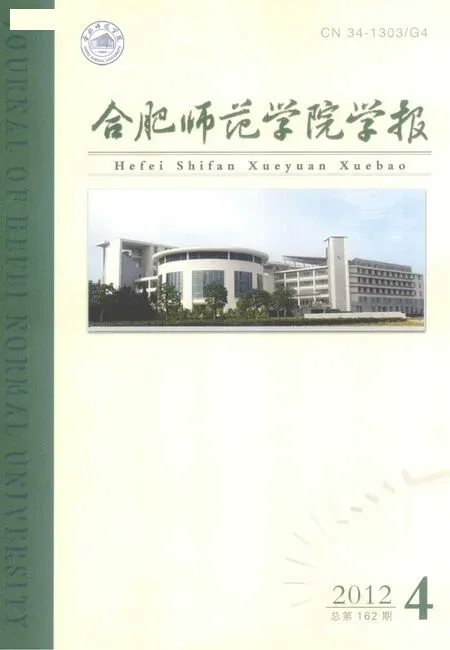曹氏家族與譙沛地域文化
方孝玲
(合肥師范學院中文系,安徽合肥 230601)
曹氏家族與譙沛地域文化
方孝玲
(合肥師范學院中文系,安徽合肥 230601)
一個家族所在的地域文化是家族賴以成長的環境,以曹操為首的曹氏家族無疑與家鄉譙沛之地的地域文化存在著千絲萬縷的聯系。譙沛之地有著自己獨特的地域文化,其悠久的軍事政治傳統、道家文化、酒文化與藥文化對曹氏家族在政治統治、思想學術、家族門風、文學創作等方面產生了深刻的影響。
曹氏家族;譙沛;地域文化
魏晉南北朝時期,世家大族在政治社會文化活動中發揮著重要的作用,如瑯邪王氏、蘭陵蕭氏、陳郡謝氏等顯赫家族,或掌握著政權,或引領著文化的前進方向。興起于譙沛之地以曹操為首的曹氏家族更是魏晉南北朝時期重要的政治文化世家,叱咤風云,不可一世,在漢末、三國時期的政治、軍事、經濟、文化等諸多層面影響巨大。目前學術界的研究局限于曹操父子政治、軍事活動和文學創作,而對于其家族與所在的譙沛地域文化之間的關系卻缺少系統、全面、細致的梳理。而一個家族所在的地域文化又是家族賴以成長的沃土,影響著一個家族的成長興衰。家族與地域文化兩點是中古社會與文化研究的重要方面。陳寅恪先生在《隋唐制度淵源略論稿》中指出:“蓋自漢代學校制度廢馳,博士傳授之風氣止息以后,學術中心移于家族,而家族復限于地域,故魏、晉、南北朝之學術、宗教皆與家族、地域兩點不可分離。”因此,無論從推進中古社會研究,還是中古文化與學術研究來看,曹氏家族與所在的譙沛地域文化之間的關系都有必要進行全面、細致的梳理。
一、曹氏家族與譙沛之地的軍事政治傳統
譙地,就是今天安徽亳州,位處安徽西北,是中國古代該地區的政治、經濟、文化中心,也是扼中州門戶、徐兗咽喉的一座軍事重鎮,其地理位置極其重要,素有“南北分疆,此亦爭衡之所”之說。亳州是商湯之國都,司馬遷《史記·殷本記》云:“成湯,自契至湯八遷,湯始居亳,從先王居。”春秋時為陳國之譙邑。戰國時屬宋。秦屬碭郡。西漢屬沛郡。東漢為沛國。古代有不少戰役都在譙地進行。秦末陳勝、吳廣于大澤鄉起義后,便先占據了譙縣。漢高祖劉邦初起時亦曾軍于此地,當時項梁剛死,楚懷王為了安撫人心,“以沛公為碭郡長,封為武安侯,將碭郡兵”。東漢時期,光武帝劉秀曾于建武四年“七月丁亥,幸譙。遣捕虜將軍馬武、偏將軍王霸圍劉紆于垂惠。”東漢時刺史部由十三個減為十二個,沛郡改為沛國,隸屬豫州,“譙刺史治”,更彰顯其戰略地位。清代顧祖禹曾曰:“昔者曹瞞得志,以譙地居沖要,且先世本邑也,往往治兵于譙,以圖南侵。”可見譙地軍事政治地位的重要性。
譙地軍事政治傳統孕育了該地區包括曹氏宗族及鄉黨的武人氣質。曹氏、夏侯氏為譙地兩大家族,是曹魏政權中“譙沛集團”的核心力量。曹操起家在軍事方面很大一部分都是依靠其家族及鄉黨的勢力,也就是“譙沛集團”。“譙沛集團”多為武將。曹魏政權中最重要的軍職四征將軍、中領軍和中護軍不是譙縣人就是沛國人,在曹操時期擔任過四征將軍的有夏侯淵、曹仁和張遼,擔任過中護軍的有韓浩,擔任過中領軍的有夏侯尚、曹休、曹真、史渙。高于四征將軍的有大將軍夏侯惇、都護將軍曹洪。統兵征戰時獨當一面者,幾乎均為譙沛人。這些領兵征討與宿衛的將領,大都是曹操的宗族、重臣,結成了強大的“譙沛集團”。
“譙沛集團”成員多勇武者。夏侯惇十四歲“人有辱其師者,惇殺之,由是以烈氣聞”。夏侯淵“為將,赴急疾,常出敵之不意”。曹仁勇略,“賁、育弗加也。張遼其次焉”。曹洪為曹操從弟,曹操起兵常追隨左右,重義氣。(《三國志·魏書·諸夏侯曹傳》)除曹氏、夏侯氏之外,譙地其他人,如典韋“形貌魁梧,旅力過人,有志節任俠”(《三國志·魏書·典韋傳》),是一位難得的勇猛武將;許褚也是一員猛將,“容貌雄毅,勇力絕人”,漢末動亂時,曾聚集“少年及宗族數千家,共堅壁以御寇”,“由是淮、汝、陳、梁間,聞皆畏憚之”,許褚投靠了曹操之后,曹操稱其為“此吾樊噲也”(《三國志·魏書·許褚傳》)。
作為曹氏家族成員之首的曹操,不僅“才武絕人”(《三國志》注引晉人孫盛《異同雜語》),也是一位杰出的軍事家。曹操自伐董卓始,奪充州、征張繡、平徐淮、戰官渡、定四州、征烏桓、占荊州,兵鋒所指,所向披靡,擊敗了一個又一個貌似強大不可戰勝的對手。曹操對兵法頗有研究,且形諸文字,《三國志》注引晉人孫盛《異同雜語》云,曹操抄集諸家兵法,名曰《接要》,又注《孫武》十三篇,皆傳于世。《隋書·經籍志》記載,曹操作《〈孫子兵法〉注》二卷、《〈孫子兵法〉集解》一卷、《〈太公陰謀〉解》三卷,自撰兵書有《續孫子兵法》二卷、《兵書接要》十卷(另有三卷本)、《兵書略要》九卷、《魏武帝兵法》一卷。
曹操諸子也多文武兼備。曹丕也自小受到良好的軍事訓練,跟著曹操轉戰南北。《典論》自敘曰:“余時年五歲,上以世方擾亂,教余學射,六歲而知射,又教余騎馬,八歲而能騎射矣。以時之多故,每征,余常從。”“夫文武之道,各隨時而用,生于中平之季,長于戎旅之間,是以少好弓馬,于今不衰;逐禽輒十里,馳射常百步,日多體健,心每不厭。”“余又學擊劍,閱師多矣。”《三國志》注引《魏書》亦云曹丕“善騎射,好擊劍。”曹植不僅“才高八斗”,也是曹操手下的一員干將。建安十九年七月,曹操東征孫權,曹植留守鄴城,二十四年,曹仁為關羽所圍,太祖以曹植為南中郎將,行征虜將軍(《三國志·魏書·任城陳蕭王傳》)。任城王曹彰更是勇武絕人,能征善戰,《三國志·魏書·任城陳蕭王傳》言其“少善射御,膂力過人,手格猛獸,不避險阻。數從征伐,志意慷慨。”“武藝壯猛,有將領之氣。”
二、曹氏家族與道家文化
譙沛之地是道家思想的發源地,產生了老子、莊子等一批道家人物。這里早在新石器至夏商時期就是夷、夏兩大文化的交會地帶。到春秋時期,這里的夷族小國深受大國欺凌與并兼,成為西南荊楚文化、東北齊魯文化、中原王朝文化、北方晉文化、東南吳越文化等五大地域文化的交互中心,即以夷文化為底色而深受多種文化影響的文化交匯地區[1]。發祥于渦水流域的道家,其流派紛呈,是南北文化碰撞的結果[2]。
曹操及其家族成員深受故鄉道家文化的影響,在家族門風、思想行為及文學創作等方面都能看到老莊哲學的影子。曹操是在家鄉譙縣成長起來的,早先也依靠鄉邦子弟兵起事爭雄,后來又多次回到故里讀書,曹操對故鄉有著深厚的感情,曹操晚年詩作《卻東西門行》末句:“狐死歸首丘,故鄉安可忘!”這里是道家文化的發祥地,其鄉人老子、莊子以“道”觀察世界,創造了中國最富思辨色彩的道家學說。老莊文化影響著渦淮地區的民風習俗,也訓練了曹操的思想習慣、思維方式,使其思想認識的境界更高,富有智慧,以致在亂世可以做到“以道御之,無所不可”(《三國志·武帝紀》)。
道家思想中“獨與天地精神往來”,“逍遙乎無為之業”所蘊含的灑脫、逍遙、恣縱、崇尚自然的精神內涵對曹氏家族成員影響最大。曹氏家族尚“通侻”,正是這種影響的集中表現。曹氏家族“通侻”之舉具體表現在以下幾個方面:
表現在家族門風上,是一種比較自然與隨意的生活作風和處世態度,其核心是不守禮法[3]。曹氏父子“為人佻易無威重”,“不治威儀”。曹操一生都比較任情率真,不拘泥于禮法。郭嘉曾比較袁、曹優劣時說到:“紹繁禮多儀,公體認自然,此道勝一也”(《三國志·郭嘉傳》注引《傅子》)。袁紹是東漢后期儒學世族精英分子的杰出代表,與之相比,更能看出曹操的文化背景。所謂“體認自然”,即不拘泥于禮法,實際上就是“通達”。《三國志·魏書·武帝紀》:“太祖少機警,權數,而任俠放蕩,不治行業,故世人未之奇。”《世說新語·假譎篇》“魏武少時”條注引孫盛《雜語》:“武王少好俠,放蕩不修行業。嘗私入常侍張讓宅中,讓乃手戟于庭。逾垣而出,有絕人力,故莫之能害也。”《三國志·魏書·武帝紀》注引《曹瞞傳》載:
太祖為人佻易無威重好音樂常以日達夕。被服輕綃身自配小鞶囊以盛手巾細物時或冠帽以見賓客。每與人談論戲弄言誦盡無所隱及歡悅大笑至以頭沒杯案中,肴膳皆沾污巾漬其輕易如此。
曹操不僅本人如此,他在教育自己子孫時也比較自由,尊重他們的個性,因此其子孫大多“不治威儀”。曹丕雖然性格較為深沉,善于矯情飾己,但仍然時時表現出放蕩“輕易”的性格特征。《世說新語·傷逝篇》載:“王仲宣好驢鳴。既葬,文帝臨其喪,顧語同游曰:‘王好驢鳴可各作一聲以送之。’赴客皆一作驢鳴。”幾乎將肅穆的喪葬儀式變成了游戲。曹丕還常以俳優取笑僚屬。《三國志·魏書·武帝紀》注引《魏略》:
王忠,扶風人,少為亭長。三輔亂忠饑乏噉人,隨輩南向武關。……拜忠中郎將從征討。五官將知忠噉人,因從駕出行令俳取冢間骷髏系著忠馬鞍以為笑樂。
至于曹植,《三國志·魏書·曹植傳》載其:“性簡易,不治威儀。”曹植的這種個性,在其初見邯鄲淳時表現得淋漓盡致:
植初得淳甚喜延入坐不先與談。時天暑熱植因呼常從取水自澡訖傅粉。遂科頭拍袒胡舞五椎鍛跳丸擊劍誦誹優小說數千言訖謂淳曰:“邯鄲生何如邪?”于是乃更著衣幘整儀容與淳評說混言造化之端品物區別之意然后論羲皇以來賢圣名臣烈士優劣之差次頌古今文章賦誄及當官政事宜所先后又論用武行兵倚伏之勢。乃命廚宰酒炙交至坐席默然無以伉者。及暮淳歸對其所知嘆植之材謂之“天人”。(《三國志·魏書·王粲傳》注引《魏略》)
表現在政治方面,則是不重視禮儀制度建設,許多舉措都違背了禮制。在用人政策與觀念上,曹操一度力糾漢代傳統的以禮法、德行取士之習,重視個人的才情。曹操在建安十五年、十九年和二十二年三次頒布了求賢令,第一次令文言士人即使有“盜嫂受金”之過,亦應“唯才是舉,吾得而用之”;第二次令文又言“有行之士,未必能進取,進取之士,未必能有行”,對人才不可求全責備;第三次令文說得更清楚:“負污辱之名,見笑之行,或不仁不孝而有治國用兵之術,其各舉所知,勿有所遺”[4]之士。王粲、杜畿、裴潛等人皆“通侻”、“闊達”、“疏誕”、“不修細行”[5],皆曾依附劉表,不受重用,后皆歸曹操而頗有功業。
表現在文學創作上,則是不守陳法及表現出清峻、通侻的文風。魯迅認為曹操是“改造文章的祖師”,“膽子很大,文章從通脫得力不少,做文章時又沒有顧忌,想寫的便寫出來。”[6]劉師培在《中國中古文學史講義》亦云:“建安文學,革易前型”,一為“魏武治國,頗雜刑名,文體因之,漸趨清峻”;二是建安時期“漸尚通侻,侻則侈陳哀樂,通則漸藻玄思”,認為建安文學有四大特點:清峻、通侻、騁詞、華靡[7]。“通脫”是隨便之意。此種提倡影響到文壇,便產生許多想說甚么便說甚么的文章。如《薤露行》、《蒿里行》,本是挽歌,古辭都是雜言,五、七句式,各曲僅為四句,曹操用來描寫社會現實,改用五言來寫,各十六句;又如《善哉行》,古詞為四言,曹操將四言改為五言。《謠俗詞》、《薤露》和《蒿里》等,語言樸實,直面現實:“生民百遺一,念之斷人腸”,赤子情懷,躍然紙上。曹操的文章以《讓縣自明本志令》及一些祭文等為代表,遣詞造句簡潔通暢,不拘繩墨,直抒胸臆,一如其詩之清峻、通達。
三、曹氏家族與譙沛之地酒文化
譙沛之地釀酒歷史悠久,酒文化發達。早在戰國時期,譙沛人士莊子在《達生》篇中第一個系統地論述酒能排除外在干擾、導向精神自由的文化作用,提出酒可以使人通向“神全”的哲學內涵:
夫碎者之墜車,雖疾不死。骨節與入同而犯害與人異,其神全也。乘亦不知也,墜亦不知也,死生驚懼不入乎其胸中,是故遷物而不懾。
漢代,這里的酒就名滿天下。東漢時期譙縣縣令郭芝用九醞酒法造酒,曹操得其法造出“九釀春酒”。“九釀春酒”釀造的方法是每隔三天下一解米,滿九解米為止。這種酒“常善,其上清,滓亦可飲。”建安元年曹操向漢獻帝獻上家鄉的“九釀春酒”(曹操《上九醞酒法奏》)。從而使此酒成為宮廷用酒。張衡在《南都賦》中說:“酒則九醖甘醴,十旬兼清。醪敷徑存,浮蟻若蓱。其甘不爽,醉而不酲”。賈思勰對這種方法釀的酒給以很高的評價:“香美勢力,倍勝常酒。”(賈思勰《齊民要術》)唐代詩人白居易在《輕肥》將其與最上等的美味相提并論:“槽罄溢九釀,水陸羅八珍”。此后,譙地釀酒作坊如雨后春筍發展起來。據《毫州志》記載,清光緒年間,出現了明流酒、雙酸酒、福珍酒、老酒、三白酒、狀元紅、佛手露等十多個品牌。
生于酒鄉,曹氏家族對酒有著特殊的愛好。曹操的先祖曹參“日夜飲醇酒。”(《史記·曹相國世家》)。曹操本人與酒有著不解之緣,不僅會釀酒,更喜歡飲酒。《三國志·武帝紀》載:“太祖到酸棗,諸軍兵十馀萬,日置酒高會”。其《短歌行》舉酒高歌:“對酒當歌,人生幾何?譬如朝露,去日苦多。慨當以慷,優思難忘。何以解優?唯有杜康。”其《氣出唱》其二“酒與歌戲,今日相樂誠為樂”,把飲酒看作是人生的一大樂事。雖然,曹操下過禁酒令,但那只是在當時戰亂不斷,經濟不振的情況下,節省糧食,整頓世風,息民養農的舉措。后來違禁的人越來越多,于是這次的酒禁也就名存實亡了。他的兒子曹丕和曹植也都好酒,并常常與朋友如應玚、劉楨等飲酒。曹丕稱酒為“旨酒”、“桂酒”、“醇酒”、“甘醪”,有“旨酒盈玉觴”(《於譙作詩》),“旨酒停杯”(《秋胡行》),“酌桂酒”(《大墻上蒿行》),“但當飲醇酒”(《艷歌何嘗行》),“大酋奉甘醪”(《善哉行》其二)等詩句。曹植《箜篌引》寫他與親朋好友飲酒:“置酒高殿上,親朋隨我游。中廚辦豐膳,烹羊宰肥牛。秦箏何慷慨,齊瑟和且柔。陽阿奏奇舞,京洛出名謳。樂飲過三爵,緩帶傾庶羞。主稱千金壽,賓奉萬年酬。”曹植經常豪飲,在《名都篇》中說“歸來宴平樂,美酒斗十千。”建安二十四年(公元219年)八月,魏軍敗北襄陽,主將曹仁所率之師被蜀將關羽揮兵圍困,曹操欲舉用曹植為中郎將,火速前去救援,結果,曹植竟然“醉不能受命”(《三國志·曹植傳》)。《三國志·曹植傳》載其:“飲酒不節。”曹植在后來的《與吳季重書》里聲稱:“當斯之時,愿舉泰山以為肉,傾東海以為酒,……食若填巨壑,飲若灌漏。”以之為“大丈夫之樂”。曹植明知貪杯的危害,也曾在所作《酒賦》中大談酒為“荒淫之源”的道理,然而,在“群庶崇飲,日富月奢”(王粲《酒賦》)的世風影響下,曹植與酒結下了不解之緣。他借酒廣交才俊之士,敘說“吾與二三子,曲宴此城隅”(《贈丁翼》)的歡快,他借酒傾訴離愁別恨,抒發“親昵并集送,置酒此河陽”(《送應氏》)的傷感。酒陡長了他的豪氣,使其舉杯高呼“君子通大道,無愿為世儒”(《贈丁翼》),酒頻添了他的才情,使其創作了大量“藏之於名山,傳之於同好”(《與楊德祖書》)的詩文。同時,酒也給他帶來了諸多的麻煩,黃初二年(公元221年),監國使者灌均上疏彈劾其“醉酒悖慢,劫脅使者”(《三國志·曹植傳》)。
曹魏時期大量公宴詩的出現與曹氏家族喜好宴飲有著密切的關系。《文選》六臣注對“公宴”詩的解釋有兩種:一是呂延濟注曹植《公宴詩》曰:“公宴者,臣下在公家侍宴也。此宴在鄴宮,與兄(曹)丕宴飲。”二是張銑注王粲《公宴詩》曰:“此侍曹操宴,時曹未為天子,故云公宴。”建安時期,規模較大的文人宴會主要有兩類:一類是正會,又稱元會。《晉書·禮志》載“每年歲首元旦,曹操正會文昌殿,用漢儀。漢儀有正會禮,正旦受賀公侯一下執蟄來庭。二千石以上升殿稱歲后作樂宴饗,諸子臨會賦詩。”朝會時先是接受百官的朝賀祝壽,后舉行宴會,會上百官上壽酒,然后飲酒賦詩,可見酒是朝會中不可缺少的一個項目。這種正規的場合下所作的詩并不多,現存全部魏詩只有曹植《正會詩》一首。另一類就是曹氏兄弟組織的游宴賦詩活動。《三國志·邴原傳》注引《邴原別傳》載“太子宴會,眾賓百數十人”。建安公宴詩的主要內容就是描述這類公宴活動的。曹丕在《與吳質書》回憶與諸子當年宴酒賦詩的情景:“昔日游處,行則同輿,止則接席,何嘗須臾相知,每至觴酌流行,絲竹并奏,酒酣耳熱,仰而賦詩,當此之時,忽然不自知樂也。”曹子建、王仲宣、劉公干直接以《公宴詩》為題,分別是侍曹丕、曹操的宴會。其他公宴詩,無論是從宴會的主持者身份“皇太子”、“大將軍”、“宋公”,還是從作詩的動機“有令賦詩”、“被命作詩”、“應詔作詩”來看,都表明此類詩歌是在公宴的場合所作的詩。王粲《公宴詩》顯然是詩人歸曹后受到優厚的禮遇和熱情的招待,而發出的一片頌揚之聲。所以李善說“此詩侍曹操宴”。全詩如下:
昊天降豐澤,百卉挺葳蕤。涼風撤蒸暑,清云卻炎暉。高會君子堂,
并坐蔭華榱。嘉肴充圓方,旨酒盈金罍。管弦發徽音,曲度清且悲。
合坐同所樂,但愬杯行遲。常聞詩人語,不醉且無歸。今日不極懽,
含情欲待誰。見眷良不翅,守分豈能違。古人有遺言,君子福所綏。
愿我賢主人?與天享巍巍。克符周公業,奕世不可追。
曹植《公宴詩》開門見山地點明了此次公宴的背景:
公子敬愛客,終宴不知疲。清夜游西園,飛蓋相追隨。明月澄清景,
列宿正參差。秋蘭被長坂,朱華冒綠池。潛魚躍清波,好鳥鳴高枝。
神飚接丹轂,輕輦隨風移。飄飖放志意,千秋長若斯。
此次宴會的主持者就是詩中的“公子”曹丕。曹丕設宴,賓主和眾人一同沉醉于宴會歡樂的氣氛中,直至宴會結束之時還不知疲倦。將賦詩與酒宴和欣賞周圍的美景聯系在一起,達到詩、酒、景的結合,酒助詩情,使得氣氛更加的和諧活潑。
建安時期,以曹氏父子為中心的宴飲活動十分頻繁。曹丕和曹植都是當時詩壇的中心人物,而且有各自的文學集團,他們經常與文人們一起詩酒唱和,流連風月。劉勰在《文心雕龍·明詩》中說三曹、七子等人“并憐風月,狎池苑,述恩榮,敘酣宴。”他們在宴飲的時候多飲酒賦詩,留下了大量詩文作品。王粲、劉楨、阮瑀、應玚等人都有以“公宴”為題的詩作。
四、曹氏家族與譙地藥文化
譙地是中國四大古藥都之一。地理、氣候條件得天獨厚,中藥材品種豐富,出產中藥材130多種,安徽的四大名藥毫州占2種(白芍、菊花),尤其是白芍、菊花、紫苑、花粉、桑皮更馳名中外。據有關史料記載,白芍年產量高達90多萬斤,花粉5萬斤。遠在西漢時,毫州的藥市就已很興隆。東漢以后華佗遺風經久不衰,藥師濟濟,傳統的中藥材培植、炮制技藝進一步提高。過去這種藥市“分鄉幫”而立門戶,較大的有兩廣幫、山陜幫和咸寧幫等,來自全國各地。明清時期,毫州藥都對藥材的炒、炮、煮、烘、曬、切、藏及制作成藥都形成獨到的特色,成為全國藥業的活動中心之一,專營中藥材的行、幫、店數以千計,形成南北藥市集散地。
譙地名醫輩出。早在東漢末年出現了神醫華佗,《三國志·華佗傳》載其醫術高超,精通方藥、針灸、養生等,他曾用“麻沸散”使患者麻醉,這是醫學史上最早的剖腹手術:
華佗字元化,沛國譙人也,……曉養性之術,時人以為年且百歲而貌有壯容。又精方藥,其療疾,合湯不過數種,心解分劑,不復稱量,煮熟便飲,語其節度,舍去輒愈。若當灸,不過一兩處,每處不過七八壯,病亦應除。若當針,亦不過一兩處,下針言“當引某許,若至,語人”。病者言“巳到”,應便拔針,病亦行差。若病結積在內,針藥所不能及,當須刳割者,便飲其麻沸散,須臾便如醉死無所知,因破取。病若在腸中,便斷腸湔洗,縫腹膏摩,四五日差,不痛,人亦不自寤,一月之間,即平復矣。
受故鄉深厚醫藥文化的熏染,曹氏家族對藥有著特殊的興趣。曹操對中藥有一定的研究,據說他曾經想考考華佗的醫術和文才,寫了一則中藥詩謎給華佗猜:“胸中藥花,西湖秋英。睛空夜珠,初入其境。長生不老,永達康寧。老娘獲利,警惕家人。五除三十,假滿期臨。胸有大略,軍師難混。醫生接骨,老買忠誠。無能缺技,藥店關門。”華佗一看曹操出的是藥名謎,就信手寫出十六句詩,其中暗指十六味藥名:穿心蓮、杭菊、滿天星、生地、萬年青、千年健、益母、防己、商陸、當歸,遠志、苦參、續斷、厚樸、白術、沒藥。”曹操一見,欣然大喜,稱贊華佗果真醫術高明[8]。曹操對藥膳頗有研究,代寫了有關“藥膳”內容的《四時飲食制》[9]。
曹氏父子注重養性,求藥延壽。《三國志·武帝紀》注曰:“太祖又好養性法,亦解方藥,招引方術之士,左慈、華佗、甘始、郄儉等,無不畢至。又習啖野葛至一尺,亦得少飲鴆酒。”據記載,華佗有輕身神方和不老延年神方[10],“潁川郤儉能辟谷,餌伏苓。甘陵甘始亦善行氣,老有少容。廬江左慈知補導之術。”(曹丕《典論》)曹操希冀延長壽命以便成就事業,在這種心態的支配下,他寫下了相當數量的游仙詩,在詩中他寄托了求藥延壽的思想。《氣出唱》其一云:“愿得神之人。乘駕云車。驂駕白鹿。上到天之門。來賜神之藥。跪受之敬神齊。當如此,道自來。”其他如“思得神藥,萬歲為期”(《秋胡行》其二),“交赤松,及羨門,受要秘道愛精神。食芝英,飲酸泉,拄杖枝,佩秋蘭”(《陌上桑》)。他想象遍游泰山、蓬萊、昆侖,與赤松、王喬、西王母等仙人共處,服神藥,食芝英,以希冀壽命得以延長。曹操“烈士暮年,壯心不已”〔《步出夏門行))),統一天下的入世、治世精神始終未磨滅,“不戚年往,憂世不治”《秋胡行》其二)是他在游仙詩中求藥延壽的最好注解。曹操的永年之求有一種積極向上的精神,他創作游仙詩是在想象中補償現實人生的缺憾和不足,在幻境中完成未竟之統一大業。
曹丕在游仙詩《折楊柳行》中也寫到了服藥,但對其抱著懷疑的態度:
西山一何高,高高殊無極。上有兩仙僮,不飲亦不食。與我一丸藥,光耀有五色。服藥四五日,身體生羽翼。輕舉乘浮云,倏忽行萬億。流覽觀四海,茫茫非所識。彭祖稱七百,悠悠安可原。老聃適西戎,于今竟不還。王喬假虛辭,赤松垂空言。達人識真偽,愚夫好妄傳。追念往古事,憒憒千萬端。百家多迂怪,圣道我所觀。
曹植對求藥延壽深信不疑。其《飛龍篇》云:“晨游泰山,云霧窈窕。忽逢二童,顏色鮮好。乘彼白鹿,手醫芝草。我知真人,長跪問道。西登玉臺,金樓復道。授我仙藥,神皇所造。教我服食,還精補腦。壽同金石,永世難老。”《平陵東行》云:“閶闔開,天衢通,被我羽衣乘飛龍。乘飛龍,與仟期,東上蓬萊采靈芝。靈芝采之可服食,年若王父無終極。”《五游詠》云:“九州不足步,愿得凌云翔。肖遙八纮外,游目歷遐荒。披我丹霞衣,襲我素霓裳。華蓋芬晻藹,六龍仰天驤。曜靈未移景,倏忽造昊蒼。閶闔啟丹扉,雙闕曜朱光。徘徊文昌殿,登陟太微堂。上帝休西欞,群后集東廂。帶我瓊瑤佩,漱我沆瀣漿。踟躕玩靈芝,徙倚弄華芳。王子奉仙藥,羨門進奇方。服食享遐紀,延壽保無疆。”從詩中可以看出,曹植所說的“仙藥”主要是以靈芝之類中草藥制成的。
總之,曹氏家族與家鄉譙沛之地的地域文化存在著千絲萬縷的聯系。譙沛之地悠久的政治軍事傳統孕育了曹氏家族的武人氣質,譙沛之地深厚的老莊文化、酒文化和醫藥文化又賦予這個家族通脫、大氣的家族氣質和喜好文藝、懂得養生的家族傳統。
[1] 陳立柱.曹操思想性格形成的道學文化背景[J].呂梁學院學報,2011,(1).
[2] 張立馳,魏宏燦.亳文化略論[J].學術界,2011,(2).
[3] 王永平.論曹操家族門風及其影響[J].學術月刊,2005,(10).
[4] 中華書局編輯部.曹操集[M].北京:中華書局,1974.
[5] (晉)陳壽.三國志[M].北京:中華書局,1982.
[6] 魯迅.而已集[M].北京:人民文學出版社,2006.
[7] 劉師培.劉師培學術論著[M].杭州:浙江人民出版社,1998.
[8] 符文軍,金波.中華國學句典大全[M].北京:北京工業大學出版社,2009
[9] 邢湘臣.藥膳史話[J].東方藥膳,2007,(9).
[10] (漢)華佗.華佗神醫秘傳[M].沈陽:遼寧科學技術出版社,2010.
CAO Family and Regional Culture of Qiao Pei
FANG Xiao-ling
(DepartmentofChineseLanguageandLiterature,HefeiNormalUniversity,Hefei230601,China)
A family where the regional culture is the family’s growth environment.CAO Family headed by CAO Cao,no doubt with Qiao Pei of the regional culture inextricably linked.Qiao Pei has its own unique regional culture.Its long military political tradition,Taoist culture,wine culture and drug culture have had a profound impact on CAO Family in politics,academic thought,family name,Literature Creation and other areas.
CAO Family;Qiao Pei;regional culture
K236
A
1674-2273(2012)04-0084-05
2012-05-09
安徽省社科聯資助項目(A2010018)
方孝玲(1968-),女,安徽廬江人,合肥師范學院中文系講師,文學碩士。
(責任編輯何旺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