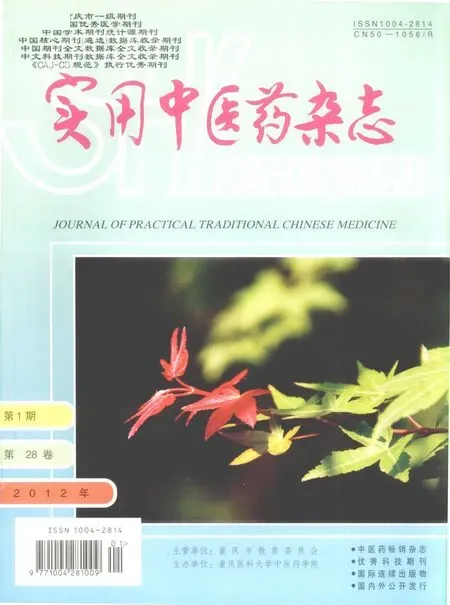“字如其人”與“方如其人”
王輝武
(重慶醫科大學附屬第二醫院中西醫結合科,重慶400010)
簽名字較之蓋私章更具有法律效應,甚至可以字跡的形態,作為刑偵破案與招生選才的依據之一,這些不爭的事實證明,手寫之字,確是書寫者的“身份證”。
在中國數千年的傳統文化中,方塊漢字本身就是象形表意文字,并受儒學倫理道德和感性思維模式的影響,因而對“字如其人”又有更深層次的理解。書家寫的字除了書寫技法的展示之外,還能流露其人品、性格、學識等精神層面的意蘊,故“書為心畫”成了評價書法作品的口頭禪,正如蘇軾所說:“書有工拙,而君子小人之心,不可亂也。”項穆《書法雅言》說得更明白:“故論書(字)如論相,觀書如觀人,人品既殊,識見亦異。”字,不論形態如何,都看得出寫字者的精神心態,如酒后有醉書,歡喜有狂書。顏真卿的字必然“忠義貫日月”,而趙孟頫的字固然圓轉流利,究竟不能擺脫其奴顏媚骨的品相。明末清初醫家傅青主,他先學趙字,因惡其“心術壞而手隨之”,后改學顏體,并為顏魯公氣節所震撼,遂作字風格遒勁,氣勢磅礴,成為影響書壇的大家,堪稱“字如其人”的典范。
中醫開方,多是漢字,除“字如其人”的效果外,尚有“方如其人”的意義。中醫之所以能夠歷千年而頑強地傳承發展,是因為其與掌握這門學術的人精神氣質、學問修養的緊密相聯。古往今來,大凡名醫,皆很重視處方書寫,其中追求書法功夫者也不乏其人。如東晉著名醫家葛洪,他為天臺山摩崖石刻寫的“天臺之觀”,被米芾尊為“為大字之冠,古今第一”;南北朝醫家陶弘景,他留在鎮江焦山摩崖石刻上的《瘞鶴銘》被黃庭堅誤為王羲之所書。近代名醫丁甘仁、惲鐵樵、施今墨、秦伯未、程門雪等,書法皆臻上境,他們留下的處方箋,多被收集珍藏。上海十大名醫之一的顧筱巖曾說:“字是一張方子的門面,是一個醫生文化底蘊、學識才華的外露。”
的確,處方字跡之優劣是給人的第一印象。舊時中醫帶徒,入門之前常強調四句話:“一手好字,二會幫忙,三指切脈,四季衣裳。”這第一句就要求把字寫得工整無誤,是很有道理的。對于寫字,不是要求每個學中醫者都成書法家,只要平正,認真即可,這種要求并不高,稍加重視都是可以辦得到的。然而就有一些醫者,一旦提筆便心浮氣躁,如同有人趕他似的,寫出來的字張牙舞爪、龍飛鳳舞、東倒西歪,或筆畫不清、墨跡難辨,或隨意簡化、生造濫用。這種處方,不用說別人不認識,就連他自己有時也會難辨,在患者心里是啥滋味?一句話,“天書”,給人以輕浮放蕩的感覺。作為醫生,如果是這種態度,試問,誰敢把“至貴之性命”交給他打理呢?
當然,有人會說,而今有電腦,開處方不用手寫,只需手指一敲,處方就搞定了。字雖是印刷體,但也能從處方內容中表露醫者的業務水平。一個熟讀經典、精通醫理的醫生,開具的處方一定是理法清晰,并依法遣方,加減配伍,有理有據,可從方中看得出為醫者對基礎知識、各家學說掌握的情況,倘《溫病條辨》都未通讀過,他肯定開不出半苓湯、雙補湯的處方來。
還有,從一張中醫處方可以看得出醫生的臨床思維情況。有人處方用藥動輒30~50味,甚至更多,美其名曰“韓信點兵,多多益善”,或曰“寒熱并用”、“攻補兼施”,但完全看不出如仲景烏梅丸一樣的組方法度,也看不出方中君臣佐使的關系,這只能說明開方者頭昏腦脹,到底要想解決何種問題,他自己也不清楚。
除此之外,從中醫處方還能測知醫者跟蹤學術發展的能力。例如對傳統認識已有所更正,或者對某一理論問題有所創新,或某些方藥有研究成果、又被學術界所公認者,但處方者全然不知。這種情況至少說明醫者平時不讀書刊,又未參加學術交流。
更有甚者,在處方中出現與證候病情毫不相干的藥味。如不需搜風通絡,不必消腫破癥,也沒有通經下乳的要求,方中用上穿山甲,且劑量不小;或迎合患者保健之意,雖胃脹腹瀉,也人參、阿膠、蟲草、鱉甲并進……。此醉翁之意不在酒,涉嫌另有他圖,從處方中可窺見其人品與德行……,行業中的斜門歪道、潛伏規則也暴露無遺了。
古往今來,名家醫方墨跡為人們收藏之珍品,病家也有保留處方的習慣,目的在于記錄診療過程,有的效驗之方可在民間沿用多年,在傳抄過程中也會把某些不雅的痕跡留了下來。如果你經常懸壺開方,黑的寫(打)在白紙上,又簽上你的大名,這處方滿天飛舞,城鄉傳遍,數年后遭人評點與非議,當作何感想?!
故“方如其人”,此非小事,當需慎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