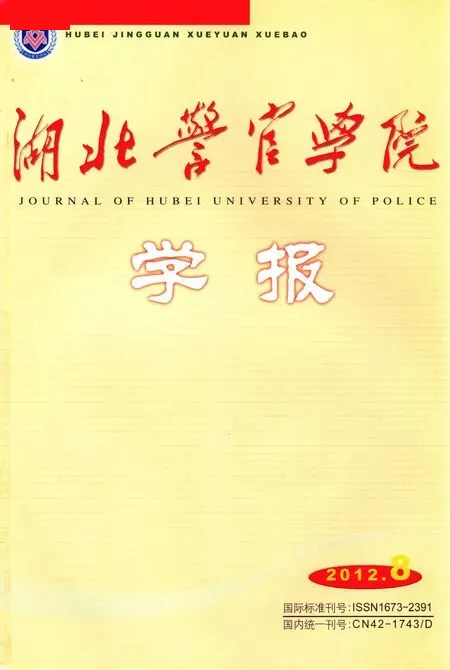危險駕駛罪醉酒駕駛行為主觀罪過辨析
黃 晴
(廣西大學 法學院,廣西 南寧530004)
危險駕駛罪醉酒駕駛行為主觀罪過辨析
黃 晴
(廣西大學 法學院,廣西 南寧530004)
《刑法修正案(八)》危險駕駛罪中的醉酒駕駛行為的主觀罪過應為過失。醉酒駕駛行為應當承擔刑事責任源于“原因自由行為”理論,我國過失理論以行為人對危害后果的主觀心態作為考量標準,因此應當將醉酒駕駛作為整體一個行為分析駕駛者造成公眾生命、財產處于危險狀態的主觀態度。危險駕駛罪是危險犯,引入過失危險犯理論討論醉酒駕駛行為的主觀罪過既符合立法實際也可以更好地保護法益。
醉酒駕駛;主觀罪過;原因自由;危險犯
2011年2月,第十一屆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常務委員會第十九次會議通過的《中華人民共和國刑法修正案(八)》第22條規定:在刑法第一百三十三條后增加一條,作為第一百三十三條之一:在道路上醉酒駕駛機動車的,或者在道路上駕駛機動車追逐競駛,情節惡劣的,處拘役,并處罰金。修正案明確將兩種行為定義為危險駕駛:第一,醉酒駕駛機動車;第二,在道路上駕駛機動車追逐競駛。對于第一種行為,行為人只要醉酒后駕駛機動車,即構成本罪,無需達到特定情節的程度;而第二種行為,在道路上駕駛機動車追逐競賽,則必須達到情節惡劣,即必須達到一定的危害程度。修正案5月1日生效至今,司法實踐中對于該罪的認定,特別是醉酒駕車行為入罪存在認定模糊,甚至忽略行為人的主觀罪過而僅判斷客觀行為的情況。究其原因,源于從本罪出臺前對于如何規制本罪的探討及出臺后最終以設立新罪的模式將醉酒駕車行為入罪后整個過程中,學界始終沒有對該行為的主觀罪過進行明確界定,因此有必要通過對醉酒駕駛行為有責性的理論源頭即原因自由行為進行定義梳理,再進一步對醉酒駕駛行為的客觀分類予以明晰,才能準確認定該行為的主觀罪過。
一、基于原因自由理論對醉酒駕駛的有責性分析
對醉酒駕駛行為主觀罪過認定爭議大的原因,在于對醉酒駕駛行為特殊的行為構成容易造成認定偏差。要準確地辨析醉酒駕駛行為的主觀罪過,必須回歸醉駕行為應當承擔刑事責任的理論淵源——原因自由行為。
(一)原因自由行為理論之濫觴
原因自由行為相關問題最早可追溯至亞里士多德《倫理學》中提及的醉酒行為,羅馬法與德意志法都認為酩酊為行為人責任能力的阻卻或減輕事由。[1]隨著刑罰理論的發展,反對客觀歸罪以及限制刑罰的理念得到肯定,刑罰理論逐漸傾向于采取責任主義。責任主義立場要求責任能力必須與犯罪行為同時,對于犯罪行為時無責任能力或者限制責任能力的不應當承擔刑事責任。隨著理論的深化,就行為人對于將自己陷于無責任能力、限制責任能力狀態是否應當承擔責任,若是應當承擔責任是否因此受罰的問題產生了極大爭論,在此爭論中原因自由行為理論才最終得以確定。現在各國刑法理論界對原因自由行為理論的可罰性是肯定的,在立法中體現為規定精神病人、生理醉酒人犯罪應承擔刑事責任。但是出于不同的理論背景,以及原因自由行為如何歸責等一系列問題的爭議,原因自由行為的定義尚未得以明確。日本有學者認為,所謂原因自由行為,系由于行為人故意或者過失,把自己陷于無責任能力的狀態,使其在無責任能力狀態下惹起犯罪構成要件之結果。[2]我國有學者認為,原因自由行為是由刑事責任能力的行為人由于自己故意或過失的行為,導致自己陷入無責任能力的狀態,并在此狀態之中造成了符合犯罪構成的事實。在對原因自由行為不同定義的爭議中,引發出以原因自由行為理論為源對原因自由行為主觀罪過討論的重大分歧。有觀點指出,原因自由行為所構成的犯罪主觀上不能是直接故意,但可以是過失犯罪或者間接故意犯罪;還有觀點認為,原因自由行為的主觀罪過應當分情況討論,首先區分行為人是陷入“無責任能力狀態”或是“限制責任能力”狀態,然后再進一步討論在此狀態下實際侵害行為的主觀罪過。大陸法系國家對原因自由行為的定義也存在狹義與廣義的分歧,上述對原因自由行為的定義都不能準確地將其特殊的行為構成及責任認定予以明確。定義混亂造成的后果是,在進一步用原因自由行為理論分析行為人主觀罪過時,就會將“故意原因自由行為”“過失原因自由行為”與“原因自由行為的故意犯”“原因自由行為的過失犯”概念相混淆,將原因自由行為的主觀罪過片面割裂成為原因行為的主觀罪過或者結果行為時主觀罪過,再以此作為行為人完整原因自由行為的罪過。
(二)原因自由行為的主觀罪過為過失
原因自由行為特別之處在于,一個行為整體由兩部分行為構成,即原因行為與結果行為。原因行為,亦稱為前行為,行為人故意或者過失地使自己陷入無責任能力或者有限責任能力的狀態,此時的行為通常沒有侵害任何法益,甚至不是刑法意義上的“行為”;結果行為也稱為后行為,具體而言就是法益被侵害的階段。通過前后相繼的兩部分,構成完整的原因自由行為。原因自由行為經過長期論證,最終才得以納入刑法理論的原因在于其特殊的行為責任構造,行為人在原因行為時具有刑事責任能力,但此時的行為不是造成法益侵害結果的直接行為,甚至不是刑法意義的“行為”;結果行為是實際上侵害法益的行為,但此時行為人不具有刑事責任能力。完成對原因自由行為構成的梳理,可對原因自由行為進行定義,首先,必須明確將原因行為與結果行為看做統一且單一的完整行為,不能將二者割裂;其次,不能片面理解原因行為中的“故意或過失”,至少不能將其認定為刑法學上的“故意”或“過失”,刑法學上的“故意”與“過失”是具有特定含義的,都是指對危害結果的心理態度而非對行為本身的心理態度,既然“原因自由行為”本身就應當認定為單一獨立的行為,又怎么能以刑法學上的“故意”與“過失”直接套用于該特殊行為的某一組成部分,從而認定為該行為人的主觀罪過?以醉酒駕駛行為而言,喝酒作為醉酒駕駛的原因行為,不是刑法評價的“行為”,更不能以喝酒的主觀心態認定醉酒駕駛行為的主觀心態。因此,本文將原因自由行為定義為:行為人將自己置于無責任能力或者限制責任能力狀態,并在此狀態下實施了符合犯罪構成要件、侵害法益的具體行為。原因自由行為人的罪過,即對其造成的危害結果的心理狀態,應當認定為過失。仍以醉酒駕駛行為為例,醉酒駕駛行為不應當被割裂為“喝醉酒+醉后駕駛”,醉酒駕駛行為本身才是一個完整的可以用刑法評價的行為。我國罪過理論對行為人主觀罪過的探討,基于行為人對危害結果的心理態度,而非對行為本身的心理態度。對于醉酒駕駛行為人而言,他作為危險后果造成者的同時也是受害者,更重要的是通過事后對行為人的考察發現,行為人對危害結果的發生是存在僥幸心理,或者不希望危害結果的出現。
二、以過失危險犯定義醉駕行為主觀罪過的合理性
(一)危險駕駛罪屬于危險犯
有人認為,將醉酒駕駛行為主觀罪過認定為過失,不符合我國刑法過失犯罪構成理論,因為傳統理論認為過失犯是典型的結果犯,我國刑法規定以危害結果的實際發生作為過失犯成立的必備條件,將犯罪造成的“危害結果”限制理解為實害結果。但是深入分析發現,上述觀點將“實害犯”與“結果犯”概念混同甚至替換,與結果犯相對應的應當是行為犯,實害犯與危險犯是結果犯的再細分,只要行為構成法律規定的危險狀態即成立危險犯,此時危險狀態作為危險犯的犯罪結果。《刑法修正案(八)》將危險駕駛罪作為《刑法》第一百三十三條中醉駕行為具體罪狀表述如下:“在道路上醉酒駕駛機動車的,處拘役,并處罰金”,罪狀表述直接反映出,醉酒駕駛機動車行為一經發生,已將公共安全及不特定多數人的生命、財產安全置于不安全狀態,對這樣的高危行為無需附加導致危害結果或情節嚴重,就可推定該行為具有法律上的危險,危險駕駛罪是典型的危險犯。
(二)過失危險犯的合理性
確定危險駕駛罪為刑法理論上的危險犯后,又涉及另一個爭議問題,即過失危險犯理論成立與否。支持與反對的雙方都已充分的論證,雖然反對者旁征博引但一些國家在立法上已經確立了過失危險犯①日本刑法典129條規定:“因過失使貨車、電車或船艦之往來發生危險或致貨車、電車顛覆、破壞或船艦覆沒、破壞者,處以500元以下之罰金”。德國刑法典第316條規定了酒后駕駛罪:“(1)飲用酒或其他麻醉品,不能安全駕駛交通工具,如其行為未依第315條a或第315條c處罰的,處一年以下自由刑或罰金刑。(2)過失犯本罪的,亦依第一款處罰。”。我國立法實踐中也存在過失危險犯,《刑法修正案(七)》第十一條修改了原妨害動植物防疫檢疫罪,在已有罪名的基礎上增加了“有引起重大動植物疫情危險”,該罪的主觀方面是過失,將危險狀態也列為犯罪。可見,立法實踐上已經趨向接受過失危險犯,將醉酒駕駛行為認定為過失危險犯不僅與我國刑法理論不矛盾,而且符合立法發展趨勢。醉酒駕駛行為侵犯的法益主要是社會公共安全,具體指不特定多數人的生命、身體健康、公私財物的安全性。醉酒駕駛時,行為人對路況、突發情況的判斷與應對已處于遲鈍狀態,交通駕駛本來是可容忍的危險,但醉酒駕駛無疑增加了危險程度,超出可容忍范圍,因此,才將法益保護提前,以降低社會的風險。
四、結語
將危險駕駛罪醉酒駕駛行為的主觀罪過認定為過失更為合理,也便于司法實踐中的認定。《刑法修正案(八)》通過增加危險駕駛罪作為《刑法》第一百三十三條之一,目的在于加強對醉酒駕車行為的打擊。危險駕駛罪中醉駕行為定性的百家爭鳴,以及司法實踐中出現的“醉駕者一律入刑”的傾向,癥結在于對醉酒駕駛行為主觀罪過認定模糊。將危險駕駛罪中醉酒駕駛行為的主觀認定為過失,不僅符合罪刑法定原則,也是現行刑法框架內的必然之舉。
[1]郭棋涌.有關原因自由行為之立法例[J].法律評論,1988(7):33.
[2][日]植松正,川端博,增根威彥,日高義博.現代刑法論爭[M].勁草書房,1984:231.
DF622
A
1673―2391(2012)08―0087―02
2012—03—10
黃晴,廣西大學法學院。
【責任編校:陶 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