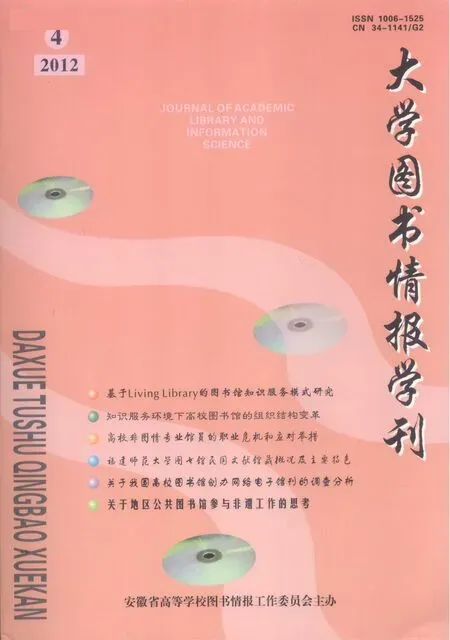朱熹對古代文獻及其傳播貢獻的研究
劉亞玲
(西北政法大學,西安 710063)
朱熹(1130-1200),字元晦,南宋徽州婺源(今江西婺源)人,著名的哲學家、思想家、教育學家,宋明理學的集大成者,儒家倫理思想體系的完成者,影響了后世學術思想的發展達六七百年之久,并波及日本、韓國以至歐洲。有學者譽他為“孔子之下,一人而已”。他非常重視前人的文獻資料,一生都在從事儒家文獻資料的編纂、整理、詮釋、傳播和收藏活動,對我國古代文獻,特別是儒家文獻整理、收藏、傳播均做出了杰出的貢獻。
1 歷史上成書最多的學者之一
朱熹在文獻學上的突出貢獻就是成果數量多。他一生仕途多舛,熱衷于教育和著書,把闡發、弘揚儒家思想和教育后學作為畢生的事業。他認為世間萬物所謂的“理”都完整地體現在圣賢的著作里面,“窮理之要,必在于讀書”,因此,朱熹把全部精力都花費在對前代文獻的整理、研究當中。關于儒家經典的注解,他著有《周易本義》、《詩集傳》、《論語集注》、《孟子集注》、《大學章句》、《中庸章句》,并指導他的學生蔡沈作《書集傳》,還和他的其他學生作《通鑒綱目》,這是對司馬光《資治通鑒》的改編,加入了所謂“春秋筆法”。朱熹沒有注解《春秋》,但以視這部《通鑒綱目》為繼續《春秋》的著作。在古典文學著作中,他作了《楚辭集注》、《韓文考異》,還作有《易學啟蒙》、《陰符經注》、《參同契注》,后二者沒有用真名。除此之外,他還把別人的不同意見,以及別人所提的問題收集起來,編成《或問》,還把《中庸》的要點特別提出來編成《中庸輯略》。朱熹還編輯有《五朝名臣言行錄》、《三朝名臣言行錄》、《近思錄》、《河南程氏遺書》和《外書》。后人把他的遺書編輯為《朱文公集》,把他的語錄編輯為《朱子語類》。[1]朱熹身體力行致力于著書立說,在其影響下,學生中以著述聞世的,也有數十人之多(見《朱子實紀》),這就為書坊提供了大量的稿源。
2 一位卓有成就的出版家
朱熹晚年僑寓建陽考亭時,“興學校,明教化,四方學者畢至”[2],先后創建了考亭書院、云谷書院、同文書院和寒泉精舍等。同時,在朱熹大力倡導下,其弟子在閩北各地創辦的書院則更多了,吸引了海內眾多的學者前來求學。創辦書院就必然要用教材,因此,他還是一名卓有成就的出版家。南宋時期的雕版印刷術已非常發達,尤以杭州、四川、福建、徽州等地為盛。誠如朱熹所說:“建陽麻沙版書籍行四方者,無遠不至。”[3]黃山書社1987年出版的《安徽省出版資料選輯》一書中,記載“南宋新安人士中,理學家朱熹、會稽郡守汪綱等,均刻過書”。1995年方彥壽先生發表《朱熹刻書事跡考》一文,考證“朱熹刻本的種數達三十幾種之多,閩、浙、贛、湘,宦跡所在,均有刻書,因此,朱熹實際上是一位相當有成就的出版家、刻書家。”[4]并且認為“朱熹擁有專門的刻書工場”。2005年林振禮先生發表《朱熹:作為編輯出版家的評價》,認為“朱熹躬親領導的編輯出版活動,以編刻載體為儒家典據擅變奠定了基礎。”[5]這些事實說明朱熹確實是一位有成就有影響的出版家。
與一般的刻書家相比,朱熹對出版業的貢獻還體現在他對文獻學的追求上。朱熹在《書臨漳所刊四經后》中明確指出自己出版編輯的方針:“一以諸篇本文為經,而復合序篇于后,使覽者得見圣經之舊,而不亂乎諸儒之說。”[6]這就是說,出版傳統的經典是出版人的責任,而辨別真偽、傳信后世更是出版者的義務!因此,朱熹刻書有兩個原則:第一,注重經典。以追求經典的本來意義為出發點,“圣賢當來立言本意”是其發揮、闡釋義理,構建理學體系的基礎。由此出發,朱熹在整理、詮釋經典的方法上,既重訓詁考據,又重義理發揮。重訓詁考據,直追圣賢本意,使其不至于偏離儒學道統而儒學之根本立;重義理闡發,因應時代的挑戰,使其能不斷創新而理學之學理盛。第二,注重辨偽與考訂。[7]前文所述《四經》之一的《尚書》,其真偽之辨貫穿了整部中國文獻學史。朱熹懷疑《古文尚書》、《尚書序》以及《孔安國傳》為后人偽作,在其《書臨漳所刊四經后》中,朱熹首先對《尚書》的真偽問題進行辨別,令人信服地指出“今文多艱澀,而古文反平易”的不正常現象,同時說明“安國之序又絕不類西京文字,亦皆可疑”。鑒于此,朱熹將《尚書序》黜于書后。對于《易》,朱熹亦認為本是古代占筮之書,不是義理之作,只是“自諸儒分經合傳之后,學者便文取義,往往未及玩心全經,而遽執傳之一端以為定說”。[8]因此,朱熹在漳州所刊刻的《易》,以呂祖謙考訂的古文《易》為底本,不穿鑿義理,也不附會象數。在長期的辨偽實踐中,朱熹對辨偽方法從理論上作了總結,他說:“熹竊謂生于今世而讀古人之書,所以能別其真偽者,一則以其義理只所當否而知之,二則以其左驗之異同而質之。未有舍此兩途而能直以臆度懸斷之者也。”[9]這表明,朱熹的辨偽思想已經達到了一個較為成熟的境地。朱熹刻書對豐富文獻版本和圖書收藏方面影響深遠,惠及現代。1972年,日本首相田中角榮應邀來中國訪問,毛澤東主席與他會談之后,還特地贈送了他一套書籍,就是由朱熹作注的全套八卷《楚辭集注》(揚州廣凌古籍刻印社刻印)。胡錦濤總書記2006年4月訪問美國耶魯大學時,向學校贈書567種共1346冊,其中就包含了《四書五經》等大量由朱熹撰著、編次、注釋、校刊的著作。由此可見,朱熹在圖書版本、藏書建設上的貢獻已經載入了中華傳統文化的史冊,在向世界傳播和進行文化交流上一次又一次地展現了中華民族的光輝風采。
3 以書院為基地,聚徒講學,傳播思想
書院是我國古代特有的一種教育組織形式,它不僅是傳道授業的教學機構,也是士人研究學術的重要基地。作為我國古代偉大的教育家,朱熹在各地創建、修復和讀書講學的書院多達60多所。其中最具代表性的有廬山白鹿洞書院、長沙岳麓書院、建陽寒泉精舍、云谷晦庵草堂和考亭書院,以及地處武夷山五曲隱屏峰下的武夷精舍。除朱熹所創建之外,其余書院也與朱熹學派密切相關,創建者或為朱熹的師長,如創建屏山書院的劉子翬,創建環溪精舍的朱松,創建文定書堂的胡安國等;或為朱熹的學生,如創建西山精舍的蔡元定,創建廬峰書院、南山書院的蔡沈,創建云莊書院的劉熗,創建潭溪精舍、環峰精舍的黃斡,創建溪山書院的葉味道,創建云巖書院的李方子,以及創建西山精舍的真德秀等。無論是在內容與形式上,這些書院與朱熹的武夷精舍、考亭書院都有一脈相承之處。這些書院的創建者幾乎都是當時的著名學者,他們或為考亭學派的前驅,或為后繼。[10]這些書院以朱熹創建的書院為中心,猶如眾星拱月,一方面大大推動了宋代的教育事業,為國家培養了大批仕子,另一方面由于這些書院的弟子或再傳弟子大都來自全國各地,他們不僅自身博覽群書、熟讀經史,而且,他們離開書院以后,也把弘揚儒學作為畢生的奮斗目標,大大推動了這一時期圖書資料的社會流通。
4 重視書院藏書事業的發展
朱熹對書院藏書建設十分重視,不僅親自編寫“三次文獻”,繪制掛圖以作教學用,還廣泛搜集散失經籍,修損補殘,建閣貯藏。朱熹為了更好地收藏和利用圖書資料,于興建書院“圖書館”方面頗費了一番心血。他在重建白鹿洞書院時,謀求藏書的事跡就成為一段感人佳話。他先是將替人撰寫傳記所獲的答謝禮品手抄《漢書》四十四通,捐給書院;同時還向各官府求援,征集圖書。事見朱熹《與黃商伯書》中,其稱:“白鹿成,未有藏書,欲于兩潛求江西諸郡文字,已有札子懇之。此前亦求之陸倉矣。度諸公必見許。然見已有數冊,恐致重復。若已呈二文,托并報陸倉三司合為之,已有不別致,則易為力也。書辦乞以公碟發來,當與收附,或刻之金石,以示久遠,計二公必樂為之也。旦夕遣人至金陵,亦當遍于諸使者也。”其求書若渴之心態,以及辦法考慮之周詳妥當,皆顯示出朱熹已將藏書當成了一種崇高的事業追求。[11]不僅如此,他還親自規劃創建書樓,其事雖未親成,但二十余年后其志得遂,白鹿終于建起了云章閣。就是離任之后,他還悠悠以白鹿藏書為念,上書朝廷,請得高宗皇帝御書石經拓本一套與國子監印本九經一部,真可謂傾心其事,孜孜不倦。正是這種不舍的追求精神和書院建設者們的不懈努力,才直接推動了宋代書院藏書的不斷發展。一般說來,朱熹廣聚圖書資料,有以下幾種辦法:其一,補損修殘,整理縣學存書。據清道光《重纂福建通志》卷六三《學校·同安縣》中引用朱熹的一段話:“同安學故有官書一匱,無籍記,文書官吏傳以相承,不復稽省,至某始發視,則皆故敝殘脫,無復次第,獨視其終篇,皆有識焉者。”朱熹在同安建了一個經史閣,整理貯藏縣學中存書,得191卷,縣學中故存書失而復得者36卷。此事在其文《同安縣學經史閣上梁文》、《經史閣上梁告先圣文》、《泉州同安縣學故書目序》中皆有記載。其二,爭取上級調撥。據朱熹在《泉州同安縣學官書后記》中曰:“熹以檄書白事大都督府廷中已事,而言于連帥方公曰:‘熹為吏同安,得兼治其學事。學有師生誦說,而經籍弗具,學者四來,無所業于其間,愿得撫府所有書以歸,使學者得肄習焉’。”[12]結果獲撫府賜書985卷。其三,搜尋散失在外的書籍。《朱子大全》中還可看到,他曾得好幾種書帖:從曹建處得程頤《與方道輔帖》的模本;從薌林向得邵雍《誡子孫語》及《天道》、《物理》二詩的手書;從顏真卿處得《尹淳帖》;從蔡廷彥、吳唐卿處得包拯青年時代詩。其四,自制圖籍資料。朱熹親自書寫或照舊摹拓,收《跋》并刻之于石碑。他為了教學需要,找來《周禮》、《儀禮》、《唐開元禮》、《紹興祀令》等參考,畫出一套儀器和衣服式樣,供生員觀覽,進行形象化直觀教學。其五,親自刻書。如《四書章句集注》。這部朱熹首刻的書籍對豐富圖書版本和藏書建設同樣有著不容忽視的作用。[13]
除此之外,朱熹理學的精義通過文獻得以傳播并滲透到世風人情、族規民約之中,對南宋及后世文化結構產生深遠的影響。如“五教之目”、“為學之序”、“修身之要”、“處事之要”、“接物之要”等內容,既是對此前儒家教育思想的總結,也集中體現了朱熹的教育思想和修身理念,即便在當今社會也仍然不失它的借鑒意義。
5 結語
雖然朱熹的主觀目的是為了從書籍中求得“致治之道”,“教化之本”,維護封建倫理綱常,但其行為在客觀上對豐富我國的歷史文獻寶庫,保存祖國的文化遺產起了非常積極的作用,對當今圖書館在彰顯教育功能、凈化學習風氣方面仍有很好的借鑒意義。總之,作為“一代宗師”,南宋杰出的教育家、思想家、文獻學家,朱熹當之無愧。
[1]馮友蘭.三松堂全集卷十[M].鄭州:河南人民出版社,2000.12.
[2](明)馮繼科修.嘉靖·建陽縣志卷八[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2.
[3]朱 熹.朱文公文集卷七[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
[4]方彥壽.朱熹刻書事跡考[J].福建學刊,1995,(1):75-79.
[5]林振禮.朱 熹:作為編輯出版家的評價[J].河南師范大學學報,2005,(4):179 -182.
[6]朱 熹.晦庵先生朱文公文集[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
[7]陳良武.朱熹漳州刻書的文獻學追求[J]佳木斯大學社會科學學報,2004,(4):93 -95.
[8]朱 熹.朱熹集卷八十二[M].郭 齊,尹 波,點校.成都:四川教育出版社,1996.
[9]朱 熹.朱子大全卷三八[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
[10]方彥壽.朱熹與福建書院文化[J].炎黃縱橫,2006,(4):35-36.
[11]鄧洪波.宋代書院的藏書研究[J].高校圖書館工作,2003,(5):73 -79.
[12]朱 熹.朱文公文集[M].上海:上海商務印書館,縮印明刊本(四部叢刊初編集部)
[13]史 娟.朱熹對書院事業及版本館藏的貢獻[J].大學圖書情報學刊,2007,(8):84 -8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