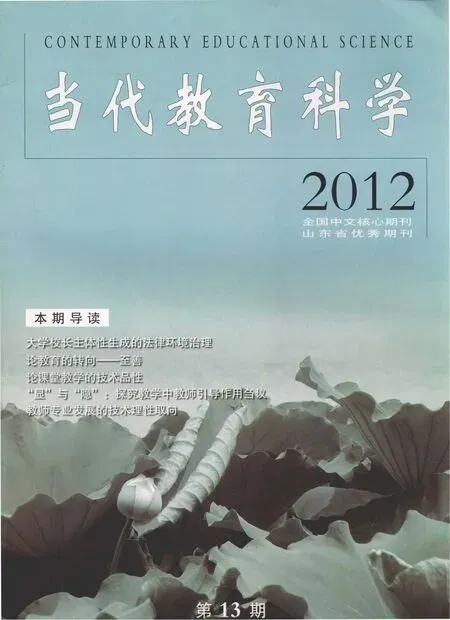教師專業(yè)發(fā)展的技術(shù)理性取向*
● 趙昌木
教師專業(yè)發(fā)展的技術(shù)理性取向*
● 趙昌木
理性是人所共有的,它構(gòu)成科學認識的基礎(chǔ)。然而,如果把理性作為人類活動的唯一根據(jù),使理性工具化,取代價值理性,成為統(tǒng)治理性,就背離人的價值,走向非人性化。教師在專業(yè)發(fā)展目標上,追求科學知識和技術(shù)的占有和應(yīng)用,成為“技術(shù)型”的專家;在教學過程中,崇尚教學設(shè)計的高度精確化和程序化,探尋教學效率的最大化。在組織管理上,處于科層組織最底層的教師是受壓抑的,其批判、否定性思考的內(nèi)心向度被削弱了,逐步形成單向度的教學思想和行為模式,背離人性化的教育生活。
教師;科學知識;技術(shù)理性;教學效率
理性是人所共有的,它構(gòu)成科學認識的基礎(chǔ)。然而,如果把理性作為人類活動的唯一根據(jù),使理性工具化,取代價值理性,成為統(tǒng)治理性,那就背離人的價值,走向非人性化。現(xiàn)時代,把科學的方法論運用到技術(shù)的種種新形式中去,技術(shù)以理性的名義和無形的力量支配著人的思想,教育也成了技術(shù)系統(tǒng)自身的理性化、客觀化和物化活動的附屬物。就教師發(fā)展而言,教學的同一化、專業(yè)化和標準化在教育領(lǐng)域逐步顯現(xiàn)。
一、在發(fā)展目標上,追求科學知識和技術(shù)的占有和運用,成為“技術(shù)型”專家
專業(yè)知識是教師教學的理智基礎(chǔ),是保證教師有效教學最重要的因素,而教師的專業(yè)性也體現(xiàn)在專業(yè)知識與技術(shù)的熟練程度上。基于此,哈格里夫斯(Hargreaves,A.)指出,教師專業(yè)發(fā)展包括知識、技能等技術(shù)性維度[1],而教師的專業(yè)知識在舒爾曼(Shulman,L.S.)看來,至少包括七個方面:[2]學科內(nèi)容知識,一般教學法知識,課程知識,教學法——內(nèi)容知識,學生及其特點的知識,有關(guān)教育宗旨、目的、價值和它們的哲學與歷史背景的知識。這種專業(yè)知識的分類框架,成為教師教育機構(gòu)確立課程體系的理論依據(jù)。教師教育的預設(shè)是:在所有教師的課堂教學中存在著普遍有效的程序、技術(shù)和原理,并能夠在教學實踐中應(yīng)用。不少學者也認為,教師職業(yè)若成為嚴格意義上“專業(yè)”,就需要由基礎(chǔ)科學和應(yīng)用科學作為專業(yè)支撐。而教育學和心理學的科學原理和技術(shù)是把復雜的教育情境與事件抽象、概括成能夠單純地明示的概念與原理,從而能夠跨越不同的教育情境和文化社會領(lǐng)域,在教育實踐中應(yīng)用,使“理論實踐化”。師范院校的教師培養(yǎng)模式就是遵從這種預設(shè)而運作的。這種技術(shù)原理模式強調(diào)的是科學知識的獲得、教學技能及與此相關(guān)的其他行為“能力”的形成,以此來提高其有效性。例如,師范生首先學習學科知識、教育學和心理學的相關(guān)知識,然后通過教育實習和模擬演練逐步掌握教學基本技能。期間,觀察教學行為,分析教學系統(tǒng)中的重要因素,力求掌握普遍應(yīng)用于各學科領(lǐng)域、各年級及其他情境的教學技巧。在職教師的培訓和研修也存在這種取向。在教師們看來,教育實踐是學科知識、教學論、心理學的原理與技術(shù)的合理利用,教師作為運用這些原理與技術(shù)的專業(yè)人員,要不斷學習和掌握與教職相關(guān)領(lǐng)域的科學知識與技術(shù)。例如,教師們最希望獲得的是 “學科思維方法”、“學科發(fā)展史及其趨勢”、“與其它相關(guān)學科的相關(guān)點、性質(zhì)、邏輯關(guān)系”方面的知識,而教師專業(yè)發(fā)展最應(yīng)補充的知識是“教育技術(shù)知識”、“教法知識”和“教育科研知識”。[3]從研究者對教師專業(yè)知識結(jié)構(gòu)的探討以及從事教育實踐的教師的訴求中,我們可以看出,學科知識、教育學和心理學類知識是教師專業(yè)知識的核心內(nèi)容。這些知識能夠經(jīng)得起“概念、判斷、推理”的理性檢驗,屬于公共的理論知識,具有客觀性和普適性,而那些通過教師個體感官或者直覺、領(lǐng)悟獲得的,不是經(jīng)過邏輯推理獲得的隱性知識,屬于非理性的知識,因而得不到認可,且受到質(zhì)疑和批判。
在技術(shù)理性支配下,教師占有科學知識和技術(shù),并在教學實踐中運用,成為“技術(shù)型”專家,這成為許多教師專業(yè)發(fā)展的目標。我國不少地區(qū)的調(diào)查數(shù)據(jù)表明:在教師專業(yè)發(fā)展內(nèi)容方面,教師希望學習的內(nèi)容依次是優(yōu)秀教師教學經(jīng)驗觀摩、學科教學法、多媒體教學技術(shù)和學科新知識;在提高教學水平方面,教師們認為最有效的途徑是校外教學觀摩、教研員的指導、教師培訓。[4]由此可見,教師把教學技巧和學科內(nèi)容知識作為自身專業(yè)發(fā)展的優(yōu)先選擇,同時也反映出技術(shù)統(tǒng)治理性和工具理性在教師專業(yè)發(fā)展中的作用。在教育實踐中,教師追求高超的教學技術(shù)和豐富的學科知識無可厚非,但是,如果他們所掌握的東西只局限在專業(yè)內(nèi)容的知識體系和教學技巧的狹窄領(lǐng)域,就嚴重地降低教師在課程開發(fā)、課堂教學決策、實施等方面的自主性和創(chuàng)造性。如果教師觀摩其他優(yōu)秀教師的課堂教學,而不去反思那些構(gòu)成課堂生活與實踐的原則,不去質(zhì)疑不同教學方法、技巧及教育理論背后的信條,不去審視教學所隱含的特定的世界觀所賦予的價值和假設(shè),就必然是導致自身教學實踐的盲從。技術(shù)理性視閾中的技術(shù)型教師往往以優(yōu)秀教師的觀摩課為樣板而一味模仿,忽略了教學情境的復雜性,忽視了教師自身所處的文化語境和條件,忽視教師自身的教育信念系統(tǒng)是否合理,很少關(guān)注教學技術(shù)或教學技能背后所蘊含的價值,缺乏對教學過程的研究和反思,因而在教學行為上很難呈現(xiàn)出自主性、創(chuàng)造性的特征,也難以成為智慧型教師。
二、在教學過程中,探尋教學設(shè)計的精確化和教學效率的最大化
在技術(shù)高度發(fā)達的現(xiàn)代社會,技術(shù)理性作為社會的中軸理性觀念,以壓倒一切的方式支配著社會文化和意識形態(tài)的各個方面。現(xiàn)存的教育實踐是根據(jù)一種理論假設(shè)來實施技術(shù)操作的。這種假設(shè)認為,所有的學生都根據(jù)相同的教材、相同的課堂教學與相同的評價模式來學習,以有效地培養(yǎng)標準化知識人才。學校作為工廠的隱喻由來已久,且影響深遠。派納(William F.Pinar)曾宣稱,工作在課程領(lǐng)域的人,有85%-95%有一種共同的視角,即要么被主導的技術(shù)合理性所束縛,要么同這種技術(shù)合理性緊密相關(guān)[5]。按照社會需要,學校制定統(tǒng)一的課程標準、統(tǒng)一的教學技術(shù)、統(tǒng)一的教學工藝流程,把受教育者納入學校教育生產(chǎn)過程中,放入教育生產(chǎn)流水線而加工制作,塑造成標準化的教育商品,輸送給社會,迎合大工業(yè)的高效率。在教學過程中,借助系統(tǒng)工程學的技術(shù)控制課堂教與學的過程,追求教學技術(shù)的精確性和教學行為的規(guī)則化,凸顯教學的操作性。譬如,教師在教學各個環(huán)節(jié)的設(shè)計上,追求高度的精確化和程序化,每個環(huán)節(jié)的前后銜接、起承轉(zhuǎn)合都設(shè)計得嚴絲合縫,每個段落用時多少都做到精心計算。把凝聚了教育價值的個人的內(nèi)在經(jīng)驗轉(zhuǎn)換成可觀察的、可量化的均值要素進行客觀、科學地分析和研究。教師過分偏重于理智性的、概念性的知識分析,忽略了學生的不同經(jīng)歷、語言習慣、文化背景與天賦,忽視了學生對現(xiàn)實世界作具體的、直觀的領(lǐng)悟和體驗,從而控制了學生的個性、自由、創(chuàng)造和發(fā)展。例如,在日常教學實踐中,教師強調(diào)“知識的系統(tǒng)邏輯組織”和“各個教學科目的編排”,忽視“學生是否有積極的情感體驗”,[6]把掌握知識本身作為教學的目的,以知識掌握的數(shù)量化和精確化作為評價標準,形成了學生以模仿、操練和背誦為主要特征的學習方式。這樣的教育注重學生的知識結(jié)構(gòu),而不是整體的精神建構(gòu),輕視了學生的意愿、興趣、情感和態(tài)度,踐踏了學生的個性、自由和責任,“這種機械的教育觀使人性支離破碎,或?qū)е路侨诵曰谴龠M其自主性。”[7]
技術(shù)理性追求高效率的教學。教師在學校中講求工作效率,在課堂上講求教學效率,效率高意味著在相同單位時間里實際完成的工作量多,對教師個人而言,意味著節(jié)約了時間。高效率的教學要求教師教學技術(shù)或教學技能嫻熟,以至達到自動化的程度,實現(xiàn)同等的時間內(nèi)教師完成工作成果的最大值。追求教學效率雖無可厚非,但這種高效率教學卻使教師付出了代價。單調(diào)、重復的教學行為不僅消耗了教師的體力,而且支配其大腦甚至靈魂,破壞了教師內(nèi)心深處對自由的追求,降低了教師教學自主權(quán),泯滅了教師的創(chuàng)造性,使教師身心疲憊,導致職業(yè)倦怠。我們不要忘記,教學不僅僅是一種復雜的認知活動,更是一項基于人的成長、快樂與理性需要而追求美的、善的事業(yè)。
三、在組織管理上,處于科層組織最底層的教師走向單向度的教學生活
學校是組織良好的、正式的社會公共機構(gòu),它有明確的架構(gòu)、清晰的科層結(jié)構(gòu)和一套精心制定的規(guī)則,[8]教師專業(yè)發(fā)展依附于這樣的組織機構(gòu),遵從組織機構(gòu)的安排和規(guī)約。教師工作和生活其中的組織機構(gòu)是按照層級形式設(shè)計的。居于教育組織最頂層的是教育政策、規(guī)章制度的制定者,對下級有發(fā)號施令的權(quán)力,而下級則有服從的義務(wù)。這種科層化組織由一些固定不變的抽象規(guī)則體系來控制,這樣的規(guī)范系統(tǒng)是為了保證不管多少人從事某項工作,其結(jié)果都能一致,而且不同的工作之間能夠相互協(xié)調(diào)。教師位于科層組織的底層,也就是說,教師屬于執(zhí)行層,處于教學最前沿。這是一種單向的體系,命令、建議、計劃從上面發(fā)出,指向金字塔的底部,處于底部的教師是執(zhí)行者和操作者。在韋伯(Max Weber)看來,科層制是歷史上技術(shù)發(fā)展最為完善的一種組織形態(tài),其專業(yè)化與客觀化的外表使得整個系統(tǒng)的“可計算性”達到最高程度。處于最底層的教師是受雇用者,其工作與收入被其上級控制,并被監(jiān)督。雖被監(jiān)督,但在一定范圍內(nèi)有自主權(quán)和權(quán)威性。比如,在課堂教學中,教師因為工作的情境太復雜,對學生的各種行為常常需要在現(xiàn)場做出應(yīng)對,這種工作的周全性便提升了教師個體行為的合法性和自主性。但這種自主權(quán)是非常有限的。教師要在法律法規(guī)、規(guī)章制度安排下從事教學活動,設(shè)計行為模式、交往方式,維持教學秩序。教師受過專業(yè)的訓練,作為被聘任者,在自己的工作崗位上必須有效地履行自己的職責。相對于學生來說,教師是課堂教學中的權(quán)威,他需要較高程度的技術(shù)能力,其專業(yè)技能由同行來認定,并受到專業(yè)規(guī)范的制約。
科層化教育體制以精確、迅速、持久、穩(wěn)定、可預計性對教師進行管理,以嚴格服從和專業(yè)化的運作維持教學秩序,以非人格化的規(guī)則和手段控制教學行為,達成整齊劃一的思想和遵從。教師在組織、權(quán)力和職責的規(guī)約下被客體化了,其教學行為的理性化和高效率,職業(yè)活動的重復性,使教師體悟自己僅僅是升學這架巨大機器上的螺絲釘,犧牲了大量時間為升學機器的正常運轉(zhuǎn)而奮力工作。“作為我們整個文化進程的結(jié)果,個人日益被限制于為職能服務(wù),為作用著的自動化和機器服務(wù)。人類失去了支配自身能力的自由,失去了使某種意志形成成為可能,從而表達出自我意志的自由,他所得到的是人類一種新的普遍的奴隸化。”[9]教師在科層組織下教學和生活,是受壓抑的,自由思想和自由言說權(quán)力喪失了,批判、否定性思考的向度被削弱了,逐步形成單向度的生活、單向度的教學思想和行為模式,形成固定的教學態(tài)度和習慣,那些超越了已確立的教學話語和行為領(lǐng)域的觀念、愿望和目標,不是受到排斥就是淪入已確立的話語和行為領(lǐng)域。這就意味著,教師已服從于某種知識和權(quán)力制度,工作中享有的自主性和個人發(fā)展機會,以及參與決策的機會,都在科層制的效率為先的原則下被剝奪了。教師教學藝術(shù)理應(yīng)是個人獨創(chuàng)性的表達,而不是技術(shù)式的復制。如果教師缺少自己的話語空間,缺失自己的表達權(quán)力,就失去了靈魂與心靈的依托,整個生活處于沒有根的“漂浮狀態(tài)”,就必然喪失教學的創(chuàng)造性,背離人性化的教育生活。
[1]Hargreaves,A.(1995).Development and Desire:a Postmodern Perspective[J].In R.Guskey& M.Huberman(E.ds.),Professional Development in Education:New Paradigms and Practices(pp.9-34)[C].New York:Teachers College Press.
[2]Shulman.L.S.(1987).Knowledge and Teaching:Foundations of the New Reform[J].Harvard Educational Review,57.1.p.l.
[3][6]常學勤.山西省普通高中教師專業(yè)發(fā)展現(xiàn)狀調(diào)查報告[J].教育理論與實踐,2006,(7).
[4]參見趙明仁,周鈞,朱旭東.北京市中小學教師參與專業(yè)發(fā)展活動現(xiàn)狀與需求的調(diào)查研究[J].教師教育研究,2009,(1);顧海根,趙必華,鐘文芳.上海市小學教師現(xiàn)狀與專業(yè)發(fā)展需求[J].上海教育科研,2008,(10).
[5]亨利·A.吉魯.教師作為知識分子[M].朱紅文譯,北京:教育科學出版社,2008,6.
[7]H.N.Kliebard,Persistent Curriculum Issues in Historical Perspective.in W.Pinar(ed.)“Curriculum Theorizing”,McCutchan,1975.
[8]Paul Willis.Learning to Labor:How working classKids Get working Class Jobs[M].New York: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1981,P.22.
[9]伽達默爾.贊美理論[M].夏鎮(zhèn)平譯.上海:上海三聯(lián)書店,1988,142-143.
*本文系全國教育科學“十一五”規(guī)劃2009年度教育部重點課題“義務(wù)教育階段教師流動機制研究”(DHA090337)成果之一。
趙昌木/山東師范大學教育學院教授、教育學博士、博士生導師,研究方向為教師教育、課程與教學論
(責任編輯:劉吉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