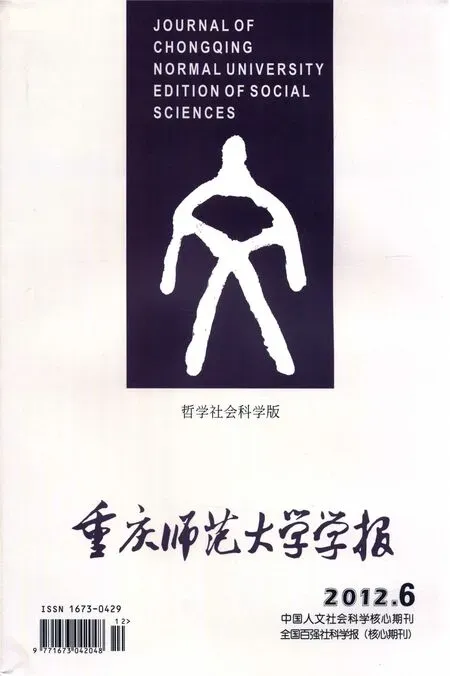清代“湖廣填川”移民帶來的社會和生態沖突及其調控
岳精柱
(重慶湖廣會館 管理處,重慶 400012)
清代“湖廣填川”移民運動,給巴蜀帶來了大量勞動力,促進了巴蜀經濟的恢復,社會的發展。但是大量移民及其后裔的繁育,巴渝人口迅速膨脹,必然引起土客之間,移民族群間的沖突和人地矛盾。同時,過度開荒種地,也造成一系列生態問題。
一、移民與土著的沖突與調節
史載,“陜西入川之人各自耕種,安分營生;湖廣入川之人每與四川人爭訟,所以四川人甚怨湖南人,或將田地開墾至三年后,躲避納糧而又他往者。”[1](4868)
云陽“土著之民,田無券契,自云洪武年間來蜀,挽草為業,謂之‘黑冊’,都不可解。蓋明初廖永忠、湯和所移之民,經闖獻之亂而僅存者也。今縣境扶、徐、向、冉、楊、譚諸族,皆其孑遺,其始頗仇客民,久乃相浹,尋結婚媾。”[2]
合川“往時新歸流戶便即力役,墾田既熟,土著訟而爭之,以故集者復散”[3]。
原籍湖廣的董子能,于康熙初年,“攜家入川,路過廣安,遇同鄉友三十余人悲啼一處。子能就問:爾等先來必得樂土安居矣,何尚倉皇失所如此?眾告:以報墾斯土,已經栽插一年,忽被豪衿何某者霸占,欲將我輩盡行驅逐,因此含冤不伸。”[4]
這是土著欺客的事例,主要是土地之爭。鑒于此,清政府于康熙二十二年左右規定:“凡地土有數年無人耕種完糧者,即系拋荒,以后如已經墾熟,不許原主復問。”[5]《清朝文獻通考》卷2《田賦二》載康熙三十九年“又以四川民少而荒地多,凡流寓愿墾荒居住者,將地畝給以永業”。有的地方官在實際操作中,亦明確規定:土地“凡一插標,即為己業,后亦不得爭論”[6](137)。隨著移民的增多,移民人口超過了土著,逐漸形成了“客強土弱”的現象,這種現象廣泛存在于巴蜀之地。四川巡撫年羹堯在康熙四十九年的一則奏疏中稱:“近年開墾一案……土著與新民年年爭訟。”[7](773)
家譜中,土客沖突記載不乏缺。重慶華巖陳氏,其入川祖陳虞塏于康熙年間,從廣東豪居鄉(平遠縣)大塘坑口,移居重慶巴縣馬王鄉楓木埡,購置沒落官第“駱家石院子”。但駱氏族人不服,遂訴公堂。為幫兒子打官司,陳虞塏之父陳炳文,到巴縣衙門,打贏官司后,父子就在冷水場的沙帽石下購置田地,修陳家老房子。次年將全家接到重慶。[8](103)豐都梁氏煥廷公“家甚貧,年十四……遭失怙,遂廢讀事農。善訓蒙,事母至孝,然處地也孤弱,屢受土豪欺凌,連年構訟不解。始入衙習刑書,留心案牘”[9]。萬縣幸氏,明代自湖廣遷萬縣南岸厚池壩,明末戰亂外逃。待亂平回到厚池壩,“已年有人開厚池壩,孝父引數人回厚池壩開陳家灣,栽種一年遭彼人情不和,顆粒未收,盡屬烏有,復轉大蒲屯種,于甲午年父復來幸家灣起屋開荒,仍遭譚守四之威,又有彼地幫撫之眾同僚為害,兩次不能落業……所有厚池壩之田業盡為譚氏霸占,至丁未年間有向奚蕘恃譚家勢力強來謀占。”[10]
文中反映,除了移民與土著之間頻生沖突外,土著之間,亦是恃強凌弱。既有因土地之爭,亦有為財產而生沖突者。但“川省訟詞,為田土者十居七八”[11]。
在沖突中,一般依官府調節為主。案例中,已有證明。當然,在勢力差距不大情況下,民間更多是采取“結親”方式,用姻親關系化解沖突。
后來移民增加,出現了“客強土弱”現象,再加政府對移民的政策優惠,土客沖突漸“被消失”。如重慶的“八省會館”勢力,完全蓋過土著。土著在重慶市主流社會中的話語權漸被消失,只能進行一些鄉場里鄰事務,無緣參與城市社會事務。乾隆時的巴縣:“各省流寓諸民,原無恒產,不能禁其不逐未營生。若土著糧民,祖宗來耕鑿事務。糜不知尺地寸土罔敢隕失,邑中皆崇崗峻嶺,夾溝之中即沃壤。一遭水旱輒典質田糧,楚、豫、閩、廣之民復以機心圖踞,遂至墮產失業。”[12]
土地爭訟激烈且多,究其原因,正如雍正五年(1927年)戶部一奏折所言:“四川昔日荒蕪田地,漸皆墾辟,從來并未丈勘,止計塊插占管業。又土著與流民各居其半,田土不知傾畝,邊界均屬混淆,此侵彼占,爭訟繁興。應委員按畝清丈,以息爭端,以絕欺隱。”有鑒于此,清政府下令清丈川省田地。雍正五年,于各部司和候補、候選州縣內揀選20人,“令其帶往,會同松茂、建昌、川東、永寧四道……逐處清厘。”到雍正七年,清丈結束。[13](621-681)
土地的清丈,有利于土地界址確認,對減少民間沖突爭訟,有一定積極意義。
除了田地爭端外,由于移民大量進入,還引起了一系列的社會沖突。包括亂占寺院,地方惡霸欺行罷市,族群間的利益爭斗等。
保存于重慶湖廣會館的《圣旨碑》記乾隆五十九年正月初一頒《抄奉總督部堂孫憲折》,其中曰:“朕以瑞得聞各處地方庵觀等院,向來競有一等愚俗痞棍,無恥蠆漢作儒子之行,妄稱名色,詐言前籍施宅為庵,于寺院中搔擾滋端,往來出入肆行無忌。此等愚輩悍不畏法,神人之所同嫉,天人之所不容。”此碑于嘉慶五年刻。一些人趁混亂不知,以其祖上為土著并施其祖宅為庵為借口,肆行寺觀。引來他人、僧侶不滿。
與開縣、城口縣相鄰的四川宣漢縣樊噲等地“時王某充茶商,凡私種私賣者致于傾家,土黃壩以上被毒尤甚”。此為道咸間事,后為當地武生吳世敏上訴,官府鑄鐵碑示民,王某方稍斂。[14]
永川縣九龍場“初名永璧,在黃茅嶺,因生事歧,乾隆十六年兩縣會臨督拆,永移今所。舊有九龍橋,因名。”興隆場“舊茅店數椽,因八角場與青峰場爭路構訟,改移于此,八角廢”。青峰場“創自康熙年間”。[15]永璧場是永川和璧山兩縣相交,但兩縣民發生沖突,由兩縣縣令“會臨督拆”。八角場與青峰場兩地民眾爭路構訟,為永川縣內事。不管這些沖突是縣內部還是縣與縣之爭,都是兩地民眾為了各自利益而爭。在這些民眾中,沒有移民與土著之別。
不管是亂占寺院,還是地方惡霸欺行罷市,族群間的利益沖突,最后都是以官府為斷。說明當時的官僚行政系統還是較為健全的,有效的。清政府處理此類矛盾沖突的政策是積極有效的。
二、移民與原籍地的沖突與調節
康熙五十一年一奏折云:“湖廣民往四川墾地者甚多。伊等去時,將原籍房產悉數變賣,往四川墾地,至滿五年起征之時,復回湖廣,將原賣房產地畝,爭告者甚多。”[16](卷二百五十)這些人,入川墾荒,待滿五年起征時,返回原籍,爭奪當年所變賣田地房產,引起爭訟。
一些移民,原是在原籍犯有罪行或者逃糧避差,趁著大移民浪潮,以移民逃到四川,逃避懲罰。四川巡撫李先復曾奏:“近有楚省寶慶、武崗、沔陽等處人民,或以罪逃或以欠糧,俱比讬名開荒攜家眷入蜀者,不下數十萬。”“臣辦事衙門見湖北撫臣年遐齡揭帖,為盜劫傷命事。沔陽州鄭錫我劫盜鄭價玉案內,續獲盜犯鄭允文,供云逃出就在四川,度了兩年等語。夫允文以盜案重犯逃入四川兩年,則此十萬楚民,豈無鄭允文者乎?”
重慶吳氏,其始祖因“田稅年年巨增難完,只得棄楚入蜀”。于康熙四十二年(1703年),自湖南寶慶府邵陽,入重慶江北。[17](13)
針對于此,清朝廷于康熙五十一年(1712年)規定:“嗣后湖廣民人,有往川蜀種地者,該撫將往種地民人年貌、姓名、籍貫查明在冊,移送四川巡撫,令其查明。其自四川復回湖廣者,四川巡撫亦照此造冊,移送湖廣巡撫,兩相照應查驗,則民人不得任意往返,而事亦得清厘,爭論可以止息。”“如因罪私逃如鄭允文之類,及欠糧避差不法者,亦令楚省州縣開明犯罪事由,何事逃出,或只身或妻子兄弟幾名口,轉咨川撫,即行逐一清查,遣送回籍,仍照原案歸結,庶奸民不致漏網而蜀省殘黎永享無事之福矣。”[18](卷二百五十)
大量民眾的移出,在初期,可以減緩移出地的人口壓力,緩解當地人的矛盾,同時減少無業游民,對地方治安也是有利的。但是,大量民眾的移出,勢必會給當地造成一些問題,特別是當地的皇糧國稅的完繳。于是移出地的地方官勢必會采取措施,勸導甚至阻止民眾移民,造成官府與移民之間的沖突。雍正年間的廣東龍川移民的《往川告帖》,就非常清楚地反映了這種現象。因民眾移出太多,廣東地方官在交通要道設卡勸阻移民,甚至遠到江西、湖南、福建等省要道設卡勸阻。[18]
雖地方政府有阻攔消極一面,但中央仍堅持有限制的移民政策。此類政策,是積極有效的。
三、過度開發引起的生態沖突與調節
移民及其后裔的大量增加,引起嚴重的人地矛盾,朝廷遂隨之鼓勵百姓墾辟田邊地角,向山地進發,于是,大批窮民,紛紛“襁負而至,佃山結屋,墾土開荒”[19]。
大量移民涌入山地,邊徼之地,山地得以開墾,而隨之而來的是生態遭到破壞,引起水土流失,環境惡化。巫山縣城之所依的陽臺山,歷年墾辟,水土流失嚴重,至縣城“每因驟雨遂至,水石并行,填街塞巷,有時城門不可啟閉”[20]。乾隆時的酉陽州移民“墾荒丘、刊深箐,附山依合,結茅廬,堅板屋”[21]。同治時的萬縣“虎豹熊羆無常產,縣境四面皆山,在昔荒蕪,尚或藏納,今則開墾幾盡土沃民稠,唯見煙蓑雨笠,牛羊寢訛而已”[22](卷三)。洪良品《東歸錄》記同治時巴縣木洞驛“蓋山舊多豺,今則人煙茂密,豺無有矣。”同治時萬縣“凡深山逃莽,峻凌層巖,但有微土者,悉皆樹藝”[22](卷六)。光緒時墊江“近日山農墾荒,砂石崩塌,積壅上流,每遇暴雨,動突溝洫填塞,交于平田,故水潦之患多于旱年”[23]。道光時綦江“現在人稠地少”[24]。道光時重慶府“渝郡土宇則由狹而廣,開辟盡也;人民則由寡而眾,滋生繁也;土著則由富而貧,習于奢也;物產則由饒而減,竭其力也”[25]。乾隆中后期石柱“民間用鐵,大山坪舊有數十廠。今以近廠木盡,次閉”[26]。因無木材提供,導致鐵廠關閉。乾隆十二年,巴縣碳戶“無碳供局,被局逼勒,只得著周文發前往涪州等處買炭供局。奈無炭買,(周)文法、(周)界法自縊涪州。”乾隆二十六年巴縣“今因附近地方無柴燒炭,炭價愈昂,七門炭鋪收關四處,蟻等只得前往相連黔省地方,并酉陽州等處地方買樹燒炭”[27](260)。因附近無柴燒炭,被官府逼迫供炭,跑到涪州都無法買到炭,情急之下,兩人自殺,可想當時森林遭破壞之嚴重,此還是在乾隆十二年。至乾隆二十六年時,就只有遠到貴州或酉陽等地“買樹燒炭”了。故史載:“自平定(平吳三桂亂——筆者注)以來,人民漸增,開墾無遺,山谷崎嶇之地,已無棄土。”[28](5025)
無論是清朝中央政府還是地方政府,面對一系列的生態沖突,皆沒有什么積極行為。我們很難在所存歷史資料中找到清朝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的應對之策,任生態災難繼續惡化。因此,又造成更加嚴重的生態惡化。面對生態沖突,清政府是無作為的。
四、人地沖突及其對策
由于人口增加,人地矛盾越來越突出,家譜中多有反映。
江津官氏,其祖于康熙四十九年自福建漳州龍巖入川江津杜里二都八甲,地名方十字老虎沱,后將家人全接來,“是時人丁方十七口而已。厥后,彩公承理家務,基業頗盛,人口漸繁,一會兒八十余人。”“四十二年間,不覺三大房人口廣生,長房八十余人,二房四十余人,三房二十余人,約其數一百余人也”。[29](4)在四十多年間,從一家幾口增至140多人的大家庭,在嘉慶戊戌冬,始分家各爨。渝北鄢氏始祖鄢應現,隨其叔、伯、哥一起于康熙九年自湖北麻城入合川,“插占為業”又于康熙四十八年,攜妻子和孫等12人,復遷渝北石船鎮。[30](1)三十多年間,從1-2人繁衍為12人。敬氏,康熙五十三年,其羅氏祖婆率四子,自湖南寶慶入川梁山(今梁平),后因“人口浩繁,土地褊狹,若不遠圖,終難支持”,于乾隆十一年,復遷東鄉(今四川宣漢)。[31]
方志中,亦有記載:道光時期的大足“昔時富足,今則窮荒,各處山村僅謀生計”[32]。人口的增長,引起人均耕地的急劇減少。雍正六年,嘗能“以一夫一子為一戶,給水田三十畝或旱地五十畝”[33](卷六十七),但以后逐漸減少。王笛按冊載耕地和人口數計算出了四川人均耕地面積數:乾隆十八年(1753年)人均耕地達33.56畝,乾隆三十八年(1773年)降為14.99畝,20年時間,人均減少18畝多。到嘉慶十七年(1812年)又急降為2.27畝,咸豐元年(1851年)降為1.04畝,到同治十二年(1873年)為0.79畝,已不足1畝。在100年后的人均耕地面積數,僅及前的23.54%。[34](62)
乾隆十八年,人均耕地達33畝,嘉慶十七年,急劇降為2畝多。當然,因清政府規定有“上田、中田丈量不足五分,下田與上地,中地不足一畝,以及山頭地角,間石雜砂之瘠地,不論頃畝,悉聽開墾,均免升科”的規定,[35](2-3)其人均耕地數,肯定沒有后期這么低。但不管怎么說,人均耕地在迅速減少。巴渝亦不例外。據胡道修研究,嘉慶初期重慶府人均耕地5畝左右,而到開埠前(1890年,中英《煙臺條約續增專條》規定開放重慶)已下降到不足3畝。[36](236)羅爾剛先生曾計算確定“溫飽常數”指標,根據巴蜀當時的農業生產力水平,人均4畝地才能維持一個人的最低生活水平。[34](62)可見,當時的巴蜀人地矛盾沖突非常突出。人多地少,地價相應漲了起來。康熙五十二年一上諭就說:“先年人少田多,一畝之田,其值銀不過數錢,今因人多價貴,一畝之值,竟至數兩不等。”同時又說:“今歲不特田禾大收,即芝麻,棉花皆得收獲,如此豐年而米粟尚貴,皆由人多田少故耳。”[1](4868)人多田少地價貴,米糧價也上揚了。同治十三年,吳濤到川任職,在其《游蜀日記》中記:“蓋川中自古講求水利,加以農勤、土沃,故往日川東之米嘗轉售于他省,然齒繁歲歉,今亦非古所云矣。”[37](7517)到清中葉后,巴蜀不再是輸出稻米之省了。
針對巴蜀越來越嚴重的人地矛盾,清政府采取了一定的措施。雍正七年(1729年),雍正帝諭戶部:“國家承平日久,戶口日繁,凡屬閑曠未耕之地,皆宜及時開墾,以裕萬民之計。”[33](卷八十)乾隆五年(1740年)“命開墾閑曠土地”,“民間多辟尺寸之地,即多收升斗之儲”[38]。又規定“四川所屬,地處邊徼,山多田少,田賦向分上、中、下三等,按則征糧,如上田、中田丈量不足五分,下田與上地,中地不足一畝,以及山頭地角,間石雜砂之瘠地,不論頃畝,悉聽開墾,均免升科。”[35](2-3)道光十二年(1832年),清政府再次規定:“凡內地及邊省零星地土,聽民開墾,永免升科。其免科地數……四川,上田、中田以不及五分,下田、上地、中地以不及一畝為斷……四川下地……俱不論頃畝,概免升科。”[35](16-17)
朝廷鼓勵百姓墾辟田邊地角,向山地進發,激發了墾民們的積極性。這一對策,雖暫時解決了眼前的人地矛盾,卻造成了更為嚴重的生態災難。其政策是消極的。隨著人口的不斷增加,到嘉慶時期,巴蜀人地矛盾逐漸加重。于是,出現了白蓮教活動,造成巴蜀社會動蕩。
面對以上系列沖突,清政府在處理移民與土著,移民與原籍地的沖突中,政策是積極有效的。面對人地矛盾,其政策是消極的,暫時的。針對生態沖突,清政府是無所作為,任其惡化。也正是清政府在人地矛盾的消極政策,使得巴蜀人地矛盾愈來愈嚴重。在生態沖突中的無作為,使得土地墑情愈來愈差,民眾生活愈來愈艱難。結果很快造成了巴蜀社會的動蕩。
[1]張廷玉等.清朝文獻通考(卷二)田賦二[Z].商務印書館民國二十五年發行.
[2]朱世鏞等.云陽縣志(卷十三)禮俗中[Z].民國十八年.
[3]鄭賢書等.合川縣志(卷三十八)名宦[Z].民國十一年.
[4]花映均等:《隆昌縣志》卷36《董子能傳》,咸豐十一年.
[5]轉引自田光煒.“湖廣填四川”的移民過程[J].四川師院學報,1981,(2).
[6]蔡方炳,諸匡鼎.于清端公(于成龍)政書(卷一)規劃銅梁條例[Z].沈云龍主編.近代中國史料叢刊讀編(第三十二輯)[Z].中華民國六十七年印行.
[7]中國第一歷史檔案館.康熙朝漢文硃批奏折總編(第二冊)[Z].檔案出版社,1986.
[8]陳協明.(重慶華巖)《陳氏家譜》轉老譜,2003年修.
[9]梁治岐等.梁氏族譜·煥廷公墓志[Z].民國三十二年修.
[10]《幸氏族譜》卷首,清道光十年修.
[11]柯劭忞等.清史稿(卷二百九十四《憲德傳》)[Z].中華書局,1977.
[12]王爾鑒.巴縣志(卷十《風俗》)[Z].清乾隆二十五年.
[13]陳嘉謨等.大清會典則例(卷三十五《田賦二》)[Z].清乾隆十二年修,文淵閣四庫全書本,臺灣商務印書館,1983.
[14]汪承烈等.宣漢縣志(卷十三《人物》)[Z].民國二十年石印本.
[15]許曾英等.永川縣志(卷三《場鎮》)[Z].光緒二十年刻本.
[16]清圣祖實錄(卷二百五十)[Z].中華書局,1968.
[17]吳心輝.吳氏宗譜續編(轉老譜)[Z].2001年修.
[18]《宮中檔雍正朝奏折》,第22輯,雍正十一年九月初九日楊永斌折。
[19]賀長齡,魏源.清經世文編(卷七十六)[Z].中華書局,1992.
[20]連山白等.巫山縣志·形勢說[Z].清光緒十九年.
[21]劭陸.酉陽州志·風俗[Z].乾隆四十年.
[22]王玉鯨等.萬縣志[Z].清同治五年.
[23]謝必鏗等.墊江縣志(卷五《風俗》)[Z].清光緒二十六年.
[24]宋灝等.綦江縣志(卷十《物產》)[Z]清道光五年.
[25]有慶,王夢庚.重慶府志·風俗[Z].清道光二十三年刻本.
[26]王縈緒.石柱廳志·物產志[Z].清乾隆四十年.
[27]四川大學歷史系,四川省檔案館.乾嘉道巴縣檔案匯編[Z].四川大學出版社,1989.
[28]劉錦藻.清朝續文獻通考(卷十九《戶口》)[Z].商務印書館,1937.
[29]官玉倫等.官氏家譜(轉老譜)[Z].1996.
[30]鄢守愚等.鄢氏族譜[Z].2005年修.
[31]敬六義等.敬氏族譜(轉咸豐譜敘)[Z].清光緒乙酉年修.
[32]郭鴻厚等.大足縣志(卷三《風俗》)[Z].民國三十四年.
[33]清世宗實錄[Z].中華書局,1968年.
[34]陳鋒主編.明清以來長江流域社會發展史論[C].武漢大學出版社,2006.
[35]昆岡,李鴻章等.大清會典事例(卷一百六十四)[Z].光緒二十五年,商務印書館發行.
[36]周勇主編.重慶通史[M].重慶出版社,2002.
[37](清)吳濤.游蜀日記[A].載劉家平,周繼鳴主編.古籍珍本游記叢刊(第十四冊)[Z].線裝書局,2003.
[38]清高宗實錄(卷一百二十三)[Z].中華書局,196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