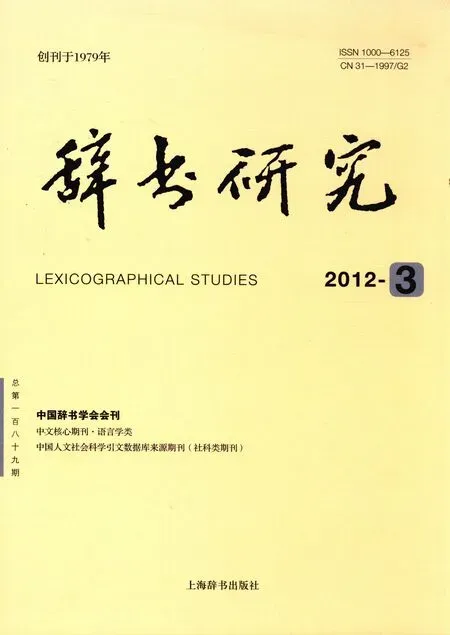辭書的文化價值
徐慶凱
2011年10月中共十七屆六中全會提出了推動社會主義文化大發展大繁榮、建設社會主義文化強國的長期戰略目標。這對我們辭書工作者來說,是巨大的鼓舞、有力的鞭策。在我國,合格的辭書,既是社會主義文化的組成部分,又是發展社會主義文化的重要工具。所以,根據六中全會的要求,我們應該有更強的自覺性和責任心,編纂更多更好至少是合格的、最好是優秀的辭書,來回報國家和人民對我們的期望。為此,我想就辭書的文化價值問題講一些粗淺的認識,與辭書界的同仁交流。
本文討論辭書的文化價值,是就辭書的總體而言的。就辭書的個體而言,其文化價值的高低差別極大,不能一概而論。我國現代的標志性辭書,如《中國大百科全書》、《辭源》、《辭海》、《漢語大詞典》、《漢語大字典》、《現代漢語詞典》、《新華字典》等,文化價值很高。還有一批獲得國家級圖書獎的辭書,以及雖未獲獎但質量優良的辭書,文化價值也很高。但是另有許多平庸的、粗糙的辭書,文化價值就不高甚至很低了。尤其是從20世紀末開始泛濫起來的偽劣辭書,非但沒有絲毫文化價值,而且恰恰是敗壞文化的精神垃圾。因此,對辭書個體的文化價值要區別對象做具體分析,而對辭書總體的文化價值,則主要是就其中較好的辭書而言的。
從總體上說,辭書的文化價值可以概括為以下六個方面。
一、反映社會的文化水平 顯示國家的文化實力
早在1915年《辭源》出版時,其主編陸爾奎就在開頭的《辭源說略》中指出:“一國之辭書,常與其文化相比例。”又說:“國無辭書,無文化之可言也。”1917年蔡元培為《植物學大辭典》所寫的序中也說:“一社會學術之消長,觀其各種辭典之有無與多寡而知之。”可見,在將近一百年前,學界的有識之士就已經對辭書的文化價值做出了精辟的評論。當代學者也有類似的論斷。如歷史地理學家譚其驤(1979)從辭書的質量著眼,指出:“工具書的質量,是一國文化水平和科學研究成就最明顯的體現。”這話說得十分中肯。看辭書的文化價值,不但要著眼于數量,更要著眼于質量。辭書出得既多又好,它的文化價值才大。不妨設想一下,如果沒有《中國大百科全書》,如果沒有《辭源》和《辭海》,如果沒有《漢語大詞典》和《漢語大字典》,如果沒有其他許多高質量的辭書,我國的文化形象將會如何?不是說現有的文化水平和文化實力將不存在,而是說它們將無法集中地展現出來,將難以像現在這樣比較充分地發揮其作用。所以,編纂優質辭書,是國家的重點文化工程之一。辭書工作者有責任、有義務把這項工程建設好。
二、薈萃本國文化精華 積累人類精神財富
與發表見解、論證觀點、討論問題、抒發感情的普通著作不同,每一部辭書應有的任務,都是按照其本身的性質和規模,在自己涉及的知識領域內,把古往今來已有的認識成果加以收集、分析、研究、考核、比較、篩選,去偽存真,去粗取精,然后以條目這種濃縮的形式,用簡明扼要的語言加以提煉、概括,從而把寶貴的精神財富保存下來,積累起來,傳播開來。嚴肅認真的辭書編纂者為此付出的長期的、艱巨的勞動,就凝結成為一部部優質辭書。有一位學者曾形象地說:“辭書工作者的神圣職責,就是在茫茫學海之中,采擷那知識的珍珠,用辛勤的雙手穿針引線,把粒粒珍珠聯綴起來,便于人們‘應手而得’,從而讓那珠鑲玉嵌的科學皇冠放射出更加燦爛的異彩!”(潘樹廣1980)優質辭書是名副其實的知識寶庫,把精神財富分門別類、排列有序地集中到一起,既便于讀者學習運用,又利于把它們留傳給子孫后代。
隨著辭書事業的發展,辭書涉及文化的廣度和深度不斷得以強化。有博大的,有專精的;有歷時的,有共時的;有本國的,有世界的;有無所不包的,也有只涉及某一類詞語、某一個劇種、某一部名著的;等等。在文化的承前啟后、繼往開來方面,辭書正在發揮越來越大的作用。
三、傳播文化知識 滿足讀者的文化需求
知識的傳播非常重要。知識只有經過傳播,為廣大人民群眾所掌握,才能成為強大的力量。在這方面,辭書較之報紙、期刊、知識性圖書具有獨特的優勢。一是針對性。辭書針對人們在學習、工作、生活中遇到的“攔路虎”,給予解惑釋疑,提供必要的信息。如果有合適的辭書,大體上可以讓問題迎刃而解。二是便查性。要到報刊和一般圖書中去查找一個問題的答案,往往難于下手,而如果有對路的辭書,查起來就很方便。一個人經常要用的辭書有限,只要把它們放在身邊,就會有得心應手之感。所以前面所說的那些標志性辭書,特別是適用面廣、一般讀者買得起的辭書,發行量很大,遠遠超過一般出版物。如《新華字典》已發行四億余冊,《現代漢語詞典》已發行四千余萬冊,即使是定價較高的《辭海》,新中國成立后也已發行六百余萬部(不包括分冊)。有一位《辭海》的讀者在1980年買了《辭海》第三版縮印本后撰文說:“我家開始有了一位永遠的全天候的老師,在學習工作中遇到什么問題,就隨時請教這位老師。我有時夜間失眠,胡思亂想,想到一些不懂的問題,也會深夜披衣而起,查閱《辭海》,請教老師。直至弄懂了問題,才會安然入睡。休息日有時閑來無事,我就信手打開《辭海》,一頁一頁地翻閱,對自己感興趣的條目認真閱讀。……我從中采擷了更多的知識來豐富和武裝自己,同時獲得了無窮的樂趣。在我的那么多書中,查閱最多、使用頻率最高的就是《辭海》。……現在,《辭海》成了全家的共同的財富,不僅我和妻子常常翻閱,女兒女婿也常常翻 閱。有時鄰居也來查閱資料。一天晚上,正在讀初三的小外孫女,從《辭海》上剛摘完‘杜甫’的條目,電話鈴驟響,原來是她的同學向她問杜甫生平的。小外孫女就在電話里一字一句地告訴對方。”(沈方德2003)像他這樣從優質辭書中獲益的讀者,何止億萬!
一大批好辭書普遍地、經常地為廣大讀者服務,向他們傳播文化知識,滿足他們的文化需求,這對民族、對國家的意義和影響是無論怎么估計都不為過的。
四、奉獻文化成果 推動文化發展
優質辭書都是科學研究的結晶,光靠現成的資料抄抄摘摘、拼拼湊湊是編不出來的。學術性的大型辭書如此,普及性的中小型辭書也如此,只是程度有所不同而已。試舉一例。《現代漢語詞典》中有一個字——“匼”。這個字的讀音,在古今辭書中,除遼代的《龍龕手鑒》注為“苦合反”(今當讀kē)外,從《康熙字典》到《國語詞典》,都注為“鄔感反”(今當讀ǎn)。《現代漢語詞典》的后期主編丁聲樹查證了古代史部、集部和小學類書籍中的大量反切和疊韻聯語的異文,尤其是調查了現在山西地名匼河鎮在晉南方言中的實際讀音,最后確定注kē。他還為此寫了一篇文章《說“匼”字音》。這篇文章被認為是貫穿古今、旁征博引、短小精悍的杰作,呂叔湘對它極為贊賞。一部辭書中,諸如此類需要研究解決的問題太多了,其中還包括更復雜、更棘手的問題。不進行認真刻苦的研究,行嗎?這樣編出來的辭書,難道不是寶貴的文化成果嗎?
這些寶貴的文化成果,當然會推動文化的發展。標志性的辭書對文化發展的巨大推動作用不言而喻,其他優質辭書對文化發展的推動作用也可想而知。2010年人民文學出版社出版了歷時二十五年編纂完成的《魯迅大辭典》,收詞九千八百余條,共三百余萬字,具有開創性的意義,也填補了辭書史、出版史上的一個空白。一位學者認為,因認真撰寫,慎于把關,錯誤與硬傷在《魯迅大辭典》中極少,有較高的學術水平、可信度和實用價值。另一位學者認為,由于編纂者的嚴謹與打磨,在魯迅研究界恐怕拿不出比這部《魯迅大辭典》更好的出版物。還有一位學者認為,此書將成為研究魯迅的入門向導。魯迅研究日漸成為一門顯學,史料在魯迅研究中非常重要,《魯迅大辭典》的出版,對于學術發展將起到重要作用。(舒晉瑜2010)
五、推廣語言文字規范化 強化語言文字作為文化主要載體的功能
語言文字是文化的主要載體,而語言文字的規范化,則是這一載體更好地發揮其功能的必要條件。因此,我國政府歷來重視語言文字規范化,已經發布了《簡化字總表》、《現代漢語通用字表》、《第一批異體字整理表》、《標點符號用法》、《漢語拼音方案》、《普通話異讀詞審音表》、《漢語拼音正詞法基本規則》、《第一批異形詞整理表》等規范性文件,以后還將補充、修訂。這些文件需要通過各種渠道貫徹落實,才能逐步實現語言文字規范化。辭書(在此主要指規范型字典、詞典)就是其中一個主要的渠道。何以見得?理由有四:
第一,正如有的學者所說:“各種語文規范標準都是一個個法規(引者按:‘法規’的稱呼不夠確切),廣大語言文字的使用者一般情況下并不理會它們的存在。借助詞典這個重要載體,語文規范標準成為看得見、摸得著、可以感受到的東西,才能在億萬群眾的語文實踐中發揮規范和引導作用。”(晁繼周2005:282)
第二,字典、詞典以字條、詞條為單元,把各種規范性文件的信息體現到一個個條目中,查檢比較便捷。如“劍”字條,查《現代漢語詞典》,可在字頭后的括注中查到其繁體字為“劍”,異體字為“劒”,并查到其讀音為jiàn。該詞典還將多音字分立字頭,如“發”字有fā和fà兩音,前者括注其繁體字為“發”,后者括注其繁體字為“髮”;以兩者開頭的多字條目,則分立在兩個字頭之下,如以前者開頭的有“發榜”、“發表”、“發車”、“發達”等,以后者開頭的有“發菜”、“發廊”、“發式”、“發指”等。
第三,字典、詞典會對規范性文件提供的信息附加必要的補充。如《第一批異體字整理表》中有“彩[綵]”,表明“彩”是規范字,“綵”是異體字。但“彩”字有多個含義,并非所有含義的“彩”都與“綵”構成規范字與異體字的關系。因此,《現代漢語詞典》在“綵”的左上角加序碼?,表明“綵”字只有表示“彩色的絲綢”(“彩”字第二義項)時才是“彩”字的異體字。
第四,對某些規范性文件中極少數不夠妥善的規定,有些字典、詞典的編纂者經過認真細致的調查研究,做了變通處理,使之合乎語言文字使用的實際。如1955年發布的《第一批異體字整理表》把“澹”作為“淡”的異體字給淘汰了,但是《現代漢語詞典》的編纂者研究后認為不宜淘汰,故在其后出版的詞典中仍立為字頭。1988年發布的《現代漢語通用字表》確定“澹”為規范字,可見當初《現代漢語詞典》未將其作為異體字處理是正確的。
六、促進各國文化交流 提高世界文化水平
鄔書林(2011)說:“任何一個國家,代表出版最高水準,拿出來跟世界交流的,是百科全書、綜合性辭典。”我們既要把本國的優質辭書推向世界,介紹本國的文化成果,也要把外國的優質辭書翻譯引進,以便于吸收外國的文化。在這方面,一個典型事例是《不列顛百科全書》的中譯本。《不列顛百科全書》是一部歷史悠久、聲譽卓著的辭書,初版于18世紀中葉,其后不斷增訂,到19世紀中葉已出第八版。隨后即有一些條目被譯為中文出版。1974年,版權已歸美國的《不列顛百科全書》第十五版問世。從1979年開始,中國大百科全書出版社與不列顛百科全書公司商討中美合作出版《不列顛百科全書》中譯本(即《簡明不列顛百科全書》)事宜,至1986年止出齊十卷。鄧小平三次接見中美雙方有關負責人,稱贊出版此書“是很好的一件事情”,“這部百科全書是非常有用的”。截至1997年,《簡明不列顛百科全書》在海內外共發行十七萬套。20世紀90年代,中國大百科全書出版社根據《不列顛百科全書》最新英文版大幅度修訂增補《簡明不列顛百科全書》,出版《不列顛百科全書國際中文版》,文字增加近一倍,圖片增加兩倍。在中文版中,有幾千個有關中國的條目是中國人自己編寫的。
在各國文化交流中,雙語詞典、多語詞典的作用是無可替代的。沒有這種工具,交流將難以進行。我國出版了許多這類詞典,如《英漢大詞典》、《大俄漢詞典》等等,我國學者還與外國學者合作編纂雙語詞典并在國外出版。據2010年5月12日《解放日報》報道,由中法學者歷經半個多世紀編纂的《利氏漢法詞典》(“利氏”指中西文化交流的先輩利瑪竇)于2001年在巴黎出版。該詞典收錄1.35萬個漢字,30萬個詞組,包羅中華文化的各個領域,是世界上最大的中外語言詞典。
結 語
辭書的文化價值不是靜態的,而是動態的。辭書工作者做得好,辭書的文化價值就會上升;做得不好,辭書的文化價值就會下降。我們的義務是不斷地提升辭書的文化價值,防止或制止辭書文化價值的下降。為此,就要擴展辭書涉及的領域,開拓辭書的新品種,發掘切合讀者需要的新選題,使用辭書的非紙質新載體,而特別重要的則是提升辭書的質量。一切圖書都要講究質量,辭書被視為標準書,被寄予高度的信任,尤其要講究質量。我們編纂的辭書,應該無愧于時代,無愧于國家,無愧于人民。無論如何,在質量問題上,我們應該做到問心無愧。辭書的質量是辭書的生命,是辭書文化價值的根源。辭書質量的高低,是決定辭書文化價值大小的關鍵性因素。以此為主要抓手,我們的工作將能更上一層樓。
1.晁繼周.語文詞典論集.北京:商務印書館,2005.
2.潘樹廣.《針線》《串珠》與辭書.辭書研究,1980(4).
3.沈方德.永遠的老師.∥李偉國等編.我與辭海.上海:上海辭書出版社,2003:71-72.
4.舒晉瑜.《魯迅大辭典》獲專家學者好評.中華讀書報,2010-03-24.
5.譚其驤.突破框框 加快步伐.辭書研究,1979(1).
6.鄔書林.提高辭書出版水平 建設辭書出版強國.辭書研究,2011(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