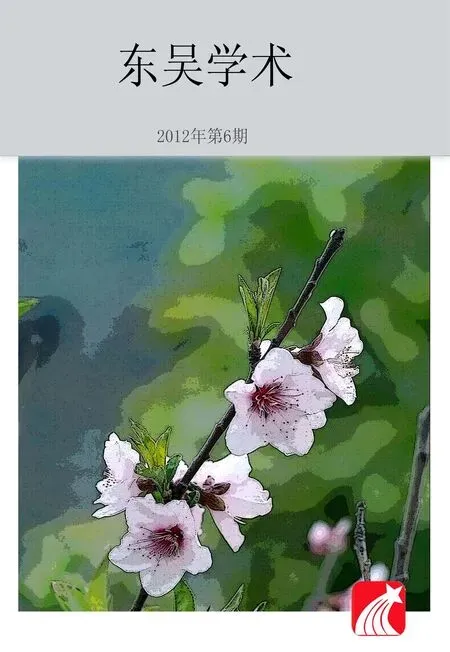雅俗的對(duì)峙:新文學(xué)與鴛鴦蝴蝶派的三次歷史斗爭(zhēng)
余夏云
魏紹昌說(shuō),鴛鴦蝴蝶派(以下簡(jiǎn)稱(chēng)“鴛蝴”或“鴛蝴派”)和新文學(xué)是“井水不犯河水”的關(guān)系,它們?cè)陂L(zhǎng)達(dá)四十年的歷程中,“和平共處,互不侵犯”。①魏紹昌:《我看鴛鴦蝴蝶派》,第47頁(yè),香港:中華書(shū)局,1990。其實(shí),歷史遠(yuǎn)比這個(gè)判斷復(fù)雜。我們知道,五四之后,它們之間就有過(guò)多次論爭(zhēng),而且往往是新文學(xué)主動(dòng)出擊,批判舊文學(xué),指摘它的是非。鴛蝴派倒是抱著不予理睬的態(tài)度,依然故我地寫(xiě)它的美麗文章。雖然偶有回應(yīng),那也不過(guò)是寥寥數(shù)語(yǔ),聊備一格。以后見(jiàn)之明的眼光來(lái)看,所謂的雅俗之辯,不過(guò)是美學(xué)上的不同選擇,但在新文學(xué)人士看來(lái)卻并非如此,他們以為這中間有著性質(zhì)上的根本差異:前者為新,后者為舊。而他們要做這樣的評(píng)判,恰恰就是為斗爭(zhēng)策略的需要。舊文學(xué)是壞的、死的、僵硬的文學(xué),所以五四起事,就要統(tǒng)統(tǒng)革命。為此,不同美學(xué)取向的文學(xué)斗爭(zhēng)也就由此拉開(kāi)序幕。這里我依據(jù)范伯群在八十年代所劃定的三個(gè)歷史階段,①范伯群:《禮拜六的蝴蝶夢(mèng)·論鴛鴦蝴蝶派》,第11-29頁(yè),北京:人民文學(xué)出版社,1989。補(bǔ)充、酌選了一些較為重要的論爭(zhēng)材料來(lái)做歷史的回顧,意圖還原現(xiàn)代文學(xué)場(chǎng)域內(nèi)的真實(shí)占位格局,以便我們更好地理解今人所謂的“雅俗高卑定位”是如何逐步生成,并固結(jié)的。
一
首先值得關(guān)注的是文學(xué)革命時(shí)期,這主要是指二十世紀(jì)的最初二十年,它包括了文學(xué)革命的醞釀、發(fā)生以及持續(xù)高潮。在這段時(shí)期內(nèi),許多五四的前驅(qū)先行參與了論爭(zhēng),而那時(shí)(一九一九年之前)鴛蝴派的名稱(chēng)并未真正出現(xiàn),但它已經(jīng)獨(dú)步文壇,所以批判也總是含糊地采用“當(dāng)今文壇”如何如何的措辭,這一做法一直延續(xù)到一九一九年錢(qián)玄同發(fā)明鴛鴦蝴蝶派這個(gè)概念為止。
一九一四年程公達(dá)在《學(xué)生雜志》第一卷第六期上撰文《論艷情小說(shuō)》,對(duì)當(dāng)時(shí)風(fēng)行的鴛蝴言情小說(shuō)予以指責(zé)。他說(shuō):“近來(lái)中國(guó)之文士,多從事于艷情小說(shuō),加意描寫(xiě),盡相窮形,以放蕩為風(fēng)流,以佻達(dá)為名士。”“纖巧之語(yǔ)、淫穢之詞,雖錦章耀目,華文悅耳,有蔑禮儀傷廉恥而已。”在程看來(lái),鴛蝴小說(shuō)“敗壞風(fēng)俗”,無(wú)功于世道人心,對(duì)讀者尤其是青年讀者是一種毒害。②陳平原、夏曉虹編:《二十世紀(jì)中國(guó)小說(shuō)理論資料》,第 480、511 頁(yè),北京:北京大學(xué)出版社,1989。
隨后一年,梁?jiǎn)⒊苍凇吨腥A小說(shuō)界》上發(fā)文《告小說(shuō)家》一篇,表達(dá)了他對(duì)以鴛蝴為主潮的小說(shuō)界的不滿和失望,以為整個(gè)文壇令人慘不忍睹,作品遺禍青年:
其什九則誨盜與誨淫而已,或則尖酸輕薄毫無(wú)取義之游戲文也,于以煽誘舉國(guó)青年子弟,使其桀黯者濡染于險(xiǎn)诐鉤距作奸犯科,而摹擬某種偵探小說(shuō)中之節(jié)目。其柔靡者浸淫于目成魂與窬墻鉆穴,而自比于某種艷情小說(shuō)之主人公。于是其思想習(xí)于污賤齷齪,其行誼習(xí)于邪曲放蕩,其言論習(xí)于詭隨尖刻。③陳平原、夏曉虹編:《二十世紀(jì)中國(guó)小說(shuō)理論資料》,第 480、511 頁(yè),北京:北京大學(xué)出版社,1989。
追隨梁?jiǎn)⒊痪乓涣昀畲筢摚ㄊ爻#┰凇丁闯跨姟抵姑芬晃闹刑岢觯航鞣轿乃嚱缫孕挛乃噥?lái)改造國(guó)民精神,促進(jìn)社會(huì)進(jìn)步,而“以視吾之文壇,墮落于男女獸欲之鬼窟,而罔克自拔,柔靡艷麗,驅(qū)青年于婦人醇酒之中者,蓋有人禽之殊,天淵之別矣。”他以青年德意志的文明光彩來(lái)比照中國(guó)文壇的現(xiàn)實(shí)黑暗,認(rèn)為鴛蝴小說(shuō)與新民的國(guó)家理想完全背道而馳。④范伯群、芮和師等編:《鴛鴦蝴蝶派文學(xué)資料》,第710-711頁(yè),福州:福建人民出版社,1984。
接著是胡適對(duì)鴛蝴派義正詞嚴(yán)的攻擊。他說(shuō) “此類(lèi)文字,只可抹桌子,固不值一駁”,像“《海上繁華夢(mèng)》與《九尾龜》所以能風(fēng)行一時(shí),正因?yàn)樗麄兌贾粍倓倝虻蒙稀谓缰改稀馁Y格,而都沒(méi)有文學(xué)價(jià)值,都沒(méi)有深刻的見(jiàn)解,與深刻的描寫(xiě),這些書(shū)都只是供一般讀者消遣的書(shū),讀時(shí)無(wú)所用心,讀過(guò)毫無(wú)余味”。⑤阿英:《晚清小說(shuō)史·晚清小說(shuō)之末流》,第197頁(yè),上海:東方出版社,1996。除了斥責(zé)鴛蝴作品品質(zhì)低劣之外,胡適又極言其質(zhì)量粗糙:“全是不懂文學(xué)方法的:既不知布局,又不知結(jié)構(gòu),又不知描寫(xiě)人物,只做成了許多又長(zhǎng)又臭的文字”。⑥胡適:《建設(shè)的文學(xué)革命論》,胡適編選:《中國(guó)新文學(xué)大系·建設(shè)理論集》,第135頁(yè),上海:上海文藝出版社,2003。
新文學(xué)的先鋒們盡管罵,可鴛蝴的名士們還是如癡如醉地寫(xiě)、踟躕滿志地編。在一九〇九-一九二〇的這十年間迎來(lái)了中國(guó)現(xiàn)代文學(xué)期刊發(fā)展的第二波。魯迅說(shuō),這是“鴛鴦蝴蝶式文學(xué)的極盛時(shí)期”,大概也就是指一九一四和一九一五這兩年前后。就目前不完全的期刊統(tǒng)計(jì)數(shù)目來(lái)看,僅一九一四年就有創(chuàng)刊雜志二十四種,一九一五年十三種。⑦范伯群:《中國(guó)現(xiàn)代通俗文學(xué)史》(插圖本),第175頁(yè),北京:北京大學(xué)出版社,2006。這些琳瑯滿目的雜志在創(chuàng)刊時(shí)就明確標(biāo)舉娛樂(lè)、消閑的趣味主義文學(xué)觀。王鈍根和陳蝶仙在《游戲雜志》第一期(一九一三)的序言中說(shuō):“不世之勛,一游戲之事也。萬(wàn)國(guó)來(lái)朝,一游戲之場(chǎng)也。號(hào)霸稱(chēng)王,一游戲之局也。”①范伯群、芮和師等編:《鴛鴦蝴蝶派文學(xué)資料》,第 4、8、7、6、5、12、4、8 頁(yè)。 標(biāo)點(diǎn)系筆者所加。許嘯天夫人高劍華女士所編輯的《眉語(yǔ)》一刊,在創(chuàng)刊詞(一九一四)中亦是開(kāi)門(mén)見(jiàn)山地表示該雜志是閑暇之伴、寂寞之友:“璇閨姊妹以職業(yè)之暇,聚釵光鬢影能及時(shí)行樂(lè)者,亦解人也。然而踏青納涼賞月話雪,寂寂相對(duì),是亦不可以無(wú)伴。”②范伯群、芮和師等編:《鴛鴦蝴蝶派文學(xué)資料》,第 4、8、7、6、5、12、4、8 頁(yè)。 標(biāo)點(diǎn)系筆者所加。
鴛蝴的經(jīng)典雜志《禮拜六》,其出版贅言(一九一四)中更是開(kāi)誠(chéng)布公地將賣(mài)點(diǎn)導(dǎo)向消遣,宣稱(chēng):
買(mǎi)笑耗金錢(qián),覓醉礙衛(wèi)生,顧曲苦喧囂,不若讀小說(shuō)之省儉而安樂(lè)也。且買(mǎi)笑覓醉顧曲,其為樂(lè)轉(zhuǎn)瞬即逝,不能繼續(xù)以至明日也。讀小說(shuō)則以小銀元一枚,換得新奇小說(shuō)數(shù)十篇。游倦歸齋,挑燈展卷,或與良友抵掌評(píng)論,或伴愛(ài)妻并肩互讀。意興稍闌,則以其余留于明日讀之。晴曦照窗,花香入坐,一編在手,萬(wàn)慮都忘,勞瘁一周,安閑此日,不亦快哉!故人有不愛(ài)買(mǎi)笑,不愛(ài)覓醉,不愛(ài)顧曲,而未有不愛(ài)讀小說(shuō)者。況小說(shuō)之輕便有趣如《禮拜六》者乎?③范 伯群 、芮 和 師等 編: 《鴛 鴦蝴 蝶 派文學(xué) 資料 》, 第 4、8、7、6、5、12、4、8 頁(yè) 。 標(biāo) 點(diǎn)系 筆者 所加。
其他的像什么“仗我片言,集來(lái)尺幅,博人一噱,化去千愁”、④范伯群、芮和師等編:《鴛鴦蝴蝶派文學(xué)資料》,第 4、8、7、6、5、12、4、8 頁(yè)。 標(biāo)點(diǎn)系筆者所加。“野老閑談之料,茶余酒后,備個(gè)人消閑之資”、⑤范伯群、芮和師等編:《鴛鴦蝴蝶派文學(xué)資料》,第 4、8、7、6、5、12、4、8 頁(yè)。 標(biāo)點(diǎn)系筆者所加。“無(wú)論文言俗語(yǔ)、一以興味為主”⑥范伯群、芮和師等編:《鴛鴦蝴蝶派文學(xué)資料》,第 4、8、7、6、5、12、4、8 頁(yè)。 標(biāo)點(diǎn)系筆者所加。等等,無(wú)不標(biāo)舉趣味、休閑之說(shuō)。盡管這些方面可以看作是鴛蝴的主要特征,但它仍有一面有待我們記憶,即其追隨梁?jiǎn)⒊?“新小說(shuō)”理論而展開(kāi)的輿論轉(zhuǎn)圜。這部分論述往往緊密地聯(lián)結(jié)在“趣味”、“休閑”之中,大有古時(shí)候“寓教于樂(lè)”的意思。比如《游戲雜志》的序末有這樣的婉轉(zhuǎn)語(yǔ):
當(dāng)今之世,忠言逆耳,名論良箴,束諸高閣,惟此譎諫隱詞,讀者能受盡言。故本雜志搜集眾長(zhǎng),獨(dú)標(biāo)一格,冀藉淳于微諷,呼醒當(dāng)世。顧此雖名屬游戲,豈得以游戲目之哉。且今日之所謂游戲文字,他日進(jìn)為規(guī)人之必要,亦未可知也。⑦范伯群、芮和師等編:《鴛鴦蝴蝶派文學(xué)資料》,第 4、8、7、6、5、12、4、8 頁(yè)。 標(biāo)點(diǎn)系筆者所加。
而《眉語(yǔ)》宣言中亦不失這樣的意思:“錦心繡口,句香意雅,雖曰游戲文章、荒唐演述,然譎諫微諷,潛移默化于消閑之余,以未始無(wú)感化之功也。”⑧范伯群、芮和師等編:《鴛鴦蝴蝶派文學(xué)資料》,第 4、8、7、6、5、12、4、8 頁(yè)。 標(biāo)點(diǎn)系筆者所加。
另外,像徐枕亞、李涵秋這些偏寫(xiě)感傷情調(diào)的鴛蝴作家,又哪一個(gè)不曾信誓旦旦表示過(guò)“小說(shuō)是為改良社會(huì)之一助”、“我輩手無(wú)斧柯,雖不能澄清國(guó)政,然有一支筆在,亦可以改良社會(huì),喚醒人民”⑨轉(zhuǎn)引自郭延禮 《20世紀(jì)中國(guó)近代文學(xué)研究學(xué)術(shù)史》,第326頁(yè),南昌:江西高校出版社,2004。之類(lèi)的豪言壯語(yǔ)。這些表面上看僅僅是追逐“新小說(shuō)”理論的時(shí)髦之語(yǔ),卻也正是鴛蝴作者善用“場(chǎng)感”來(lái)減輕自己文學(xué)主張阻力的聰明舉動(dòng)。至少在用輕松愉快招徠讀者的同時(shí),他們也需要安撫那些舊式文人,使其以為文學(xué)也不總是一無(wú)是處的。
當(dāng)然,這樣的措辭確實(shí)掩過(guò)了那些冬烘道學(xué)的耳目,但對(duì)于五四的新文學(xué)而言,國(guó)事蜩螗,豈容笑謔,于是新文化運(yùn)動(dòng)之后,這些“寓教于樂(lè)”、“寓教于惡”(王德威)的篇目和言論又統(tǒng)統(tǒng)遭受了挫折。其中最主要的抨擊就集中在一九一八和一九一九這兩年,因?yàn)槠鋾r(shí)的 “黑幕書(shū)”⑩此處所說(shuō)的“黑幕書(shū)”與鴛蝴作品中的“黑幕小說(shuō)”有本質(zhì)區(qū)別,不可混同,討論見(jiàn)范伯群《中國(guó)現(xiàn)代通俗文學(xué)史》(插圖本),第226-229頁(yè)。已引起了極大的民憤。
一九一六年上海 《時(shí)事新報(bào)》、《報(bào)余叢載》一欄刊登“黑幕大懸賞”的征文啟事,“務(wù)乞以鑄鼎象奸之筆,發(fā)為探微索引之文。本本源源,盡情揭示……共除人道蟊賊,務(wù)使若輩無(wú)逃形影,重光天日而后已”。起首,揭黑是以改良社會(huì)為宏愿,用意純良,但誰(shuí)知此風(fēng)一開(kāi),便從此不可收拾,連續(xù)二十五個(gè)月,“日無(wú)間斷”,導(dǎo)致黑幕泛濫,許多齷齪不潔之事也竟相借此風(fēng)混雜魚(yú)目:“夫開(kāi)男盜女娼之函授學(xué)校,則直曰開(kāi)男盜女娼之函授學(xué)校耳;賣(mài)淫書(shū)直曰賣(mài)淫書(shū)耳,而必曰宣布黑幕也。”事易時(shí)移,黑幕已經(jīng)變質(zhì),其惡劣習(xí)氣使得教育部也不得不下文告誡,希望其見(jiàn)好就收,最后事情終以《時(shí)事新報(bào)》在一九一八年十一月七日的頭條發(fā)布“裁撤黑幕欄通告”而告一段落。①這一段歷史見(jiàn)范伯群 《中國(guó)現(xiàn)代通俗文學(xué)史》(插圖本),第221-224頁(yè)。文中兩處引言分別見(jiàn)第221、226頁(yè)。
其后的故事就是,剛剛登上文壇不久的新文學(xué)欲借批駁此事來(lái)樹(shù)立自己良好的公眾形象,同時(shí)趁機(jī)打壓橫亙文壇已久的鴛蝴派,以此來(lái)擴(kuò)大自己的文學(xué)地盤(pán),爭(zhēng)取必要的讀者。這其中首先發(fā)難的是錢(qián)玄同。其發(fā)表在《新青年》六卷一號(hào)上(一九一九)的文章《“黑幕”書(shū)》,不僅第一次明確提出了“鴛鴦蝴蝶派”的名稱(chēng),更是詈責(zé)“‘黑幕’書(shū)之貽毒于青年,稍有識(shí)者皆能知之。然人人皆知‘黑幕’書(shū)為一種不正當(dāng)之書(shū)籍,其實(shí)與‘黑幕’同類(lèi)之書(shū)籍正復(fù)不少。如《艷情尺牘》、《香艷韻語(yǔ)》,及‘鴛鴦蝴蝶派小說(shuō)’等等,皆是”。他認(rèn)為這些文類(lèi)之所以甚囂塵上,那是與袁世凱的專(zhuān)政、復(fù)辟潮流脫不了干系的:“清未亡時(shí),國(guó)人尚有革新之思想,到了民國(guó)成立,反而提倡復(fù)古,袁政府以此愚民,國(guó)民不但不反抗,還要來(lái)推波助瀾,我真不解彼等是何居心。”②范伯群、芮和師等編:《鴛鴦蝴蝶派文學(xué)資料》,第 823-824、717-718、720 頁(yè)。雖然錢(qián)玄同并未主攻鴛蝴,而只是裙帶連及,但他一出手就為它扣上了一頂 “政治帽”,這實(shí)在不能不說(shuō)是間接將其推上了道德大不韙的境地。
錢(qián)玄同之后,魯迅發(fā)表《有無(wú)相通》,周作人以“仲密”的筆名發(fā)表《論“黑幕”》和《再論“黑幕”》二文,志希(羅家倫)則發(fā)表了《今日中國(guó)之小說(shuō)界》等。這些文章仍主攻黑幕,并順批鴛蝴。因此,鴛蝴在這次被批過(guò)程中始終是處于敬陪末座的位置。周作人的兩篇文章,幾乎通篇談?wù)摵谀唬⒉簧婕傍x蝴;倒是志希的討論,在黑幕之外,提到了“濫調(diào)四六派”和“筆記派”。他說(shuō)前者“這一派的人只會(huì)套來(lái)套去,做幾句濫調(diào)的四六,香艷的詩(shī)詞”,辭藻匱乏,結(jié)構(gòu)千篇一律,代表就是徐枕亞、李定夷等人的言情作品。他說(shuō),批判這類(lèi)的作品,“把我的筆都弄污穢了”。③范伯群、芮和師等編:《鴛鴦蝴蝶派文學(xué)資料》,第 823-824、717-718、720 頁(yè)。同前兩人的批判姿態(tài)不同,魯迅是本著規(guī)勸的態(tài)度來(lái)寫(xiě)《有無(wú)相通》的,因?yàn)樵谒磥?lái)這些“江蘇浙江湖南的才子們、名士們”完全有能力憑著自己的才華“譯幾頁(yè)有用的新書(shū)”。所以,他希望“我們改良點(diǎn)自己,保全些別人,想些互助的方法,收了互害的局面”。④范伯群、芮和師等編:《鴛鴦蝴蝶派文學(xué)資料》,第 823-824、717-718、720 頁(yè)。
所以,我們看到在二十世紀(jì)最初二十年所進(jìn)行的這場(chǎng)批判中,鴛蝴派并不是新文學(xué)重點(diǎn)批判的對(duì)象,它總是被順帶提及,而且由于鴛蝴的概念并沒(méi)有被廣泛地采納,所以總是以對(duì)個(gè)別作家、作品或含糊其詞的“當(dāng)今文壇”如何如何的用語(yǔ)來(lái)進(jìn)行,因而顯得有些火力不夠集中,并未引起鴛蝴方面的重視。當(dāng)然,最重要的是鴛蝴本身發(fā)展勢(shì)頭正猛,雖然五四崛起給它帶來(lái)了一定沖擊,但畢竟遠(yuǎn)遠(yuǎn)沒(méi)有到傷筋動(dòng)骨的嚴(yán)重地步,而且為了避開(kāi)五四摧枯拉朽式的尖銳鋒芒,鴛蝴抱持著不予理會(huì)和不應(yīng)理睬的態(tài)度,照樣我行我素地去編撰各類(lèi)以移情逸樂(lè)為尚的報(bào)刊雜志,試圖用讀者來(lái)維護(hù)自己獨(dú)步文壇的一尊地位。
二
鴛蝴派與新文學(xué)的第二次交鋒主要集中在一九二〇到一九二九的這十年間。它上起茅盾改組《小說(shuō)月報(bào)》,下至三十年代黎烈文接編《申報(bào)》副刊《自由談》。這十年一改從前新文學(xué)獨(dú)唱專(zhuān)場(chǎng)的形式,而變?yōu)殡p方的你來(lái)我往,沖突不斷。幾乎就是這十年,斗爭(zhēng)雙方基本確立了其在文學(xué)場(chǎng)域中的占位格局,而變得意義非凡。
從一九二〇年茅盾參與《小說(shuō)月報(bào)》的編輯開(kāi)始,到第二年元月,他正式走馬上任,全權(quán)接編《小說(shuō)月報(bào)》,不過(guò)幾個(gè)月的時(shí)間,新文學(xué)與鴛蝴派的梁子由此結(jié)下,并于隨后全面爆發(fā)。茅盾在回憶錄中這樣寫(xiě)道:
我偶然地被選為打開(kāi)缺口的人,又偶然地被選為進(jìn)行全部革新的人,然而因此同頑固派結(jié)成不解的深仇。這頑固派就是當(dāng)時(shí)以小型刊物《禮拜六》為代表的所謂鴛鴦蝴蝶派文人。鴛鴦蝴蝶派是封建思想和買(mǎi)辦意識(shí)的混血兒,在當(dāng)時(shí)的小市民階層中有相當(dāng)影響。①茅盾:《回憶錄 (三)》,《新文學(xué)史料》(第三輯),1979年5月。
一九二一年一月,革新后的《小說(shuō)月報(bào)》第十二卷第一號(hào)出版,上面刊載了于同月成立的文學(xué)研究會(huì)的宣言,宣言中說(shuō):“將文藝當(dāng)作高興時(shí)的游戲或失意時(shí)的消遣的時(shí)候,現(xiàn)在已經(jīng)過(guò)去了。我們相信文學(xué)是一種工作,而且又是于人生很切要的一種工作;治文學(xué)的人也當(dāng)以這事業(yè)為他終身的事業(yè),正同勞農(nóng)一樣”。文中的“游戲”、“消遣”等字眼,顯然是針對(duì)鴛蝴而發(fā)。因?yàn)椴痪们皠?chuàng)刊的 《游戲新報(bào)》(一九二〇年十二月)又一次明白無(wú)誤地使用了“游戲”兩字,并在發(fā)刊詞中極言消遣之樂(lè):
今世何世,乃有吾曹閑人?偶爾弄翰,亦游戲事耳,乃可以卻暑。歲月如流,涼飆且至,孰能知我輩消夏之樂(lè)?盍謀所以永之,余曰:無(wú)已,裝一書(shū)冊(cè),顏以游戲,月有所刊,署曰:新報(bào),不亦可乎?眾曰:善……堂皇厥旨,是為游戲,誠(chéng)亦雅言,不與政事……②范伯群、芮和師等編:《鴛鴦蝴蝶派文學(xué)資料》,第14頁(yè)。標(biāo)點(diǎn)系筆者所加。
而與茅盾等人的文學(xué)研究會(huì)及其宣言針?shù)h相對(duì)的是,在這年的三月十九停刊將近五年的《禮拜六》一聲炮響,又復(fù)刊了。而且在其一〇三期的《編輯室》中明確寫(xiě)道:“本刊小說(shuō),頗注重社會(huì)問(wèn)題,家庭問(wèn)題,以極誠(chéng)懇之筆出之。”③轉(zhuǎn)引自范伯群《中國(guó)現(xiàn)代通俗文學(xué)史》,第254頁(yè)。這一措辭顯然是要與文學(xué)研究會(huì)所說(shuō)的文學(xué) “是于人生很切要的一種工作”叫板、抗衡。
茅盾已經(jīng)明顯地感覺(jué)到了來(lái)自鴛蝴派的壓力,在這一年八月給周作人的信中,他不無(wú)感慨地寫(xiě)道:
上海謾罵之報(bào)紙?zhí)啵毒?bào)》常與《小說(shuō)月報(bào)》開(kāi)玩笑,我們要辦他事,更成功少而笑罵多;且上海同人太少,力量亦不及。④轉(zhuǎn)引自董麗敏《想象現(xiàn)代性:革新時(shí)期的〈小說(shuō)月報(bào)〉研究》,第53頁(yè),桂林:廣西師范大學(xué)出版社,2006。
關(guān)于這段故實(shí),鄭振鐸在《〈文學(xué)論爭(zhēng)集〉導(dǎo)言》中予以了證實(shí),他講:
當(dāng)《小說(shuō)月報(bào)》初改革的時(shí)間,他們卻也感覺(jué)到自己的危機(jī)的到臨,曾奪其酒色淘空了的精神,作最后的掙扎。他們?cè)谒麄儗?shí)力所及的一個(gè)圈子里,對(duì)《小說(shuō)月報(bào)》下總攻擊令。冷嘲熱罵,延長(zhǎng)到好幾個(gè)月還為已。可惜這一類(lèi)的文字,現(xiàn)在也收集不到,不能將他們重刊于此。⑤魏紹昌編:《鴛鴦蝴蝶派研究資料》(上卷),第51頁(yè),上海:上海文藝出版社,1984。
這些鄭振鐸所不能尋找到的文字,就是茅盾文中所說(shuō)的《晶報(bào)》開(kāi)的玩笑,此類(lèi)玩笑包括了寒云(袁寒云)的《辟創(chuàng)作》以及寄塵(胡寄塵)的《一個(gè)被強(qiáng)盜捉去的新文化運(yùn)動(dòng)者底成績(jī)》。前者明明白白地批評(píng)新文學(xué)是“一班妄徒、拿外國(guó)的文法、做中國(guó)的小說(shuō)、還要加上外國(guó)的圈點(diǎn)、用外國(guó)的款式、什么的呀、底呀、地呀、鬧得烏煙瘴氣、一句通順的句子也沒(méi)有”,而且其矛頭直指全面革新的《小說(shuō)月報(bào)》。文章說(shuō):
海上某大書(shū)店出的一種小說(shuō)雜志、從前很有點(diǎn)價(jià)值、今年忽然野心起來(lái)了、內(nèi)容著重的、就是新的創(chuàng)作、所謂創(chuàng)作呢、文法、學(xué)外國(guó)的樣、圈點(diǎn)、學(xué)外國(guó)的樣、款式、學(xué)外國(guó)的樣、甚至連紀(jì)年、也用的是西歷一千九百二十一年、他還要老著臉皮、說(shuō)是創(chuàng)作、難道學(xué)了外國(guó)、就算創(chuàng)作嗎、這種雜志、既然變了非驢非馬、稍微有點(diǎn)小說(shuō)智識(shí)的、使決不去看他、就是去想翻他、看他到底是怎么回事、頂多看上三五句、也要頭昏腦漲、廢然掩卷了……
文章最后還說(shuō),“如果都照這樣做下去、不但害盡青年、連我國(guó)優(yōu)美高尚的文字、恐怕漸漸都要消滅哩”。①范伯群、芮和師等編:《鴛鴦蝴蝶派文學(xué)資料》,第 170-171、171-173、733、177、729 頁(yè)。寒云的這些論調(diào)可謂是和新文學(xué)來(lái)了一個(gè)以牙還牙。而更甚者是寄塵的后一篇小說(shuō),極盡挖苦之能事,講一個(gè)新文學(xué)作家被強(qiáng)盜抓去后,如何丑態(tài)百出地宣講“奮斗”和“改造”,并在被放后又如何在同伴面前邀功自夸,講自己成功地改造了強(qiáng)盜,使其覺(jué)悟。②范 伯 群、芮 和師 等 編: 《 鴛鴦 蝴 蝶派 文 學(xué)資料》,第 170-171、171-173、733、177、729 頁(yè)。小說(shuō)諷刺了新文學(xué)那些所謂的崇高政治理想,不過(guò)是紙上談兵、癡人的夢(mèng)囈,不切實(shí)際。
為了對(duì)這些冷嘲熱諷來(lái)一次有力的還擊,文學(xué)研究會(huì)專(zhuān)門(mén)創(chuàng)辦了自己的機(jī)關(guān)刊物 《文學(xué)旬刊》,并在上面撰文回應(yīng)。鄭振鐸說(shuō):“《文學(xué)旬刊》對(duì)于他們也曾以全力對(duì)付過(guò),幾乎大部分的文字都是針對(duì)他們而發(fā)的。都是以嚴(yán)正的理論來(lái)對(duì)付不大上流的污蔑的話。”③范伯群、芮和師等編:《鴛鴦蝴蝶派文學(xué)資料》,第 170-171、171-173、733、177、729 頁(yè)。這些文章包括了鄭振鐸(西諦)本人的《思想的反流》、《新舊文學(xué)的調(diào)和》、《血與淚的文學(xué)》、《消閑?! 》、《中國(guó)文人(?)對(duì)于文學(xué)的根本誤解》,葉圣陶(圣陶)的《侮辱人們的人》等二十余篇文章。
而其他一些發(fā)在別的雜志或報(bào)章上的文章,如魯迅的《“一是之學(xué)說(shuō)”》、《所謂“國(guó)學(xué)”》、《名字》、《關(guān)于〈小說(shuō)世界〉》,茅盾的《“寫(xiě)實(shí)小說(shuō)之流弊”》、《真有代表舊文化舊文藝的作品么》、《反動(dòng)?》,以及郭沫若、李芾甘等人的文章都參與了這場(chǎng)聲勢(shì)浩大的新文學(xué)保衛(wèi)戰(zhàn)。
在這些人當(dāng)中,鄭振鐸身先士卒,他撰文《悲觀》、《“文娼”》等,對(duì)鴛蝴文學(xué)進(jìn)行定位,并毫不猶豫地將其稱(chēng)為“文娼”和“文丐”。他認(rèn)為時(shí)代“到處是榛棘、是悲慘、是槍聲炮影”,人們的靈魂被擾,心神苦悶,因而“所需要的是血的文學(xué)、淚的文學(xué),不是‘雍容爾雅’‘吟風(fēng)嘯月’的冷血的產(chǎn)品”。④范伯群、芮和師等編:《鴛鴦蝴蝶派文學(xué)資料》,第 170-171、171-173、733、177、729 頁(yè)。對(duì)于鄭的批評(píng),鴛蝴人士不但不予辯解,反以“文丐”自豪,認(rèn)為“靠著一支筆拿來(lái)生活”并不可恥,反倒“比著自己做了某小說(shuō)雜志主任,在化了名,譯了小說(shuō),算是北京來(lái)的稿子,要支五塊錢(qián)一千字的,我覺(jué)得還正大光明得多啊”。⑤范伯群、芮和師等編: 《鴛鴦蝴蝶派 文學(xué)資料》,第 170-171、171-173、733、177、729 頁(yè)。
此外,葉圣陶還曾針對(duì)鴛蝴“寧可不娶小老嬤,不可不看《禮拜六》”一句大加撻伐,認(rèn)為“這實(shí)在是一種侮辱、普遍的侮辱,他們侮辱自己,侮辱文學(xué),更侮辱他人……無(wú)論什么游戲的事總不至卑鄙到這樣,游戲也要高尚和真誠(chéng)的啊!如今既有寫(xiě)出這兩句的人……這不僅是文學(xué)前途的渺茫和憂慮,竟是中國(guó)民族超升的渺茫和憂慮了”。⑥范伯群、芮和師等編:《鴛鴦蝴蝶派文學(xué)資料》,第 170-171、171-173、733、177、729 頁(yè)。
通過(guò)以上的這些例子我們看到,盡管文學(xué)研究會(huì)的成員對(duì)鴛蝴多有不滿,但批判并未上升到鄭振鐸所說(shuō)的“嚴(yán)正的理論”高度上,它們更多的是一種情感性的評(píng)判。在理論方面做的較好的其實(shí)是李之常和沈雁冰。前者《支配社會(huì)底文學(xué)論》一文在直陳鴛蝴小說(shuō)的種種是非后,明確提出了文學(xué)的功用 “是為人生的,為民眾的,使人哭和怒的,支配社會(huì)的,革命的,絕不是供少數(shù)人賞玩的,娛樂(lè)的”。⑦轉(zhuǎn)引自董麗敏《想象現(xiàn)代性:革新時(shí)期的〈小說(shuō)月報(bào)〉研究》,第56、57頁(yè),桂林:廣西師范大學(xué)出版社,2006。而為了實(shí)現(xiàn)這些功用,就必須以“自然主義”作為當(dāng)前文學(xué)的基本規(guī)范:
中國(guó)底病的黑暗的現(xiàn)狀,亟待謀經(jīng)濟(jì)組織底更變,非用科學(xué)的精密觀察描寫(xiě)中國(guó)地多方的病的現(xiàn)象之真況,以培養(yǎng)國(guó)人革命底感情不可,非采用自然主義作中國(guó)今日底文學(xué)主義不可。中國(guó)文學(xué)采用自然主義是適應(yīng)環(huán)境。⑧轉(zhuǎn)引自董麗敏《想象現(xiàn)代性:革新時(shí)期的〈小說(shuō)月報(bào)〉研究》,第56、57頁(yè),桂林:廣西師范大學(xué)出版社,2006。
同李之常的觀點(diǎn)相近,且又更進(jìn)一步的是茅盾發(fā)表在《小說(shuō)月報(bào)》第十三卷第七期上的長(zhǎng)篇論文《自然主義與中國(guó)現(xiàn)代小說(shuō)》。這篇檄文:
……引用了《禮拜六》第一百零八期上所登的名為 《留聲機(jī)片》的一個(gè)短篇小說(shuō)(未點(diǎn)作者的姓名)作為例子,用嚴(yán)正的態(tài)度,從思想內(nèi)容以至描寫(xiě)方法,做了千把字的分析,然后下了判斷:“作者自己既然沒(méi)有確定的人生觀,又沒(méi)有觀察人生的一副深炯眼光和冷靜頭腦,所以他們雖然也做了人道主義的小說(shuō),也做描寫(xiě)無(wú)產(chǎn)階級(jí)窮困的小說(shuō),而其結(jié)果,人道主義反變成了淺薄的慈善主義,描寫(xiě)無(wú)產(chǎn)階級(jí)的窮困反成了譏刺無(wú)產(chǎn)階級(jí)的粗陋與可厭了。”又批評(píng)他們寫(xiě)得最多的戀愛(ài)小說(shuō)或家庭小說(shuō)的中心思想,無(wú)非是封建思想的 “書(shū)中自有黃金屋,書(shū)中有女顏如玉”的各色各樣的翻版而已。
這篇文章,義正詞嚴(yán),不作人身攻擊,比之稱(chēng)他們?yōu)槲呢ぁ⑽逆剑蝰R路文人者實(shí)在客氣得多。但也許正因?yàn)槭窃~嚴(yán)義正的批判,不作謾罵,必將引起“禮拜六派”小說(shuō)讀者的注意,以及同情于此派小說(shuō)者的深思,故“禮拜六派”恨之更甚。他們就對(duì)商務(wù)當(dāng)局施加壓力……①茅盾:《復(fù)雜而緊張的生活、學(xué)習(xí)與斗爭(zhēng)》,茅盾:《茅盾全集(34):回憶錄一集》,第 208頁(yè),葉子銘校注、定稿,北京:北京人民文學(xué)出版社,1997。
這施壓的后果正是茅盾的離職和商務(wù)又衍出一個(gè)《小說(shuō)世界》來(lái)專(zhuān)供鴛蝴使用。對(duì)于此事,茅盾曾和王統(tǒng)照等人在《時(shí)事新報(bào)》的《學(xué)燈》欄擬文予以嘲諷和批判,小題為《“出人意表之外”之事》。②范伯群、芮和師等編:《鴛鴦蝴蝶派文學(xué)資料》,第 851-854、237、181、183、181 頁(yè)。
事實(shí)上,讓茅盾等文學(xué)研究會(huì)成員出乎意料的事情,不光來(lái)自鴛蝴,同樣也來(lái)自新文學(xué)內(nèi)部。盡管彼時(shí)文學(xué)研究會(huì)和創(chuàng)造社因著“文學(xué)為什么”的問(wèn)題而酣戰(zhàn)不止,但茅盾等人還是不能理解其對(duì)鴛蝴姑息縱容的做法。他在回憶錄中這樣記道:
當(dāng)時(shí),同樣使我們不能理解的一件事,是創(chuàng)造社諸公的大多數(shù)對(duì)于鴛鴦蝴蝶派十分吝惜筆墨,從來(lái)不放一槍。也有一個(gè)例外,就是成仿吾在《創(chuàng)造季刊》第二期上曾寫(xiě)了一篇《歧路》,對(duì)“禮拜六”狠狠地開(kāi)了一炮。③范伯群、芮和師等編:《鴛鴦蝴蝶派文學(xué)資料》,第 851-854、237、181、183、181 頁(yè)。
由此可以看出,鴛蝴派和新文學(xué)的第二次交鋒雖然深入而持久,但其牽涉的新文學(xué)面顯然要小過(guò)第一次。在上一次,新文學(xué)的左、中、右各部都投入了火力,但這一次更多的是左翼力量在發(fā)揮作用,他們著力強(qiáng)調(diào)文學(xué)的社會(huì)功用。
新文學(xué)來(lái)勢(shì)洶洶,通常的看法是鴛蝴派就此吃了虧,變得一蹶不振,而其實(shí),卻是它的不甘示弱,越挫越勇,迎來(lái)了通俗期刊小說(shuō)的第三波高潮。一九二一年創(chuàng)刊的著名報(bào)刊不下十種,一九二二年又辦十五種,一九二三年十七種,一九二四年十余種……生生不息,滾滾向前。④孔慶東:《1921:誰(shuí)主浮沉》,第189頁(yè),濟(jì)南:山東教育出版社,2002。他們成立青社和星社,專(zhuān)以“吃喝玩樂(lè)”為結(jié)社方式,每月小聚,吟詩(shī)作賦,頗有一些與文學(xué)研究會(huì)、創(chuàng)造社等一本正經(jīng)、照章辦事的文學(xué)組織抗衡、搗蛋的意思。青社的社刊《長(zhǎng)青》,雖然時(shí)日不久,但對(duì)待新文學(xué)的態(tài)度倒是清清楚楚的:《止謗莫如無(wú)辯》。⑤范伯群:《中國(guó)現(xiàn)代通俗文學(xué)史》,第239-241頁(yè)。這篇文章雖然看不到了,也無(wú)從知曉這“謗”字到底何指,但我們卻可以借其他的一些文章看出點(diǎn)端倪。這些文章多數(shù)都發(fā)在張枕綠所編的《最小》報(bào)上。比如胡寄塵的《消遣?》、《一封曾被拒絕發(fā)表的信》,張舍我的《批評(píng)小說(shuō)》、《創(chuàng)造自由》、《什么叫做 “禮拜六派”》,樓一葉的《一句公平話》,畢倚虹的《婆婆小記》,聽(tīng)潮聲的《精神……原質(zhì)》,等等。
這些文章基本上都是在表明,鴛蝴是本著“井水不犯河水”和“公好饅頭婆好面”的態(tài)度來(lái)看待此次批判的,他們同樣也希望新文學(xué)方面的作家“不必把新舊的界限放在心里。不必把人我的界限放在心里”。⑥范伯群、芮和師等編:《鴛鴦蝴蝶派文學(xué)資料》,第 851-854、237、181、183、181 頁(yè)。“大家平心靜氣。破除成見(jiàn)。細(xì)細(xì)搜求一些對(duì)方高深優(yōu)美的作品來(lái)看看。便自然知道都誤解了。他們所不同的。只是一點(diǎn)形式。那原質(zhì)是一樣。也有好也有壞呀。”⑦范伯群、芮和師等編:《鴛鴦蝴蝶派文學(xué)資料》,第 851-854、237、181、183、181 頁(yè)。
胡寄塵還在給鄭振鐸的信中明確表示,文學(xué)改革不是黨同伐異,而是要自由競(jìng)爭(zhēng),最終的優(yōu)劣存亡,應(yīng)當(dāng)讓歷史自己去做抉擇。他講:
……前清初行郵政的時(shí)候。并不曾將有的信局(即民間寄信機(jī)關(guān))一例封閉然后再開(kāi)設(shè)郵政局。只將郵政局辦好了。老式的信局自然而然的減少了。久之終必要消滅。又如上海初行電車(chē)。并不曾禁止人力車(chē)馬駛行。然后行電車(chē)。只將電車(chē)的成績(jī)辦好了。人力車(chē)馬車(chē)自然要減少了。久之終必也要消滅。改革文學(xué)。何嘗不是如此呢。⑧范伯群、芮和師等編:《鴛鴦蝴蝶派文學(xué)資料》,第 851-854、237、181、183、181 頁(yè)。
盡管胡寄塵句句在理,可惜這畢竟是一場(chǎng)斗爭(zhēng),這樣“委曲求全”的方式不免有些天真了。新文學(xué)陣營(yíng)內(nèi)的宋云彬也曾主張用此法對(duì)待鴛蝴,但旋即遭受責(zé)難:
(宋云彬)先生說(shuō):“我們不必怕《禮拜六》式的‘瓦釜雷鳴’,我們但教把自己的‘黃鐘’敲得響。”我們以為不然,因?yàn)槿粼凇拔淖帧眱勺至⒛_點(diǎn)上說(shuō),《禮拜六》簡(jiǎn)直不配稱(chēng)為文學(xué)作品,他根本的不能成立,何論高低,便無(wú)所謂“黃鐘”與“瓦釜”之分了。①轉(zhuǎn)引自魏紹昌:《我看鴛鴦蝴蝶派》,第46-47頁(yè)。其實(shí),魯迅的觀點(diǎn)也是同胡寄塵、宋云彬的相近的,見(jiàn)其《關(guān)于〈小說(shuō)世界〉》一文,范伯群、芮和師等編:《鴛鴦蝴蝶派文學(xué)資料》,第858-859頁(yè)。
可見(jiàn)新文學(xué)方面是絕沒(méi)有“平等競(jìng)爭(zhēng)”的意識(shí)的,他們想除之而后快,所以胡寄塵的這封信“曾被拒絕發(fā)表”。
與胡寄塵等人的低調(diào)姿態(tài)不同,亦有像袁寒云式的盛氣凌人,畢竟他是一代貴胄,說(shuō)話難免有些傲氣。他的《小說(shuō)迷的一封信》,挖苦新改版的《小說(shuō)月報(bào)》是看也看不懂,賣(mài)給舊書(shū)店的不要,送給醬鴨店做包裝紙,老板還要嫌上面的字太臭。②范伯群、芮和師等編:《鴛鴦蝴蝶派文學(xué)資料》,第174-175頁(yè)。又與這兩種斗爭(zhēng)方式都不一樣,且更為高明的是范煙橋。這位鴛蝴派的十八羅漢之一:
……曾在一九二七寫(xiě)過(guò)一冊(cè)堂而皇之的《中國(guó)小說(shuō)史》,追流溯源,把民初以來(lái)便盛行不衰的鴛鴦蝴蝶式通俗小說(shuō)正式納入中國(guó)本土小說(shuō)發(fā)展的“全盛時(shí)期”,大書(shū)《玉梨魂》和《廣陵潮》的承前啟后,同時(shí)只字不提五四以來(lái)方興未艾的新文學(xué),也算是給新文學(xué)運(yùn)動(dòng)健將們針對(duì)鴛鴦蝴蝶派發(fā)出的種種責(zé)難攻擊一個(gè)不卑不亢的回應(yīng)。③唐小兵:《蝶魂花影惜紛飛》,《讀書(shū)》1993年第3期。
一個(gè)批,一個(gè)應(yīng),盡管方式千差萬(wàn)別,但最終是誰(shuí)也沒(méi)有勝過(guò)誰(shuí),倒是那新與舊的界線被清清楚楚地畫(huà)了個(gè)分明。而沿著這涇渭分明的分水嶺,斗爭(zhēng)的雙方把這場(chǎng)沒(méi)有完結(jié)的戰(zhàn)役延伸到了三十年代的舞臺(tái)。但那里時(shí)有戰(zhàn)爭(zhēng)的炮火,所以情形又更為復(fù)雜。
三
到了一九三〇年代初,武俠小說(shuō)的熱潮引發(fā)新一波的論爭(zhēng),這場(chǎng)論爭(zhēng)最終泯于戰(zhàn)爭(zhēng)的硝煙,大致也是十年的時(shí)間。其間,魯迅發(fā)表了《上海文藝一瞥》、《偽自由書(shū)·后記》、《答徐懋庸并關(guān)于抗日統(tǒng)一戰(zhàn)線問(wèn)題》,瞿秋白發(fā)表了《鬼門(mén)關(guān)以外的戰(zhàn)爭(zhēng)》、《論大眾文藝》、《財(cái)神還是反財(cái)神?》、《學(xué)閥萬(wàn)歲!》、《吉訶德的時(shí)代》,鄭振鐸發(fā)表了《論武俠小說(shuō)》、《文學(xué)論爭(zhēng)集·導(dǎo)言》,沈雁冰發(fā)表了《封建的小市民文藝》,錢(qián)杏邨發(fā)表了《上海事變與鴛鴦蝴蝶派文藝》等文章參與批判。
從一九二二年起,平江不肖生(向愷然)的《江湖奇?zhèn)b傳》“在上海《紅》雜志(后更名《紅玫瑰》)連載,邊寫(xiě)邊刊邊出書(shū),經(jīng)過(guò)六個(gè)年頭,到一九二八年全書(shū)一百三十四回才告完成”。④魏紹昌:《我看鴛鴦蝴蝶派》,第153頁(yè)。這個(gè)過(guò)程中,上海的市民階層中掀起了一股巨大的 “武俠狂潮”。這個(gè)狂潮據(jù)說(shuō)歷廿年而不衰,“一直熱到一九四九年”。⑤袁進(jìn):《鴛鴦蝴蝶派》,第120頁(yè),上海:上海書(shū)店,1994。而根據(jù)小說(shuō)第六十五回至八十六回內(nèi)容改編的電影 《火燒紅蓮寺》,在放映時(shí),更是場(chǎng)場(chǎng)爆滿,電影院里叫聲、掌聲一片。茅盾目睹盛況而撰文《封建的小市民文藝》,文中說(shuō):
一九三〇年,中國(guó)的“武俠小說(shuō)”盛極一時(shí)。自《江湖奇?zhèn)b傳》以下,摹仿因襲的武俠小說(shuō),少說(shuō)也有百來(lái)種罷。同時(shí)國(guó)產(chǎn)影片方面,也是“武俠片”的全盛時(shí)代;《火燒紅蓮寺》出足了風(fēng)頭以后,一時(shí)以“火燒……”號(hào)召的影片,恐怕也有十來(lái)種。
……
《火燒紅蓮寺》對(duì)于小市民層的魔力之大,只要你一到那開(kāi)映這影片的影戲院內(nèi)就可以看到。叫好、拍掌,在那些影戲院里是不禁的;從頭到尾,你是在狂熱的包圍中,而每逢影片中劍俠放飛劍互相斗爭(zhēng)的時(shí)候,看客們的狂呼就如同作戰(zhàn)一般,他們對(duì)紅姑的飛降而喝彩……
從銀幕上的《火燒紅蓮寺》又成為“連環(huán)圖畫(huà)的小說(shuō)”的《火燒紅蓮寺》實(shí)在是簡(jiǎn)陋得多了,可是那風(fēng)魔人心的效力依然不滅……在沒(méi)有影戲院的內(nèi)地鄉(xiāng)鎮(zhèn),此種“連環(huán)圖畫(huà)小說(shuō)”的《火燒紅蓮寺》就替代了影片。①范伯群、芮和師等編:《鴛鴦蝴蝶派文學(xué)資料 》, 第 841-843、841、838、835-836、795-796、812頁(yè)。
鴛蝴的這股“武俠狂浪”著實(shí)是激起了茅盾等左翼人士的極端不滿。他批評(píng)道:“一方面,這是封建的小市民要求‘出路’的反映,另一方面,這又是封建勢(shì)力對(duì)于動(dòng)搖中的小市民給的一碗迷魂湯。”②范伯群、芮和師等編:《鴛鴦蝴蝶派文學(xué)資料 》, 第 841-843、841、838、835-836、795-796、812頁(yè)。而鄭振鐸則認(rèn)為:“武俠小說(shuō)的發(fā)達(dá)……最重要的原因之一,便是一般民眾,在收了極端的暴政的壓迫之時(shí),滿肚子的填塞著不平與憤怒,卻又因力量不足,不能反抗。”③范伯群、芮和師等編:《鴛鴦蝴蝶派文學(xué)資料》, 第841 -843、841、838、835 -836、795 -796、812頁(yè)。同上述觀點(diǎn)近似,瞿秋白的文章《吉訶德的時(shí)代》還提出,武俠小說(shuō)不僅會(huì)造成“濟(jì)貧自有飛仙客,爾且安心做奴才”的愚民思想,更會(huì)使得“夢(mèng)想者青天大老爺?shù)那嗵彀兹罩髁x者,甚至于把這種強(qiáng)盜當(dāng)作青天大老爺,當(dāng)作救苦救難觀世音菩薩。”④范伯群、芮和師等編:《鴛鴦蝴蝶派文學(xué)資料》, 第841 -843、841、838、835 -836、795 -796、812頁(yè)。認(rèn)定武俠小說(shuō)百害而無(wú)一益。這些文章主要是站在階級(jí)論的基礎(chǔ)之上,從政治斗爭(zhēng)的角度對(duì)武俠小說(shuō)予以了批駁,并沒(méi)有真正就文學(xué)而論文學(xué)。
同左翼方面一味的攻訐謾罵不同,魯迅在《上海文藝之一瞥》一文中,保持了必要的客觀態(tài)度。他對(duì)鴛蝴既作批判,也示肯定。文章高屋建瓴,回顧了二十世紀(jì)初鴛蝴興起和變遷的具體情形及模式,將它當(dāng)作歷史上一個(gè)真實(shí)的現(xiàn)象來(lái)處理,并批評(píng)那些所謂的無(wú)產(chǎn)階級(jí)作家說(shuō):
但是,雖是僅僅攻擊舊社會(huì)的作品,倘若知不清缺點(diǎn),看不透病根,也就是革命有害,但可惜的是現(xiàn)在的作家,連革命家和批評(píng)家,也往往不能,或不敢正視現(xiàn)社會(huì),知道它的底細(xì),尤其是認(rèn)為敵人的底細(xì)……一個(gè)戰(zhàn)斗者,我認(rèn)為,在了解革命和敵人上,倒是必須更多的去解剖當(dāng)面的敵人的。要寫(xiě)文學(xué)作品也一樣,不但應(yīng)該知道革命的實(shí)際,也必須深知敵人的情形,現(xiàn)在的各方面的狀況,再去斷定革命的前途。惟有明白舊的,看到新的,了解過(guò)去,推斷將來(lái),我們的文學(xué)的發(fā)展才有希望。⑤范伯群、芮和師等編:《鴛鴦蝴蝶派文學(xué)資料》, 第841 -843、841、838、835 -836、795 -796、812頁(yè)。
可以說(shuō),魯迅的態(tài)度是公允的,他并未僅僅將鴛蝴看作是一文不名的新文學(xué)敵人,而是自己傳統(tǒng)的一部分,是一個(gè)可以團(tuán)結(jié)的同路人。面對(duì)抗敵御侮的嚴(yán)峻形勢(shì),魯迅主張建立最廣泛的抗日聯(lián)合戰(zhàn)線,號(hào)召全國(guó)的文藝界人士團(tuán)結(jié)起來(lái):“文藝家在抗日問(wèn)題上的聯(lián)合是無(wú)條件的,只要他不是漢奸,愿意或贊成抗日,則不論叫哥哥妹妹,之乎者也,或鴛鴦蝴蝶都無(wú)妨。”在倡導(dǎo)聯(lián)合的同時(shí),魯迅也強(qiáng)調(diào)“在文藝問(wèn)題上我們?nèi)钥梢曰ハ嗯小薄"薹恫骸④呛蛶煹染帲骸而x鴦蝴蝶派文學(xué)資料》, 第841 -843、841、838、835 -836、795 -796、812頁(yè)。一九三五年十月,《文藝界同人為團(tuán)結(jié)御侮與言論自由宣言》發(fā)表,宣言上列名者二十一人,包天笑、周瘦鵑也在其列,王稼句說(shuō):“這并不是‘恩賜’,而是鴛鴦蝴蝶派作家的自覺(jué),表明抗日救亡的決心,共赴國(guó)難。 ”⑦王稼句:《關(guān)于鴛鴦蝴蝶派》,《十月》2007年第3期。
從上面的這個(gè)例子可以看出,此次爭(zhēng)論的一個(gè)特點(diǎn)就是,斗爭(zhēng)雙方既有糾葛又有團(tuán)結(jié)。但總的說(shuō)來(lái)還是斗多于和的。比如,就在宣言發(fā)表的當(dāng)月,鄭振鐸便在《中國(guó)新文學(xué)大系·文學(xué)論爭(zhēng)集》的導(dǎo)言里批斗了鴛蝴,他說(shuō):
鴛鴦蝴蝶派的大本營(yíng)是在上海。他們對(duì)于文學(xué)的態(tài)度,完全是抱著游戲的態(tài)度的。那時(shí)盛行的“集錦小說(shuō)”——即一人寫(xiě)一段,集合十余人寫(xiě)成一篇的小說(shuō)——便是最好的一個(gè)例子。他們對(duì)于人生也便是抱著這樣的游戲態(tài)度的。他們對(duì)于國(guó)家大事乃至小小的瑣故,全是以冷嘲的態(tài)度處之。他們沒(méi)有一點(diǎn)的熱情,沒(méi)有一點(diǎn)的同情心。只是迎合著當(dāng)時(shí)社會(huì)的一時(shí)的下流嗜好,在喋喋地閑談著,在裝小丑,說(shuō)笑話,在寫(xiě)著大量的黑幕小說(shuō),以及鴛鴦蝴蝶派的小說(shuō)來(lái)維持他們的“花天酒地”的頹廢的生活。幾有不知“人間何世”的樣子。恰和林琴南輩的道貌岸然是相反。有人謚之曰 “文丐”,實(shí)在不是委屈了他們。①范伯群、芮和師等編:《鴛鴦蝴蝶派文學(xué)資料》,第805頁(yè)。
此外,瞿秋白針對(duì)鴛蝴也發(fā)表了各式議論,但由于過(guò)于散亂,容易為人忽略。范伯群教授將其歸納為五,我這里摘要轉(zhuǎn)錄如下:
一、他提出了鴛鴦蝴蝶派作品的思想實(shí)質(zhì)是“維新的封建道德”,是“改良禮教”,是資產(chǎn)階級(jí)“民族主義”……
二、瞿秋白還批判了鴛鴦蝴蝶派的“笑罵一切的虛無(wú)主義”……指出的就是那種鴛鴦蝴蝶派中“趕潮流”者的“命不可不革,也不可太革”的論調(diào),是起著消極的歷史作用,實(shí)際上是障眼法,有利于搖搖欲墜的現(xiàn)制度。
三、瞿秋白指出,鴛鴦蝴蝶派在接受白話的問(wèn)題上雖然并沒(méi)有與新文學(xué)營(yíng)壘進(jìn)行斗爭(zhēng),但他們之廢除文言主要是受市場(chǎng)公律的支配的……鴛鴦蝴蝶派的一些作品是“草臺(tái)班上說(shuō)的腔調(diào)”,是“清朝測(cè)字先生的死鬼的掉文腔調(diào)”,他們就是“運(yùn)用下等人容易懂得的話……來(lái)勾引下等人”,其作用也是很惡劣的。
四、在討論“大眾文藝”時(shí),瞿秋白指出:我們左翼文藝不大善于運(yùn)用大眾文藝的體裁,而鴛鴦蝴蝶派卻巧妙地運(yùn)用了。結(jié)果是,他們反倒可以“到處都在鉆來(lái)鉆去,窮鄉(xiāng)僻壤沒(méi)有一處不見(jiàn)它們的狗腳爪的”……鴛鴦蝴蝶善于利用舊有的大眾化的形式傳播庸俗的思想內(nèi)容……
五、瞿秋白從理論上批判了鴛鴦蝴蝶派的“趣味主義”,以趣味而達(dá)到消遣的目的,是鴛鴦蝴蝶派的寫(xiě)作信條。②范伯群:《禮拜六的蝴蝶夢(mèng)·論鴛鴦蝴蝶派》,第24-26頁(yè)。
除了魯迅、鄭振鐸、瞿秋白等人就鴛蝴的整體特征作出評(píng)介和批判外,亦有人對(duì)具體的鴛蝴作家和作品提出批評(píng),比如錢(qián)杏邨的《上海事變和鴛鴦蝴蝶派文藝》、夏征農(nóng)的《讀〈啼笑因緣〉》,就對(duì)張恨水、徐卓呆、顧明道以及小說(shuō)《啼笑因緣》等提出了嚴(yán)正指責(zé),認(rèn)為他們是“封建余孽的小說(shuō)作家”,作品雖然披上了“國(guó)難”的外衣,“所表演的思想,無(wú)疑的是充分帶有近代有產(chǎn)者的基調(diào)的”。他們的作品“是談不上技術(shù)的,雖然在偶爾一兩篇內(nèi),作者稍稍加以描寫(xiě),大部分是連新聞通信都不如”。③三處引言分別見(jiàn)范伯群、芮和師等編《鴛鴦蝴蝶派文學(xué)資料》,第 877、882、869 頁(yè)。
面對(duì)新文學(xué)的咄咄逼人,鴛蝴派或抱排斥態(tài)度,或持“新舊兼容”心態(tài),④范伯群主編:《中國(guó)近現(xiàn)代通俗文學(xué)史》(下卷),第658頁(yè),南京:江蘇教育出版社,2000。并未對(duì)此類(lèi)批評(píng)做過(guò)多回應(yīng),想來(lái)是這些“文妖”、“文氓”、“封建小市民”的論調(diào)他們?cè)缫延谏蟼€(gè)十年聽(tīng)膩味了,故而也就聽(tīng)之任之。但有一件事是真正觸動(dòng)了鴛蝴的,那便是一九三二年十二月,史量才起用剛從法國(guó)留學(xué)歸來(lái)、二十八歲的黎烈文,改革《申報(bào)》副刊《自由談》。這樣,周瘦鵑長(zhǎng)達(dá)十二年零七個(gè)月的主編生涯就此宣告結(jié)束。“于是平地一聲雷,來(lái)了個(gè)大轉(zhuǎn)變,換上了一幅新面目”。⑤王智毅編:《周瘦鵑研究資料》,第276、34頁(yè),天津:天津人民出版社,1993。但旋即,在“一九三三年春,《申報(bào)》經(jīng)理史量才不忍周瘦鵑賦閑,又在《申報(bào)》辟《春秋》副刊給他。任《春秋》副刊編輯后,周瘦鵑暗下決心,有心和《自由談》較量一番,想盡一切辦法與《自由談》爭(zhēng)奪讀者”。⑥王智毅編:《周瘦鵑研究資料》,第276、34頁(yè),天津:天津人民出版社,1993。從表面上看,由《自由談》而《春秋》,完全是《申報(bào)》自身的改革和經(jīng)營(yíng)策略,但事實(shí)上,這中間卻是摻雜了許多微妙的明爭(zhēng)暗斗的。關(guān)于此事,魯迅在《偽自由書(shū)》的后記中這樣寫(xiě)道:
最近守舊的《申報(bào)》,忽將《自由談》編輯禮拜六派的巨子周瘦鵑撤職,換了一個(gè)新派作家黎烈文,這對(duì)于舊勢(shì)力當(dāng)然是件非常的變動(dòng),遂形成了今日新舊文壇劇烈的沖突。周瘦鵑一方面策動(dòng)各小報(bào),對(duì)黎烈文作總攻擊,我們只要看鄭逸梅主編的《金剛鉆》,主張周瘦鵑仍返《自由談》原位,讓黎烈文主編《春秋》,也足見(jiàn)舊派文人終不能忘情于已失的地盤(pán)。而另一方面周瘦鵑在自己編的《春秋》內(nèi)說(shuō):各種副刊有各種副刊的特性,作河水不犯井水之論,也足見(jiàn)周瘦鵑猶惴惴于他現(xiàn)有地位的危殆。周同時(shí)還硬拉非蘇州人的嚴(yán)獨(dú)鶴加入周所主持的純蘇州人的文藝團(tuán)體“星社”,以為拉攏而固地位之計(jì)。不圖舊派勢(shì)力的失敗,竟以周啟其端……周瘦鵑作了導(dǎo)火索,造成了今日新舊兩派短兵相接戰(zhàn)斗愈烈的境界!以后想好戲還多……①范伯群、芮和師等編:《鴛鴦蝴蝶派文學(xué)資料》,第803頁(yè)。
這里魯迅講的好戲,恐怕更多的是指一九三三年以來(lái),以范煙橋主編的《珊瑚》半月刊對(duì)新文學(xué)的反攻。因?yàn)橹挥羞@些才“比較算得上論爭(zhēng)的”。②范伯群:《禮拜六的蝴蝶夢(mèng)·論鴛鴦蝴蝶派》,第27頁(yè)。《珊瑚》的第二十號(hào)上發(fā)了一篇署名彳亍的短文 《新文學(xué)家的陳?ài)E》,歷數(shù)劉半農(nóng)、魯迅、施蟄存、戴望舒、黃中、俞長(zhǎng)源、老舍、樓建南、葉紹鈞、吻云、蘇鳳、杜衡、滕固等新作家都曾在鴛蝴的雜志上發(fā)表過(guò)作品。文章單列姓名以及雜志的名稱(chēng),不作任何評(píng)論,但意圖卻很明顯,那是要揭新文學(xué)的老底。為了更進(jìn)一步地表明態(tài)度,《珊瑚》上自第十三期起就開(kāi)辟“說(shuō)話”欄目,對(duì)中國(guó)的現(xiàn)代文學(xué)創(chuàng)作進(jìn)行了系統(tǒng)總結(jié)。認(rèn)為“新文學(xué)派里,確有當(dāng)?shù)闷稹隆瑝虻蒙稀膶W(xué)’的作品。 《禮拜六》派里,也有極‘新’,極‘文學(xué)’的作品”。 關(guān)于“九·一八”和“一·二八”的作品,對(duì)于新文學(xué)作家只注重形式不注重內(nèi)容的片面批評(píng),也表示了異議,“才子穿了西裝,佳人剪了頭發(fā),放到小說(shuō)里,就不算鴛鴦蝴蝶了,把自殺做結(jié)局,就算文藝的至上者了,這種觀念,我們也得轉(zhuǎn)變些”。“要是嚕離嚕蘇,記些新式簿記,或是舊式流賬,都不配稱(chēng)他為好小說(shuō)。”③轉(zhuǎn)引自范伯群主編 《中國(guó)近現(xiàn)代通俗文學(xué)史》(下卷),第 658-660頁(yè)。
這次的論爭(zhēng),同樣是一攻一守,而且其中又牽扯著“京派”、“海派”的爭(zhēng)斗,所以看上去不免有些情形復(fù)雜。而事實(shí)上呢,雖然京派批判的對(duì)象包括了鴛蝴,但自有杜衡等海派人士的回應(yīng),所以他們又是不應(yīng)戰(zhàn)的。而此后戰(zhàn)爭(zhēng)肆虐,新文學(xué)的作家們紛紛奔走抗日,上海成為“孤島”,這所謂的新舊之爭(zhēng)又不了了之。以后的時(shí)間,雖有人舊事重提,④葉素:《禮拜六派的重振》,佐思,《禮拜六派新舊小說(shuō)家的比較》,見(jiàn)魏紹昌編《鴛鴦蝴蝶派研究資料》(上卷),第116-131頁(yè),上海:上海文藝出版社,1984。但畢竟微乎其微。倒是在一九四七年的時(shí)候,朱自清寫(xiě)了一篇《論嚴(yán)肅》,態(tài)度平正,對(duì)鴛蝴作了恰當(dāng)?shù)脑u(píng)論。
- 東吳學(xué)術(shù)的其它文章
- 從回憶到閱讀:低收入家庭對(duì)兒童語(yǔ)言和讀寫(xiě)發(fā)展的影響*
- 現(xiàn)代詩(shī)語(yǔ):陌生化張力的新思考
- 差異還是障礙?理解神經(jīng)發(fā)展障礙的文化問(wèn)題*
- 現(xiàn)實(shí)關(guān)懷·價(jià)值關(guān)懷·理論關(guān)懷
——評(píng)《馬克思恩格斯弱者權(quán)益保護(hù)思想》① - 兩大詩(shī)學(xué)場(chǎng)域的開(kāi)拓與話語(yǔ)建構(gòu)
——尹錫南《梵語(yǔ)詩(shī)學(xué)與西方詩(shī)學(xué)比較研究》①之解讀 - 闖入者、誤-會(huì)、身體的焦慮
——從讓-呂克·南希的《闖入者》談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