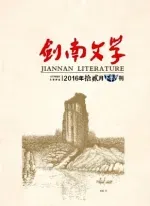飄 逝
◆ 劉 琴

背著一本沉重的專業書,來到圖書館,本來是打算復習復習的,因為下周有次檢測。但一坐下來,就望著窗外飄飛的細雨發呆。幾天前,天氣還悶熱得讓人心情狂躁,可突地一場秋雨下來,炎熱愣是被席卷一空,甚至發出澀澀的寒意來,讓人好不習慣。隨著秋雨而來的,當然還有秋風。綿綿的細雨,看似柔弱無力,而一旦和秋風結成伴,便立即有了席卷宇宙,橫掃六合之勢,硬是將整個季節都換了顏色。“悲哉秋之為氣,蕭瑟兮草木搖落而變衰!”那個第一個站在歷史的高坡上唱秋之悲歌的人已經不見了。“秋風起兮白云飛,草木黃落兮雁南歸!”后來跟著唱和的人也已逝去多年。現在,秋風又起,伴著這落落秋意,悲不悲,我不知道,只覺得前些日子還枝繁葉茂碧色濃郁的櫻花樹,經不起這風雨的折騰,只幾日光景,已疏落得讓人心疼,枝頭幾片寥寥的黃葉,一副風燭殘年之態,全不似當初的那副生機盎然。不禁有些感嘆,這才是初秋啊,怎已零落到這般田地,我不由打了個寒顫。
又是一陣風起,幾片黃葉飄飄蕩蕩,我知道,葉子終是要落盡的。
忽然想起父親來,他離開才不到一年,而我卻覺得好像已經過了十數載,甚至幾十個春秋。記不得他離開時,我是怎樣的痛不欲生,只隱約覺得好像自他離開后,我就再也沒真正地笑過了。人都說時間是最好的療傷藥,可我的傷口卻故意在外面結痂,不讓藥物進入,病菌在里面肆無忌憚地發炎化膿。而我又不敢讓醫生揭開這層疤,算了,就這么隱隱地疼吧。
也許是從小就被父母寵壞了吧,我只是一味地要求身邊的人關心我愛護我,滿足我合理不合理的要求,卻似乎從來沒認真關心過身邊的人,也從未意識到身邊的人同樣也是需要我的關心的。記得好像是中學的時候,學了朱自清的《背影》,當時還真被作者父親那無言的愛感動了一通,于是一時興起,決定等到周六的時候也打量打量我自己的父親(我是住校生,每周周六下午回家,周日晚上返校,一周只在家里呆一天)。當時,我好像是以一種欣賞的態度決定觀察父親的,因為在我心里,父親是能夠讓我一生撒嬌依靠的,他有力的臂膊結實的肩膀是我永遠的港灣,而歲月似乎是不可能在他身上留下任何印記的。
父親是個建筑工人,每周六下午收工后,騎著一輛破舊的黑色自行車,到公交車站接我。車子沒有腳架,可憐巴巴地靠在一棵高大的梧桐樹身上。父親長得不高,站在一旁,在梧桐樹的映襯下越發顯得矮小瘦弱了。每有一輛公交車到站,他便上前查看。一看見我,便露出一臉的歡愉,和我打了招呼,才轉身去推車。于是,在漸漸沉下來的暮色中,父女兩個,移動著兩個差不多長的影子,伴著自行車唧唧嘎嘎的交響曲,向家里走去。
趁著和父親說話的時候,我開始既定的計劃,偷偷打量起我那個應該孔武有力的父親來。或許,這是我有生以來第一次認真地看我自己的父親吧,心一下子懵了——這哪里是我的父親啊!我記得照片里的父親明明是很年輕的,臉上雖不是堆滿了肉,可也不至于這般黑瘦啊,還有一片片的曬斑。本來一雙大眼睛加上又長又彎的睫毛是讓很多女生都羨慕不已的,可如今卻深凹下去,在瘦削的臉上顯得有些突兀,白色的眼球里又無故添了許多暗黃,還有那我記憶中應該平整的額頭,不知什么時候,留下了幾道深深的皺褶。看到這一切,我原本歡樂的心情一下子煙消云散。恍惚中想起,父親來接我,總是和我一起走路回家。當我吵著累了餓了,要父親載我時,他總是說:“乖幺女,我們兩個擺會兒龍門陣就到家了,多快的。”然后我就撅著嘴,一邊抱怨一邊很不情愿地和父親一起走路。
回家的這段路并不是很長,但全是上坡路,就是一個人騎自行車都很累,要是再載上我這么一個玉環一樣的女兒,那該是多么辛苦的一件事啊!更何況父親來接我時,是剛收工,早就累得精疲力竭了,哪里還有力氣載我啊。可當時的我根本就沒想過這些,只一個勁埋怨父親,甚至懷疑他是不是不愛我了,連載我一下都不愿意,所以對他的態度總是很差。想到這,我心里更加難受,但又不敢表露出來,只好拼命給父親講笑話,待那酸澀的眼淚流下來時,我就可以理直氣壯地說是讓笑話給逗的。父親是個硬漢,從不肯輕易掉眼淚,也不允許我掉眼淚,他愛看水滸,經常說寧肯掉頭不許掉淚,我便也養成了不哭的習慣。而看著父親笑起來滿是皺褶的臉,我終于明白,原來父親是會老的,照片上的那個父親早就被時間啃食的面目全非了。
不忍再看父親的臉,于是,我伸手去拉他的手,卻被割得生生的疼,那上面布滿了大大小小深深淺淺的裂口,全然一塊龜裂的木頭。忽然想起來,一到冬天,父親就用母親洗衣服的刷子刷手,每當把那些灌在裂口里的沙石洗出來后,鮮紅的血液也就跟著流了出來,然后他就用工業膠布把傷口纏起來。而愚蠢如我,竟還嘲笑他:“爸,人家彈古箏纏指頭,你也學著人家彈火磚呵!”而此時,我無話可說,只是用自己的手,緊緊地拽住父親的手。
第二天返校,父親照例把我送上公交車,上車時,我對父親說了句路上小心,然后就回學校了。后來聽母親說,因了我那句話,父親興奮了一個星期,不停地說:“我幺女長大了,曉得關心老漢了!”聽母親那么一說,我頓感羞愧難當。十多年來,父母不知說了多少關心我的話,做了多少關愛我的事,應該說他們的青春都澆灌在了我的身上,而我從來就認為那是理所當然的,反而有時稍有不順,就抱怨不停,而自己居然從來沒有說過一句關心他們的話,甚至連這種意識也沒有。一句“路上小心”,就足以讓父親擁有一周的開心快樂。那他們給我的三春之暉,豈是我這一生消受得起的幸福。記得中學老師說過這么一句話:“你們都是獨生子女,你們的父母都是第一次當父母,你們怎么能要求他們做的像個經驗十足的老者呢!”現在想來確實,他們也是剛從孩子的角色變為父母,什么都不知道,而我們卻要求他們做著做那,即使他們已經做得很好,我們還挑三揀四,嫌他們不夠稱職,但卻從未檢討過自己是否是個稱職的孩子!
當時想效仿朱自清,也寫一篇《面容》來表達自己對父親的慚愧,但終因了學習繁忙的借口而擱下了,只是把所有的感動留在了心底。更何況,我總覺得來日方長,以后有的是時間來觀察父親,了解父親。
上大學后,我似乎也開始懂事了,第一次打電話回家時,讓父親要保重身體,沒想到竟讓父親在那頭哽咽得不能言語。現在想來,一個錚錚鐵漢,竟讓自己小女兒的幾句話弄得淚流滿面。
大一快結束的時候,父親病了,病得很重,人也變得更加黑瘦了,連手臂上那些曾做過我小時候的玩具的肌肉都瘦得不見了。大家都說得了那種病是很痛的,病人脾氣也會跟著變得很壞,經常向家人亂發脾氣。可是父親自從得病以來,從未向我和母親發過一次脾氣,也沒在我們面前叫過一次疼,甚至連一聲輕輕的呻吟也沒有,只是變得異常得沉默。每當我問他有沒有哪里痛時,他只是淺淺地說不礙事。
沒到半年時間,父親就離開了。我還是因著學習的借口,沒能陪在父親身邊,和他走完人生的最后一段路程。只是到他離開前的幾個小時才從學校匆匆趕回家,為他送終。應該是失去了意識吧,當我守在他的床邊時,第一次聽到了父親的呻吟。而那聲音像亂箭一樣,箭箭射在我心口。不過我沒有哭,因為父親不準我哭,母親也不許我哭(家鄉有一種習俗,人死后道士來開路以前,家人是不能哭的,否則死者無法順利轉世)。
父親終于還是走了。
秋風繼續吹著,葉子繼續飄落著,樹枝也繼續搖晃著,無論樹木愿不愿意。但是樹葉今秋落了,明年春來,又可繁鬧依舊。而人呢?
我沒有再想下去,停止了發呆,拿出壓在手肘下的書,算不上認真地看了起來……
(西南科技大學生命科學與工程學院生物技術080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