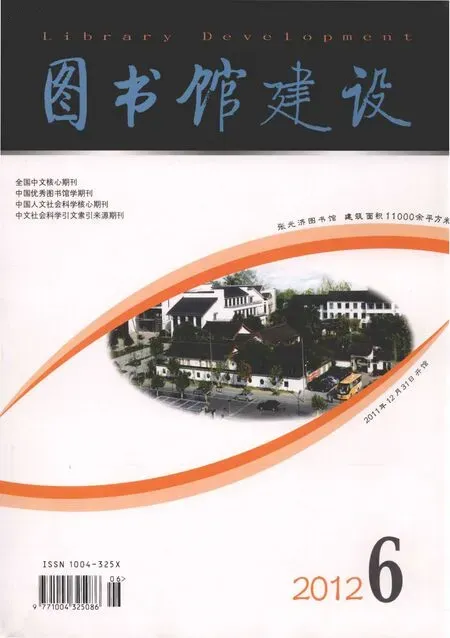加強圖書館學術史研究的幾點思考
韓 玨 (深圳職業技術學院圖書館 廣東 深圳 518055)
近年來圖書館學術史研究得到了業界的廣泛響應[1],如吳年對“新圖書館運動”及這一時期的圖書館學術史進行了研究[2-5],還有一些研究者對某些圖書館學家及學術流派進行了研究。業界對圖書館學術史研究的重視表明圖書館和圖書館學發展正在走向成熟。為使圖書館學術史的研究和發展能夠順利進行,本文針對其中的幾個重點問題進行商討,以得到方家的指教。
1 圖書館學術史研究的意義
古代圖書館學術的發展在一定程度上是由目錄學承擔的,我國古代目錄學在長期發展中形成了“辨章學術,考鏡源流”[6]的傳統,體現了圖書館學術發展沿革。隨著網絡時代文獻數量和文獻載體類型的增多,目錄學的這種功用日漸衰微,學科學術史逐漸承擔起記錄學術發展沿革的重任,這是科學文化發展的必然結果。圖書館學術史成為研究圖書館和圖書館學學術思想的專科學術史。
學術史亦稱學術思想史,相對一般“史”而言,處于更高的層次。如果一般“史”只是描述“是什么樣的”,那么學術史除此之外還要給出“何以如此”的解釋。學術史的任務是描述并解釋歷史,這不僅要求史實確鑿,還要論述有理。就理論層次而言,與哲學史較為接近的是思想史,其次是學術思想史。李澤厚喜歡用思想史的概念來描述,因而他的一些理論著作都以思想史冠名,如《中國古代思想史論》、《中國近代思想史論》等[7]。學術史重視學術理論變化,與思想史重視哲學思想及政治哲學思想的變化有所不同,如梁啟超關于清代三百年學術發展演變的論述就是典型的學術思想史研究。
我國近代圖書館已經經歷了百余年的歷程,圖書館在長期發展中積累了豐富的思想資源和學術資源。然而,我國圖書館界較為重視學術資源的研究和梳理,對于思想資源的研究相對較少,目前已知的僅有《20世紀中國圖書館思想論綱》[8]。深化圖書館學術史研究有助于開展圖書館學術思想史研究,進而推進圖書館學理論研究的發展。例如,通過對20世紀80年代和21世紀初圖書館學術發展變化的研究可以發現,20世紀80年代的圖書館學理論研究較為注重圖書館“效率”問題。圖書館界在這樣的價值觀指導下開展了諸如“全國文獻資源布局”[9]、“圖書館事業發展戰略研究”[9]等學術活動,在圖書館學術史上頗具影響。而在21世紀初的圖書館學研究中,圖書館服務平等理念成為業界研究和倡導的重要理念,平等享受圖書館服務成為圖書館精神的重要支柱。平等和效率是哲學中的重要概念,研究圖書館效率和平等服務與不同圖書館學術發展階段的主導思想密切相關。因此,如果從哲學、社會學、政治學、倫理學等視角審視圖書館學發展的一些現象,則可使一般的圖書館學術史研究逐漸上升到圖書館學術思想史研究,從而得出更使人信服的結論。
圖書館學術史研究有助于理性把握圖書館學研究的本質問題。我國開展圖書館學研究的時間較短,研究層次不深,研究課題和研究方向具有一定的盲目性。圖書館學術史研究有助于學者從圖書館學發展的規律出發,將研究中的盲目性轉變為遵守圖書館學發展規律的自覺性。例如,關于圖書館學研究對象的研究是圖書館學術史發展中的一條重要線索,可以通過眾多學者幾十年的研究發現圖書館學研究對象的發展和變化。在19世紀初圖書館學建立之初,圖書館學的研究對象被認為是從事圖書館工作所具有的知識與技術的總和(亦稱“總和說”)[10],此觀點的代表人物有德國的施雷廷格、艾伯特等。20世紀以來,世界范圍的圖書館事業得到了空前的發展,圖書館學研究對象從“總和說”逐漸發展為“事業說”,而且這種觀點長期在蘇聯和我國圖書館學界占有主導地位。“50年代劉國鈞先生倡導的‘事業說’及后來出現的‘矛盾說’、‘規律說’,雖然其表述有所不同,但都是在探尋‘圖書館事業’的矛盾、規律,仍屬‘事業說’。而且80年代出現的‘抽象圖書館’、‘層次說’、‘活動說’、‘過程說’未脫離此宗旨”[11]。“總和說”的問題在于過于強調技能因素,這導致圖書館學朝著技術化方向惡性發展;而“事業說”的缺點在于將圖書館學研究限定在圖書館這一狹小圈子內。80年代出現的“交流說”擴大了圖書館學的研究視野,但是忽視了知識組織等問題。20世紀末,圖書館界提出了圖書館學研究對象的“知識集合說”和“文獻可獲得性說”等,反映了圖書館步入網絡時代對圖書館學研究對象的新認識。站在學術史視角考察圖書館學研究對象的變化,有助于發現圖書館學研究的一些規律和特征,深化對圖書館學的認識,使對圖書館的本質性追問一步步趨向本真。
圖書館學術史研究是通過對學術發展的比較研究而深化圖書館學理論研究的。這不同于理論命題的求證,因為求證理論命題具有一定的難度,需要一定的理論抽象和嚴密的邏輯推理論證,如“知識集合說”[11]和“文獻可獲得性說”[12-13]就反映出學者的學術睿智和知識功底。相對而言,圖書館學術史研究是對圖書館和圖書館學發展的深層思考,其得出的一些規律性認識反映了學科理論的深化過程,為圖書館學研究和圖書館管理提供了寶貴的歷史經驗。
2 圖書館學術史研究范疇
圖書館學術史研究與圖書館史、圖書館學史和圖書館思想史的研究之間都有著密切的聯系,同時它們之間又相互區別,而且研究其異同是十分有必要的。學科的發展總是要經歷由粗到細的過程,學科中的某些領域將隨著研究成果的豐富而從學科中逐漸剝離出來。
2.1 與圖書館史研究的聯系與區別
圖書館史研究是圖書館學研究中發展較早的領域,早在20世紀80年代以前我國圖書館學專業本科教學就普遍開設了圖書館史課程,于80年代初設置了圖書館史研究方向,而且研究成果頗豐。圖書館學術史與圖書館史之間可說是一種源與流的關系,圖書館史是圖書館學術史研究的基礎,圖書館史蘊含的豐富材料為圖書館學術史研究提供了諸多研究線索和事實材料。然而,圖書館學術史研究的范圍又不僅限于圖書館史研究,它還包括圖書館學研究的歷史發展。對于圖書館發展的研究,圖書館史重視的是發展的外部因素影響,而圖書館學術史除此之外還十分關注發展的內部因素,關注圖書館學對圖書館發展的影響。例如,21世紀初的圖書館史研究關注的是這一時期社會政治、經濟、文化、科技對圖書館的重要促進作用,而21世紀初的圖書館學術史研究則不僅包括對上述社會影響因素的深入研究,還關注圖書館所受的自身因素的影響,如圖書館學研究對圖書館發展的影響。對此,有的學者認為我國圖書館的百年發展曾經歷過3次重要的思想啟蒙,第一次是20世紀二三十年代的新圖書館運動時期,第二次是20世紀80年代的中國圖書館大發展時期,第三次是21世紀初的理念創新時期[9]。這3次思想啟蒙各有特點,并且形成了不同的核心價值觀,這些價值觀與理念之間既存在聯系又相互區別。例如,第三次思想啟蒙提出要“尋找失落的圖書館精神”,即找回“平等服務”、“免費服務”等基本核心價值,這實質上源于第一次思想啟蒙所倡導的“平民理念”,只不過該理念發展至21世紀初已轉變為“讀者權益”。諸如此類研究顯然是圖書館學術史研究要關注并深入探討的。
2.2 與圖書館學史研究的聯系與區別
圖書館學術史包括圖書館學史的基本內容,此外還包括圖書館史的相關內容,即對這些內容的學術探討。例如,圖書館服務是否收費等與圖書館管理相關的問題在圖書館史研究中會有所涉及,但是在圖書館學史研究中一般不予討論; 而在圖書館學術史研究中則會記錄對此問題進行的學術探討,如論述圖書館服務的公益性質、指出免費服務是圖書館服務的主流、論證有償服務是圖書館特定環境下的產物、具體地論述免費服務和有償服務的產生環境等。
圖書館學史與圖書館學術史的區別表現為對某些問題的研究方法不同。圖書館學史注重全面描述某一研究本身,會涉及到當時產生這一理論的社會因素和文化學術因素以及這一理論的發展過程、主要代表人物、理論突破和理論局限等,是一種全景式的描述,如對20世紀80年代“文獻交流”理論的描述。而圖書館學術史不只關注某一研究本身,還關注與其有內在聯系的研究及其發展演變過程,并通過探析其發展演變過程得出某些規律性的認識。由此來看,圖書館學術史的研究方法與圖書館學史的研究方法有相似之處,即關注的不是一個點,而是一條連續的線。因而,圖書館學術史研究是更具理論深度的研究。
2.3 與圖書館思想史研究的聯系與區別
盡管我國目前圖書館思想史研究尚處于初始階段,但是仍有必要將其與圖書館學術史聯系起來加以研究。總體來看,圖書館學術史與圖書館思想史對于某一問題的著眼點不同,圖書館學術史關注某一問題發展中的學理、學派和技術工具的變化,圖書館思想史則更加關注某一問題的相關社會環境變化及由此帶來的管理思想的變化。例如,圖書館學術史對于我國文獻信息資源共建共享問題的探討和描述,20世紀50年代的關注點在于《全國圖書協調方案》[14]的協調組織和聯合目錄的重要作用,20世紀80年代的關注點在于“全國文獻資源布局”時期涌現的各種學術流派,如“學科布局方案”、“系統布局方案”、“地區布局方案”及綜合性的“三級布局方案”等[15];而圖書館思想史對于我國文獻信息資源共建共享問題的探討和描述,則較為關注不同時代文獻信息資源共建共享的價值追求、不同時代文獻信息資源共建共享形式的主要特征及社會環境影響等。文獻信息資源共建共享在不同時代有不同的價值追求。圖書館共建共享在印本書時代的價值指向是為科學研究服務,而到了網絡時代,信息傳遞成本大大降低,這時的共享不再是僅為科學研究服務,共享服務的范圍擴大到普通民眾。例如,上海中心圖書館的組建就很好地反映了這種變化,上海中心圖書館不僅包括上海交通大學圖書館、上海社科院圖書館等研究型圖書館,還包括一些區縣圖書館和街道圖書館等公共圖書館,而且共享范圍逐步擴大。從文獻信息資源共享的組織形式來看,20世紀80年代的“全國文獻資源布局”強調三級布局①,而網絡時代的共建共享則是優先選擇開展難度較小且有共建共享傳統的系統和區域進行,如運行平穩的CALIS(China Academic Library & Information System,中國高等教育文獻保障系統)、NSTL(National Science and Technology Library,國家科技圖書文獻中心)、上海中心圖書館、廣東圖書情報協作網絡等。圖書館思想史研究就是關注此類具有全局性的重大問題。
3 加強圖書館學術史研究的建議
3.1 重視對學術發展中重要階段和事件的研究
圖書館學術史研究是對于圖書館學術發展的研究,其中對于學術發展階段的劃分非常重要。在圖書館學術史研究的初期將學術發展階段劃分準確是較為困難的,只有在學術研究進行到一定時候且研究成果較為豐富時,學術發展階段才可能顯現并劃分出來。對此筆者建議,在當前學術發展階段尚不十分明確時,以一些重要的事件為核心進行劃分,如圖書館創建初期的新圖書館運動,20世紀80年代的“全國文獻資源布局”,20世紀90年代的特殊圖書館服務,21世紀初的“21世紀新圖書館運動”及人文圖書館學、制度圖書館學、技術圖書館學等應用圖書館學研究的發展,等等。近年來圖書館學術史研究一反常態地顯現出蓬勃發展的勢頭,程煥文、范并思、張樹華、吳 年等知名學者紛紛涉足這一領域,并且在其論著中均論述了圖書館學術史的相關內容。圖書館學術史研究之所以越來越受到重視,是因為業界正在大力倡導免費服務、平等服務等理念。由于這些新理念在我國圖書館發展初期就已有了一些宣傳和提倡,而且有長期的圖書館實踐,所以發展這些理念實際上是對原有理念的繼承,是在續接“公共圖書館精神的歷史鏈條”[16]。這種“續接”之中蘊含著發展,如從“平民理念”到“讀者權益”的轉變。圖書館界在20世紀初提倡平等服務、免費服務理念更多地是從人文關懷的視角考慮的,因而這些理念并未上升到制度的高度。而21世紀初,圖書館界在公民權利的基礎上提出平等服務、免費服務理念。公共圖書館為公民提供免費的圖書館服務,由于其設置主體是政府,因而這種普遍均等的服務有了制度上的保證。我們如果在圖書館學術史研究中對同類現象進行認真梳理,便能科學地解釋現象背后隱含的本質,從而提升圖書館學術史研究的水準。
3.2 重視對學派和圖書館學家的研究
學派的形成和發展是圖書館學多元化發展的重要標志,是學科趨于成熟的表現。20世紀80年代以來,我國出現了一批圖書館學學派,這些學派的代表者均較為活躍,而且研究成果頗豐。例如,20世紀80年代以周文駿、宓浩、黃純元為代表的“知識交流學派”,以彭修義為代表的“知識學派”,以劉訊為代表的“波普爾學派”;20世紀90年代末以黃純元為代表的“圖書館機構/制度學派”,以王子舟為代表的“知識集合學派”,以梁燦興為代表的“文獻可獲得性學派”;21世紀初以蔣永福為代表的“人文圖書館學派”,以李國新為代表的“圖書館自由學派”,以范并思為代表的“公共圖書館精神學派”,等等[17]。研究這些學派的產生與發展、學派與社會學術文化的關系、某一圖書館學家在學術發展中的思想歷程,都是頗為重要的課題。例如,黃純元于20世紀80年代初是“知識交流學派”的代表學者,90年代末是“圖書館機構/制度學派”的代表學者,研究其學術思想發展歷程有助于了解從“知識交流”到“機構/制度”再到“公共圖書館精神”的學術發展路徑,結合圖書館學家理論發展的學術史研究深層的學術因果關系。
3.3 重視國際學術文化交流和影響
我國圖書館事業發展和圖書館學研究受國外的影響較大。清朝末年五大臣考察國外政治、經濟、文化時對國外圖書館留下深刻印象。湖南圖書館等早期圖書館在創建時曾派人員考察日本的圖書館,并從日本購回一批圖書。民國時期,韋棣華在武昌創辦文華圖書館學專門學校期間,曾派沈祖榮等人赴美國學習圖書館先進的辦館理念和技術,1917年他們學成回國后掀起了新圖書館運動,宣傳平等服務、免費服務等平民圖書館理念,使我國圖書館教育在創辦之初便有了正確的引導。20世紀50年代,我國受蘇聯圖書館學的影響較大,蘇聯的圖書館體制和書目方法給我國圖書館界很多啟發,彭斐章、趙世良等老一輩圖書館學家在蘇聯留學,加強了中蘇兩國圖書館界之間的交流,并引入蘇聯的推薦書目、聯合目錄、專科目錄等新技術、新理念。20世紀80年代末,歐美國家和日本的圖書館思想重新引起我國圖書館人的關注。21世紀初,國外的圖書館制度和理念促使我國圖書館界在信息社會到來時重新確立了公益、公共的性質。由此可見,圖書館學術史研究不能忽略與國際圖書館界進行學術文化交流,只有深入探討國際圖書館和國外圖書館學對我國的影響,才能很好地解釋我國圖書館學術史發展中的某些現象。
4 結 語
目前我國圖書館學術史研究尚處于起步階段,隨著研究的深入,研究資料的收集、建庫將成為圖書館學術史研究的重要工作。建立圖書館學術史資料數據庫有助于研究者掌握此領域的研究動態和成果,避免重復研究。如果我國圖書館學術史研究能夠在此基礎上再考慮未來形態和學科結構問題,將具備更為詳實的研究資料。
注 釋:
①三級布局,即一級布局是國家級布局,由國家圖書館牽頭;二級布局是省、市、自治區布局,由省級館或實力較強的高校館作為牽頭館;三級布局是系統布局,其又可分為三級網絡結構,包括本系統的文獻信息中心、本系統的一些專門學科文獻中心、本系統的基層圖書情報單位。
[1]陳光祚.重視圖書館學學術史研究[J].圖書館論壇, 2006(6):20-21.
[6]小議辨章學術和考鏡源流的思想哲學[EB/OL].[2011-12-01].http://www.zhazhi.com/lunwen/zxsh/sxzx/15140.html.
[7]李澤厚, 劉緒源.該中國哲學登場了:李澤厚2010年談話錄[M].上海:上海譯文出版,2011.
[8]吳星溪.20世紀中國圖書館思想論綱[J].圖書館, 2002(2):1-7.
[9]韓繼章. 中國圖書館百年史中的三次思想啟蒙[J]. 圖書館, 2006(1):3-10.
[10]王子舟.圖書館學研究對象的認識過程及范式特征[J].江西圖書館學刊, 2002(3):4-8.
[11]王子舟.知識集合論初論:對圖書館學研究對象的探索[J].中國圖書館學報, 2000(4):7-12.
[12]梁燦興.可獲得性論的文獻及相關概念[J].圖書館, 2002(1):9-15.
[13]梁燦興.可獲得性論的知識自由和知識共享闡釋:重新定義可獲得性論[J].圖書館, 2003(6):9-11.
[14]張樹華, 趙華英.新中國圖書館事業發展的一次浪潮:記“全國圖書協調方案”及其協作、協調活動[J].中國圖書館學報, 2009(3):21-26.
[15]葉繼元. 高校外刊資源合理布局模式與實施辦法新探[J]. 江蘇圖書館學報, 1995(4):24-25.
[16]梁燦興.重續圖書館精神的歷史鏈條:蘇州年會隨感[J].圖書館,2004(6):56-57.
[17]柯 平, 趙益民, 高 爽. 改革開放30年圖書館學基礎理論研究回顧與思考[J].中國圖書館學報, 2008(5):72-7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