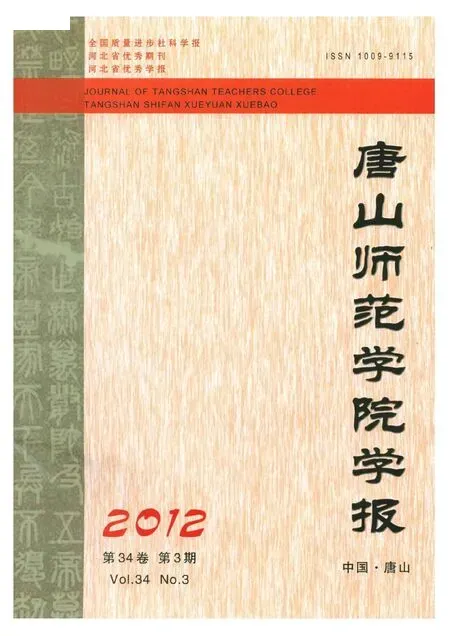邀約記憶:在創造與還原的裂縫中窺見理論的屬性
欒靜艷
(河北師范大學 文學學院,河北 石家莊 050000)
邀約記憶:在創造與還原的裂縫中窺見理論的屬性
欒靜艷
(河北師范大學 文學學院,河北 石家莊 050000)
理論被視為一種記憶,它不僅具備了個人記憶的主體性、客觀歷史性以及自我完善、自我超越屬性,而且吸納了個人記憶作為對人類普遍生存困境的關注的公共襟懷,重建理論具有公共政治意味的政治維度,是理論的方法。
理論;個人記憶;集體記憶;主體性;客觀歷史
近年來,隨著解構主義思潮的引進,文藝理論界及其文藝理論工作者對文藝理論的基礎概念、基本問題,如什么是文學、什么是理論等進行了前所未有的大反思,這些反思打破了我們過去本質論的、大一統的看問題的思維方式。通過歷史的、復數的思維方式考量這些問題,為我們重新深入認識文學、理論奠定了基礎。目前關于文學何為的探討已經很多了,而關于理論何為的探討研究卻少之又少。其中探討較多且較深刻的當屬卡勒的《文學理論入門》,在此書中,卡勒通過對“性”、德里達的“異延”的分析,提出了理論的四個屬性,即理論是對常識的批評;理論是分析和話語;理論是跨學科的;理論具有反射性,是關于思維的思維。毋庸置疑,這種理論觀關于理論屬性的洞察是相當深刻全面的,但仔細分析這四重屬性,我們會發現其思辨性較強,道出的是理論作為高高在上的“理想之域”的不可觸及性,理論似乎就是一種只可逐漸趨近的理想。那么既可以觸及又相對具體些的理論具有什么樣的屬性呢?
一、個人記憶·個人·歷史
個人記憶是見證文學敘事中經常使用的一個概念,它指的是災難幸存者的個人記憶,這種記憶基于個人的直接過去經歷,既是個人內心深處隱晦的、富有震撼力的一幕,也是對歷史的另一種客觀描述。當然,這里所說的個人記憶是遠遠超過災難幸存者的,個體內心深刻的、富有洞見的記憶,表現于文學或文學創作中乃是一種文學記憶。
記憶是個體與世界建立聯系時所形成的感受、體驗和經驗,它作為一種主體的精神存在總是以各種或隱或現的方式左右著人們的生活。因此,個人記憶既是個體經驗得以形成的基礎,又是個體生命史的組成部分。作為個體生命史的組成部分,記憶承載著個體過去的想象,表達著微妙而復雜的生命體驗,對個人記憶的尊重就是對個體生命的尊重。依托于個體生命的心理流變,記憶呈現為一種變動不居的狀態,具有較強的可塑性,包括以現時性的眼光對記憶的重審,一定程度上,它是個體生命的發生和存在具有創造性品格的根本依據,然而這種創造性也是有限的。羅蘭·巴特“設想通過一種先鋒派的語言形式,來抵制資產階級的意識形態,并追尋一種純粹的無止境的語言實驗,同時賦予這種寫作以一種革命性的意義。他也同樣設想除去資產階級殘余,甚至清除傳統和記憶”[1,p118]。巴特設想的這種激進式的寫作是一種寫作自由的理想境地,但對于這種自由,巴特也始終搖擺不定。他認為一位作家的各種可能的寫作是在歷史和傳統的壓力下被確立的,“因此存在一種寫作史,但是這種歷史有其雙重性:當一般歷史提出(或強加)一種新的文學語言問題時,寫作中仍然充滿著對先前慣用法的記憶,因為語言從來也不是純凈的,字詞具有一種神秘地延伸到新意指環境中去的第二記憶。寫作正是一種自由和一種記憶之間的妥協物,它就是這種有記憶的自由,即只是在姿態中才是自由的,而在其延續過程中已經不再自由了……”[1,p119]。巴特認為個人寫作的自由應該可以超越于歷史、現實、社會壓力之上,但字詞的記憶形式卻頑強地把寫作拉回到過去的狀態。巴特也不得不承認寫作本身,也具有自由和妥協的頑強性。個人記憶雖然依托于個體生命的心理流變,呈現出一種變動不居的狀態,具有創造性的品格,但這種創造性也是有限的。人是社會的存在,亦是一種歷史的存在,特定歷史的精神履歷,在個人記憶中留下深刻的印跡,它具有還原歷史、補充歷史,并受到客觀歷史的制約。將個人記憶視為一種歷史,承認個人記憶的歷史功能、歷史制約性,一方面是肯定了記憶的客觀性和實證價值,而更重要的一方面是將歷史視為一種具有“歷史化”意味的人類的共同記憶、集體記憶,是一種廣義上的歷史。
總而言之,個人記憶作為個體內心深刻的、具有洞見的記憶,它具有其自身的獨特性——既依托于個體生命的心理流變的自由度,表現出強烈的創造性,同時又具有人類共同記憶的“歷史化”意味。這二重性看似矛盾,卻又聚交于個人記憶互為張力,并且通過文化認同在某種程度上創造一個想象的共同體來實現個人記憶向集體記憶的挺進以及個人記憶的自我變遷、自我完善。認同是“個人與他人、群體或模仿人物在感情上、心理上趨同的過程,是個體與他人有情感聯系的原初形式”[2]。而“想象的共同體”又是基于一種濃厚的、沉浸在“集體的信奉狀態”之中的能夠超越阻隔的關系,因此建立在文化認同基礎上的共同體想象則構成了個人記憶具有“歷史化”意味的集體記憶,使它打上了客觀存在的印跡。然而個人記憶本身又“不是一成不變的客觀存在物,隨著時間的流失和生命自身遺忘本能的作用,記憶常會出現流失、模糊乃至變異”[3]。但這種流失、模糊乃至變異并不意味著文化風格的喪失,相反地,“個人記憶將會隨著時間和空間賦予的新的內容,在內部進行重新組合、重新表述,然后以嶄新的姿態又不失集體記憶的超越自我,反而能使集體記憶的生命力更加旺盛,更加富有生機和活力。這種變化并不是它自身變成了另外一種質態的東西,而是它自身內部的不斷擴充、豐富、增長和深化,用辯證法的語言講是自我發展、自我運動、自我完善”[4,p136]。
二、理論·個人記憶
集體記憶作為一種建立在文化認同基礎上的文化實體,是一個民族或社會共同體通過歷史的積淀與延續展現出來的一種文化上的根本記憶,是一個民族賴于組織個人和集體生活的意義結構,它內化在民族的靈魂中,深入到民族的血液里,已然在群體的思維范式、價值觀念、社會心理等深層結構中保存下來,體現著一個民族對自己生命存在方式的選擇、認可與認同。社會成員正是沉浸在這種“集體的信奉狀態”之中,靠著一種“對作為一個整體的群體之高大權威形象的真心實意的崇拜”來維系民族的存在、團結以及道德情感風尚。與具有“歷史化”意味的個人記憶——集體記憶,享有的“集體的信奉”以及“真心實意的崇拜”相類,理論應該作為一種記憶,一種能夠在理論研究者群體中激起集體信奉、真心實意崇拜的記憶,而非一種意識形態,權力意志角逐的手段、工具。
與此同時,考慮到個人記憶的多重屬性,即依托于個體生命的心理流變,對過去進行的創造性想象和重構以及在這種創造性的限度內保留烙印在群體深層意識中的具有“歷史化”意味的集體記憶,甚或在此二者的緊張張力、沖突中進行的自我完善、自我運動。理論作為一種個人記憶,一方面它可以借鑒個人記憶的創造性功能、獨特的生命體驗、價值判斷、理論視域、興趣、興奮點等,形成主體獨到的理論見地、理論思想。所謂理論探討的并非完全是事實本身,而是它的可能性解釋,對理論主體性的承認,是理論排除主流意識形態、權力話語壓制,遮蔽得以推陳出新的前提;而另一方面它也可以透過個人記憶文化認同的共同想象功能重塑客觀歷史。理論作為建立在客觀事實基礎上的理論總結,雖然依托于理論研究者主體獨特的生命體驗、理論視域,但它必須以客觀事實為基礎,沒有事實依據的理論是不存在的。然而,作為個人記憶的理論,它除了具有自身的主體性、文化認同的集體記憶(客觀事實)功能外,更重要的是在這二者之間存在一種自我更新、自我超越的回歸張力,它構成了理論發展的重要動力。理論需要發展,需要在新的理論的沖擊下不斷地否定自我、更新自我,但又必須在客觀事實、集體記憶的限度內,不斷創造出新的形式、新的理論視域,以適應理論發展需要的否定之否定的過程。而理論也只有“在永不停息的變動中不斷回到自身、肯定自身的意志力和想象力,一種在自我否定過程中的自我確認、自我理解、自我超越,才能永葆旺盛的生命力”[4,p138]。
最后,個人記憶作為個人內心深處深刻的、富有洞見的記憶,之所以被追問,之所以要通過文化認同喚醒模糊的集體記憶,最根本的是想直面和思考人類群體普遍生存困境。而把理論作為一種個人記憶,也是希望通過對理論的思考,來達至對人類思維、人類認識的進一步發掘。
三、“重返八十年代”理論的方法
“重返八十年代”是近些年來我國當代文學研究界的重要話題,現在卻成了文學理論與批評界重新審視20世紀80年代文學觀念的課題。《南方文壇》《文藝爭鳴》《當代文壇》以及《當代作家評論》等學術研究雜志,都開辟了相關的專欄對這個話題進行討論。所謂的“重返”“只是一種修辭性的說法,它遵循的是一種‘回到歷史現場’的情景再現主義邏輯,意在以歷史的‘后見之明’,展示那些曾經廣為流行甚至被奉為圭臬的概念和范疇之所以成其所是的背景、條件和關系”[5],對這種重返的努力,“實際上是對自己業已流逝的青春所作的一次努力的挽回”[6]。然而與文學史方面的回顧大多沉溺于 80年代曇花一現的文學的黃金時代的思路不同,“文學理論與批評界對80年代的審美自律等觀念彌漫了一種檢討與自責的情緒”[5]。理論工作者們一方面解構了80年代的一些概念、范疇,一方面也對那個時代所折射出來的激情、沖動迷戀不已。
20世紀80年代作為十七年、“文革”和改革開放至今的重要聯結點、過渡,“是20世紀中國文學各種問題、各種文學觀念和寫作傳統形成緊張對話、轉換的時期,也是把握、思考20世紀中國文學經驗、進程的節點”[7]。我們知道社會主義前三十年即十七年、文革時代,文藝為政治服務、為工農兵群眾服務是文學的根本屬性,為了打碎束縛文學自由與美創造的“枷鎖”,與西方啟蒙主義和現代性追求似乎有著天然聯系的“人道主義”、“人性論”,被高高豎立,“審美自律”及其之后的“純文學”概念被高度強調,文學的“主體性”獲得了廣泛認同,文學理論在走向“先鋒和實驗”的形式化探險之旅時,也脫去了“庸俗社會學”的可恥外衣。然而過猶不及,對“審美自律”、“主體性”的過分強調,致使文學及其理論話語在市場經濟和消費文化的沖擊下岌岌可危。
與此同時,20世紀80年代中后期也存在著另一股潮流,那就是具有強烈解構色彩的理論,如后殖民、后現代,尤其是福柯權力話語的引進,對“審美自律”、“純文學”等概念作了“反本質主義”的闡釋,由此它們也變成了特定時代、特定語境中各種政治與權力介入與調和的結果,變成了另一種不同于十七年、“文革”時代政治、意識形態的新意識形態、新政治。只不過此意識形態非彼意識形態,此政治非彼政治,不能以十七年、文革時期的政治一言以弊之,并且政治也并不意味著對國家權力或者主流意識形態的認同,在認同政治與反抗政治之間的政治亞形態,也是政治的多種可能形態。
眾所周知,正是70年代末至80年代初從“文革”到“改革”的轉折,造就了所謂的“八十年代”,之所以要重返80年代,是因為以它為中心,向上可以回溯到“十七年”和“文革”中政治與“去政治化”的審美自律之間的特殊形態,向下則能把握住整個“八十年代”甚至“九十年代”審美“政治”的新走向。在政治與審美自律的斷裂與縫合中,理論正尋求著自己的發展方向,重建以“公共政治”、“公共關懷”為基礎的理論的政治維度。
那么何謂“公共政治”呢?陶東風認為“公共政治”的內涵有兩個,一個是阿倫特理想化的平等個體在“公共空間”中通過“言語而進行的”協調一致的“行動政治”,另一個是哈維爾基于其自身的政治參與實踐,“從對整個現代性,特別是現代科學主義和理性主義的反思”而提出的“存在的政治”,提倡向“道德和人性”的回歸,既反對“現代科學理性主義”將政治變成“權力游戲”,又懷疑“政治制度的轉換”能解決現代社會的問題,從而強調“要根據全球人類存在狀況來思考政治、思考我們的未來,而不是向傳統政治那樣局限于民族國家內部的政治制度”[8]。理論作為一種個人記憶,除了理論研究者個體自主性、理論視域與理論客觀事實之間通過文化認同達成張力,并實現自我更新、自我超越外,更重要的還是它把堅持公共關懷,積極應對現實生活中的重大問題,思考人類普遍的生存困境,作為一種“集體的信奉”、“真心實意的崇拜”,重建具有公共政治意味的理論的政治維度。
[1] 陳曉明.個人記憶與歷史的客觀化[J].當代作家評論, 2002(3):118-119.
[2] 車文博.弗洛伊德主義原理選輯[M].沈陽:遼寧人民出版社,1988:375.
[3] 洪治綱.文學:記憶的邀約與重構[J].文藝爭鳴,2010(1):56-61.
[4] 余曉慧,張禹東.文化認同的世界歷史語境[J].東南學術,2011(2):136-138.
[5] 趙牧.“重建八十年代”與“重建政治維度”[J].文藝爭鳴,2009(1):15-19.
[6] 毛時安.重建八十年代及其他[J].上海文學,2008(6):143.
[7] 洪子誠.“作為方法”的八十年代[J].文藝研究,2010(2):7-9.
[8] 陶東風.重建文學理論的政治維度[J].文藝爭鳴,2008(1):54-55.
(責任編輯、校對:任海生)
Memory Offer: A Glimpse of Properties of Theory through Cracks between Creation and Restoration
LUAN Jing-yan
(School of Literature, Hebei Normal University, Shijiazhuang 050000, China)
Theory is seen as a memory, because it offers subjectivity, objectivity, self-improvement and self-transcendence for personal memory, and it absorbs attention to human plight typical of personal memory. Therefore, it is a theoretic approach to reconstruct the political dimension of theories, a dimension of public political implications.
theory; personal memory; collective memory; subjectivity; objective history
2011-11-01
欒靜艷(1987-),女,河北石家莊人,碩士研究生,研究方向為西方文論。
J02-2
A
1009-9115(2012)03-0030-0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