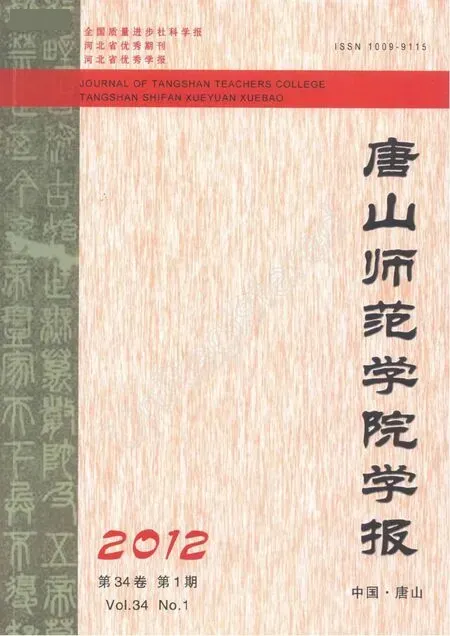蘇聯書報檢查制度研究
曹 群
(北京師范大學 歷史學院,北京 100875)
歷史學研究
蘇聯書報檢查制度研究
曹 群
(北京師范大學 歷史學院,北京 100875)
意識形態對于蘇聯國家和社會具有異乎尋常的意義,在蘇聯形成了一套獨特的意識形態管理模式。在這一體系之中,書報檢查乃是最重要的核心機制,在意識形態控制中所起的作用至關重要。書報檢查的嚴酷程度可以說是與意識形態控制相對應的,研究書報檢查制度不僅能令人們了解在出版和其他媒體行業中書報檢查具體如何施行,能對蘇聯的意識形態控制問題更加清楚明了,同時也在一定程度上填補了國內學界對于蘇聯書報檢查制度相關內容的研究空白。
蘇聯;書報檢查;意識形態
所謂“書報檢查”,其英語censorship①和俄語цeнзypa的表述皆是從拉丁語census和censere發展而來。Censere也就是英文中的censor,意即古羅馬專司公民戶口調查、公眾道德行為監督和指導的行政官[1]。《簡明不列顛百科全書》認為:“進行書報檢查,就是進行判斷和批評,做出評價和估計,以及實行禁止和壓制。”[2]在蘇聯解體之前,蘇聯官方長期以來并不承認蘇聯存在書報檢查。《蘇聯大百科全書》、《蘇聯百科辭典》都只介紹西方國家和沙俄政府的書報檢查機關,而不拒承認蘇聯存在這種機構。《蘇聯大百科全書》對此問題論述如下:“為人民利益和鞏固發展社會主義制度,蘇聯憲法保障公民的出版自由。建立國家監督是為了防止構成國家秘密的信息以及其他損害勞動人民利益的信息在公開的出版物上公布并在大眾傳媒中傳播。”[3]直到1986年2月戈爾巴喬夫在回答法國《人道報》的采訪提問時才承認蘇聯存在書報檢查[4]。
通過研讀已解密的檔案,我們不難發現,在蘇俄的各個時期都存在一整套規章制度非常完備的書報檢查系統。在蘇聯文化領域的許多歷史事件中都有書報檢查的身影,與其相關的機構甚多,許多都是黨和國家的重要機構,如蘇共中央政治局、蘇共中央宣傳鼓動部、西方所謂“政治警察”等等。
一、蘇俄書報檢查制度的初建
在長期地下活動中,布爾什維克黨積累了豐富的對敵斗爭經驗,這其中重要的一部分便是以報刊為媒介宣傳革命,辦報往往是其組織活動的中心。因此,布爾什維克黨深知輿論陣地的重要性,對其極為重視。十月革命剛剛勝利,作為人民委員會主席的列寧便頒布了《人民委員會關于出版的法令》(1917-10-27)。這一法令對出版的管制非常嚴厲,遭到了一些文人的強烈抗議,如持反布爾什維克立場的女作家基匹烏斯(З. H. Гиппyc)便激烈批評:“該法令禁止資產階級的報紙,其實等于禁止和廢除布爾什維克以外其他的所有報紙。”[5,p4-6]在革命中大聲疾呼言論自由的布爾什維克黨為何會在奪取政權之后便嚴格控制出版呢?聯系當時的事態情勢,原因便一目了然。布爾什維克取得政權之時,一次大戰尚未結束,而在戰爭狀態下不論是沙俄政府還是二月革命勝利后的資產階級臨時政府都采取了對出版業的嚴厲管制。作為世界上第一個社會主義政權,面對著無比強大的敵對勢力,暫時采取對出版加強管制的措施是非常有必要的。
十月革命勝利后,面對外國武裝干涉和國內戰爭的險惡環境,蘇維埃政府采取果斷措施將整個國家生活轉上戰爭軌道,蘇俄進入“戰時共產主義”時期。戰時共產主義政策在書報檢查方面反映非常明顯的是,1918年6月底建立了隸屬于軍事人民委員部作戰部的戰時書報檢查局,實施對出版書報的軍事檢查,并開始嘗試對出版物進行全面總體的出版前預審②,此一經驗為后來的出版總局所繼承和發展。1919年,蘇俄的書報檢查逐漸正規化,成立了國家出版社,國家出版社建立了在書報檢查事務上擁有極大全權的宣傳鼓動部(后改名為政治部)。在蘇俄書報檢查的“國家出版社時期”,宣傳鼓動部可以說是書報檢查事務的最高機構,當時俄羅斯所有的出版物發行都要經過它的許可,它也是出版總局的原型。在出版總局成立之后,宣傳鼓動部的工作便只限于檢查本社(即國家出版社)的出版物。
1922年6月6日,所有書報檢查的職能都轉歸新成立的專門機構——圖書文獻和出版事務管理總局(簡稱出版總局)。自此至1991年11月22日,出版總局活動了將近70年。在出版總局建立之初,其地方機構并沒能同時建立起來,各地書報檢查事務仍由國家出版社下設的政治部主管。但同時,內務部下設的“國家政治管理局”對書報檢查擁有超然的權力,如所有編輯、出版社負責人、書店負責人、印刷所長等都必須領取國家政治管理局的許可證[6]。許多秘密事務(可歸入寬泛的書報檢查范疇)也都屬于國家政治聯合管理部所負職權,在其中央機構之下設置了政治管理局(“輔助”出版總局和劇目檢查主管委員會完成書報檢查,進行郵件和電報通函暗查),秘密政治部第四和第五分局(主管諜報資料、組織文藝和科研領域告密網和收集間諜情報)。政治管理局的工作人員負責籌備對文藝作品的評價,有權提出建議撤銷出版總局和劇目檢查主管委員會的決議[7]。除此之外,國家政治聯合管理部有時可以國家機密為由違反章程和法律越過出版總局對書報檢查進行干涉而無需說明理由[8]。
在1923年之后,在蘇聯書報出版業中,編輯和書報檢查之間的差異不斷消減。1925年9月7日,首次頒布了《為保衛蘇聯政治經濟利益而嚴禁傳播的包含機密的消息目錄》,內容包括可能對政府產生負面影響的幾乎所有方面,如失業情況、反革命襲擊、民眾與政府部門的沖突、監獄衛生條件、關于自殺和神經病的報道、任何對蘇聯書報檢查的提及或暗示等等。此后,《目錄》定期頒布成為出版總局領導各檢查機構的重要方法。另外,值得補充的是,1927年之后,國家出版社獨立審核的歷史最終結束,自此所有出版社都必須有出版總局的特派全權代表按照出版總局的規程進行預審,所有出版物必須由特派全權代表簽署“批準刊行”[9]之后方能刊印出版。
二、斯大林統治下的書報檢查
20世紀20年代末到30年代初,是蘇聯“大轉變”的年代,黨內斗爭激烈而復雜。正是在這一時期,黨的機關開始直接實施對書報檢查的集中管理。1930年5月,蘇聯人民委員會正式下令改組出版總局,削弱一些出版總局的職權,如“解除出版總局中央機構從政治思想和軍事、經濟觀點方面對出版物進行事前檢查的所有業務”[5,p183](將設黨的機關代之)。改組工作直至1931年6月才正式告終,出臺了新的規程條例,關于出版檢查的領導和具體工作有一些變動:對印刷物的出版前檢查劃入國家出版社協會系統(此時早已完成了出版行業的國有化),出版總局特派全權代表由出版社負責人擔任,其下有專管政治檢查問題的副職負責對該出版社“政治編輯”③的實際領導[10]。通過這次改組,黨加強了對出版總局的監督,甚至直接參與書報檢查的管理,這與當時黨政不分、以黨代政局面的進一步發展相伴隨。
斯大林在聯共(布)18大上的報告中提出建議“集中黨的宣傳和鼓動事務,合并主抓宣傳鼓動的部門與主抓出版事務的部門,在聯共(布)中央會議組織下設置統一的宣傳與鼓動事務管理局”[5,p291]。根據斯大林的提議,1938年8月3日,黨中央原宣傳與出版事務部經過改組成為了黨主要的意識形態管理部門——宣傳與鼓動事務管理局,該局第一任領導是政治局委員、中央書記處書記日丹諾夫(A. A. Ждaнoв)。宣傳鼓動事務管理局下設五個處:黨宣傳處、干部馬列知識培訓處、出版事務處、鼓動處、文化與教育設施處。出版事務處所負職責有“對中央、地區、省、共和國的報紙與雜志實行監察……推行黨中央關于報紙的路線問題的指示……參與報紙與雜志干部人員的擇選與查檢……審查主要出版社的主題計劃……決定報紙的印數……監督塔斯社和出版總局的工作”。原檢查員索羅金(B. A. Coлoдин)在接受采訪時曾說:“出版總局雖然建制在人民委員會(之后是部長會議)之下,但實際上直屬于蘇共中央宣傳部,宣傳部監督著出版總局,對其直接下達指令。之后,在級別上出版總局還從屬于黨中央管理意識形態問題的書記處(通常設有兩個書記)……除了宣傳部,出版總局還部分接受中央文化部的領導。”[11]
衛國戰爭爆發之前,蘇聯政府可能已經嗅到了戰爭迫在眉睫的味道,1941年6月2日,蘇共中央下達了加強軍事檢查的指令《軍事總檢查員規章》:“為了加強蘇聯的軍事檢查,設立直屬蘇聯人民委員會的軍事總檢查員,所有不同類型的書報檢查都從屬于軍事總檢查員……軍事總檢查員還負責審查所有郵件……”[12]在全民渴望勝利的期盼下,適應戰時需要,書報檢查的施行準則、責任追究與懲罰條例愈益清晰,一定程度上實現了“自我檢查”(caмoцeнзypa),極大地簡化了書報檢查的程序和工作。
在斯大林逝世之前,在“冷戰”不斷加劇的國際背景下,自1946年開始,蘇聯在意識形態領域展開了一系列批判運動。在對文學雜志《星》、作家左琴科和阿赫馬托娃的批判中,在有關哲學、經濟學、遺傳學的爭論中,在反對打擊“列寧格勒反黨集團”和“反革命猶太醫生恐怖集團”的斗爭中,在“反猶太人主義”和“反猶太復國主義”④的運動中,出版總局堅定不移地遵循支持黨中央的相關決議,對“有害”作品進行封殺。
三、赫魯曉夫時期的書報檢查
斯大林去世后,1953年3月15日,根據蘇聯部長會議769號決議,原直屬蘇聯部長會議的出版業軍事與國家保密事務全權管理局轉歸蘇聯內務部轄下,改稱為蘇聯內務部出版業軍事與國家保密事務全權管理局。1953年6月26日,蘇聯部長會議第一副主席兼內務部長貝利亞被逮捕并被剝奪一切職務,內務部開始進行改組,許多部門被合并或裁撤。出版業軍事與國家保密事務全權管理局又復直屬蘇聯部長會議,再次成為獨立部門。不久,國家安全機關也從內務部獨立出去,1954年3月14日,蘇聯最高蘇維埃主席團頒令成了直屬蘇聯部長會議的國家安全委員會(亦即眾所熟知的“克格勃”)。在國家安全委員會里,與書報檢查和意識形態監督具有緊密聯系的是其轄下的第四局(主要負責與反蘇秘密組織、極端民族主義組織和敵對分子作斗爭)。1955年,在第四局下創立第六特別處,原由第十處履行的職能(暗中檢查郵件和電報通函)轉歸第六特別處[13,p305-306]。
1958年1月,蘇共中央召開了第一屆意識形態委員會⑤,其職責為研究國際宣傳問題、國際工人運動理論問題,監督以上問題在出版流通中的闡釋,監督情報局和國際文化交流委員會的政治傾向性……監督具有政治和意識形態意義的科學、文學、藝術等領域重要事務。該委員會主席由蘇斯洛夫(M. A. Cycлoв)擔任,其成員不是蘇共中央主席團和書記處的委員便是候補委員。委員會經常對具體事務下達指令⑥,依照傳統,黨中央組織機構的決議一般具有與“中央指令”相同的效力,而且一般都是“機密”或“絕密”文件。1958年2月,出臺了新的《出版總局工作條例》。《條例》明確指出政治意識形態監控不再由出版總局負責,并且廢除舊的“檢查員—兼職編輯”的體制,改由各地報刊的編輯直接負責,且為了不令與各地方當局產生矛盾,各出版社完全從屬所在地黨和政府。1962年10月之后,意識形態委員會職權范圍大大縮小(只增加了管理和監督教育問題的職責),不再負責研究國際問題和運動問題,不再對具體機關的工作進行監督。委員會的地位也大大降低,它不能做出任何決議,只負責討論草案和提交建議,而由蘇共中央主席團和書記處下達決議[13,p313-314]。
在意識形態和政治書報檢查系統中,起著重要作用的還有國家安全委員會。1960年,蘇共中央主席團和蘇聯部長會議做出決議對國家安全委員會的組織結構進行一些調整,增強了其在意識形態和政治檢查方面的監督作用⑦。國家安全委員會與蘇共中央和出版總局及其他相關單位聯合一起進行政治檢查,并利用其特殊技術和手段監控文學藝術領域中的個別流派和具有代表性的作家、藝術家。出版總局是國家安全委員會在文藝領域實行打擊和鎮壓措施的不可或缺的助手,它總是在第一時間通知黨中央和國家安全委員會在出版業中所發現的“違規事件”或者反蘇言論,而且國家安全委員會也常就有關文學和藝術的評論問題(確定相關作品是否有意識形態誤導或反蘇反社傾向)發函咨詢出版總局。如此,便形成了一個操控社會的三角形:黨中央——國家安全委員會——出版總局。書報檢查中的事前檢查逐漸形成雙層模式:出版總局——黨中央——出版總局,出版總局審查完畢做出評論,然后提交給黨中央的相關部門(如蘇共中央宣傳部、文化部),黨中央部門做出指示發給出版總局,由出版總局依照指示許可出版、禁止出版或要求作者對作品進行修改。
在1953-1957年和1958-1964年間發生的一系列文化——政治事件使得蘇聯高層的意見分歧公之于眾,而正是這些高層分歧使一些原本難以出版的作品借此“解凍”得以面世。不論高層分歧還是赫魯曉夫的改革都沒有弱化書報檢查系統,更沒有削弱黨對文化事業的領導。當然,在黨希望脫離斯大林模式、導引政府和社會走向現代化的大局勢下,書報檢查系統也進行了改革,其各機關間的關系和職責得以逐步“有法可依”,這便是所謂“書報檢查系統的現代化”(1956-1968)。這一“現代化”進程由赫魯曉夫啟動,一直延續到勃列日涅夫執政初期。
四、勃列日涅夫時期的書報檢查
早在1963年6月的蘇共中央全會上,便確定了傾向保守的關于文化監控的決議,強調了從前“文學藝術黨性”的論點,對“自然主義”的、“陰暗”的、“形式主義”的、“反人民”的現代派作品進行了批判。以上所列各種文學作品與蘇聯政府意識形態是相矛盾的,但此時政府對于這些偏流尚無意直接打壓,主要是教育這些作者認識到自己的意識形態錯誤。但是當蘇聯歷史邁入勃列日涅夫時代,赫魯曉夫時代的寬松氣氛消亡殆盡,政府對于知識分子的政策也逐漸嚴苛。
在國家安全委員會1965年12月11日呈交蘇共中央的報告[14]中,指出了一些刊物的路線錯誤以及國內許多作家在國外出版社出版著作的問題,國家安全委員會的結論很明顯——需要采取果斷措施,實行公開打壓。蘇聯政府書報檢查制度的“預防性檢查”和官方的政治宣傳運動使蘇聯知識分子發生了分裂:大多數擁護黨的政策,而少部分則持反對態度,即所謂“持不同政見者”。政府對“異端分子”的公開壓制不僅引發了長期的持不同政見運動以及之后的人權保障運動,也導致了蘇聯文化分裂為書報檢查下的官方文化和通過“地下出版物”(caмиздaт и тaмиздaт)⑧傳播的非官方文化。這樣,不與政府妥協的知識分子便只能“隱蔽”起來偷偷寫作,或者被逮捕、審判、拘禁以至驅逐出境。
蘇共中央——國家安全委員會——出版總局的三角關系也發生了一些變化,國家安全委員會逐漸恢復昔日國家保安機構的強勢,而黨組織機關在文化操控方面的行政指揮功能也愈益膨脹,出版總局在意識形態監控領域卻越來越走向非中心的邊緣:自1963年8月至1966年8月,出版總局與特權機構的關系比較疏遠,權勢也不復以往,由蘇聯部長會議的直屬單位改為隸屬于部長會議下的國家出版事務委員會。出版總局對自己的地位下降非常不滿,一直努力恢復昔日的輝煌。1966年,出版總局終于恢復了以前的地位,在新出臺的書報檢查工作章程中,強調了意識形態路線限制以及檢查員的責任,重新直屬蘇聯部長會議直至1991年初。出版總局重新開始從事以前在預先監控和調度中的工作,并且在監控社會意識形態中的分析角色有所增強。同國家安全委員會的保安人員一起,出版總局的工作人員為蘇共中央準備關于國內文化和社會生活、知識分子的主張和傾向、國外媒體對上述現象的報道等等的詳細情報資料,這種情報偵察和監控的交叉方法使蘇共能夠在最短時間最大限度掌控意識形態。
1968年的布拉格事件促使蘇聯國內外形勢發生劇變,書報檢查制度亦隨之發生了重大變化。“布拉格之春”令保守派對于改革益加恐懼,保守派與改革派的斗爭日益尖銳。同時,勃列日涅夫開始破壞“三駕馬車”的領導機制走向個人集權,而蘇聯的政治斗爭又往往是以理論、意識形態批判的形式進行,這必然使得意識形態問題突出重要,而這也必然要求加強意識形態控制的重要環節——書報檢查制度。蘇共中央書記處1969年1月7日下達的密令《關于加強出版、廣播、電視、電影、文化藝術部門領導對于出版物和劇目思想政治水平的責任》更加表明了高層的立場:“在意識形態斗爭極其殘酷的形勢下……各組織、部門和編輯部集體的領導應對出版物的思想傾向負直接責任……出版社和印刷、廣播、電視機關以及文藝部門的某些領導對于主題思想謬誤作品的出版沒有采取盡職的預先防止措施,與創作者之間的工作進行得非常不好,在思想謬誤作品的出版問題上表露出了自身的妥協退讓和意識形態無原則。意識形態機關的一些個別領導試圖將這方面的責任推給蘇聯部長會議下的出版業國家保密事務管理總局……”[15]這種嚴苛的書報檢查制度不僅令創作人難以忍受,同樣也使出版社的領導十分頭疼,由于責任的威脅,他們經常被推入抉擇艱難的境地,不得不在自己的良心同職位二者中進行唯一抉擇。
自此,蘇共中央將所有意識形態監控調節的權力都集中到自己手中(所有出版前檢查都由編輯部尤其是編輯部領導對黨和國家負責),只把出版后檢查留給了出版總局,幾乎所有會引發沖突的問題都在出版前檢查時解決了,出版總局進行的出版后檢查不過是在“捉跳蚤”。這種檢查制度雖還不是1970-1980年代的“自我檢查”(caмoцeнзypa),但已經十分接近。這一階段,出版總局履行的并不是自己應負的主要職責(出版業國家和軍事保密事務),而只是執行黨中央意識形態方面的指令。后來,這種書報檢查制度大體便成為了即將到來的全面滲透政治檢查的70年代“停滯時期”的基礎組成部分。
在出版總局1971年6月29日提交給蘇共中央的《咨詢報告》[16]中,提出蘇聯主要的反對力量來自知識分子,正是以索爾仁尼琴和薩哈羅夫為首的知識分子發動了所謂“抵抗運動”和“民主運動”。該《咨詢報告》預示著1970年代前半期對于“政治檢查”將進行一系列戰略戰術改良。這一時期,國家安全委員會在事前檢查中所起的作用不容忽視,尤其是它采用偵察手段暗查作家的皮包和抽屜,將所獲相關作家的意圖和計劃的情報匯報蘇共中央。主要負責“預防性檢查”工作的國家安全委員會機關為其轄下第五局。在1975年10月31日國家安全委員會的公函《國家安全委員會機關的預警行動總結報告》中,指出對蘇聯公民進行偵察的主要原因便是意識形態監控,在1959-1974年間便有約6萬公民曾被“預防警告”,其中近三千人的罪名是從事反蘇宣傳鼓動活動[17]——典型的即是閱讀和傳播“地下出版物”和其他“反蘇文藝作品”。
在勃列日涅夫執政后期,保守勢力始終在蘇聯政治和意識形態中處于主導地位,改革傾向遭到壓制,蘇共二十四大后,連“改革”這個詞匯也不再出現于正面宣傳中,輿論宣傳被規限于“完善”既有體制模式即“發達的社會主義”。書報檢查制度與勃列日涅夫時期的大局勢基本符合,仍然完全維續嚴苛的政治檢查與粗暴打壓。
五、蘇聯書報檢查的衰亡
1982年11月10日,蘇共中央總書記勃列日涅夫病逝。自此蘇聯歷經安德羅波夫和契爾年科的短暫執政,越來越接近蘇聯發生巨變的大改革時期,雖然書報檢查系統一直努力在新環境下繼續保存自己以往的地位,但是隨著1985年3月戈爾巴喬夫上臺,一切都不得不改變了。隨著以“公開性”、“民主化”和“政治多元化”為基調的政治改革的深入,書報檢查機制對出版的限制也越來越寬容。
1990年6月,蘇聯最高蘇維埃在經過長期討論之后,終于最后批準了蘇聯出版法《關于出版和其他大眾媒體》,該法案以法律的形式結束了早已形同消亡的出版前檢查。出版總局經過改組變成了出版業與大眾媒體國家保密事務管理總局,1991年4月改為隸屬蘇聯信息與出版事務部,1991年6月改名為蘇聯信息與出版事務部下的大眾媒體國家保密事務管理辦事處[13,p377]。
出版總局在改組過程中也進行了一些粉飾門面的改革,最明顯的便是出版總局的工作人員數額縮減了30%,但出版總局的領導層基本沒有任何變化,與此同時,依據蘇聯最高蘇維埃指令《關于維護社會道德和制止殘暴、色情宣傳的緊急措施》和《蘇聯總統名譽和威嚴保護法》,仍然有不少人被判有罪和處以刑罰[18]。
在不及三日的“八一九”事變中,出版總局再次試圖恢復以往的輝煌,雖然事變很快平息,但事變后依然不放棄其努力,開始采取更加隱蔽形式——尤其是以“經濟和商貿資訊保密”為根據繼續進行廣泛的書報檢查。1991年10月,俄羅斯聯邦部長會議通過決議終止在俄羅斯聯邦境內的出版總局機構的活動,而蘇聯的出版總局,直至蘇聯解體之后,才正式結束了其近70年的歷史[19]。
蘇聯解體之后,俄羅斯曾一度盛行自由主義,經過休克療法的慘痛教訓,現在俄羅斯的學者和民眾逐漸開始重新審視一些西方的舶來品,更加注重從本民族傳統和實際國情出發選擇適合自身的道路。2001年曾經進行過一次社會調查,結果顯示,57%的民眾認為政府應當實行書報檢查。三年之后,贊同此觀點的人數增加了,70%以上的被調查者認為,必須回到以前蘇聯的做法,贊同對各種大眾傳媒實行這種或那種形式的檢查制度[20]。
[注釋]
① 部分學者建議用censorship表示出版前檢查(prepublishing censorship),用censure表示出版后檢查(postpublishing censorship),本文采用主流說法以censorship統稱書報檢查。
② 在1922年6月6日出版總局(Глaвлит)成立之前,沒有加蓋許可印章P.B.Ц.(Paзpeшeнo Boeннoй Цeнзypoй,意為已通過軍事書報檢查),不可能出版任何題目的出版物。
③ “政治編輯”負責具體的檢查工作,要對出版物進行分析和評論。“政治編輯”必須具有絕對穩定的黨性,根據不同出版物的所屬的不同類型和重要性,對“政治編輯”的黨齡要求為5~10年。
④ 對猶太人的態度,蘇聯完全繼承了沙俄時代打壓的傳統,而且有過之無不及。絕大多數與“猶太問題”相關的著作在蘇聯是嚴禁的,在蘇聯的猶太人也一如既往地受到歧視,對于猶太作家的作品出版有嚴格限制。
⑤ 在1958至1964年間,意識形態委員會實際上是文化管理和政治書報檢查的核心機構。1966年5月,根據中央政治局決議,裁撤了意識形態委員會。
⑥ 嚴格依照職權規定,意識形態委員會只負責問題和理論的研討,而不能對具體問題下達指令,但是由于與會的大都是重要的黨政干部,因此一些問題討論之后便直接作出決定,另一些問題也能通過“公函咨詢”方式達成決議,至于極其重大的問題則須呈請蘇共中央主席團批示。
⑦ 國家安全委員會新的組織結構和職權分配有了一些變化,由第二總局(反間諜機關)負責主抓意識形態問題,直至1967年鑒于國家政治領導系統發生了變化,意識形態問題重新劃歸第五特局掌控。(Гopяeвa T. M. Пoлитичecкaя цeнзypa в CCCP 1917-1991, M. POCCПЭH, 2002: 315.)
⑧ 關于caмиздaт(指“不合法”地使用簡陋的印刷機器刊印和復印的出版物或與之相關的印刷出版體系)和тaмиздaт(指在國外出版發行后運回國內的蘇聯地下出版物或與之有關的印刷出版體系)的譯法:現在一般將caмиздaт譯為“地下出版物”,筆者認為,此譯法尚有待學界討論。本文將caмиздaт和тaмиздaт統稱為“地下出版物”。
[1] Lesley Brown. The New Shorter Oxford English Dictionary on historical principles (Vol. 1)[M]. Oxford: Clarendon Press, 1993: 360
[2] 中國大百科全書出版社《不列顛簡明百科全書》編輯部.簡明不列顛百科全書[Z].北京:中國大百科全書出版社,1986:342.
[3] Бoльшaя coвeтcкaя энциклoпeдия. Bтopoe издaниe [M]. T. 46. Фyce-Цypyгa. M.:Гoc. нayч. изд-вo "Бoльшaя coвeтcкaя энциклoпeдия". C. 518-519.
[4] Лeвчeнкo И. E. Пapaдoкcы цeнзypы?. Цит. пo: Цeнзypa в Poccии: иcтopия и coвpeмeннocть: Cбopник нayч. тpyдoв. Bып. 2[M]. Peдкoл.: Фиpcoв B. P. и дp. CПб.: Изд-вo Poc. нaц. б-ки, 2005: 172-182.
[5] Блюм A. B. Цeнзypa в Coвeтcкoм coюзe. 1917-1991. Дoкyмeнты[M]. M.: POCCПЭH, 2004.
[6] Цeнтpaльный гocyдapcтвeнный apxив литepaтypы и иcкyccтвa в Caнкт-Пeтepбypгe, Ф. 35, Oп. 1, Д. 24, Л. 22. Цит. пo: Блюм A. B. Цeнзypa в coвeтcкoм coюзe 1917–1991. Дoкyмeнты, M.: POCCПЭH, 2004: 33-34.
[7] Цeнтpaльный гocyдapcтвeнный apxив литepaтypы и иcкyccтвa в Caнкт-Пeтepбypгe, Ф. 35, Oп. 1, Д. 5, Л. 12. Цит. пo: Блюм A. B. Цeнзypa в coвeтcкoм coюзe 1917-1991. Дoкyмeнты, M.: POCCПЭH, 2004: 19.
[8] Цeнтpaльный гocyдapcтвeнный apxив литepaтypы и иcкyccтвa в Caнкт-Пeтepбypгe, Ф. 31, Oп. 2, Д. 55, Л. 248-253. Цит. пo: Блюм A. B. Цeнзypa в coвeтcкoм coюзe 1917-1991. Дoкyмeнты, M.: POCCПЭH, 2004: 130-131.
[9] Apxив Poccийcкoй Aкaдeмии нayк в Mocквe, Ф. 597, Oп. 6, Д. 4, Л. 16-17. Ццит. пo: Блюм. A. B. Цeнзypa в coвeтcкoм coюзe 1917-1991. Дoкyмeнты, M.: POCCПЭH, 2004: 123.
[10] Цeнтpaльный гocyдapcтвeнный apxив литepaтypы и иcкyccтвa в Caнкт-Пeтepбypгe, Ф. 281, Oп. 1, Д. 56, Л. 61. Цит. пo: Блюм A. B. Цeнзypa в coвeтcкoм coюзe 1917-1991. Дoкyмeнты, M.: POCCПЭH, 2004: 206.
[11] Гocyдapcтвeнный apxив Poccийcкoй Фeдepaции (ГAPФ, бывший Цeнтpaльный гocyдapcтвeнный apxив Oктябpьcкoй peвoлюции, выcшиx opгaнoв гocyдapcтвeннoй влacти и opгaнoв гocyдapcтвeннoгo yпpaвлeния CCCP), Ф. 9425, Oп. 2, Д. 19, Л. 99-136. Цит. пo: Блюм A. B. Цeнзypa в coвeтcкoм coюзe 1917-1991. Дoкyмeнты, M.: POCCПЭH, 2004: 289-294.
[12] Poccийcкий гocyдapcтвeнный apxив coциaльнoпoлитичecкoй иcтopии (PГACПИ, бывший Цeнтpaльный пapтийный apxив Инcтитyтa тeopии и иcтopии coциaлизмa ЦК КПCC, зaтeм PЦXИДHИ -Poccийcкий цeнтp xpaнeния и изyчeния дoкyмeнтoв нoвeйшeй иcтopии), Ф. 17, Oп. 125, Д. 65, Л. 126. Цит. пo: Блюм A. B. Цeнзypa в coвeтcкoм coюзe 1917-1991. Дoкyмeнты, M.: POCCПЭH, 2004: 314-315.
[13] Гopяeвa T. M. Пoлитичecкaя цeнзypa в CCCP 1917-1991, M. POCCПЭH, 2002.
[14] PГAHИ - Poccийcкий гocyдapcтвeнный apxив нoвeйшeй иcтopии (бывший ЦXCД – Цeнтp xpaнeния coвpeмeннoй дoкyмeнтaции), Ф. 5, Oп. 30, Д. 462, Л. 249-256. Цит. пo: Гopяeвa T. M. Пoлитичecкaя цeнзypa в CCCP 1917-1991, M. POCCПЭH, 2002: 325.
[15] PГAHИ - Poccийcкий гocyдapcтвeнный apxив нoвeйшeй иcтopии (бывший ЦXCД – Цeнтp xpaнeния coвpeмeннoй дoкyмeнтaции), Ф. 4, Oп. 19, Д. 131, Л. 2-6. Цит. пo: Гopяeвa. T. M. Пoлитичecкaя цeнзypa в CCCP 1917-1991, M. POCCПЭH, 2002: 339.
[16] ГA PФ – Гocyдapcтвeнный Apxив Poccийcкoй Фeдepaции, Ф. 9425, Oп. 1, Д. 1396. Л. 111-113. Цит. пo: Гopяeвa T. M. Пoлитичecкaя цeнзypa в CCCP 1917-1991, M. POCCПЭH, 2002: 347.
[17] 魯·格·皮霍亞.徐錦棟,等譯.蘇聯政權史1945-1991 [M].北京:東方出版社,2006:403.
[18] ГA PФ – Гocyдapcтвeнный Apxив Poccийcкoй Фeдepaции, Ф. 9425, Oп. 2, Д. 1092. Л. 183-187; Д. 1117. Л. 15 и дp. Цит. Пo: Гopяeвa T. M. Пoлитичecкaя цeнзypa в CCCP 1917-1991, M. POCCПЭH, 2002: 377-378.
[19] ГA PФ – Гocyдapcтвeнный Apxив Poccийcкoй Фeдepaции, Ф. 9425, Oп. 2, Д. 1119. Л. 40-41. Цит. Пo: Гopяeвa T. M. Пoлитичecкaя цeнзypa в CCCP 1917-1991, M. POCCПЭH, 2002: 378.
[20] Блюм A B. Cyщecтвyeт ли вoзмoжнocть pecтapвaции цeнзypы в Poccии?. Цит. пo: Цeнзypa и дocтyп к инфopмaции: иcтopия и coвpeмeннocть: Teзиcы дoклaдoв мeждyнap. нayч. кoнф., Caнкт-Пeтepбypг, 16-18 мapтa 2005 г. Poc. нaц. б-кa и дp. ; Peдкoл.: Кoнaшeв M. Б. (oтв. peд.) и дp. CПб. : Изд-вo Poccийcкoй нaциoнaльнoй библиoтeки, 2005: 88-90.
(責任編輯、校對:韓立娟)
The Study on Soviet’s Censorship
CAO Qun
(School of History, Beijing Normal University, Beijing 100875, China)
Ideology is extraordinary important for the Soviet Union. And it formed a peculiar ideological management model in the country. The censorship is the core mechanics in the model. The severe level of ideological control can be said to correspond to the censorship. The study of it can not only make people know about the specific operation of censorship through the publication industry in books, newspapers and other media to understand the problem of the Soviet’s ideology more clearly, but also fill the research gaps in the domestic academia to some extent.
The Soviet Union; censorship; ideology
K512.5
A
1009-9115(2012)01-0036-06
2011-09-22
曹群(1981-),男,河北唐山人,博士研究生,研究方向為中外關系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