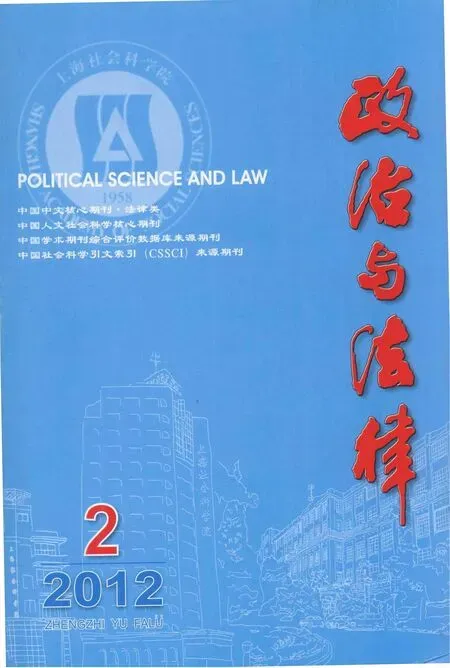“農民工”身份問題的法律分析
溫晉鋒 鄭立俊
(南京工業大學法政學院,江蘇南京211816;安徽省滁州市瑯琊區人民檢察院,安徽滁州239000)
一、“農民工”身份定位的困局
“農民工”1這個稱謂由張雨林教授在1984年首次提出,2當時是指代“離鄉不離土進廠不進城”的在鄉鎮企業工作的從農民中分化出來的那一部分人員。隨著時間的推移“農民工”已經成為日常生活中對進城務工農民的總稱。但在提到這個詞時,我們往往會聯想到它的隱性評價意義。隱性評價意義是指人們對所指對象的委婉含蓄的評價,反映了人們對所指對象的非本質屬性的主觀認識。3這種隱性評價是社會對這類群體地位卑微的自然反應,來自于深藏在人們心中根深蒂固的歧視意識,從而導致在名稱稱謂上也帶有強烈的主觀色彩。
身份是指人的出身和社會地位,《現代漢語詞典》將身份解釋為“人在社會上與法律上的地位”。4身份作為一個法律概念是取得權利和承擔義務的基礎,但“農民工”包含了多種身份屬性。
“農民工”從字面上來看包含著兩個詞:“農民”和“工人”。“農民”在我國是一個多位一體的復雜概念,它可以是一種職業、一個階級,更多地也是一種身份符號。5“工人”是一個職業概念。“農民工”一年中的全部或大部分時間都在城鎮中從事第二產業以及第三產業的勞動,他們屬于廣大產業工人的一部分,卻又是其中極為特殊的一類群體。“農民工具有的身份屬性使其與農民一樣是一種存在,是對自我的一種整體的和靜態的規定,而其他的職業是人們獲得的和占有的“所有物”。6
河南青年張海超“開胸驗肺”事件的發生,表面上是他的具體權益得不到有效、及時的保護,實質上是“農民工”身份定位的搖擺造成的。我們可以將“農民工”理解為農民或是工人,也可認為“農民工”既不是農民也不是工人。城市在經濟層面上接納進城務工農民的同時,在社會身份的層面上排斥這一群體,除了每年一度的春運和討薪時人們會想起“農民工”,其他時候他們常常被社會所遺忘。
二、“農民工”身份固化的表現
稱謂,指人們因為婚姻和社會關系,以及由于身份、職業等等而建立起來的名稱。“農民工”這個稱謂的出現顯然是由身份和職業的雙重屬性所決定的,是這兩種屬性使“農民工”這個概念在社會大眾的觀念中固定下來,并得到廣泛運用。
(一)“農民工”稱謂固化的政策表現
2003年9月召開的中國工會十四大提出,“農民工”已經成為我國工人階級的新成員和重要組成部分,“農民工”加入工會被首次寫入這次大會的報告。每年年初出臺的中央一號文件都關注了“農民工”群體,并提出了許多保護“農民工”權益的政策措施,其中2004年初的中央“一號文件”——《中共中央國務院關于促進農民增加收入若干政策的意見》,第一次明確認定“進城就業的‘農民工’已經成為產業工人的重要組成部分”。200年3月國務院在嚴控新設辦事機構的要求下,經國務院總理溫家寶特別批示,加設了一個新的辦事機構——國務院“農民工”工作聯席會議辦公室,由專門的“農民工”工作聯席會議制度負責處理“農民工”事務。
(二)“農民工”稱謂固化的法律表現
雖然國家對“農民工”的規定,并沒有上升到全國人大制定法律的高度,但其出現于某些規范性文件中,而這些規范性文件具有法的一般屬性。在國務院的許多規范性文件中就規定了“農民工”概念,如2003年9月18日國務院辦公廳轉發的《國務院辦公廳轉發農業部等部門2003-2010年全國“農民工”培訓規劃的通知》、2006年3月27日國務院頒發的《國務院關于解決“農民工”問題的若干意見》以及2006年3月31日頒發的《國務院關于同意建立“農民工”工作聯席會議制度的批復》。2004年12月21日最高人民法院也頒布了《最高人民法院關于集中清理拖欠工程款和“農民工”工資案件的緊急通知》。地方政府的法律文件中關于“農民工”的規定多如牛毛。有些地方的權力機關甚至準備出臺《“農民工”權益保護法》,以此將“農民工”徹底固化為一種特定的法律主體予以規范。
(三)“農民工”稱謂固化的輿論表現
社會輿論是社會上的大多數人對某一事件或某一群體有效的公共意見。張友漁認為“輿論是把少數人排除在外的社會多數人的意見。”7社會輿論對外來進城人員的主觀惡意猜測是全世界的普遍現象,科亨就舉了個例子來說明這種現象:人們一般都采用移民中少部分人最為消極的特性——犯罪、占用大量福利、素質低下來涵蓋其他的移民,8認為這類人群中的成員都是這樣的人,是社會的“二等公民”。其實“農民工”這個稱謂并非是進城務工農民用來自我稱呼的,而是新聞媒體、城市居民對于這一群體的稱呼,體現著社會輿論對“農民工”群體進城后衍生的負面影響的感受。
(四)“農民工”稱謂固化的學術表現
社會熱點一般都是學術界所研究的對象,“農民工”一直是學界關注的學術問題,學者們以“農民工”為對象進行了多方面的研究,如“農民工”身份認同、“農民工”子女教育“農民工”就業、“農民工”權利救濟、“農民工”社會保障、“農民工”自身的個體差異、“農民工”群體內部的代際分化等等。這些學者都從一定程度上認可了“農民工”這一概念,并將其作為邏輯起點進行“農民工”具體權益保護以及代際差異的理論研究,從而使得“農民工”這個概念在學術上日漸固定化,并影響到政府決策和社會輿論導向。
三、“農民工”概念的法律質疑
(一)“農民工”概念的詞義分析質疑
“農民工”作為一個日用語,不僅僅是對進城務工人員的稱呼,還是一種社會文化現象,帶有社會公眾的主觀印跡。一般詞語所蘊含的主觀態度可能是公正的,也可能是有失偏頗的。而包含著偏見和歧視的詞語在社會輿論和規范性文件中廣泛使用是一種極為不正常的現象。在國外的媒體組織中,如美聯社對其新聞工作人員的要求就是少用俚語,因為許多俚語如“胖子”、“黑鬼”等都帶有歧視意味。但在我國的社會習慣用語和新聞媒體的報道中,有不少“農民工”這樣的概念。雖然與“農民工”具有相同意義的稱謂“打工仔”“打工妹”也很盛行,但是“打工仔”、“打工妹”只是一種客觀性的描述,而“農民工”概念卻體現了國家和城市居民對于“農民工”群體的貶損。一個歧視性詞語的通用,顯示出了這個社會對這種不公平現象的默認甚至縱容,因此,筆者認為應當堅決拋棄如此使用歧視性詞語的作法。
(二)“農民工”概念的規范法學質疑
1.“農民工”概念的不確定性與法律概念的特征相悖
法律在維護社會秩序方面起著重要的作用,為能成功地完成這一任務,就必須在法律制度中形成一些有助于對社會生活中多種多樣的現象與事件進行分類的專門觀念與概念。9法律概念是法律的構成要素之一,其作用在于對社會中已經出現或將要出現的并且需要法律進行規制的事實進行定性,既要確定這個事實的自然性質和社會性質,還要確定其法律性質。法律概念應當是精確的,具備明確的內涵與外延,如果只有自然屬性和社會屬性,就不能確定這個概念是否能夠包含所指向的對象的權利和義務或者所包含的權利義務是否明確、合理;法律概念必須是規范的,即在語言學上和法學上都是標準的。10只有符合以上兩個條件,社會習慣用語才能轉化成為法律概念,為法律規范所確定。
現在“農民工”儼然已成為了一個法律概念,但雙重身份下的“農民工”稱謂不管在學術界還是在社會輿論中都頗具爭議,其概念的內涵與外延還沒有廓清。如果沒有針對進城務工農民嚴格限定的法律概念,我們就不能理性地去思考與“農民工”群體相關的法律問題,對于“農民工”身份界定、權益保護理論的研究和政策、法律的制定也無異于空中樓閣。現在界定的“農民工”概念,只是考慮社會輿論所體現出來的典型性特點,而沒有考慮“農民工”概念在身份角度上所體現的兩可性,這就使得“農民工”概念載入法律規范之中時其界限范圍無法確定,讓依附于概念之上的權利義務無所適從,導致了“農民工”群體權利保障的虛置。
2.“農民工”概念與法律精神相悖
政策法規對于“農民工”概念內涵的界定包含兩種:農民的身份與產業工人。其實無論農民還是工人,他們的第一身份都公民。農民本是公民,在進城工作之后成為工人,享受工人的待遇,但其仍然遭受身份的歧視,處于社會階層的底部。實際上這種不合理的法律規則和原則與“農民工”概念的指引有相當大的關系,當法律原則和法律規范使“農民工”概念合法化,用法律的形式公然規定不平等的概念時,其顯然偏離了現代法律的平等精神。
(三)“農民工”概念的制度法學質疑
1.“農民工”立法對“農民工”權益保護的損害
我國在制定相關“農民工”法規的時候,出發點是為了重點保護“農民工”的具體權益。但事與愿違,對“農民工”群體的專門性立法在形式上似乎對“農民工”非常重視,但實質上所起到的作用是以立法的形式變相地承認“農民工”身份的特殊性,將“農民工”與公民割裂開來進行特殊對待。這反而成為一種對“農民工”權益保護的障礙。立法應該是具有一定普遍性的,而不是去區分適用對象的身份來“頭痛醫頭,腳痛醫腳”。如今,對“農民工”權益的保護不應僅僅停留于不斷出臺法規和政策,而應該解決“農民工”的身份問題從根本上解決基本法律不適用于“農民工”的難題,這樣才能走出針對“農民工”的專門立法卻保護不了其權益的怪圈。
把“農民工”和普通公民同等對待,使他們和城市居民一樣享受到應有的權利,就足以保證其地位的平等。《勞動法》第3條規定:“勞動者享有平等就業和選擇職業的權利。該法第12條規定:“勞動者就業,不因民族、種族、性別、宗教信仰不同而受歧視。”這里就沒有所謂的“農民工”的專有概念。2011年7月1日開始生效的《社會保險法》中也沒有“農民工”的概念。
2.“農民工”身份的現實難題
在現實中,法律對“農民工”身份的認定只停留在形式層面,特別是涉及政府或“農民工”個人的利益時,“農民工”法律主體的認定就產生了爭議。“農民工”進城后,應該享有公民待遇。但在許多事件中,政府、企業和城市居民為了維護自身的利益,仍然認定其具有農民身份,而不認可其工人身份。
四、“農民工”身份重新定位的語義規范路徑
(一)取消身份歧視的稱謂——“農民工”
身份是指生而有之的東西,可以成為獲得財富和地位的依據。契約是人自由意志的體現,是民主社會的基本要求,是對身份的根本否定。契約將人們從身份的不平等中解放出來,體現了人與人之間的平等關系,是對個人價值、個人權利、個人自由的尊重。可以說“所有進步社會的運動到這里為止,都是一個‘從身份到契約’的運動”。11
“身份化的社會狀態正是中國在近代落伍的重要標志之一”,梁治平指出,“中國的現代化所面臨的基本問題之一正是要以契約取代身份”。12而當今的中國社會正在處于“從身份到契約”的運動過程中,既殘留了“身份社會”的身份對“農民工”的影響,又沒有完全進入“契約社會”,這個時期可以稱之為“身份+契約社會”。13在這個特殊時期,一種隱性的身份對契約起到了極大的影響,削弱了契約對農民就業的人身保障,這樣就使得務工農民因為身份原因而不能享有與城市居民平等的待遇。
“農民工”是二元社會結構的產物。雖然在中國,二元社會結構解體不可能一蹴而就但也不能等到二元社會消除以后再取消“農民工”這個稱謂。這不僅不符合法律的基本精神,而且是對現行政策的違背。溫家寶總理在2010年3月5日作政府工作報告時強調“我們所做的一切都是要讓人民生活得更加幸福、更有尊嚴,讓社會更加公正、更加和諧。”如果這一帶有歧視意味的稱謂不能在政策、法律、學術研究以及社會輿論中消除,那么在立法和科學研究中就有可能對“農民工”有先入為主的歧視,從而不可能解決“農民工”的身份問題。
(二)還“農民工”以產業工人身份
由于城鄉二元社會體制影響,使得“農民工”身份定位十分模糊:是農民,有獲得土地的權利;是工人,就有拿工資以及享受包括年終分紅、養老保險等權利。那“農民工”是什么?是為城市建設提供廉價勞動力的農民?或者是工人、是城市的重要組成部分?“農民工”是一個帶有矛盾的復合概念,又是一個充滿歧視性的概念。全社會對“農民工”的習慣稱謂,讓“農民工”在城鎮社會日益被邊緣化,要解決“農民工”不平等的身份問題,就應該從賦予“農民工”明確的身份出發,還“農民工”普通工人的身份。
2003年9月召開的中國工會十四大指出:“農民工”已經成為我國工人階級的新成員和重要組成部分。2006年在《國務院關于解決“農民工”問題的若干意見》中,把“農民工定位為普通產業工人,認為其是中國改革開放和工業化、城鎮化進程中涌現的一支新型勞動大軍,是現代產業工人隊伍的主體。
“工人”通常是指為掙工資而被雇用從事體力或技術勞動的人,他們本身不占有生產資料,只能通過自己的勞動才能獲得工資性質的收入。“農民工”完全符合工人的性質。大多數“農民工”與土地的聯系越來越弱,特別是數量巨大的新生代“農民工”,對土地的感情已比較淡薄,他們在生活方式、收入來源、價值觀念等方面與普通城市職工已經沒有太多的差距。在法律層面上將“農民工”身份工人化也沒有制度障礙,我國《工會法》規定“以工資收入為主要生活來源的體力勞動者和腦力勞動者,可確定為職工身份。”
(三)彰顯“農民工”的公民身份
公民身份是一個歷史概念,是伴隨著近現代的權利斗爭的歷史而產生的,是民族民主國家的產物。1789年3月,法國頒布了《人權與公民宣言》,這個憲法性文件較為系統地闡述了現代公民權的原理和內容,就此公民身份從特權身份開始向普遍身份過渡,并對世界各國人民爭取普遍平等的公民身份產生了重要影響。公民權是一種具有法律效力的社會地位,一種政治認同資源,一種履行義務和公民責任的要求,或者一種獲取社會或福利服務的保證和一種取得政治權利的保證。14公民身份一般包含四種權利:公民權利政治權利、社會權利以及文化權利。15
《中華人民共和國憲法》第33條第1款規定,“凡具有中華人民共和國國籍的人都是中華人民共和國公民”,并用專章規定了“公民的基本權利和義務”。公民身份是作為社會的個體享有權利和承擔義務的基礎。從憲法意義上來看,包括“農民工”在內的每一個公民在一些最基本的社會、政治、經濟權利方面都享有同等的待遇。因此,確認“農民工”的公民身份,不僅是要求在法律上完成對“農民工”地位的平等保護,而且在對待“農民工問題上要以“公民權利”為衡量標準和優先價值選擇。
注:
1“農民工”一詞,是社會大眾對進城務工人員習慣性的稱謂,本文為了行文過程中敘述方便,仍然使用“農民工”這個稱謂,但這不代表筆者贊同用這個帶有歧視性意味的概念來界定具有農村戶籍但進城務工的群體。
2張雨林:《縣屬鎮的農民工:吳江縣的調查》,載《小城鎮大問題》(第一集),江蘇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第286-29頁。
3王志愷:《關于“農民工”的稱謂》,《語文建設》2007年第5期。
4中國社會科學院語言研究所詞典編輯室編:《現代漢語詞典》,商務印書館2005年第5版,第1028頁。
5劉豪興:《農村社會學》,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2004年版,第36頁。
6[法]H.孟德拉斯:《農民的終結》,李培林譯,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05年版,第42頁;單飛躍、范銳敏:《農民發展權探源——從制約農民發展的問題引入》,《上海財經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2009年第5期。
7李廣智:《輿論學通論》,黑龍江教育出版社1989年版,第22頁。
8 Cohen Robin,The New Helots:M igrants in the international Division of labor,1st ed,Avebury,1987,pp 186-187。
9[美]博登海默:《法理學》,鄧正來譯,中國政法大學出版社1999年版,第506頁。
10張文顯:《法哲學研究范疇》,中國政法大學出版社2001年版,第59頁。
11[英]梅因:《古代法》,沈景一譯,商務印書館,第97頁。
12梁治平:《“從身份到契約”:社會關系的革命——讀梅因〈古代法〉隨想》,《讀書》1986年第6期。
13劉懷廉:《中國農民工問題》,人民出版社2005年版,第126-129頁。
14[美]蘇黛瑞:《在中國城市中爭取公民權》,王春光、單麗卿譯,浙江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7頁。
15對于文化公民身份是后現代公民理論的新發展,特別是對少數族裔的文化習慣的保護具有重要作用,詳細內容可以參考[英]斯廷博根編:《公民身份的條件》,郭臺輝譯,吉林出版集團有限責任公司2007年版,第174-190頁[加]金里卡:《多元文化公民權》,上海譯文出版社2009年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