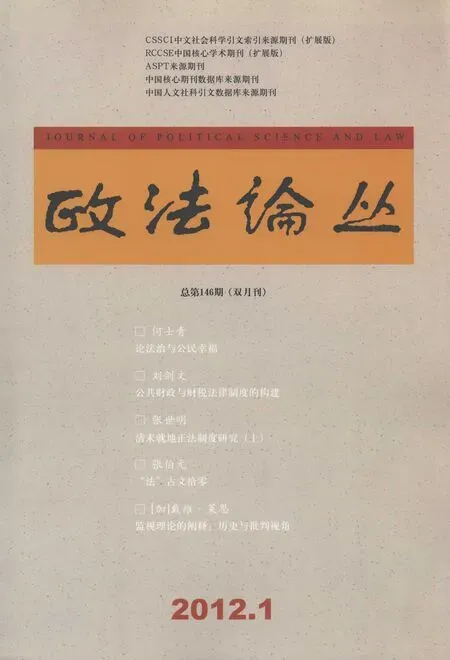監視理論的闡釋:歷史與批判視角*
[加]戴維·萊恩
劉建軍譯
(女王大學,加拿大金斯頓K7L 3N6)
監視,已經迅速成為公眾爭論與政治關注的一個中心話題,同時,作為一個流行主題出現在大眾媒體中,而且高科技公司也通過不斷更新設備來獲取大量利潤,這些現象都清晰地展示了當代的監視。但是,為什么會產生這些現象?其所隱含的趨勢是什么?以及為什么監視會呈現出差異性,或者說為什么在不同組織背景和國家背景下對監視的體驗是不同的?如果不能對上述問題做出解釋或僅僅提供無法讓人信服的解釋,那么監視研究領域就不會有太大意義。
雖然對存在監視的每個領域都必須根據其自身的情形來考慮,而且要讓其接受與其具體特點相適應的理論上的質問,但是在某些方面,我們必須在更廣闊的范圍內來討論監視理論,這也是本文的主要目的。由于監視在不同國家都會出現,也常常以相似類型的計算機軟件和硬件為媒介,而且監視的增長經常與整體目標如“國家安全”或“安全”相關聯,所以必須通過超越監視的地方性和具體的表現來建構監視理論。換言之,監視的全球的、科技的和政策的層面需要某些具有巨大包容性的理論來講清楚這樣一幅大畫卷。然而,對于抽象的宏大的監視理論的探求是徒勞無益的,特別是如果這種理論與特定概念緊密相連,而且該理論被認為具有普遍適用性。因此,把理論性的工作看作是一種持續進行的對話會更好一些,在該對話中應探究和使用那些被證明有幫助的概念或原理,這些概念或原理不應該左右爭論。比如全景監視等概念已經被毫無裨益地過度使用了,在這種背景下,監視理論的任務就是要展示普通人的真實生活,以及用來對他們進行觀察、記錄、詳細說明、追蹤和分類監視模式之間的關系。也就是說,要想提出好的監視理論,使其既能夠真正解釋重要事項又不會變得過度抽象或多疑或技術決定論,我們就必須一直集中關注日常生活的實踐與過程。
任何理論的構成要素均包括要具有歷史性以及能夠承受經驗上的制約和道德上的批判。對監視理論的定位有幫助作用的各種要素包括:盡管監視結果具有保護、授權或照顧的成份,但是,由于通過官僚組織所呈現的軍事動力、地緣政治動力和經濟動力,它在現代社會中主要是作為一種權力工具而擴張的。然而,自二十世紀后半期,基于上述同樣動力的刺激而引起的數碼科技的應用已經幫助產生了交叉系統的相似性、系統網絡與融合以及監視對日常生活的進一步延伸,這些又重疊于以往的監視形態之上且與之相互作用。在較早和稍晚的形態中,主權權力和積極的主觀性一起塑造了在任何特定的環境中監視權力是怎樣有效地發揮作用的。自早現代開始,視覺與可視性一直是監視的中心,但是這種對視覺的強調也影響了我們對以直接的視覺影像為基礎的、非視覺的相似物例如“數據庫監視”的認識。
在本文中,筆者將集中關注理論所試圖解釋的內容。為了獲得最好的工具,我們必須清楚解釋下述內容的監視理論:第一,現代社會中監視的起源,進而,在某種意義上,監視的驅動力;第二,在任何特定時期,重點在當前,監視運作的主要方式;第三,監視對個人、團體和整體社會關系架構的影響。簡言之,我們可以在有助于解釋監視的起因、過程和后果的理論中做出區分,即使基于它們的相關性把它們放在一起考察也仍然會有幫助。隨后,審視監視理論的各個方面:從監視理論在一些學科中的根源開始,討論“現代”和“后現代”的監視理論,進而討論關于“規誡”與“控制”的更具體的爭論,最后關注作為監視理論潛在核心概念“治理”和“禁止”。上述每一部分均構成監視研究中的一個概括的理論問題,而且為了使該理論有意義,必須始終將其與特定的情境、過程和實踐相關聯。但是,上述這些問題也是與批判性立場和規范性立場必要而又強烈地相關聯的,這些立場必須清楚表達出來且接受審查和質疑。
一、監視理論的根源
對于工作場管理領域,正因伊萊亞·朱雷克所指出,諸如馬克思等學者已經注意到“對工人的監控、工作任務的分散、腦力勞動和體力勞動的分工以及工作的系統化”,馬克思把這些看作是使勞動力服從于資本的一種工具。[1]P31但是也如朱雷克繼續說到的,這些主題是與工作場所的監視聯系在一起的,特別是通過利用能夠影響權力關系的新科技。這種監視表現出一種持續的主題是,那些利用某些手段來監視他人的人展現出他們對被監視者的不信任,在當前情況下是指對工人的不信任。工作場所的監視研究經常遵從福柯的對規誡的微觀技術的關注,這些技術瞄準人的身體而且把身體看作需要觀察和檢測的物件[2]P4;朱雷克也指出,細微的和散亂的方法顯示對科技利用的差異會產生不同的結果。但是他也提醒我們仍然需要把更大的政治經濟問題牢記在心,其中某些問題來自于馬克思。現在我們轉向第二個領域即軍事權。克里斯托弗·丹迪科爾認為,福利與軍事發展對西方自由民主的增長是多么重要,過去是,現在也是。[3]并主張利用它們把監視擴展成為民主國家構造的中心。這種主張特別來源于馬克斯·韋伯的理論,而且也來自于遵從“馬基雅維利式”路徑的意大利理論家如帕累托和莫斯卡。早期現代國家必須監控其公民,同時把其權力領域和公民的權力領域相區分。因為戰爭是這些國家生命中的一個重要特征,所以軍事組織最先被官僚化,監視隨之而來。為了便于軍事目標的實現,國家對社會的監控權力得以擴展,隨著“福利國家”在二戰后被創造出來,這些目標變得甚至更為清晰。此外,只要官僚化和技術化的軍事權力的存在被認為是一種維持和平的工具,那么軍事與監視的關聯也將持續。就刑事司法領域而言,從為了警察巡邏而使維多利亞時期的街道具有可視性,[4]到為了秘密工作而對警察裝備高科技設備[5],監視也是其無數進步中的一個關鍵特征。的確,當我們聽到某人“被監視”時,幾乎會自動認為他們正被某種警察人員監控和追蹤。但是為何急劇增加的一般性監視,包括新科技的利用,會出現在某些時間而不是其它時間?涂爾干的犯罪理論很好地闡明了這個問題。他主張,當相對富裕人員與相對貧窮人員之間的差距不斷拉大時,每一個群體都會越來越把另一群體看作是對自己安全的威脅。由于不斷拉大的不平衡的差距,在社會上會存在真實的和想象的犯罪率的增加,而且富人會通過支持更加嚴苛的針對措施以及擴大“犯罪”的定義來應對。這包括富人獲得自我保護的科技,這樣就進一步排除了更加邊緣化的人員,并把違法人員和無辜人員同樣都作為犯罪目標對待。正如佩里陸所表明的,從涂爾干的觀點可以推斷認為將會出現更多的監視,特別是對公共空間保持警惕,而這又會不合比例地影響某些“嫌疑人”的種類,進而增加他們的不名譽的標記。[6]
正如我們可以從上述三個領域的事例所看到的,某些早期社會科學家雖然沒有打算創立“監視研究”,但至少間接說到了監視問題,初步繪制了該領域的藍圖,并使人們注意到現代資本監控的規誡(馬克思)或者軍事官僚體系的記錄保存(韋伯),或者在社會和經濟的不平衡不斷增加時監視會增強的可能性(涂爾干)。人們也可以添加其他事例,如在大都市中對眼睛的強調,這也是喬治·齊美爾作品的中心。[7]對于后者,現代性包含著“陌生人社會”的建立,理想的監視滋生地替代了某種信任關系,是我們可以在長期關系和個人關系占主導地位的情景下看到這種信任關系。更具體地講,我們可以思考經典的社會理論和政治理論是怎樣集中關注眼睛的,甚至無需援引杰里米·邊沁的全景監視,這樣的觀念可以在始于笛卡爾時期的“現代性的視覺的組織管理”[8]的框架下更寬泛地審視。二十世紀后半期,許多理論通過對視覺中心提出批評來做出回應,從中我們可以看出眼睛受優待的程度。通過將此限縮到某些人可以怎樣“看護”另外一些人,我們可以清晰地知道這種“觀察”可以是比喻意義上的(工廠里的工作計時器、辦公室文檔以及城市規劃),也可以是字面意義上的。注意到啟蒙時期“視覺中心主義”的潛在影響及二十世紀對它的批判是很重要的,因為,即使我們看不到真正的眼睛與圖像,許多監視理論背后仍隱藏著對“注視”的“觀察”隱喻與考量。視覺以及對它的批判問題在監視研究中是極其重要的,尤其是因為正是監視概念本身預設了視覺。正如我們將要看到的,更寬泛地講,知識來自于監視的對象,新技術可以被用來提供這種知識。例如,理查德·瓊斯論述在“數字統治”的文章中表明,在許多事例中福柯式的“注視”是如何已經讓位于依賴數字技術的新型監視的。[9]盡管存在明顯的諸多對時間和空間的限制(不過這在封閉空間中不再典型),但控制、排除和懲罰等形式仍持續存在,在某些情形下,看護、監控或監督可以變換為電子眼,具有不能輕易忽略的后果(這種后果在某種程度上已經被忽視了)。
二、現代的與后現代的監視理論
現代監視理論與那些經典觀點相關聯,這些觀點把監視理解為資本主義企業、官僚組織、民族國家、機器式的工藝和新型社會連帶的發展(包括較少的“信任”或至少是不同種類的信任)的自然結果。[10]P109另一方面,后現代監視理論則涉及威廉·斯特普爾斯所認為的新型的“警戒與可視性”,即以科技為基礎的、以身體為監視對象的、日常的和普遍存在的監視。[2]P11
把“現代”和“后現代”術語作為有助益的標記來使用,人們并不一定要認可圍繞著它們的其他爭論。此外,最好將它們看作為處理社會的、經濟的、政治的和文化的圖景中的重大變遷而做出的不斷變化的努力,而不是將它們理解為內在的“理論”運動。在筆者看來,我們需要新的理論來處理日常生活組織管理和全球關系中的某些重大改變,這些改變在20世紀80年代以后凸顯出來。雖然我們無法期待有一個概念可以承擔涵蓋史無前例的社會經歷轉型的重任,但是在此背景下“全球化”具有極大相關性,而且“后現代性”也能較好地說明問題。[11]“后現代性”概念的一個特別有用維度是其指向并承認“現代性”。無需爭論我們是否經歷過現代(這是個好問題),[12]即使后現代性概念,或“后現代理論”被接受,它并非必然地取代之前所獲得的,記住這一點很重要。考慮到上面提及的后現代監視的要素,顯然,很早以前特定種類的監視技巧和技術就已經普遍存在了,而且對人的身體的監視、當地監視以及大范圍的對人口資料的占用(人口普查,自古代就已經在使用)都不是新的想法。相反,這些要素已經引起人們的注意,而且現在正以前所未有的方式主宰著監視圖景。這些都是一般性的概括,旨在僅僅提供一個情景化的大畫卷。
現代監視理論的主要輪廓除了來自于前述的分析,包括馬克思、韋伯、涂爾干,另外兩個也很有意義,一個是法國社會學家和法學者雅克·埃呂爾的(大體上確定但不是明確的)韋伯式的作品,另一個是小說家和社會批評人士喬治·奧威爾的作品的理論影響。他們一個遺留下對監視的技術動力的強烈興趣,另一個遺留下的則是全面監視社會的一個模式(或者“理想類型”,如果有人也愿意在此看到韋伯的影響的話),可將其作為在給定場景下對監視權力進行度量的一種標準。在二十世紀中后期,這兩個人物也都利用道德上的嚴肅性和政治上的緊迫性來發展監視理論。
埃呂爾的描繪粗枝大葉,其中主要一筆是“技術”。這是趨向于“手段”而不是“目的”的文化導向,這也產生了與韋伯作品的部分共同性。這種導向使得對許多人造產品和技術過程的楔入變得可欲可求。技術建造了機器所需的社會,以自身為食物來源,并以一種涵蓋一切而且通常不可逆轉的方式擴展。例如,埃呂爾是那些首先注意到技術化的治安維護所帶來影響的人之一,這種技術化的治安維護要求越來越多的人應該被監控,希望更有效地逮捕那些違反規則和法律的人。警察工作中的技術穩妥地把所有人都置于巧妙的監視之下。[13]就其對極權主義的批判,埃呂爾的作品被許多早期的研究人員和作者看作是對監視研究一個重要貢獻。就從埃呂爾那里獲得某些重要線索的理論家而言,加里·T.·馬克斯關于秘密警察監視的作品以及奧斯卡·甘迪關于個人信息經濟的作品就是恰當的例子。而且“監視蔓延”觀念也是起源于埃呂爾的作品,經由蘭登·溫納的“功能蔓延”概念[14],現在監視領域中被廣泛使用,雖然其也被馬克斯[5]在論述DNA指紋時使用。在溫納的手中,這個術語或者更確切地說是其所指向的趨勢被用來建立例如數字化的識別卡系統,它很容易被擴大到包括其原初的倡議者并沒有設想到的其他功能。[10]P111-113
奧威爾的作品提供了監視研究中某些最持久、最著名和公眾知曉的概念,首當其沖的是“Big Brother”這個人物形象。理論上講,下述觀念是與莫斯卡、帕累托、索雷爾和米克爾斯的作品相聯的,即認為民族國家監視起源于與軍事斗爭和地緣政治斗爭相關的特定的政治命令,而且可能會以消極的和壓迫的方式來控制整個社會。但是在大多數的學術界的和公眾的想象中,這些理論觀念在奧威爾的小說中被賦予了生命。國家權力的集中、技術的運用(無處不在的電視屏幕將大哥的面孔傳送到每個角落,而且通過它也可以監控公民)、扭曲語言來創造“玄虛言詞”,所有這些都是奧威爾所描述的險惡的、以國家為中心的監視社會中我們所熟悉的方面。然而,奧威爾的作品的另外一個方面也值得提及,即他對《1984》社會的實際所在是含混不清的。雖然許多人認為他的作品是對國家社會主義(和“鐵幕”后的舊的“共產主義”國家或東歐)的批判,但奧威爾也并沒有讓西方自由民主輕易逃脫。這一點是非常清晰的,即他的作品,連同像漢娜·阿倫特或安東尼·吉登斯一樣多元化的理論家的作品一起,將極權趨勢,其中國家監視占有顯著位置,看作是任何官僚化組織的民族國家的內在部分。正是在自由民主的民族國家(記錄保存、監控和觀察變得常見且借助科技不斷累積)中,我們可以預見到對自由和(特別是9·11事件之后)人口流動性的限制。這已經成為監視研究的一個永久主題。
兩組患兒診療護理2周后觀察其臨床治療效果,本次研究參考中華醫學協會制定的小兒急性腎炎臨床診療指南,治愈:患兒水腫、腹水等癥狀完全消失,各項檢查指標均恢復正常水平。有效:患兒水腫、腹水等癥狀明顯好轉,各項檢查指標均接近正常水平。無效:患兒水腫、腹水等癥狀未明顯好轉,各項檢查指標未明顯改善甚至惡化(總有效率=顯效率+有效率)。
有一位著名的理論家的確主張監視處于現代生活的中心位置,那就是安東尼·吉登斯。吉登斯主張我們必須看到監視和軍事主義(另一個被忽略的要素)的自身正當性,而不能僅僅將其看作是資本主義或官僚制的產物。[15]對吉登斯而言,監視既指編碼信息的不斷累積,也指對社會生活的直接監控,[15]P13而且它也會成為一個重要的支配手段。雖然吉登斯看到了官僚行政中的極權趨勢,但他也想使自己遠離尼采的更加憤世嫉俗的理性或者福柯的“無處不在的權力”,并讓歷史保有民主化的可能性。雖然吉登斯的作品因為對社會理論中對監視的相對忽視的改變而受到歡迎,但是對于他的貢獻我們還需注意到兩點:一是在數字世界中“監控”與“編碼信息”的區分變得越來越難以為繼,因為在數字世界中編碼信息已經成為監控的一種手段。計算機化的監視也促成了上述區分的崩潰;二是當被用于管理目的個人數據在許多非政府領域被混亂地處理,但具有確定無疑的與政府相關的后果時,吉登斯的論斷即監視主要是民族國家的一個特征就很難站得住腳。
三、邁向后現代監視
到二十世紀后半期,隨著政治經濟環境向“消費者資本主義”邁進以及新數字科技在組織中的利用,監視正在經歷著某些重要的改變。這意味著,舉例來說,那些主要以“奧威爾式”的術語思考問題的人必須在民族國家范圍之外(比如在廣告與營銷中)來思考監視實踐,也必須考慮到這些監視實踐涉以及具有更快速度與更強大能力而且比任何之前的技術更細微的相互作用的技術。新技術使得自動化和恒久的記錄保存成為可能;人的身體也可能會以新的方式被觀察、評價和控制;日常監視具有地方性和即時性;而且大范圍人口數據被采集用來分類和篩選。最后一點特別重要,但也必須非常小心地處理。任何試圖涵蓋技術的社會理論和政治理論都很容易被指控為“決定論”。也就是說,新的人造產品和系統的沖擊會很容易地控制上述主張,進而由于夸大了技術能力,已經存在的情景和過程被輕視而且“固有的”要素被掩蓋。同時,忽視或輕視數字技術在助成創造當今監視圖景中的作用看上去像是對一個有害的危險類別的視而不見。沒有現代技術的啟動,“視覺”的延伸會受到限制[5]P217-19,跨系統的利用和網絡融合也是不可能的,而且“社會分類”(即普遍存在的數字歧視使得對不同類別的人群的不同對待成為可能[16])也不會以今天這樣的規模出現。正如斯特普爾斯所言,更“后現代”的監視理論會強調以技術為基礎的、以人的身體為對象的、日常的和普遍存在的監視。技術使得監視易于自動化而且越來越依賴雙數據或視覺上的自身,對此我們需要重新思考。馬克·波斯特爾對此做了一些重要的觀察,顯示后結構理論是如何幫助我們把數據庫看作“商談”以及把雙數據看作是同時獨立和依賴的實體。[17]對波斯特爾來講,這意味著我們生活在“超級全景監視”的時代。因此,數據庫商談遠非創制福柯的“觀念深入內心”的對象(已經認識到他們的自決權),利用分散的數據“身份”(其中某些人不一定認識到這些“身份”)來創造客體化的個體。身體不再是被保護為“私人空間”的堡壘,它已經是超級全景監視的一部分。后現代監視以人的身體為對象的層面可以從對監視機構來說人的身體的可視性得到觀察。現在,人的身體的可視性在某些情況下幾乎是經常而且不斷受到關注(關注把人的身體本身作為一個監視數據資源)。這種情況并不局限于外部機構,隨著新型監視滲透到各類生活領域,某些監視是相當細致和系統的自我監視。例如,健康“狂熱者”一直檢查時間、血壓、體重和心率,或者某些女士利用秤、身體脂肪測試儀和卡路里表等所實施的低層次的自我監視。[18]就外部機構使用身體數據而言,生物統計信息和DNA的利用會另外著文詳述。
后現代監視的日常特性指的是對日常生活的控制現在已經遠遠超出了刑事違法或工作場所違法的范圍。監視種類現在包括地緣人口生活方式群體、心理學上的分類、教育差別和健康差異。其中的某些監視會追溯到出生甚至出生之前旨在計算未來的生活機會。例如,在英國,根據兒童《保護法》(2004)所建立的兒童登記數據庫甚至被用來檢查兒童每日的水果攝入量。[19]正如德勒茲所言,監視已經超越了具體界限而蔓延到生活的各個方面。從沒人能逃脫被注視,從這個意義上講,監視是無所不在的。無論何處每一種新系統的采用,它們都傾向于具有相似的技術特征,在這個意義上,監視也是無所不在的。威廉·博加德利用讓·博德里亞的作品作為一個跳板來表明監視是怎樣被模仿的。[20]計算機系統的運轉速度使得其可能超越其自身(正如已經發生的),也使得其試圖預言或預測事件成為可能。這是技術能力直接助成監視的變化中的特征的一個事例,使得其具有一種決定性的未來導向。這種觀念就是先觀察,再預測。當然,早期的社會學家如奧古斯特·孔德相信他們能夠預測進而改變事件的進程,在電影小說中,有代表性的最近的闡釋是斯蒂芬·斯皮爾伯格改編自菲利普·K.·迪克的短篇小說《少數人報告》,其中謀殺能夠被有洞察力的“預測人”“看”到。但是作為模仿的監視將之從哲學和小說中拿來并運用到實際的警察工作或營銷中,例如利用在停車場閉路電視中的形態識別軟件提醒操作人員在事件發生之前注意“可疑的行為”。
然而,在實地與日常生活中所實際發生的事情可能展現出監視的“現代的”和“后現代的”特征的混合。雖然在事先的數據收集或“預測性的”閉路電視(尋找行為形態而不是實際違法)中可以看到風險管理與新的治理模式,但是國家的權力仍然強大。例如,公共空間的閉路電視系統雖然可能在商業場所運轉或被外包給運營公司,但操作時仍與警察部門相連,而且國家情報部門仍可以向其索取由之產生的圖像。[21]無論情景是多么的“后現代”,“現代”仍普遍存在于詞匯和社會現實中。
四、全景監視之內與之外
某些可能會被認為橫跨“現代”和“后現代”標題的監視理論起源于米歇爾·福柯或吉勒·德勒茲的作品,但悖論的是,二者均沒有多少時間來闡釋“現代性”或“后現代性”。米歇爾·福柯在其二十世紀中后期的作品中提出有力的解釋性主張,明確指出向現代視覺組織管理的精確轉型(首要的是在全景監視中)[22]。杰里米·邊沁所設想的監獄的半圓形建筑通過單體的背后照亮的牢房提升了囚犯的可視性,并通過中央監視塔中百葉窗的使用減少或消除“監視者”的可視性。權力主要在于監視者一方,他能夠看到別人而不被別人看見,由之所產生的不確定性正是監視者的權力得以保障的手段。
對福柯而言,全景監視的規誡性注視的是現代性的權力原型,是可以充斥于所有社會組織的規誡模型。然而有意思的是,考古工作最近發掘出一些在“全景監視”詞語產生之前的古代的全景觀測點,這就潛在地使福柯主張全景監視具有獨特的現代特性觀點顯得不那么重要。[23]然而,他的作品的確賦予邊沁某些古怪的想法新的一線生機,這些想法雖然在19世紀具有影響力,但就其細節而言,則仍然會塵封在某些失敗的監獄藍圖的歷史中(相反,它們現在已經成為思考監視的某些方面的范式[24])。賦予監視者單方權力的觀念,雖然看上去一直是福柯的意圖,但它激活了一系列的、遵循全景監視而進行的研究。這就產生了對監視的一種相當片面的論述,即著重于忍受生活在被監視的不確定中的潛在的強制經歷,這種經歷或好或壞也有幫把監視推開到一個幾乎不可視的電子監視的時代。在這種論述中,正如福柯自己所言,“可視性是一個陷阱”。[22]P200但是這種論述不但將人們的注意力從監視權力和服從監視的那些人的態度及行為之間的細微相互作用轉移開去,而且它也將所有的重點置于理性控制之上。我們所得到的印象是監視明白無誤地充斥著主權權力的控制利益。邊沁是一位令人奮進的世俗的社會改革家,英國功利主義學派的一個重要貢獻者。十八世紀后半期,英國正充斥著急需刑法改革的各種觀念,而且對此具有貢獻的其他人均來自基督教的福音教派。但是邊沁的洞察力區別于這些人的地方在于,雖然他持有同樣的觀念,認為道德上的洗心革面和非單純的報應性懲罰應當是監獄經歷的核心,但他主張無需任何宗教基礎“德性的產生”[25]也應會出現。因此,雖然他在其全景監視藍圖從《圣經·贊美詩139》中挑選詞句作為序言:“你……深知我的一切。如果我說,或許黑暗會籠罩我,那么我的白天會變成黑夜”,但他拋棄了任何關于監視應當關心個人(與《贊美詩139》同樣的主題)的觀念,完全集中于控制機制。尼古拉斯·羅斯很好地總結了全景監視:對福柯而言,全景監視就是“一種政治技術的示意圖,該政治技術基于持久的監視正將分類個體化和常態化;一種不間斷的和持續的評判,這種評判能夠實現對多樣性的管理,減少人體的抵抗力量,同時實現人體的經濟的和社會的效用的最大化”。[26]P187但是在福柯的模型中有一些過程發揮著作用:一個過程涉及規誡,正如在全景監視藍圖中所看到的;另一個集中于生物權力。第一個有助于把個體常態化,而第二個,通過例如普查等工具,利用群體或類別把人們社會化。在第二個事例中,個人會受到他們的群體身份或關聯的影響。然而,即使是在全景監視中,也會存在對囚犯類別的區分,因此生物權力在那里也是存在的。
雖然福柯聲稱他的主張是當前的歷史,但是他有意地沒有提及大眾媒體或計算機在助成規誡和生物權力的類型方面的作用,相反,他對規誡和生物權力已經表達出真知灼見。然而,其他人已經把福柯的觀念運用到數字監視領域,以此表明全景監視也會變得電子化[17]。當我們沿著從(根本就沒有建成、但據稱其原理已經彌漫現代社會的)監獄到(邊沁根本不可能想到、而且也被福柯奇怪地忽略的)電子形式監視的軌跡前進時,對于這種軌跡人們是有理由持懷疑態度的。回想到下述一點是重要的,即福柯在一些其他不同的語境中(比如《性史》[27]和其他作品中得到探討)來看待他的監視作品,同時以其他概念如“懺悔”[28]為中心。而且同樣重要的是,并不總是可能來全面總結全景監視。一方面,全景監視最主要的示意圖就是監獄,雖然監獄的某些操作可以在其他情景如工作場所中發揮作用,但是監視對象能夠走出監視地點的程度的確是不一樣的;另一方面,全景監視的一個核心要素是其有助于福柯所稱的“靈魂訓練”,因此,雖然可視性對閉路電視系統極其重要,但是如果沒有靈魂訓練要素,閉路電視在多大程度上可以被稱為是全景監視就大打折扣。[29]在《規誡與懲罰》[22]中,福柯認為監視發生在封閉的空間(監獄、工作場所和學校),在那里人們是受到限制的。每一種情景都有其發揮作用的全景監視規則,將監視對象收納、塑造和包括在一個自動權力系統中。福柯的主張表明,自我規誡是如何通過全景監視和相關措施得到提升的。人們對其是否受到監視的不確定性產生使自己的行為與當下組織所認為的正常的事情相一致的欲望。通過這樣一種過程就形成了一種內在強制力去做組織所規定的“做正確的事情”,這就產生了監視者所希望的“馴服的軀體”。上述簡短的說明強調權力和知識維度(其與視覺相關聯),而且也突出了許多人認為福柯所意欲達到的,即因為“視覺”在現代支配形式中的作用而對“視覺”的曝露和批判。毫無疑問,全景監視模式說明了監視發展的某些有趣的方面,而且也必須說它也面對著許多重要的批評。一方面,它幾乎沒有關注大眾媒體的增長,進而也沒有關注“壯觀場面”的持續存在,該主題最初由托馬斯·馬西森在其論述“多數監視少數”的作品中首先提出。[30]另一方面,雖然存在一些富有想象性的努力,但是仍然很難把數字化提升的監視的所有各不相同方面借助于視覺導向的全景監視的權力和知識動力而聚合在一起。此外,福柯對主觀性也有額外的觀察,在考慮到這些批評之后上述觀察仍具有相關性。
接著,目前的討論會轉向監視理論如何可能走“出”全景監視的問題。首先與數字科技和“控制社會”主題相關;其次與另一個福柯式的主題即統治(或者不那么別扭的表述,治理)主題相關。在德勒茲的控制社會觀念中存在并不明顯的對全景監視理論的批判,即這種監視已經被其他形式的權力而不是規誡所替代,且借助電子技術而得到緩解;并且在“統治”論證中,監視被看作是更廣的權力概念中的一小部分或一種策略。
關于全景監視之后的監視的爭論呈現出許多不同形式,其中羅伊·博伊恩主張“后全景監視主義”應該被看作是全景監視范式的后繼者(然而,根據界定,這種立場并不具有全景視角那樣的融貫性)。[31]首先,從齊格蒙·鮑曼那里,博伊恩借用了各種形式的對消費者的引誘正在取代全景監視統治;其次,他還表明,自我監視在西方資本主義社會可以實施的如此有效以至于使得最初全景監視動力顯得多余。第三,他還提及威廉·博加德的主張,即模仿、預測和事實發生前的行為可以減少對舊的監視形式的需求。第四,博伊恩拿來馬西森的論點,即大眾媒體的同景監視(多數人對少數人的監視)與全景監視(少數人監視多數人)并行,進而就使得其影響不那么明顯。最后,全景監視沒有產生馴服的主體的主張(這是可以爭論的)可以看作是對全景監視理論的最后一個挑戰。
德勒茲在一篇精煉但論點鮮明的名為《控制社會后記》的文章中勾勒出從“規誡”到“控制”的轉換。[32]盡管福柯在限制且固定的空間如全景監視中已經將監視理論化,但德勒茲主張這些舊的限制地點不再是監視唯一的或主要的地點。過去“相似的”地點現在則因新數字手段而變得一致,這種觀念與保羅·維里里奧的觀念相似,其提及“視覺機器”迅速的不受約束的控制。[33]新的監視被個體化且具有競爭性,適合于自二十世紀后半期重構而出現的新經濟,其中持續的監控核查著工人的活動,而且個體激勵提供了服從的動力。根據德勒茲的看法,在規誡社會中利用署名和數字,個人能夠被個體化和聚合。現在所需要的僅僅是“單個個體”的密碼,這樣他們就可以順利通過普遍的調控體系:刷卡以及把拇指指紋放在屏幕上。工作可以外包,消費者可以為自己服務,病人可以盡快地通過傳送系統,違法者可以被標記。事實上,德勒茲的“控制社會”主張與同一時間在英語世界提出的另一種理論即“新刑罰學”觀念具有鮮明的相似性。[34]該理論的倡導者主張新刑罰學涉及“識別、分類和管理根據危險性等級而區分的群體的技術”,而不是把罪行和責難歸屬到個體身上以及施加懲罰和處理。[35]P180對待犯罪的新的風險管理方法要求監視,這是為了做出評價而不是以懷疑為基礎的監視的個體化形式。一般性地接受該主張的其他人包括邁克爾·哈特和安東尼奧·內格里,他們在《帝國》中主張,隨著20世紀60年代消費者膨脹之后而出現的“政府危機”涉及對既有權威的整體性轉向,這種轉向導致一種明顯的“后規誡”情景。[36]當局不能再依賴舊的內在強制(部分孕育自全景監視政體),出現了兩種不同的策略來替代內在強制:“壓制”策略和“民主”策略。前者,以工作場所為基礎,區分特權工人和邊緣化的工人,特別是利用新技術來監視邊緣化的工人。后者則與民主的、分散的和分配的方法相關,這是以消費過程為基礎且產生包容與排除的新形式。《帝國》的主張反過來非常容易使人回想起齊格蒙·鮑曼的“可以接受的”和“有瑕疵的”消費者的分析,其中后者由于他們的不服從而被排除在體系之外。[37]P38然而,鮑曼所省略的是有瑕疵的消費者(他主要用此來指貧窮的人)是如何可以通過社會分類過程而被積極地排除在外的。今天,“懷疑的商業化”意指監視技術甚至出現在日常生活中,出現在住宅、家庭,當然也包括工作環境中。
對監視理論而言,全景監視觀念仍然具有某些可取之處:因為某些監視的確仍然會存在于封閉的空間,首要的是存在于監獄中,全景監視的示意圖起初就是關于監獄的。此外,人們對自己是否被觀察的不確定性仍然可以阻止違法行為的發生,這也是即使攝像頭并沒有真正打開或錄像,為何某些閉路電視系統也會被說成“發揮作用”。但為了解釋當前其他諸多監視形態,監視理論必須拋棄全景監視。全景監視,依據其最無助益的表述,是極權權力控制不幸受害者的一個隱喻。我們可以利用許多更好的方式來從理論上思考監視,探討在電子化的格局中權力的實際運轉方式、服從于監視體系且與之相互作用的人的體驗,以及監視體系與監視對象之間的復雜政治在實踐中是如何得到解決的。
五、治理、分類和“禁止”
在監視討論中,福柯的作品也會被用來思考“統治”或治理。正如戴維·加蘭在涉及控制文化時所言,“至少在該領域,刑事司法國家正在擺脫通過自上而下的命令的‘主權’支配模式,而且正在形成一種接近于‘統治’的控治形式:一種涉及包容其他、激勵塑造以及形成新形式的合作行為”。[38]P125這并不必然地意味著管制形態會一直呈現在政府統治中或者這種轉型在其他方面是消極的。的確,加蘭本人認為現代性后期的復雜世界要求市民社會的管理能力應該得到治理,從而與民族國家一起發揮作用。
從理論上講,福柯認為治理并不是控制而是自由,雖然這是有限制的自由,這是尼克拉斯·羅斯的作品《自由的權力》[26]中的思想。羅斯主張,當前的政府統治涉及作為人類行為能力的擴展的“自由”是如何成為核心主題的。如果監視與控制戰略有關的話,那么,羅斯認為,這些控制戰略就必須被看作是借助于自由而為政府統治所支付的代價。[26]P273羅斯強調,福柯并不是在為劃時代的“規誡社會”而辯護,但福柯認為在規誡社會中充斥著規誡戰略和策略;[26]P234而且德勒茲的作品也應當以同樣的方式來理解。通過探求僅僅當前“控制”的新的可能性和復雜性,而不是從一開始就在固定場所中規誡監控對象,我們會發現,監視是事先設計在并彌漫于日常生活進程中的。羅斯強調他的作品是經驗性的而不是現實性的,旨在探索福柯而不是局限于福柯。正如凱文·哈格蒂所尖銳論辯的,就其模糊性與復雜性而言,治理與監視研究具有某些強烈的共鳴,其中首要的是治理的知識依賴。[29]可視性對治理是至關重要的。各種知識被用來通過識別、分類和監控來管理人群;而且各種研究,例如羅斯的研究,并非致力于“宏大理論”建構如“后現代性”或者甚至“控制社會”,焦點永遠集中于具體的監視計劃。其中每一種都具有自己的準則,且都被監視對象以不同方式來看待。但是哈格蒂也正確地主張,當統治路徑拒絕考慮政治要素中的規則與關系的實際體系時,它也是具有自我限制性的。他提出,無論我們可以從統治性視角中獲益多少,監視研究都應該為現實主義的探索留有空間,探討監視對象的體驗以及表明哪些群體能夠利用監視權力來實現其目的的具體分析。
正是為了此類目的,許多監視研究集中于“社會分類”過程,將其作為一種理解實際的監視實踐如何具有特定后果的手段。[39]這些研究取材于但又超越了統治性,表明在具體情景下,權力、不平等和不正義的模式是如何形成的,以及它們更廣的社會和政治后果是什么。根據某些具有代表性的分歧,我們可以探討,例如性別化的、種族化的和基于階級的區分是如何可以通過當代的治理政體和相互聯系的通常的監視行為而得到緩解或加強的。[40]因此,例如,安·巴托提出,以特殊方式,通過在線營銷技巧,婦女被鎖定為服務目標,其中25~49歲的女性“被高度重視”,被認為是最有價值的消費者。雖然在該領域仍有許多工作要做,但她主張,婦女特別容易受到在線消費者分析儀的追蹤。[41]同樣,監視研究也會調查“種族”群體是如何受到特別追蹤的,并不僅僅通過明顯的9·11之后的發展,如在機場不斷增強的資料分析,[39]也會通過基因測試。奧斯卡·甘迪主張在預防性模式如健康醫療中,種族和性別標簽造成“傷害的不平等分配”。此外,由于過往的決定常常與未來的選擇相關,此類困難情形會在被稱為“累積的劣勢”模型中聚集。[42]另一個基于監視的重要挑戰出現在羅杰·伯羅斯和尼古拉斯·甘恩的作品中,他們展現社會階級理論是如何面對當前市場營銷實踐的。他們主張利用地緣人口統計數據,根據人群的居住位置來對他們進行分類在目前是如此重要,以至于它對某些傳統的構想社會階級的傳統方法提出挑戰。[43]雖然地緣人口統計分類在市場營銷產業中被廣泛應用,但是正如伯羅斯和甘恩所提到的那樣,幾乎沒人提及它們與階級的社會學之間的關系。對不同的城市規劃區域確定等級首先是政策制定者的一項工作。他們試圖決定住房許可的優先性,而且具有諷刺意味的是,僅僅是后來試圖區分富人居住區的種類。人們通過瓦解一些社會學變量,如階級、住房、生命歷程、收入、健康和居住區的教育來探索消費模式,這就產生了粗略的劃定如“年輕有權勢的人群”或者“游泳池和庭院”,或者可能對營銷人員稍微不那么理想的“族群的下層階級”。然而,在信息資本主義下,伯羅斯和甘恩主張,這些分類在新的方面正變得具有社會學上的重要意義,也有助成重構日常生活的地緣社會空間,即使是在諸如道路利用或網絡使用領域,為了優先的和日常的服務而對社會空間進行分類。
然而,隨著分類系統的詳細資料可以在網絡上獲得,以及消費者居住于與這種或那種消費群體相關的郵區,他們也開始意識到自身是如何被分類的。對伯羅斯和甘恩而言,這意味著韋伯的對(作為生存機會的)階級和(作為生活方式的)身份的傳統區分可能會更難以維持。例如在住宅市場中,生存機會可能會與文化信念相關,這些信念幫助決定機會和選擇;而且分類權力、治理存在于商業公司領域,而不是在國家手中,身份(或者更準確地說是身份識別)再一次變得可以用地點來清晰表達。因此,當人們尋求與他們的社會地位相稱的居住社區和郵區時,自我分類就會出現,但是地緣人口統計分類的過程仍然是神秘的。對許多普通人來說,這種分類過程在技術上是難以理解的。而且能夠對消費者首先做出自我分類選擇的能力具有實質性影響。取材于福柯作品而且建立于其之上的另外一種方式是去思考結構化的權力和普通的日常生活的關系。特別是喬吉奧·阿加姆本的作品提出了關于他所稱的“主權權力”和“透明生活”的嶄新見解,這種觀念與分類和排除的新監視統治密切相關。[44]然而,在該作品中,監視研究繞了一個圈子重新聚焦于國家活動而且也聚焦于公民或非公民。阿加姆本赤裸裸地從集中營視角來看待整個世界,其中死亡被宣判而且生命被指引。阿加姆本認為,福柯和其他人從未成功地把主權國家與組織如監獄(如出現在《規誡與懲罰》中的)觀念和日常生物權力(如出現在《性史》中的)概念聚合在一起。阿加姆本說,在一種新的意義上,極權主義和民主在特定事項上具有共同點。在《例外狀態》中,阿加姆本討論了一個當前事例,即喬治·W.·布什總統宣傳在“針對恐怖的戰爭”中他是“總指揮官”,這種宣稱具有較長的歷史,其中,正如所表現的那樣,例外已經成為規則。[45]在9·11事件之后的“緊急狀態”下,布什行政當局授權,對被懷疑有恐怖主義活動的非美國公民的無限拘留權和隨后由軍事委員會對其進行審判。阿加姆本主張,最初旨在是一種臨時措施的例外狀態在20世紀進程中已經成為一種常態的統治模式,且在9·11事件之后得到增強。
對于迪迪爾·比格而言,阿加姆本的體系化地排除某些群體的“禁止”分析[44]會引起人們思考一種進一步的后福柯的新詞,“禁止的監視”。[46]雖然北半球的大多數公民以前面提及的方式通過他們置身于消費者資本主義之中而被常態化,但對無合法證件者、潛在的恐怖主義者、難民(那些“陷于遷徙命令困境中”的人)仍保留著集中監視。警察、軍事專家和其他專家集合起來變成新的“不安全專家”。該“監視”具有具體目的,用來“禁止”某些人以及用來排除某些人。不同來源的混合資料導致新的分類,這樣對阿加姆本來說可以畫這么一條系譜線索:從二戰納粹集中營,經過同一時期在美國和加拿大的日本人拘留營,再到近海設施如古巴關塔納摩灣基地(用來關押9·11事件之后的“恐怖主義嫌疑人”)或澳大利亞的用來關押未處理的難民的拘留中心。當然,可以爭論說,這些僅僅是針對被排除的人群的、明顯且嚴格界定的“集中營”;也可以說,通過外籍勞工許可證、永久居民卡和其他類似證件的使用,許多不確定的狀態得以維持。但是要想探討這些就需要超越這種簡短的說明中的觀點,就要表明,雖然監視研究可以從統治研究的學者那里獲得洞見,但為了審視監視的政治,也為了理解這些統治的對象對他們所處的情景是如何反應和應對的,仍也有空間來詳細說明這些具體的治理機制所創造的實際條件。
六、理論與反監視
如果監視研究需要一個理論伙伴的話,筆者建議最好選擇一個普遍性的路徑,如治理而不是具體的包容一切的概念如全景監視。即使具有這樣一個伙伴,監視研究也應通過為更現實的分析(使其自身關注監視的實際條件、過程和主觀性的理論化)留有空間,來努力保持其自身的完整性。這就應重視諸如社會經濟階級、種族和性別等關鍵層面,這些層面也是今天必須運用于字面意義上的“監視”(閉路電視)和文學意義上的“監視”(數據采集)領域的。這里并不需要提及“監視名單”,即建立多元的網絡化數據庫、數據采集和在當今的“禁止與監視”中發揮作用的跨部門的備忘錄。
福柯曾提到,權力具有創造性和權力會產生反權力。許多關于監視抗爭的研究表明,需要一種能包含人們如何與監視進行斗爭的理論。這種對監視的抗爭可以是下列任一層面的:運動、具體的反監視組織(如國際公民自由監控小組或紐約攝像頭表演者組織)或日常的明顯臨時性的協商和抵抗。[47]諸如柯爾斯蒂·鮑爾[48]、希爾·科斯科拉[49]、約翰·麥格拉斯[50]等理論家表明了,作為一種挑戰監視權力的手段,在日常生活中,人們是如何提出質疑、拒絕合作(“我要在沒有尿壺的地方撒尿”)、減少公開露面或謹慎地遵守。當然這種抗爭也可能含有某些其他相關運動的因素,如公民自由、女權主義、反種族主義、遷徙自由和身份識別等。最終,監視研究必須超越一般性的(甚至全面性的)規誡或控制理論,進而觀察具體的行為方式,即這種或那種組織是如何被牽涉到監視中的,以及由于監視對象的服從或拒絕,監視是如何得到調整的。當然這本身也可能遇到反對措施。例如,將要進入特定國家領域的入境者的“不受歡迎的”群體的邊境抵抗促使相關專家把檢查向上游移動,正如我們在機場所看到的事先的旅客信息和旅客姓名記錄系統。這構成了此處筆者所倡導的理論的敘述式路徑。
與此同時,還存在一條筆者認為其具有核心重要性的理論線索(其實也可以說是一種努力),即致力于某種體現人格的觀念。與某些理論家的明顯的結構或技術的路徑相反,我們必須強調主觀性的類別:這些主觀性類別是建立在社會現實主義視角下的物質性之上的,這種物質性既不是排除肉體(貶低身體),也不是極度肉體(將身體置于社會解釋的中心)。受到監視的積極或消極的影響的是具體的個人,也是具體的個人或好或壞地與監視進行斗爭。這樣,米歇爾·德·塞爾托[51]的貢獻對監視研究就變得極為重要,正如保羅·利科的貢獻那樣,利科強調自我敘事(如在“自我認同”中)作為對“身體”的補充。[52]這尤其與身份卡系統密切相關,首當其沖的是把對自我和對他人的關心作為從事監視研究的目的,特別是處于“禁止”領域中,這種“禁止”會極度地和殘酷地影響著那些其“差異性”被消極地解釋的人們。[53]P149-55
同時,一定不能忘記資本主義、官僚制、政府部門、公司、警察、安全機構等等,每一種組織都在創造的更廣的監視領域中發揮著各自的作用,其中主觀性部分重疊。監視不僅僅是實現其他目的的一種手段,也是一種治理手段,包括關懷和保護。古典理論家和更近的文化理論家對于理解監視的諸多層面持有重要的洞見,但最終這些觀念的真正價值只有在與其他兩個要素相聯系時才能實現:一個是現實世界的經驗條件限制。正是以這些條件為背景的所有的理論得以立住腳跟、或者失敗或至少證明它們的有用性和閃光特性;另一個用來表明那些理論的努力,這絲毫不比經驗性條件少。對筆者來說,這種努力體現在對正義的追求中,該正義要特別考慮到最脆弱和最邊緣化的人,而且要求一個雙重回應:一個是要傾聽他們的聲音和故事;一個是大規模的組織機構、網絡和監視過程要對它們對個人數據的使用負責。這就是體現人格的理論與當今普遍存在的監視現實的對話。
七、結論
在此,筆者試圖總結我們關于監視理論所討論過的一切,并表明對從事監視研究而言它們的內在涵義。通過歷史性地考察對監視的解釋是如何形成和發展的,分析性地考察監視過程和實踐是如何運轉的,批判性地考察監視的主要后果是什么,就能夠把對監視的起因、過程和后果的論述聚合在一起。
就當代監視的起因而言,可以追溯到現代形態的資本主義實踐和官僚制實踐的增長,但是它們也獲得了某些獨特的自身特性。例如,個體化均是兩種模式的基礎,但后來極易在以計算機為基礎的系統中合并。在民族國家中,行政權的加強、對工人的資本主義式控制的驅動、原料與市場都為監視提供了一個持續的催化劑。對理性、效率和速度的追求,加上多樣化地對人口的控制和關懷(例如,在福利國家中)也促成了不斷提升的監視。同時,正如涂爾干提醒我們,現代性也帶來了社會不平等和沖突的不斷升級,這又促進對更好的警察監控的探求和對壓制異議者的技巧的尋找。站在當前及全球高度,技術助成的監視可以看作是南北差距不斷增長的產物,并因對暴力抵抗的應對而進一步加劇。
如果那些是當今監視的起因,那么,我們所實際親眼目睹正在發生的就是監視在技術上不斷增強的基礎,這又呈現出另一些特點——邁向風險管理的轉型。從福利國家到安全國家路徑,從犯罪的社會基礎到新刑罰學,從一種更久遠的、更多家長制的管理方式到一種精算會計的“新管理主義”,預示計算模式的軌跡,能夠被考慮到的因素發揮著重要作用。所有變化必須得到仔細考慮,與之并肩的是兩個其他特征:一是分類的驅動力,用監視語言意思是“社會分類”;另一個是體系融合的驅動力,這可見于“聯合”的政府服務,或者更抽象些,于監視集合的增強中。然而沒有任何一種“轉型”在任何意義上已經完成,這些是大的趨勢和傾向。舊的和新的實踐以各種不同形態混合在一起,在一些領域,這就是重要的監視發展過程。
最后但同樣重要的,這些監視過程的后果包括如下方面:對融合的持續追求意味著要求“協同性”,例如在諸如北美或歐洲要求標準的機讀旅行證件,這會產生持續的對數據的強迫,即為了某一特定目的采集的數據卻被用于另外目的。一種觀點認為,如果來自電話公司或信用卡公司的消費者資料能夠被用于警察調查或犯罪預防,暫且不論其成本與收益,這會有多大作用。網絡化的監視形態也產生了一種情景,其中越來越多的平凡的日常生活被檢查和控制。刷卡、取消個人識別碼、制作帶照片的身份證明,所有這些以及更多的其他事項現在都已成為日常生活中被看作是理所當然的協議,而且它們也會帶來一種不斷傾向于未來的監視世界。
此處所討論的以風險為基礎的管理路徑的目的是要在事件發生之前先發制人(如犯罪或暴力襲擊),而不是僅僅核實過去發生的事件或者知曉當前正在發生什么。這種對可能性、模仿和來自數據的推斷的集中關注就把某些監視轉向一種明顯抽象的推理模式,而且看上去也是關注點偏離了受監視影響的現實的具體人們。這難道就是為什么在目前產生“例外情形”的“緊急”情景下,法治(例如在人身保護令詞組中,其明顯地指向實際的身體)可以被認為是可有可無的?是抽象的“懷疑的種類”,而不是可以觀察到的事實使得人們有罪,除非被證明無罪。同時,這些監視體系并不總是以所期望的方式運轉,這至少有兩個原因:一方面,技術只是可能不會實現其制造者的或更有可能是其政治支持者的要求;另一方面,這些體系可能會遭到受其影響的人的抵制或至少是協商。前一種情形的事例可以在本文的各個地方找得到,而后一種情形的事例會專門著文具體探討。然而任何令人滿意的監視理論都必須把這些要素作為其理論的一部分。無論是什么驅動了監視,也無論其具有公開的還是不公開的邏輯,我們不能忽視這樣一個事實——監視系統可能不起作用或遭到顛覆。
[1]Zureik,E.Theorizing surveillance:the case of the workplace[C].Lyon,D.Surveillance as social sorting.London and New York:Routledge,2003.
[2]Staples,W.Everyday surveillance:Vigilance and visibility in postmodern life[M].2nd ed.New York:Rowman&Littlefield Publishers,2000.
[3]Dandeker,C.Surveillance,Power and Modernity[M].Cambridge:Polity Press,1990.
[4]Cohen,S.Visions of social control[M].Cambridge:Polity,1985.
[5]Marx,G T.Undercover:police surveillance in America[M].Berkley: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1988.
[6]Perri 6.The governance of technology:concepts,trends,normative principles and research agenda[C].The“Human Choice and Technological Change”Conference.Lisbon,Portugal,2003.
[7]Simmel,G.The metropolis and mental life[C].Wolff K H.The sociology of Georg Simmel.Glencoe,IL:Free Press,1950.
[8]Jay,M.In the empire of the gaze:Foucault and the denigration of vision in twentieth-century thought[C].Appignanesi,L.Postmodernism.London:Free Association Books,1989.
[9]Jones,R.Digital rule:punishment,control and technology[J].Punishment and Society,2000,2(1):5-22.
[10]Lyon,D.Surveillance society:monitoring everyday life[M].Buckingham:Open University Press,2001.
[11]Lyon,D.Postmodernity[M].Buckingham:Open University Press,1999.
[12]Latour,B.We have never been modern[M].Cambridge,MA:Harvard University Press,1993.
[13]Ellul,J.The technological society[M].New York:Vintage,1964.
[14]Winner,L.Autonomous technology:technics out-of-control as a theme in political thought[M].Cambridge,MA:MIT Press,1977.
[15]Giddens,A.The nation-state and violence[M].Cambridge:Polity,1985.
[16]Graham S,Wood D.Digitizing surveillance:categorization,space,inequality[J].Critical Social Policy,2003,23:227-48.
[17]Poster,M.Database as discourse or electronic interpellations[C].Lyon D,Zureik E.Computers,surveillance and privacy.Minneapolis:University of Minnesota Press,1996.
[18]Bordo,S.Unbearable weight:feminism,western culture and the body[M].Berkley: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1993.
[19]Roberts,J.Beware the parent trap[N].The Guardian,2006-06-26,www.guardian.co.uk/commentisfree/story/O,1808379,OO.html.
[20]Bogard,W.The simulation of surveillance[M].Cambridge and New York: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1996.
[21]Norris C,McCahill M.CCTY:Beyond penal modernism?[J].British Journal of Criminology,2006,46:97-118.
[22]Foucault,M.Discipline and punish:the birth of the prison[M].Harmondsworth:Penguin,1979.
[23]Yekutiel,Y.Is somebody watching you?Ancient surveillance systems in the Southern Judean Desert[J].Journal of Mediterranean Archaeology,2006,19(I):65-89.
[24]Lyon,D.Theorizing surveillance:the panopticon and Beyond[M].Cullompton,UK:Willan,2006.
[25]Evans,R.The Fabrication of virtue:english prison architecture 1750-1840[M].Cambridge: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1982.
[26]Rose,N.Powers of freedom[M].Cambridge: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1999.
[27]Foucault,M.The History of sexuality[M].Volume 1.Harmondsworth:Penguin,1976.
[28]Cole,M.The role of confession in reflective practice:monitored continued professional development(CPD)in health care and the paradox of professional autonomy[C].Lyon,D.Theorizing Surveillance:the panopticon and beyond.Cullompton,UK:Willan,2006.
[29]Haggerty,K.Tear down the walls!On demolishing the panopticon[C].Lyon,D.Theorizing Surveillance:the panopticon and beyond.Cullompton,UK:Willan,2006.
[30]Mathiesen,T.The viewer society:Michel Foucault's panopticon revisited[J].Theoretical Criminology,1997,1(2):215-34.
[31]Boyne,R.Post-panopticism[J].Economy and Society,2000,29(2):285-307.
[32]Deleuze,G.Postcript on the societies of control[J].October,1992,59:3-7.
[33]Virilio,P.The vision machine[M].London:British Film Institute,1994.
[34]Feeley M,Simon J.The new penology:notes on the emerging strategy of corrections and its implications[J].Criminology,1992,30(4)449-74.
[35]Feeley M,Simon J.Actuarial justice:the emerging new criminal law[C].Nelken,D.The futures of criminology.London:Sage,1994.
[36]Hardt M,Negri A.Empire[M].Cambridge,MA:Harvard University Press,2000.
[37]Bauman,Z.Globalization:the human consequences[M].Cambridge:Polity,1998.
[38]Garland,D.The culture of control:crime and social order in contemporary society[M].Chicago: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2001.
[39]Lyon,D.Surveillance as social sorting:privacy,risk and digital discrimination[M].London and New York:Routledge,2003.
[40]Amoore L,De Goede M.Governance,risk and dataveillance in the war on terror[J].Crime,Law and Social Change,2005,43:149-73.
[41]Bartow,A.Women as targets:the gender-based implications of online consumer profiling[EB/OL].www.fic.gov/bcp/workshops/profiling/comments/bartow.htm,2005-09-01.
[42]Gandy,O.The panoptic sort:a political economy of personal information[M].Boulder,CO:Westview,1993.
[43]Burrows R,Gane N.Geo-demographics,software and class[J].Sociology,2006,40(5):793-812.
[44]Agamben,G.Homo Sacer:sovereign power and bare life[M].Stanford,CA: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1998.
[45]Agamben,G.State of exception[M].Chicago: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2005.
[46]Bigo,D.Globalized(in)security:the field and the banopticon[C].Solomon J,Sakai N.Traces:a multilingual series of cultural theory and transition.Hong Kong:University of Hong Kong Press,2005.
[47]Gilliom,J.Overseers of the Poor[M].Chicago: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2001.
[48]Ball,K.Power,control and computer-based performance monitoring:repertoires,resistance,and subjectivities[C].Lyon,D.Surveillance as social sorting:privacy,risk and digital discrimination.London and New York:Routledge,2003.
[49]Koskela,H.“Cam era”:The contemporary urban panopticon'[J].Surveillance and Society,2003,1(3):292-313.
[50]McGrath,J.Loving big brother:performance,privacy and surveillance space[M].London and New York:Routledge,2004.
[51]de Certeau,M.Heterologies:discourse on the other[M].Manchester:Manchester University Press,1986.
[52]Ricoeur,P.Oneself as another[M].Chicago: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1992.
[53]Lyon,D.Surveillance after September 11[M].Cambridge:Polity,200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