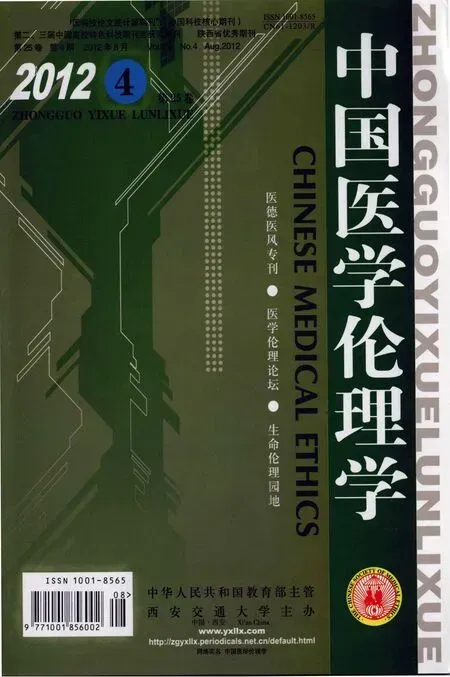“差序格局”與“團體格局”對村級衛生人力資源配置的影響研究——基于北京市M縣的實地觀察分析*
王曉燕,呂兆豐,高 清,彭迎春
(首都醫科大學衛生管理與教育學院/首都衛生管理與政策研究基地,北京 100069,wxy@ccmu.edu.cn)
農村醫療衛生工作歷來受到各級政府和衛生行政部門的高度重視,這是毋庸置疑的事情。但在研究中發現,北京市M縣的村級醫療衛生人力資源無論是數量、質量,還是分布,都與國家和北京市的目標有一定差距。根據課題組于2011年底對M縣17個鄉鎮衛生資源配置情況進行兜底調查的結果顯示,截止到2011年底,M縣17個鄉鎮的332個行政村中,有282個村設有村衛生室,設衛生室的村占行政村總數的84.94%,高于北京市的78.8%,低于全國的90.4%。17個鄉鎮共有常住人口28.15萬人,鄉村醫生473人,平均每個常住人口擁有鄉村醫生和衛生員人數為1.68人,高于北京市的1.34人及全國的1.19人。M縣每千農業人口擁有村衛生室1.47所,高于北京市的1.14所及全國的0.72所;平均每個行政村鄉村醫生數為1.42人,高于北京市的0.93人,低于全國的1.75人。從數量來看,除了設衛生室的村占行政村總數的比例及平均每個行政村鄉村醫生數低于全國水平外,其他指標均高于全國和北京市的平均水平。在衛生人力資源的質量方面,本次觀察的27位村醫平均年齡已經達到54.11歲,只有2人取得執業助理醫師資格。而兜底調查顯示,M縣僅有1.90%的村醫具有執業助理醫師證書,1.27%的人具有執業醫師證書。在分布方面,目前仍有約12.35%的行政村沒有村級醫療衛生服務機構。
從表面上看,村級衛生人力資源的配置及承載的服務等是衛生系統的制度安排,不涉及其他領域,實則不然。在實地觀察中我們發現,“差序格局”與“團體格局”相互滲透,共同影響著村醫這個農村村民健康“守門人”作為衛生資源核心要素的服務水準和配置情況。而農村改革和衛生改革引發的“團體格局”的變化以及村落“差序格局”的變化,成為影響村級衛生人力資源配置的一個不可忽視的重要因素。
1 影響村級衛生人力資源配置的“格局”的變化
早在2001年,國務院體改辦等指出,“農村衛生工作是建設社會主義新農村的重要內容,是保障廣大農民健康,保護農業生產力,振興農村經濟和維護社會穩定的大事,是我國衛生工作的重點”;2008年,中國共產黨第十七屆三中全會明確提出,“基本醫療衛生服務關系廣大農民幸福健康,必須惠及全體農民”,要“支持衛生室建設,向農民提供安全價廉的基本醫療服務”;2011年7月,國務院辦公廳提出,要“實現村衛生室和鄉村醫生全覆蓋”,“原則上每個行政村設置1所村衛生室”,“原則上每千人應有1名鄉村醫生”。[1]足見黨和政府對農村衛生工作的重視是一如既往的。同時,衛生行政部門的文件也是紛沓而來。關乎農民健康福祉的村級衛生室和村醫隊伍建設得到了中央和地方的積極重視。但是,為什么如此重視卻效果不盡人意呢?通過本次觀察我們認為,對于村醫所處的兩種“團體格局”的變化和由此帶來的“差序格局”的變化必須納入研究的視野。
1.1 農村改革后,國家行政權力上移,導致了“差序格局”作用的增強
1978年,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勝利召開,把國家工作的重心轉移到經濟建設上來。置身于這樣的改革大環境中,無論是廣大的農村還是醫療衛生系統,都適應國家大的戰略轉變,在各自的領域內相繼出臺了改革措施。在農村,“廢除人民公社,確立以家庭聯產承包經營為基礎、統分結合的雙層經營體制”,并被視為“黨的農村政策的基石,必須毫不動搖地堅持”,開啟了農村經濟和政治體制改革的序幕。在經濟上實行家庭聯產承包制后接踵而來的村民自治,準確的說是“鄉政村治”(即鄉鎮一級設立基層政權依法對鄉村進行行政管理,鄉鎮以下的村實行村民自治)使得從1958年人民公社開始的一直滲入到村落的國家權力被上收至鄉鎮,鄉鎮政府成為國家權力在鄉村的最低層級。村民獲得了自主管理村落事務的權力,國家制定的《村民委員會組織法》讓村委會的選舉在政府不直接干預候選人提名的情況下進行差額選舉。農村改革政策的實施,在給廣大農民松綁的同時,這些“團體格局”的變化,特別是國家權力的上移,也使得衛生系統不得不面對農村新的政策環境,即農村改革導致了家庭經濟的回歸以及家族勢力的抬頭,在以血緣為基礎的村落中,大姓中的利益代表往往被家族甚至宗族群體推舉為村干部,從而使農村的“差序格局”得到進一步的鞏固。
1.2 農村衛生管理體制在村一級發生懸置
在農村醫療衛生系統中,隨著人民公社的解體,集體經濟逐漸瓦解,衛生室、合作醫療和村醫賴以生存的經濟基礎也隨之瓦解。1980年,國務院批準《衛生部關于允許個體開業行醫問題的請示報告》中規定,“在某些經濟貧困、群眾居住分散的地區,成立醫療機構有困難,也可考慮根據當地的需要,允許經考核合格的赤腳醫生個體經營,以解決群眾的看病吃藥問題”。由此,私立衛生室在農村地區開始出現,并且以較快的速度發展,原來集體性質的衛生室逐漸演變成自負盈虧的個體診所,村醫(當時被稱之為赤腳醫生)也就逐漸成為了個體醫生。1981年,國務院批轉《衛生部關于合理解決赤腳醫生補助問題的報告》中提出,“凡經考核合格、相當于中專水平的赤腳醫生,發給‘鄉村醫生’證書”,首次提出了用“鄉村醫生”代替“赤腳醫生”的問題。在1985年2月24日的全國衛生廳局長會議上,陳敏章部長在總結報告中正式提出,停止使用“赤腳醫生”這個名稱,“今后凡經過考核,已達到相當于醫士水平的,稱為鄉村醫生;達不到醫士水平的,都改稱為衛生員”。[2]從此,農村村一級的衛生室就由村醫個體經營,不少當年的“赤腳醫生”雖然通過了考試但由于難以維持生計而另擇他業。雖然這當中衛生行政部門也出臺了各種政策文件,但是農村醫療衛生網底的破損是不爭的事實。在2000年世界衛生組織對于191個國家醫療衛生公平性的評估中,我國位居188位,這樣的現狀引起了各級衛生行政部門的關注。2001年,國務院辦公廳轉發國務院體改辦《關于農村衛生改革的指導意見》,明確提出要改革農村衛生的管理體制,其中,核心內容就是對農村衛生工作實行全行業管理。2002年10月,中共中央、國務院頒發的《關于進一步加強農村衛生工作的決定》中明確提出,“衛生院的人員、業務、經費等劃歸縣級衛生行政部門按職責管理”,[1]北京市在2003年也發文強調對農村衛生管理體制進行改革,提出從“2003年起,遠郊區(縣)鄉鎮衛生院的人員、業務、經費等上劃到區(縣)衛生行政部門按職責管理”。于是,作為農村三級醫療衛生網絡樞紐的鄉/鎮衛生院從此脫離了鄉/鎮政府的領導,而上劃到縣級衛生行政部門。實際上,從中央及北京市的農村衛生管理體制改革的文件中不難看到,農村的衛生管理體制是止于鄉鎮衛生院的,村衛生室實際上處于衛生體制之外。
于是,出現了這樣的現象:無論是農村改革后行政權力上收至鄉鎮政府,還是農村衛生管理體制改革在“上劃”的同時止于鄉鎮衛生院,兩個“團體格局”的體制于村一級都處于“懸置”狀態。因此,雖然從“團體格局”的制度安排上說,國家和北京市乃至M縣都沒有忽略村落中村民的醫療衛生問題,制度的觸角一直延伸到村落,出臺了諸如對村衛生室實行一體化管理等一系列政策,但問題出在兩種“團體格局”在體制上的“懸置”與“差序格局”環境的進一步鞏固結合。這就容易導致衛生制度的各種安排在村落中出現不同程度的“末端失靈”。
2 “團體格局”中體制的懸置導致衛生管理“末端失靈”
2.1 體制懸置下“團體格局”設計與村衛生室歸屬之間的矛盾
在農村經歷了經濟、政治的變革和衛生系統的一系列改革之后,農村醫療衛生網底建設靠市場調節失敗出現破損,有的村衛生室關閉,一些村落成為村衛生室的空白村。我們在觀察時了解到,M縣332個行政村,有50個村沒有衛生室,即空白村占到15.11%。當然,國家在制度設計上并未遺忘農村衛生人力資源配置的核心要素之一的分布問題,但問題是怎么建,誰來建。于是就出現了制度設計方和舉辦方分離的問題。2002年12月,衛生部等部門聯合頒發了《關于農村衛生機構改革與管理的意見》,意見指出,村衛生室“可采取村民委員會辦、鄉(鎮)衛生院辦、鄉村聯辦、社會承辦或有執業資格的個人承辦等多種形式舉辦”。為此,北京市也在2003年頒發的《關于北京市鄉村醫療機構改革與管理的實施意見》中提出,“原則上村衛生室由村委會舉辦”。問題在于,村委會作為農民自治的權力機構,特別是在經歷了聯產承包這個農村經濟體制改革后,實際上是沒有能力舉辦村衛生室這一承擔基本醫療和公共衛生服務機構。這種衛生人力資源區域規劃制定方,即“團體格局”的衛生行政領域在要求另一“團體格局”的農村領域超出自身能力范圍去建設和完善村衛生室和村醫的配置時,矛盾就會不可避免的產生,事實也的確如此。據《2010年北京市衛生工作統計資料簡編》顯示,北京市2972所村衛生室中,有2594所為村辦,5所為衛生院設點,5所為聯合辦,343所為私人辦,25所為其他方式辦。在我們觀察的30個村中,除了3個空白村外,27個村衛生室沒有一個是真正由村委會舉辦的。在衛生室的產權、所有權、經營權等一系列歸屬問題未得到解決的情況下引發了一系列問題。比如,雖然北京市在2007年推出“1486”工程,對一部分村衛生室進行了標準化建設,但是也只是對房屋和設備進行了配置;而且觀察中我們了解到,M縣被納入“1486”工程的衛生室并不多,很多村醫甚至不知道“1486”為何物。另外,在訪談中我們也發現,村委會不僅無力舉辦村衛生室,而且還無法做村衛生室的法人,因為根據衛生部辦公廳的文件,“村衛生室的設置應當由能夠獨立承擔民事責任的單位或個人按照《醫療機構管理條例》和《醫療機構管理條例實施細則》有關規定申請,其法人代表根據國家有關法律法規承擔相應的法律責任”。[3]用村干部的話說,“村醫賠了賺了是個人的事,我們也不懂。不能賺錢是他們的,賠錢是村委會啊。”所以,M縣很多村衛生室營業執照上負責人填的是村醫,而“法人代表”一欄都是空的,即使有些衛生室“法人代表”一欄填村委會書記或主任,也沒有實際意義。一旦發生醫療事故,村醫將面臨傾家蕩產的風險,這也帶來很大的法律隱憂。
2.2 體制懸置下“團體格局”設計與村醫身份的矛盾
如前所述,村衛生室實際是由村醫個人或者家庭舉辦的是目前村衛生室的基本現狀。國家在衛生政策中明確提出,基本醫療衛生制度屬于公共物品的范疇,提供公共醫療衛生物品和服務,充分保障其公平性和公益性是政府公共管理職責的必然要求。也正是基于這樣的理念,“團體格局”即衛生行政部門給村衛生室性質做了規定,早在2001年,國務院體改辦在《關于農村衛生改革與發展指導意見》中就指出,“村衛生室為非營利性機構”。就此,北京市衛生局也提出“區縣衛生行政部門批準設置的村衛生室,一般定為非營利性醫療機構”,它是“為社會公眾利益服務而設立和運營的醫療機構,不以營利為目的”。[4]在本次觀察中我們看到村衛生室墻上掛的執照上都明確寫著“非營利機構”,而矛盾也就出現了,因為不僅村衛生室是個人辦的,處于國家醫療衛生體制外,而且村醫也是醫療衛生體制外的,讓村醫這個又當農民種地又從事醫療衛生工作,還不“營利”只為“社會公眾利益服務”,那這個人或家庭拿什么維持家庭的生活?這里不能不涉及村醫的身份問題。也可以說,“團體格局”的設計與村醫的身份產生了矛盾。第一,村級醫療衛生機構分為體制內和體制外。2007年,由北京市人民政府辦公廳轉發市衛生局等部門《關于建立健全鄉村醫生社會養老保險制度與基本待遇保障機制的意見》中提出分類管理思路,于是,在村一級的醫療衛生機構中,出現了置身衛生管理體制內的社區衛生服務站和體制外的村衛生室。社區衛生服務站是“隸屬鄉鎮衛生院,崗位人員由鄉鎮衛生院派出,實行統一管理”;而“村衛生室和健康工作室隸屬于行政村委會,崗位人員由村委會聘用,衛生院對其實行業務‘一體化’管理”。第二,體制外村醫分為政府購買服務和非政府購買服務。北京市衛生局提出對“鄉村醫生待遇實行分類管理、分項補助,在‘規劃設崗、優先聘用、統一標準’的基礎上,積極發揮鄉村醫生作用,規范鄉村醫生待遇”,也就是說,對“鄉村醫生承擔的村級公共衛生和村級常見病防治兩項職能,采取‘政府購買服務’的方式分別給予補助”。于是村衛生室又分為政府購買服務的衛生室和非政府購買服務的衛生室。所以,在我們觀察的27個村衛生室當中,有11個就是非政府購買服務的衛生室,沒有被政府購買服務的村醫不享受每個月800元的政府補貼(400元是賣零差率藥品的補貼,400元是承擔村公共衛生服務的補貼),同時,他所在的村衛生室既不實行零差率藥品的銷售也不承擔村里的公共衛生服務任務。
通過查閱文件可以看到,衛生行政部門將對村級醫療衛生機構的人員分成體制內和體制外,接著又將體制外分為政府購買和非政府購買服務兩類村醫。但在村級基本醫療、公共衛生服務的內容上卻一視同仁,賦予了相同的使命。用X鎮Z村村醫Z的話說,“村醫不是在編人員,卻做了在編人員的工作”。村醫體制外的處境和所要承擔的職責之間的矛盾,使村醫處在心理不平衡的狀態。在觀察中不難發現,一方面,村醫中技術好的不愿意其服務被政府購買,因為他們每年幾萬甚至幾十萬的收入大大高于被政府購買服務后按規定銷售零差率藥品、提供公共衛生服務而僅有的每年9800元收入和一點賣藥的收入;另一方面,村醫中技術不好又年老體衰的則希望被政府購買服務,因為他們認為,9800元雖然不多,但也比沒有強。并且,同樣在村級醫療衛生機構為村民服務,待遇卻不同,在社區衛生服務站工作,每天工作8小時,每年幾萬元的工資待遇;在村衛生室工作,一天24小時服務鄉里,風險自擔。兩種體制也造成了村醫心理的不平衡,村醫這樣尷尬的身份處境使他們對農村醫療衛生事業缺少歸屬感和使命感。這些因素加之各種現實的原因,勢必會對村醫對于是否被購買服務的選擇以及其日常的執業行為和服務提供情況造成影響。
3 “團體格局”的政策安排在“差序格局”落地中出現“水土不服”
任何“團體格局”的制度安排必然要落入或者說要被“嵌”入“差序格局”中,因為所有“團體格局”的制度安排、政策要求都要在村落的“差序格局”場景中進行,而無論村醫、村民還是村干部,在很大程度上不是依“團體格局”的規則,而是依“差序格局”的習俗來參與“團體格局”的生活。“團體格局”中的制度安排和政策要求,必然要在村醫、村民和村干部的眼睛里和實踐中過濾成與所處的血緣、姻緣甚至地緣,即“差序格局”能接納的東西。村落是自然形成的以血緣為基礎的社區,它在歷史的流淌中脈絡清晰地發展著,與城市社區所具有的功能社區不同。因此,在設計農村衛生人力資源配置的方案時,如果采用像城市社區一樣的制度安排,無論在制度出臺前經過多少次“頭腦風暴”和專家論證,“團體格局”與“差序格局”的水土不服都在所難免。而目前存在的兩種格局的不兼容、不和諧正是影響村級醫療衛生人力資源配置的一個重要因素。
3.1 制度“外搬”——按人口配置方案與村落實際的矛盾
衛生行政部門多次提出,要“本著方便群眾和優化衛生資源配置的原則,合理制定鄉村醫生配置規劃”。[5]2007年,國務院批轉衛生事業發展“十一五”規劃綱要的通知提出,“到2010年采取多種形式支持每個行政村設立1個衛生室”。2007年,衛生部辦公廳和國家發展改革委辦公廳聯合發文指出,“一個行政村只建設一所村衛生室,鄉鎮衛生院所在村原則上不支持建設衛生室”。[6]2011年7月,國務院辦公廳《關于進一步加強鄉村醫生隊伍建設的指導意見》中又提兩個原則,“原則上每個行政村設置1所村衛生室”,“原則上每千人應有1名鄉村醫生”。可以說,每個行政村建設一個村衛生室,是國家制度安排的一貫主張,也是考慮到村落在自然形成過程中規模大小不一,不能照搬城市功能社區簡單的按千人口來配置衛生人力資源。M縣衛生局《關于2010年鄉村醫生聘任的實施意見》中提出了關于鄉村醫生配置的標準,規定“根據服務范圍和服務人口,原則上1000人口以下的行政村配置鄉村醫生1名;1001~2000人的行政村配置鄉村醫生2名;2001~3000人的行政村配置鄉村醫生3名;3001~4000人的行政村配置鄉村醫生4人;4000人以上的行政村配置鄉村醫生5人”,但這個村級的衛生人力資源配置方案在實踐中也出現了問題。由于村衛生室由個人舉辦,因此,一個村有沒有村衛生室和村醫不是取決于政府的文件安排,而是取決于村醫基于有無營利和營利多少而作出的是否做村醫和行醫地點的選擇,這樣的結果就是小的行政村,即200人以下的村沒有村衛生室和村醫,出現了“空白村”。村中沒有衛生技術人員使得當地村民就醫非常不便,村民若患病則需要途經幾公里的山路到鄰村的衛生室或距離更遠的鄉鎮衛生院就醫,而年齡較大、行動不便的村民則只能請鄰村的村醫到家里出診。一旦村民突發急癥,也可能因無法得到及時有效的應急處理而錯失最佳搶救時機。此外,由于出村醫療的花費較多,很多村民便選擇根據以往的治療經驗自我醫療。觀察中發現,盲目用藥和服用過期藥物的現象比較普遍。如T鎮E村村書記F反映,“村民家里基本都有一抽屜的常用藥,有些是自己買來以備不時之需的,有些是之前生病開了藥沒吃完的。不過這些藥放的時間一長也就過期了”。沒有任何醫學專業知識而僅僅憑借自己以往的經驗進行自我醫療,這無疑為村民的健康埋下了巨大的隱患。村內衛生技術人員的缺乏不同程度地影響了基本醫療和公共衛生的公平性和可及性。
另外,面對村級衛生人力資源匱乏的局面,政府還出臺了另一種解決的辦法,北京市的特點是大城市小農村,因此,其具體做法是在城市大力發展社區衛生服務的背景下,北京市衛生行政部門在農村也積極推行和開展社區衛生服務。于是,2007年以來,農村鄉鎮衛生院又掛起了一個新的牌子:社區衛生服務中心,兩個牌子一套人馬,下面分別是村衛生室和社區衛生服務站。可以說,從政府的支持力度來說,無疑是向體制內的社區衛生服務站傾斜的。于是,在農村參照社區衛生服務站的布局安排,按照平原和山區的村民分別出行二、三十分鐘以內可及的標準建立社區衛生服務站。但這樣的布局安排在人員安排和布局上出現了與村落現況不相適宜的情況,影響了村民健康需求的滿足。因為在幾個村之間建立社區衛生服務站,在城市交通極為便利的情況下沒有問題,但在郊區,特別是山區就很不便利。另外,于幾個村之間建立社區衛生服務站使得鄉鎮衛生院在人力資源本不充裕的狀況下更不堪重負。在觀察中我們了解到,M縣曾響應北京市的要求,在村中建立社區衛生服務站,最多時全縣建有98個社區衛生服務站,但經過幾年運行后,大部分社區衛生服務站都撤回到鄉鎮衛生院(社區衛生服務中心)了,目前只有20個社區衛生服務站。因為按照北京市相關文件的要求,[7]農村社區衛生服務機構每2000~3000名服務人口配備1名全科醫生和至少1名社區護士;每2000名服務人口配備1名預防、保健人員;還要配備藥劑師、財務人員等等。在服務時間上要求社區衛生服務站每天實行9~21點即每天12小時服務,每周7天提供服務。可以想象,要達到這樣的要求,沒有大量衛生人力資源投入是不行的。因為根據勞動法,每人每天工作8個小時,每周工作5天。如果一個社區衛生服務站要維持正常運營,沒有6~7人是達不到衛生行政部門要求的。M縣當初按要求積極建立社區衛生服務站時,尚未完全按照該標準配備人員,便已經使衛生院陷入了人力資源匱乏和運轉困難的局面了。基于這種現實情況,M縣在村一級重新定位,重點發展衛生室。
3.2 制度“外搬”——高門檻準入方案與村落實際的矛盾
2002年10月19日,中共中央、國務院《關于進一步加強農村衛生工作的決定》提出,“到2010年,全國大多數鄉村醫生要具備執業助理醫師及以上執業資格”,[1]2004年,北京市衛生局關于貫徹實施《鄉村醫生管理條例》的意見(京衛基字[2004]3號)指出,“原則上今后本市不再核發《鄉村醫生證書》,《鄉村醫生管理條例》公布之日起進入村醫療衛生機構從事預防、保健和醫療服務的人員應具備執業醫師資格或者執業助理醫師資格。本市不再另行規定執業注冊資格的其他標準”。也就是說,從2004年以后,北京市農村村醫的門檻提高了,鄉村醫生的考試不再進行了,以后要做村醫,就要和城市中的醫生一樣去考執業醫師和執業助理醫師;另外,北京市(京發[2008]5號文件,即中共北京市委、北京市人民政府《關于推進北京市農村基本醫療衛生制度建設工作的若干意見》)還指出,“力爭在3至5年內實現村村有衛生專業大學畢業生的目標”。目前準入門檻的提高已經過去了8年,學歷提高的目標已經過去了4年,但現狀不容樂觀。課題組在觀察中發現,27名村醫只有2人考取了執業助理醫師資格,其余都還是鄉村醫生執業證書。也就是說,門檻提高后,也就鮮有村醫進入村級醫療衛生機構工作;至于“村村有衛生專業大學畢業生”的目標,只有5人達到,占18.5%,還基本是民辦學校畢業國家不承認學歷或者參加繼續教育后取得的。也可以說,國家或者北京市提出這樣的目標放在城市推行起來并不難,可是在農村這樣的門檻就不能說不高。在本次觀察中通過訪談,27名村醫中有18人認為目前村醫準入標準非常高和比較高,占66.7%。像G鎮G村的村醫Z雖然取得了執業助理醫師資格,但也認為,“執業助理醫師考試的內容和村醫的實際工作內容并不相符,因為在農村看病不像大醫院分的特別細,它主要是解決一些小傷小病。另外,村醫的學歷多是專科生,不是正規醫科院校5年、7年畢業的學生,他們很難通過執業助理醫師考試。所以應該降低村醫準入標準”。可以說,一個在村落中服務的村醫,他日常接觸到的疾病、診斷、治療與國家執業醫師考試的內容距離比較遠,有的內容他從來沒有遇到或者是不可能遇到的,因此,高門檻的結果是村醫在年老體衰同時還出現后繼乏人。
另外,村落是有著明確地域邊界的以血緣為基礎的社區,在歷史的流延中村民之間形成血緣、姻緣和地緣交織的藤蔓網,外面的人要融入村落即“差序格局”之中并被村民信任不是件容易的事情。在觀察的27個村醫中,只有一個村醫是從外地來到M縣T鎮工作,因學歷不被國家承認才做村醫的,而他在“差序格局”即村落中的服務酸甜苦辣的味道只有他自己品味的出來,所以他表示村醫還是本鄉本土的好。在訪談中,在問及村醫將來的來源時,27名村醫有15人表示從本村派出去學習回來服務村落比較好。因為本村人就住在村里,與村民彼此熟悉,能夠方便就近的為村民提供服務,雖然政府補貼不多,但是沒人看病時,還可以干點其他的事情。當然,目前對村醫的補貼也無法讓一個外地人在村衛生室工作,用村醫的話說,“外地人要是指著當村醫每月800元補助,很難維持生計,根本沒人愿意來這里干”。再有,外地來的大學畢業生在村衛生室服務,以后住房、成家、子女入學等都會有很多問題;還有,目前連鄉鎮衛生院作為國家醫療衛生體制內的單位,享受國家各種政策的傾斜尚且都很難吸引年輕的大學畢業生,讓一個能夠順利通過國家執業醫師考試,擁有執業醫師或執業助理醫師的年輕人拿著每個月800元的補貼踏踏實實服務村落更為困難。
也可以說,各級衛生行政部門制定政策的初衷是好的,但是高門檻的準入與村落中的應該和能夠準入的村醫實際存在較大距離,造成了目前村醫青黃不接的現象。
[1]中共中央國務院.中共中央國務院關于進一步加強農村衛生工作的決定[Z].中發〔2002〕13號.
[2]陳敏章.陳敏章同志在全國衛生廳局長會議上的總結講話[J].中國醫院管理,1985,(2):16-20.
[3]衛生部辦公廳.衛生部辦公廳關于推進鄉村衛生服務一體化管理的意見[Z].衛辦農衛發〔2010〕48號.
[4]北京市衛生局.北京市醫療機構分類管理實施細則[Z].京衛醫字〔2001〕49號.
[5]衛生部辦公廳.衛生部辦公廳關于做好鄉村醫生執業證書有效期滿再注冊有關工作的通知[Z].衛辦農衛發〔2009〕149號.
[6]衛生部辦公廳 國家發展改革委辦公廳.關于印發《中央預算內專項資金(國債)村衛生室建設指導意見》的通知[Z].衛辦規財發〔2007〕138號.
[7]北京市衛生局,北京市人事局,北京市財政局,等.關于進一步加強全科醫學人才培養的實施意見[Z].京衛科教字〔2006〕13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