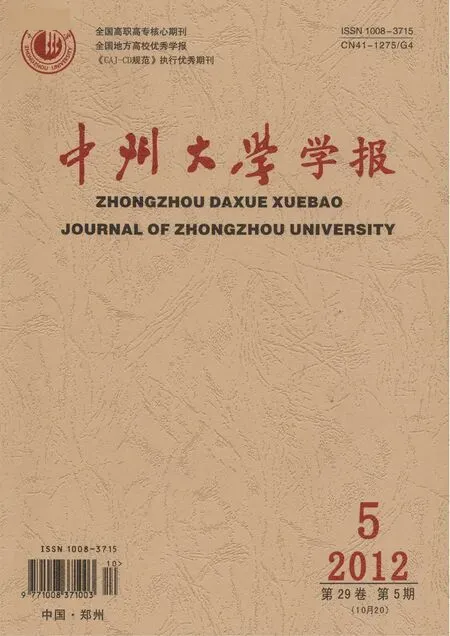文本的陷阱與被建構的歷史
李 瑞
(中國傳媒大學傳播研究院,北京100024)
一、文本的局限:消逝在潛語言層的歷史
《莊子》記載有輪扁和齊桓公辯論的故事。輪扁是個制造車輪的工匠,但這個工藝的訣竅只有他自己心里明白,只有在做的時候才能把握,卻無法用語言表達。他試圖把這個訣竅傳給兒子,卻說不清楚,兒子也聽不明白。“是以行年七十而老斫輪”,不得不親自動手。輪扁推而論之“古之人與其不可傳也死矣”,不贊成齊桓公讀古人的治國之法,他認為古代的圣人死掉了,那么這些關于治國之道的一切不可言傳的訣竅也一起死掉了,而能夠用語言和文字表達出來的東西從來都不是最精妙、最智慧的東西。
中國自古就有辯者不言、述而不作之說。“道可道,非常道;名可名,非常名”與禪宗所謂的“不可說”有著異曲同工之妙,都認為一旦說出來就“破”了,就“低”了。古人常謂“名醫不談病,名將不談兵”,不僅是因為病情與軍情同樣瞬息萬變,更因個人體質或戰場形勢的不同而無法套用。語言不能盡意,文字不能盡言,這樣的詭辯近乎有陷入“不可知論”的嫌疑了。“世之所貴道者,書也。書不過語,語有貴也。語之所貴者,意也,意有所隨。意之所隨者,不可以言傳也,而世因貴言傳書。世雖貴之,我猶不足貴也,為其貴非其貴也。故視而可見者,形與色也;聽而可聞者,名與聲也。悲夫!世人以形色名聲為足以得彼之情。夫形色名聲,果不足以得彼之情,則知者不言,言者不知,而世豈識之哉!”[1]清代史學家章學誠在論述上古三代與后世歷史知識傳播方式的不同時,指出:“三代盛時,各守人官物曲之世氏,是以相傳以口耳,而孔孟以前,未嘗得見其書也。”“后世竹帛之功,勝于口耳;而古人聲音之傳,勝于文字;則古今時異,而理勢亦殊也。”[2]
世界新聞記者協會在伊拉克戰爭不到一年的時候,將“文理不通獎”授給了拉姆斯菲爾德,因為他說了這樣一段話:We don’t know what we know or we don’t know,though we think we know,but we are not sure we know or we don’t know.翻譯過來尤為拗口:對于伊拉克的情報,我們并不知道哪些是真實的情報,哪些是不真實的情報,即使我們認為是真實的,它也可能是真實的,也可能是不真實的。文本與文本之間很難證偽,在面對繁蕪叢雜的歷史文本時,為了避免陷入不可知論的詭辯之中,應當在盡可能多地占有第一手歷史資料的前提下,對歷史文本進行互文性的解讀和分析,盡可能地對歷史原貌進行無限接近的忠實解讀,藉此讀出掩藏在歷史文本“字里行間”的真相。
歷史文本的局限性不僅表現在其不能盡意之處,而且還存在著大量消逝在潛語言層的史實“流失”現象。弗洛伊德一度將“潛意識”比喻為隱藏在表層意識背后的體積龐大的冰山。反觀歷史不難發現,那些被保存下來的歷史文本相較于事件本身的完整真相來說無異于冰山一角。早在1948年美國人就開始了“口述歷史”的嘗試,國內知名主持人崔永元也正在從實踐探索的角度開展著“口述歷史”的記錄與傳播工作。口述歷史固然可以對文本歷史起到一定的補充作用。尤其是那些經過親歷者選擇性記憶和突出的事件細節,這種立體化的親歷性和帶有立場的偏頗性使得歷史事件變成了具有特定意義的歷史故事。但同樣也無法規避敘述者的主觀性、立場性和個人偏好的左右。個人的歷史記憶總是片面的和微觀的歷史,同樣也是個性化的歷史。歷史學家在還原史實真相的時候要仔細甄別歷史資料,去偽存真,盡量還原歷史的本來面貌。對于同一樁史實,要通過至少三個以上的親歷者進行考察,而這些人所講述的交集部分從概率統計的角度來講也會離歷史的原貌更接近一些。往者已逝不可追,生者猶可貴。筆者認為,在人類的歷史記錄方式已悄然變遷的新媒體時代,有必要對近現代歷史人物的“口述歷史”資料進行“搶救性發掘”。
二、文本的“羅生門”:被粉飾和篡改的歷史
隨著媒介的發展與變遷,作為歷史記錄功能的文本樣態也有著多種表現形式:從上古的口耳相傳到如今足以調動起人類視聽感官通感的歷史題材紀錄片,從史書文獻到近代的新聞紙,從民間力量主導下的野史雜記到政治話語權主導的教科書文本,碎片化的文本呈現出萬花筒式的斑駁迷離,絕對真實已如巴別塔一般難以企及。文本以或粉飾或魅惑的面孔向我們打開一道道通向事件原貌的“羅生門”,探索者卻往往因為缺乏高屋建瓴的宏觀視角而最終走失在文本曲幽的迷宮里。而對于那些僥幸進入“相對真實”之假面舞會中的人,又難以避免地陷入更加龐大的歷史謎團之中。
春秋筆法作為中國歷史書寫所獨創的“為尊者諱,為親者諱,為賢者諱”的敘述傳統,是一種文人們在政治高壓下直陳時弊的慣用手法。春秋筆法來源于孔子編撰的《春秋》,其精妙之處在于運用曲筆的手法或隱諱或粉飾一些歷史事實,以達成“微而顯,志而晦,婉而成章,盡而不污”的傳播效果。春秋筆法在記述歷史時暗含褒貶,記錄者在行文中雖然不直接闡述對人物和事件的看法和態度,但是卻通過細節描寫,影射和修辭手法,材料和詞匯的篩選,委婉而巧妙地表達作者的主觀看法,以隱蔽曲折的文本形式發出公開敘事的聲音。《通志·氏族略第三》中記載:“著書之家,不得有偏徇而私生好惡,所當平心直道,于我何厚,于人何薄哉。”[3]然而,歷史的絕對真相猶如深淵,若想窮盡何其難也。
“一切真歷史都是當代史”,這是意大利學者克羅齊1917年提出的一個著名命題。1947年1月,朱光潛先生在《克羅齊的歷史學》論文中探究克羅齊的史學思想時,曾對這一命題作了如下闡發:“沒有一個過去史真正是歷史,如果它不引起現實底思索,打動現實底興趣,和現實底心靈生活打成一片。過去史在我的現時思想活動中才能復蘇,才獲得它的歷史性。所以一切歷史都必是現時史……著重歷史的現時性,其實就是著重歷史與生活的聯貫。”[4]反觀當下,歷史教科書的編纂主旨就是這一說法的具體體現。不同民族對于同一歷史坐標系中的世界史橫切面會有截然不同的敘述視角和立場解讀,這種尷尬的“羅生門”現象也恰是由歷史記錄者和解讀者所共同參與構建的。
在索緒爾的符號理論中早就有“再現世界”和“真實世界”的二元劃分。在這種二元關系下,索緒爾將符號和參照物加以區分,同時也相應指出,前者次于后者,受到后者的控制。符號世界只能指稱既有的真實,媒體只能反映已經存在的事物。符號存在于它所映照的真實之下,符號世界駕馭于真實之上,就像一種附著于真實之上的稀薄物質,這種物質好像從反映的層面衍生出來。在西方有這樣一種觀點,認為媒體是“社會真實的定義者”,也就是說,對于新聞事件的真相,媒體是怎樣說的,在社會輿論中起著至關重要的作用。哪些事件被報道了,是如何報道的,與我們感知世界的方式有直接的關系。媒體在報道某個事件時,事先有一個解釋事件的架構,這個架構基本與受眾心目中的架構契合。然而,受眾心目中的架構是哪里來的,是媒體長期培養的。媒體的解釋架構久而久之型塑了我們的意識,因而,媒體與社會真實并沒有分離開,也不是被動反映世界,媒體就是社會真實的一部分,媒體通過與社會各種話語的關聯,型塑我們的感知習慣,也就是習慣媒體真實,同時媒體的報道影響了這個社會真實的發展方向。新聞報道過程中意識形態的作用也逐漸成為人們關注的焦點。意識形態對新聞報道的作用與影響,首先就是將原初事實“符號化”,在這一“符號化”的過程中,意識形態是一種架構,這一架構在人們不注意的情況下,具有自然化的效果。而這種自然化的效果自然是對某些政治權力集團有利的。
革命既是“發生”的,更是被“發動”的。而要“發動”廣大底層民眾起來革命,需要建構一套具有說服力的革命話語。這種對于革命義舉的正當性、合理化論證就是通過一定意識形態主導下的媒介架構才得以實現的。舉例來講,如果抽掉或無視具體有血肉的歷史內容和時代背景,抹去戰爭帶來的巨大災難,而僅僅作為一種“純文本”闡釋,即從理論到理論,從概念到概念,那么我們今日甚至可以拿時下流行的“后殖民”、“反對跨國資本”等理論來論證和詮釋當年日本進行“大東亞圣戰”的合理性和正義性。很顯然,這樣的文本推理是相當危險的。在歷史題材紀錄片的拍攝中,也同樣存在著類似的歷史誤讀,陸川導演的《南京!南京!》之所以遭到國內史學家的強烈質疑和詬病,一方面是因為該片是根據一位日本士兵的日記改編拍攝的,故而文本形態的轉換中難免會偏向于日方的立場,另一方面在于導演這種全息化多角度的視角在進行歷史文本的創新性敘事嘗試時,過于追求意識形態的模糊化和全球化,而這樣的缺失和去立場化,正是歷史文本的一大致命傷。
黑格爾指出,語言具有一種顛覆真理的本性。因為每一個言說者都必須借助“概念”才可能告訴他人所說的是什么,而概念總是把言說者本人的真實感受抽象化、概括化,才可以成為名詞性的“概念”,才可以藉此進行共時性的人際溝通和歷時性的代際傳遞。所以,當我們為了要說我們各自眼中的世界和感受,我們不得不為我們所感受的世界命名。然而文字未必能準確地表達語言者的思想和情感,語言者的思想和情感又未必能準確地表述和描繪這個世界。這樣的雙重困境使得最終由語言織成的文本更加面臨著真實性的拷問。
三、歷史文本的互文性解讀
20世紀60年代,互文性理論建立了新的文本關聯,打破了文本封閉存在的傳統觀念,賦予文本以開放和互滲性質。傳統文本所具有的社會學的和歷史主義的性質,在當下語境下被更改了——文本不是一種封閉的存在,而是處于對話和不斷建構的狀態。同樣,歷史編撰本身也是具有互文性的。被編撰的歷史總是種種歷史碎片的堆砌。每一個歷史時段都不是孤立地發生的,而總是以前歷史時段的一種變形式移置。尤其是我們的當下歷史,總是交替閃現出以往種種歷史殘片。不僅歷史文本之間具備互文性解讀的可能,而且歷史本身也具有互文性。
美國史學家海登·懷特曾總結了歷史事件和歷史事實的區別:前者是實際發生過的孤立事件,后者則是經過歷史學家篩選,并用一種虛構的制式或概念裝置串聯起來的敘事對象,即在編織歷史材料的過程中使用修辭手段。懷特對歷史事件和歷史事實的區分消解了傳統史學關于事實和虛構的二元對立,這是因為所謂的“事實”在本質上就是一種虛構。在不可勝數的事實中篩選出一部分與作者的概念裝置或敘事制式相符的事實,這個篩選事實的過程本身受制于事先存在的寫作目的和意識形態。經過了作者如此過濾之后,這些事實已經與它們原來的樣子相去甚遠。傳統史學認為,歷史學家的職責就是發現歷史真相、描述新的史實并且對它們作出解釋。
在互文性理論觀照下的“歷史真相”可以有不同的理解。首先,歷史事件在發生之后就不能被再次經歷,于是了解過去發生的事實真相只能通過文檔資料或回憶進行,這就牽涉到如何理解記憶以及由記憶編織的故事或文本的問題。歷史事件一經發生,就無法按原樣復原,歷史研究的最理想結果無非是接近真相而已。以德國史學家蘭克為代表的實證主義史學所致力其中的使命就是發現這樣的真相,這種史學觀把歷史研究的對象當成一座倒塌的房子,通過一磚一瓦的整理和修復,最終把房子按照其原來的樣子復建出來。其次,對于大部分歷史學家而言,發現史實只是治史的第一步工作——即編纂史書的素材搜集工作,要完成一部史書的撰寫還須找到把分散的一系列史實以某種方式連接起來的線索,因為對他們而言歷史并非孤立發生的事件,而是一個有著背后思想和目的的滲透過程。[5]
對歷史的互文性解讀乃是一種較為通透的史學觀,在掌握盡可能忠實的歷史文本后,因循以史鑒今,以此文本鑒彼文本的互文性解讀方式,撥開文本交織魅惑的帷幕,力圖無限接近歷史的真相和本質規律,或許才是一種明智的讀史方式。
[1]王先謙.莊子集解[M].北京:中華書局,2006.
[2]章學誠.文史通義校注·詩教下[M].北京:中華書局,1985:78.
[3]鄭樵.通志略[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0.
[4]于沛.如何看待“一切真歷史都是當代史”[N].光明日報,2006-03-27.
[5]林慶新.歷史敘事與修辭:論海登·懷特的話語轉義學[J].國外文學,2003(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