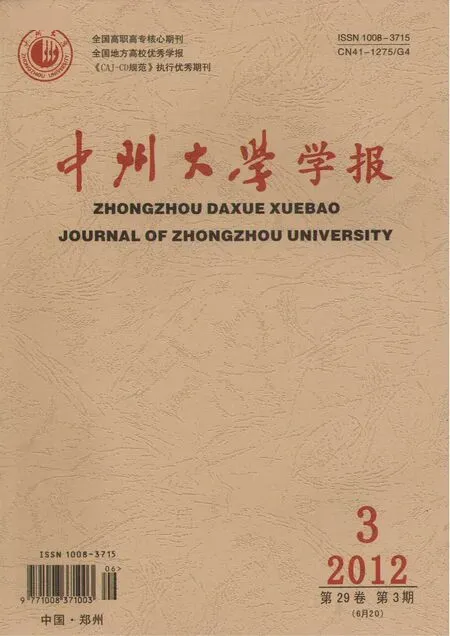素心清謠:清貧自守與消費社會
——讀陶淵明札記
魯樞元
(蘇州大學生態批評研究中心,蘇州215021)
陶淵明的一生從沒有大富大貴過,早年為了家人的生計,“投耒去學仕”,曾經到官府謀過幾次差事,由于受不了官場規矩的約束,就又毅然回家種地去了。
莊子曰:“鷦鷯巢于深林,不過一枝;鼴鼠飲河,不過滿腹。”(《莊子·逍遙游》)返鄉歸田后的陶淵明,始終恪守道家信條,只愿過一種自食其力、且有余閑、溫飽無虞、寧靜平和的儉樸日子,“弊廬何必廣,取足蔽床席”,“耕織稱其用,過此奚所須”,“園蔬有余滋,舊谷猶儲今。營己良有極,過足非所欽。”盡管如此,在遇到天災人禍時,基本的溫飽仍然難以保障,一家人往往陷于饑寒交迫之中,“環堵蕭然,不蔽風日。短褐穿結,簞瓢屢空。”“夏日常抱饑,寒夜無被眠”,“弊襟不掩肘,藜羹常乏斟”,“傾壺絕余瀝,窺灶不見煙”,“弱年逢家乏,老至更長饑。菽麥實所羨,孰敢慕甘肥。惄如亞九飯,當暑厭寒衣。歲月將欲暮,如何辛苦悲。”有時甚至不得不出門乞討,“饑來驅我去,不知竟何之。行行至斯里,叩門拙言辭”,求親告友的尷尬浮于紙上。以今天的生活標準看,陶淵明晚年這種忍饑挨餓、朝不保夕的日子已遠在“貧困線”之下了。
盡管如此,他仍不改初衷,“寧固窮以濟意,不委曲而累己。既軒冕之非榮,豈缊袍之為恥?誠謬會以取拙,且欣然而歸止。擁孤襟以畢歲,謝良價于朝市。”對于《論語》中頌揚的“固窮”精神,陶淵明始終念茲在茲,“斯濫豈彼志,固窮夙所愿”,“竟抱固窮節,饑寒飽所更”,“誰云固窮難,邈哉此前修”,“不賴固窮節,百世當誰傳”。陶淵明身罹貧苦困厄,仍能心安理得,并通過親近自然,通過與鄉曲鄰里的融洽相處,甚至通過身體力行的隴畝勞作,在物質生活貧困的條件下營造出一種充滿詩意的高品位生活。從陶淵明詩文集中我們可以發現,生活盡管貧苦,卻不乏優美清雅的謳歌,“今日天氣佳,清吹與鳴彈”,“清歌散新聲,綠酒開芳顏”,“日暮天無云,春風扇微和。佳人美清夜,達曙酣且歌。”“清謠結心曲,人乖運見疏。擁懷累代下,言盡意不舒。”“榮叟老帶索,欣然方彈琴。原生納決屨,清歌暢商音。”詩中講述的榮叟與原生,即春秋時代的榮啟期、原子思,都是亂世中的隱居之士,是陶淵明引為知音的“素心人”。在他們看來,貧苦并非病患,只不過是“無財”而已;真正的病患在于“學道而不行”。“古之得道者,窮亦樂,通亦樂。所樂非窮通也,道德于此,則窮通為寒暑風雨之序矣。”(《莊子·讓王》)對于這些得道的素心人來說,苦日子是完全可以唱著過的,這就叫做“安貧樂道”。
“先師有遺訓,憂道不憂貧。瞻望邈難逮,轉欲志長勤。”這里援引的是孔夫子《論語·衛靈公》中的話。孔子曰:“君子謀道不謀食。耕也,餒在其中矣;學也,祿在其中矣。君子憂道不憂貧。”在孔子看來,道與祿本來是可以雙得的,但不能以祿害道,衛道第一,為了守道不惜擇貧。在“憂道不憂貧”這一點上,道家與儒家是交叉匯流的。但是,孔子之道與老莊之道畢竟存有差異。孔子傾心于“王道”,不無功利之心,總期待著當政者的賞識與錄用;老莊寄情于“天道”,旨在“弗有”、“弗恃”、“弗居”,一切隨順自然。故孔子一生周游列國,不得不與權貴豪門苦苦周旋;莊子則終生廝守園林,種漆樹,打草鞋,清凈度日。晚年的老子甚至連圖書館的館長也不做了,獨自騎著頭青牛,消失在茫茫天地間。陶淵明的《詠貧士十首》之三中就曾批評做了衛國之相的子貢:“賜也徒能辯,乃不見吾心。”他的心思更多地寄予黔婁、壤父、長沮、桀溺、荷蓧丈人等隱逸者的身上。
儒家能夠做到的,只是窮困之際“不憂貧”,不以困厄失去操守;道家卻主張只有主動放棄、不持不有、散放恬淡、甘守貧窮才能得道。“貧”與“窮”反而成了“得道”的前提。“無不忘也,無不有也,澹然無極而眾美從之。此天地之道,圣人之德也。”“夫恬淡寂漠虛無無為,此天地之本而道德之質也。”(《莊子·刻意》)在莊子看來,“平為福,有余為害者,物莫不然,而財其甚者也。”(《莊子·盜跖》)富貴之于人反而害多于利,富人更與天道無緣。道家的“貧”,是放棄,是舍得,是盡量減少對于外物的“占有”;道家的“清”,是胸襟的坦蕩真率,是懷抱的澄明潔凈。陶淵明詩曰:“不覺知有我,安知物為貴”,“若不委窮達,素抱深可惜”,其中的“深惜素抱”與“不以物貴”,即可看做“清貧”的釋義。
在古漢語詞典中,“清貧”差不多總是一個褒義詞,不僅用于形容物質生活的匱乏,更經常彰顯文人學士的品格與操守。“清”者,潔凈、明晰、單純、虛靜也,固然為褒義;“貧”,乃空缺、匱乏、虧欠、稀少、不足,在老莊哲學的原典中也絕不是貶義。“保此道者不欲盈,夫唯不盈,故能蔽而新成”,“大成若缺,大盈若沖”,“無欲而民自樸”。老莊哲學中尚虛、尚無、尚靜、尚儉、尚樸、忌得、忌盈、忌奢的精神無不與“清貧”二字通。陶淵明清貧自守的節操是他自覺的選擇,是老莊哲學中少私寡欲、見素抱樸精神的體現。對于“清貧”的自守,也是對于“素樸”之道的堅守。素者,不染之絲也;樸者,不雕之木也,皆為“自然而然”者。道法自然,因此“見素抱樸”即得“道”。不染不雕即物之本色與初心,素樸于是又具備了原初、本真之義。老子曰:“常德不離,復歸于嬰兒”,“常德乃足,復歸于樸”,返樸歸真便成了道家修成正果的至高境界。從這一意義上來說,陶淵明的“返鄉歸田”就是“返樸歸真”。而清貧于此不再是困頓難捱,反而成為回歸本真、回歸自然的不可缺少的“元素”。本書開頭講到的金岳霖先生推重的“素樸人生觀”,講的也是這種回歸型的、單純的、尚未完全分化的生存觀念,幾近于“孩子氣”,這與老子講的“復歸于嬰兒”,也是一致的。
人類社會卻并沒有遵照老子等人的意圖退回到那個“嬰兒”狀態,而是一天天發展、強大,成為一個無所不能、無所不包的巨人。遺憾的是,這個強大的巨人距離自己扎根其中的本源、本性卻越來越遠了。陶淵明活著的時候,那個社會就已經“真風告逝,大偽斯興”,他所指的不外乎是“閭閻懈廉退之節,市朝驅易進之心”,即社會上已松懈了廉潔謙讓的品節,官場上勃起投機鉆營的心態。看看當下的現實,如今官場、市場中人們的貪欲及污行不知比那時又“壯大”了幾多倍。
現代人無不視貧困為洪水猛獸,避之唯恐不遠,于是競相爭富。富者富可敵國,窮則窮到無法活命,于是社會各階層、世界各國家之間的矛盾沖突日益激烈。世事紛爭,清靜、清潔、清平的日子不再有;人欲橫流,貪污腐惡隨社會富裕的程度日益攀升。如果說陶淵明時代就已經“真風告逝”,如今已“逝”得更遠。內心的自然與真誠還有多少姑且不論,人們對自己的身體甚至也已完全失去誠意。近年來,各種媒體極力宣揚的“人造美女”成了現代社會一道炫目的風景,據稱改造這樣一個美女要實施高密集的外科手術:隆鼻、隆胸、割眼、吸脂、截皮、拉皮、銼骨、延骨,其酷烈程度無異于舊時刑罰中頂級的“凌遲”。盡管“千刀萬剮”,無數的青年男女仍趨之若鶩。當年,莊子對于人們給馬上了籠頭、給牛穿了鼻繩就已經大為傷感,以為破壞了牛馬的本性與天真,如果莊子再世,遇上這樣一位暴殄天物的“人造美女”,不知將作何感想!
由此觀之,陶淵明的清貧操守無疑是更接近道家精神的。“清”,則有益于精神生態的陶冶,“貧”則有助于自然生態的養護。如果判定1600年前的中國古代詩人陶淵明同時也是一位“生態文學家”的楷模,并不為過。
王先霈教授曾著文指出:“在中國古代卓越的詩人中間,陶淵明的生態思想和他的行為實踐,最富有啟迪意義。”“他看重的是個人精神的自由,是不以心為形役,不讓精神需求服從于物質需求,看重的是人在與自然的和諧相處中得到寧靜、恬適。”就其人生價值的取向而言,“他尊奉的‘道’并不是孔孟之道,而是自然之道……孔子所憂的‘道’離他太遠,他是‘樂道忘其貧’,他所欣樂的是田野上春景體現的自然之道。”文中還指出:“把他的思想歸結為知足常樂不很準確,甚至很不準確。這不是量‘足’或‘過’的問題,而是人要不要有精神追求的問題,是生活哲學的方向問題,是個人精神境界以至于社會精神生態的高下、雅俗、清濁的問題。”王教授還接過美國當代生態批評家艾倫·杜寧的話說:陶淵明的生態思想應是人類文化中彌足珍貴的“古老教誨”。[1]
令人痛心的是,這一“古老的教誨”,在詩人陶淵明自己的國度被徹底遺棄了,近年來更是以最快的速度被遺忘的。
近年來中國社會最大的變化之一,表現在消費觀念上,最引人矚目的是“奢侈消費”,說出來幾乎就是一個難以置信的天方夜譚。
在全球深深陷入經濟衰退之際,據世界奢侈品協會的最新報告稱,中國內地去年的奢侈品市場消費總額已經達到107億美元,占全球份額的1/4,已經超過美國,預計中國將在2012年超過日本,成為全球第一大奢侈品消費國。消費的內容從名包、名表、名車、名牌服裝、古巴雪茄、瑞士煙斗,到游艇、別墅、海灣度假酒店、高爾夫俱樂部、貴族學校、紳士名媛培訓班等。奢侈消費的趨勢是消費者的年齡越來越年輕,提升速度越來越快,消費規模正由一線城市波及二線、三線城市,消費的欲望大大超過消費的能力,內地的奢侈消費已遠遠超過香港、臺灣。更可怕的是,在一些地方政府、甚至國家級別的大型活動中,對于超級奢華的追求似乎也成了向外界顯示“軟實力”、“硬實力”的表演技藝。
《環球時報》海外記者近日著文稱,有關中國奢侈消費的報告正“扎堆”涌現。“亞洲國際豪華旅游博覽”與“胡潤百富”共同發布報告稱,2010年中國旅游者的購物花費首次成為全球第一,占全球跨國消費的17%。英國《衛報》引述某研究機構的預測稱,到2020年,中國的名牌時裝購買能力預料將占到世界的44%。美國全球廚衛設備公司瞄準中國消費者口味推出天價高智能超感坐便器及邊洗澡邊打電子游戲的浴缸、浴盆。英國“市場觀察”網站稱,中國內地消費者已經成為世界奢侈品銷售增長的主要驅動力。德國財經網稱,德國經濟直接獲益于中國人的奢侈品熱情。2010年,中國的消費者平均在德國采購金額為454歐元,而歐洲最富有的瑞士人僅有127歐元。同時還有文章披露,中國人均GDP只相當于發達國家的1/10。2008年中國人均GDP僅為世界平均值的三分之一,排在世界第106名,略高于剛果、伊拉克![2]
上述報道使人頓時升起這樣一個幻覺:在一個市聲喧嘩的十字街頭,各色人等都在圍觀一個涂脂抹粉、披金掛銀、渾身名牌、撓首弄姿的“傻妞”,難道這就是富裕起來的中國人!奢侈消費或許已經成了21世紀流毒于中國大地上的“新的鴉片”。中國有一句古老的格言:“玩物喪志”,當代中國人卻“玩物上癮”,玩到最后,“物”越來越尊貴、強勁、美好、偉大,“人”卻注定越來越卑微、脆弱、空洞、渺小。令人費解的是,一個擁有勤儉傳統、不久前還在高唱“勤儉是我們的傳家寶”(其中“儉”為老子的“三寶”之一)的當代中國,為什么會如此輕而易舉、變本加厲地接受了資本運營體系中如此粗鄙的消費觀念?
中國古漢語詞典中并沒有“消費”一詞,人作為自然界的生物,在生物圈內總是要消耗一定的物質和能量以維持生命的延續,如果把“生計日用”的開支也叫做“消費”,那么在此意義上建立的生產與消費的關系乃屬天經地義。
進入現代社會之后,“消費”(consumption)的性質發生了根本的變化。牽制人們日常生活行為的不再是自然生態的戒律,更不是精神上的道德感召,而是資本運營的價值規律。資本市場借助高科技的力量,全力刺激人們的消費欲望,以獲取高額回報。消費純粹成了為資本開發市場、賺取利潤的工具。人們不是為了需要而消費,而是為了消費而消費;不是為了消費而生產,而是為了生產而消費,整個社會成了一架制造消費欲、消費品的機器。現代中國缺少資本主義的傳統,也欠缺資本主義的免疫基因,因此,中國當代消費者就更容易被市場俘獲、被固定在這臺機器上,完全喪失了自我。
法國著名思想家波德里亞(Jean Baudrillard,1929—2007)一生與消費主義做對,人稱“消費文化解碼專家”,他深刻地揭示了西方現代“大型技術統治組織”如何通過消費建立起資本對社會的嚴密控制,揮霍錢財的程度,成了一個人事業成功、一個國家國力強大的標志,消費主義已經成為資本主義經濟學中最邪惡的邏輯。現代社會變成了“消費社會”(consumer society),消費異化為無益的“消耗”與“浪費”,而鋪天蓋地的廣告,仍在日夜不停地為現代消費演奏勝利的凱歌。現代文明已經變成“垃圾箱文明”,現代社會秩序、生產秩序已淪落到“厚顏無恥”的地步。消費社會成為現代人的一個“白色的神話”,一個除了自身之外再沒有其他神話的社會,一個近于猥瑣卻又惡魔般掌控著人類的社會,它“正在摧毀人類的基礎”、“時時威脅著我們中的每一位”。[3]24
波德里亞是否在故作驚人之語呢?
只要看一看處于消費社會中的自然的生態狀況與人類的道德精神狀況,就不難看出波德里亞批判的現實性與急迫性。
據世界自然基金會發布的公告稱,1961年至2003年之間,地球上的生態足跡增長了3倍多,到2050年,地球人類將消耗掉相當于2個地球的自然資源,地球已經被人類的消費行為大大透支了。在當代社會以8%的速度發展國民經濟的同時,自然界的淡水生態系統卻以8倍于以往的速度減少;當人們獲得了五花八門的享樂方式時,作為生命基本需要的空氣與水源卻成為“卡脖子”的要命問題。更不要說為了爭奪石油,中東地區已經成為國家之間血火交織的戰場!據有人統計,中國國民經濟增長率的75%是依靠自然資源與環境的超額投入為代價的。中國環境與發展國際合作委員會2010年會公布的《中國生態足跡報告》稱,2007年中國的生態足跡增加速度遠高于生物承載力的增長速度,生態足跡已是生物承載力的2倍,生態赤字還在逐年擴大。[4]如此“寅吃卯糧”,對于我們這個家底并不豐厚的人口超級大國家來說,后發的劣勢與潛伏的危機無益是十分險惡的。
至于伴隨消費主義風行在精神領域引發的病變,在當下中國,似乎已經不必多加舉證。各級黨政部門的貪腐行為在逐年攀升,達到令人發指的程度,嚴重的貪腐之風已成為國家安全的最大威脅。“上梁不正下梁歪”,在神州大地上橫行肆虐的“毒奶粉”、“瘦肉精”、“地溝油”、“吊白塊”、“蘇丹紅”、“黑哨”、“假球”、“假煙”、“假酒”、“假文憑”、“假刊物”、“假疫苗”、“醫療陷阱”、“旅游陷阱”等等見怪不怪的種種劣跡,便可以印證國家總理溫家寶最近發出的感嘆:“國民的道德狀況已經到了何等嚴重的地步!”
自然生態的惡化,精神生態的淪喪,已經讓經濟飛升的意義大打折扣。至于個人的日常生活領域,英國伯明翰學派文化研究的代表人物理查·霍加特(Richard Hoggart)曾指出:“一種健康的、淳樸的生活方式正在逐步被墮落的消費主義文化所取代。”[5]19那位美國生態批評家艾倫·杜寧(Alan Durning)更是得出這樣的研究結果:“消費與個人幸福之間的關系是微乎其微的”,“生活在90年代的人們比生活在上一個世紀之交的他們的祖父們平均富裕四倍半,但是他們并沒有比祖父們幸福四倍半。”[6]22他還引用牛津大學心理學家的判斷:幸福生活的真正條件“是那些被三個源泉覆蓋了的東西——社會關系、工作和閑暇。并且在這些領域中,一種滿足的實現并不絕對或相對地依賴富有”。[6]22
對照這些當代西方學者批判消費主義社會的話語,我們不能不再度回望我們的古代詩人陶淵明。“幸福生活”的“源泉”,原本在陶淵明這里,請看他的這首題為《移居·之二》的詩:
春秋多佳日,登高賦新詩。
過門更相呼,有酒斟酌之。
農務各自歸,閑暇輒相思。
相思則披衣,言笑無厭時。
此理將不勝,無為忽去茲。
衣食當須紀,力耕不吾欺。
公元408年,陶淵明在柴桑郊外的故居蒙受火災,后來移居到更為偏僻的南村,這里雖然偏遠,卻住著與他聲氣相投的諸多“素心人”。陶淵明在這首詩中既寫到鄰里間親密無間的和諧融洽,又寫到生活中必不可少的農務,更寫到春秋佳日、登高賦詩的閑暇時光。杜寧書中羅列的幸福生活三要素,全都具備了(在陶淵明這里還應多出一點,即親近自然)。這樣的生活是清貧的,也是健康的、淳樸的,因而也是幸福的。“清貧”、“寒素”一類的字眼,在古代漢語中從來就不只是一個經濟學的概念,而總是散發著濃郁的道德芬芳,閃爍著晶瑩的精神光芒。
最初的啟蒙主義者大約也沒有料到,理性主義的極致竟把人完全變成“經紀人”,進而變成“貨幣人”。波德里亞在他的《消費社會》一書的結語中發出強烈呼吁,要人們面對“消費社會之弊端及其無法避免的整個文明悲劇”,務必保持批判的“反話語”,“重要的是要給消費社會額外附加一個靈魂以把握它”。[3]230那么,這里我們就推薦一個東方的、古老的、詩界的“靈魂”——陶淵明,他曾經在貧苦生活中獲取精神上的最高愉悅,在最低“消費”的前提下,為人類文化作出最大貢獻。
注釋:
①“生態足跡”也稱“生態占用”,20世紀90年代初由生態學教授里斯(William E.Rees)提出,通過測定人類為了維持自身生存而利用自然的量來評估人類對生態系統的影響。如同一只負載著人類的巨腳,在地球上留下的腳印越大,對生態的破壞就越嚴重。該指標的提出可以在全球尺度上比較人類對自然資源的消費狀況。
[1]王先霈.陶淵明的人文生態觀[J].文藝研究,2002(5).
[2]李珍.中國奢侈品消費“稱王”令西方興奮[J].環球時報,2011-06-17.
[3][法]波德里亞.消費社會[M].南京:南京大學出版社,2000.
[4]章軻.中國生態足跡報告:生態赤字正逐年擴大[EB/OL].東方網,2010-11-10.
[5]莫少群.20世紀西方消費社會理論研究[M].北京: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06.
[6][美]艾倫·杜寧.多少算夠[M].長春:吉林人民出版社,198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