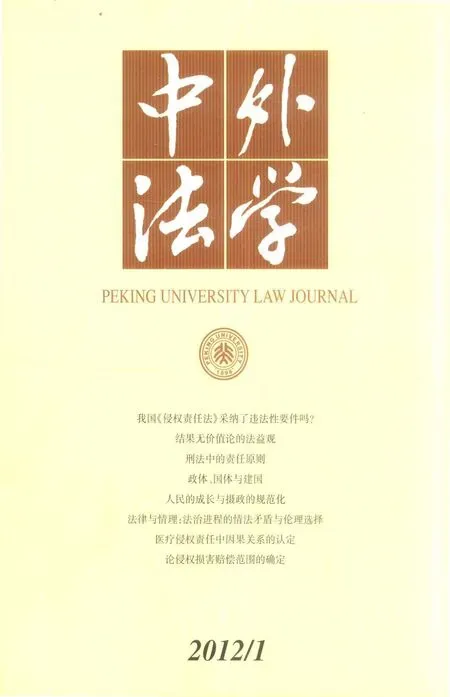結果無價值論的法益觀與周光權教授商榷
張明楷
周光權教授在《中外法學》2011年第5期上發表了《行為無價值論的法益觀》一文(以下簡稱周文),一方面修改了他以前的行為無價值論觀點,另一方面對結果無價值論提出了若干批評意見。盡管周文向結果無價值論邁進了一大步,但不無商榷之處。
一、關于“一元的結果無價值論”
周文為了說明“行為無價值論是‘新規范違反說’和‘法益侵害導向性說’的統一體”(第945頁),首先將矛頭指向所謂“一元的結果無價值論”。周文的說法是:“像一元的結果無價值論那樣,只將法益置于違法性評價的核心,完全不考慮行為本身的不妥當性的主張,存在諸多顯而易見的缺陷,是令人難以接受的。”(第945頁)問題是,誰主張的一元的結果無價值論“完全不考慮行為本身”?
如所周知,行為無價值論與結果無價值論原本是在違法性領域的分歧,但是,由于構成要件是違法類型,所以,表明違法性的要素當然成為構成要件要素。結果無價值論認為,違法性的實質是法益侵害(包括危險),所以構成要件的要素都是表明法益侵害的要素。結果無價值論并不是“完全不考慮行為本身”,而是不在倫理、社會的相當性、規范違反的意義上考慮行為本身,只是在法益侵害的意義上考慮行為本身。
周文還使用了“純粹的結果無價值論”的概念。周文在注腳〔3〕中指出:
二元的行為無價值論的對手是純粹的結果無價值論。其實,在日本及我國部分學者看來,為了防止結論過于極端,對結果無價值論還需要進行各種修正。但是,我認為,如果對純粹的結果無價值論可以進行某種修正(二元的結果無價值論),那么,其理論是否還站在結果無價值論的陣營,值得質疑。個別學者雖然宣稱自己的理論是結果無價值論的,但是,其方法論和結論可能都是行為無價值論的。所以,這里所批評的是典型的、純粹的結果無價值論。(第945頁)
筆者對此存在若干疑問:
第一,純粹的結果無價值論究竟是什么含義?如果說與一元的結果無價值論是同義語,那么,可以肯定,不存在“完全不考慮行為本身”的純粹的結果無價值論。
第二,日本及我國部分學者對結果無價值論進行的各種修正,究竟指什么?是對結果無價值論本身的修正,還是在結果無價值論的前提下或者基礎上,對某些具體問題存在不同看法?此外,哪位結果無價值論者的“方法論和結論可能都是行為無價值論的”?為什么在其中加上一個“可能”?這些都需要周文回答。
第三,即使結果無價值論者的某些觀點與行為無價值論相同,也不意味著結果無價值論者采取了所謂二元論。如所周知,結果無價值論與行為無價值論并不是在任何問題上都存在分歧。例如,就不能犯的判斷而言,結果無價值論既可能采取客觀危險說,也可能采取具體危險說,〔1〕參見(日)平野龍一:《刑法總論II》,有斐閣1975年版,頁326。還可能采取修正的客觀危險說。〔2〕參見(日)山口厚:《刑法總論》,有斐閣2007年版,頁275。但是,具體的危險說、修正的客觀危險說并不是對結果無價值論的修正,更不是向行為無價值論靠近,只是對不能犯的判斷提出的主張,而且這種主張與結果無價值論并不矛盾。如果說結果無價值論的某種觀點與行為無價值論相同,就意味著“結果無價值論存在缺陷”,那么,行為無價值論的某種觀點與結果無價值論相同時,也意味著“行為無價值論存在缺陷”。而且,如所周知,結果無價值論產生在行為無價值論之前。按照周文的邏輯,當行為無價值論的結論與結果無價值論的結論相同時,首先應當肯定“行為無價值論存在缺陷”。
再如,周文在注釋〔7〕指出:
贊成結果無價值,就應該在因果關系上堅持徹底的條件說。但是,由于條件說所確定的因果關系范圍過于廣泛,況且,在出現介入因素的場合,用條件說不能很好地處理案件,所以,各種修正理論開始出現。這些理論的出現,似乎與結果無價值論背離,而更多地體現了行為無價值的思路。(第947頁)
在本文看來,這一說法并無道理。首先,結果無價值論主張因果違法論,認為行為造成了法益侵害結果時,該行為就是違法的。所謂行為造成了法益侵害結果,意味著行為與結果之間具有因果關系。至于如何認定因果關系,則是另一問題。但是,一方面,條件關系并不等于因果關系。所以,認為結果無價值論應當堅持徹底的條件說,是缺乏根據的。另一方面,在認定行為與結果之間的因果關系時,對條件說的限定或者修正,并沒有背離結果無價值論所主張的任何觀點。其次,對條件說的限定或者修正,抑或采取客觀歸責理論,反而是以法益保護為導向的。德國學者羅克信(Claus Roxin)教授指出:
從法益保護原則出發經過一定的必然發展衍生出了客觀歸責理論……因為如果刑法希望保護法益免受人為的侵害,恰恰只有藉此理論方能實現:刑法禁止威脅法益存在的不允許危險的制造,并且將以法益侵害的形式違反禁止規定的實現該種危險的情形評價為刑事不法。因此,構成要件行為始終都是以實現人為制造的不允許危險的形式存在的法益侵害行為。〔3〕Claus Roxin,Das strafrechtliche Unrecht im Spannungsfeld von Rechtsgüterschutz und individueller Freiheit,in:Zeitschrift für die gesamte Strafrechtswissenschaft,116(2004),S.929ff.
第四,退一步說,即使結果無價值論進行了某種修正,形成了所謂的“二元的結果無價值論”,也不能得出“其理論不是還站在結果無價值論的陣營”的結論。周文明顯是二元論的觀點,卻仍然認為自己站在行為無價值論的陣營,并且聲稱自己的法益觀是“行為無價值論的法益觀”,而不是二元的行為無價值論的法益觀。既然如此,就不能認為結果無價值論經過某種修正就不再屬于結果無價值論的陣營。
周文指出:“行為和法益損害共同決定違法性的有無及其程度。”(第945頁)可是,行為在什么意義上與法益損害共同決定違法性的有無與程度呢?如果說行為只是在規范違反的意義上決定違法性的有無及其程度,那么,行為的意義就僅僅在于說明行為違反規范,何來“行為無價值論的法益觀”?如果說行為引起了法益損害因而決定違法性的有無及其程度,那么,就完全是結果無價值論了。
二、關于“脫離行為討論法益侵害的缺陷”
周文將批判對象限定為“典型的、純粹的結果無價值論”,這種典型的、純粹的結果無價值論,大概就是周文所言的脫離行為討論法益侵害的結果無價值論。但是,如前所言,結果無價值論并不是脫離行為討論法益侵害,而是將行為的意義限定為對法益的侵害或者威脅。所以,周文所批評的“典型的、純粹的結果無價值論”是根本不存在的。筆者的感覺是,周文按照自己批判的需要設定了結果無價值論的觀點。盡管如此,接下來還是要對周文所提出的幾點批判作些回應。
(一)關于“不全面”
1.周文指出:
在很多犯罪中,都不得不承認行為的無價值。刑法對許多犯罪構成要件的規定,其不法都以客觀的主體要素或特殊的行為方式作為其成立條件。例如,身份犯的身份,這一要素明顯屬于客觀不法要素,但難以劃入結果無價值的范疇,而必須將其列入行為無價值的討論要素。再比如,我國刑法規定了大量單位犯罪,作為主體存在的單位就是行為要素。(第945頁)
其實,結果無價值論不可能忽視身份要素。但應注意的是,由于犯罪的實體是違法與責任,所以,身份要么是違法身份,要么是責任身份。就違法身份而言,身份的意義不在于說明行為的規范違反性,更不在于說明行為的反倫理性與缺乏社會的相當性,而在于說明法益侵害。例如,受賄罪中的國家工作人員身份,就是表明行為侵害了職務行為不可收買性的要素。再如,國家機關工作人員的身份,就是表明濫用職權行為侵害了國家機關公務的合法、公正、有效執行以及國民對國家機關公務的客觀、公正、有效執行的信賴的要素。違法身份當然是不法要素,周文所說的身份“難以劃入結果無價值論的范疇”的觀點,顯然是難以成立的。此外,不管是單位犯罪中的行為主體還是自然人犯罪中的行為主體,本身都是違法要素。這不是結果無價值論與行為無價值論的分歧所在。
周文指出:“刑法分則對許多單位犯罪的自然人的處罰輕于個人犯該罪的情況,實際上也是認可單位這一主體要素對違法性有影響。”(第945頁)可是,這一說法并不表明結果無價值論的缺陷。其一,刑法分則中,對單位犯罪中的自然人的處罰同于個人犯該罪的情形,遠遠多于對單位犯罪的自然人的處罰輕于個人犯該罪的情形。周文以少數否認多數的做法,難以被人接受。換言之,倘若認為,刑法分則中“對單位犯罪的自然人的處罰輕于個人犯該罪”就是行為無價值論的結論,那么,刑法分則中更多的“對單位犯罪的自然人的處罰同于個人犯該罪”,就否認了行為無價值論的結論。其二,仔細考察就會發現,刑法分則對少數單位犯罪的自然人的處罰輕于個人犯該罪的情況,要么是為了限制死刑(如刑法第200條),要么是因為對單位判處了罰金而不再對其中的自然人判處罰金(如刑法第158條),要么是特定的單位犯罪時自然人所起的作用較小(如刑法第180條)。顯然,這些規定與行為無價值論、結果無價值論沒有直接關系。其三,行為主體之所以成為違法要素,也是因為行為主體通過實施侵害法益的行為造成了法益侵害的結果。周文顯然是想說明,行為主體是在行為無價值意義上對違法性有影響。可是,如果說行為主體本身影響所謂主觀惡性,那就不是所謂行為無價值論的法益觀,而是主觀主義理論;如果說行為主體本身影響行為的規范違反,則是難以成立的,因為違反規范的是行為而不是主體本身。
2.周文指出:
根據結果無價值論的邏輯思路進行司法判斷,在實踐中,容易導致一些錯誤。例如,對侵害人身權利的犯罪,司法人員往往從有無死亡結果發生出發,反過去看被告人是否實施有意地促成他人死亡的行為,來決定是否成立故意傷害致死,從而不當地擴大了故意傷害罪的適用范圍,在一定程度上混淆了故意傷害罪和過失致人死亡罪的界限,使得過失致人死亡罪的適用空間被壓縮,行為人輕輕拍打被害人身體的某個部位、推搡被害人、打人耳光等誘發被害人死亡的,都可能被錯誤評價為故意傷害罪,這明顯是不妥當的。(第946頁)
筆者的觀點剛好相反。實踐中混淆故意傷害罪和過失致人死亡罪界限的現象,正是行為無價值論乃至主觀主義理論造成的。
第一,從法益侵害角度來說,凡是致人死亡的行為,都是“殺人”行為。所謂的故意傷害致死,并不是說其行為不是殺人,只是說行為人對死亡沒有故意而已。如果說故意傷害致死的行為不是殺人行為,就難以解釋為什么被害人死亡了。過失致人死亡,在客觀上也是“殺人”,這是不言而喻的。在被害人的死亡由行為人的行為造成時,首先要判斷行為人對死亡有沒有故意,如有,則認定為故意殺人罪,不需要考慮其他犯罪;如無,則進一步判斷行為人是否有傷害的故意,如有,且行為人對死亡具有預見可能性,則認定為故意傷害(致死)罪;如果沒有傷害故意,則再判斷行為人對死亡有無過失,如有,則認定為過失致人死亡罪;如無,則認定為意外事件。不難看出,按照結果無價值論的觀點,不存在混淆此罪與彼罪的問題。
第二,行為無價值論將故意、過失納入違法要素,進而成為構成要件要素,于是,將故意殺人行為、故意傷害致死與過失致人死亡視為性質不同的行為。在認定犯罪時,首先追問行為性質是什么?答案只能是行為的性質取決于故意、過失內容不同(因為客觀內容完全相同)。同樣,不管行為造成了何種結果,關鍵在于行為人具有什么樣的故意與過失,故意、過失的內容成為區分上述犯罪的關鍵。司法機關正是在這種思路下混淆了故意傷害罪和過失致人死亡罪的界限。最為典型的是,即使行為不可能致人死亡,但只要行為人承認自己想殺人,也會被認定為故意殺人罪。
第三,按照結果無價值論的觀點,“行為人輕輕拍打被害人身體的某個部位、推搡被害人、打人耳光等誘發被害人死亡的”,也不成立故意傷害罪,只能認定為過失致人死亡罪或者意外事件。〔4〕參見張明楷:《刑法學》,法律出版社2011年版,頁772。換言之,將上述行為認定為故意傷害罪,是司法實踐沒有合理判斷故意與過失、沒有妥當區分刑法上的故意與日常生活中的故意所致,而不是結果無價值論的缺陷。
周文指出:
行為無價值論沿著“行為——結果”的邏輯出發思考問題,并沒有否定刑法的任務是保護法益。正是為了更加周延地保護法益,在評價上,才應當以行為為出發點;在手段上,才應當將禁止一定行為的規范(或者命令實施一定行為的規范)明確地告訴公眾,同時對違反規范的行為進行處罰,引導公眾遵守規范,通過規范來約束人的行為,使之在規范的指引下過一種有規律的生活。因此,越是要更好地保護法益,就越是應該強化公眾的規范感覺和規范意識,促使或者強制其不實施違反規范的行為。(第946頁)。
這是當今的規范違反說的核心所在。亦即,為了保護法益,必須維護旨在保護法益的規范的有效性;只要行為方式、手段違反了規范,即使現實上沒有侵害、威脅法益,也必須認定為違法行為;因為該行為雖然在此時此地沒有造成法益侵害,但在彼時彼地會造成法益侵害;將此時此地的行為認定為違法行為,就有利于預防彼時彼地的類似行為;所以,行為無價值論并沒有否定刑法的任務是保護法益。概言之,只要某種行為方式在彼場合可能造成法益侵害,那么,即使在此場合不可能造成法益侵害,任何人也不得實施。可是,行為是否可能造成法益侵害,是不可能離開時間、地點與其他條件的。相同的行為方式在不同條件下,所起的作用完全不同:在沒有發生火災的影劇院大喊“發生火災了”和在發生了火災的地方大喊“發生火災了”,意義完全不同。前者是擾亂公共場所秩序的法益侵害行為,后者是保護法益的行為。顯然,單純考慮行為方式或者手段本身的作用是不合適的,只有在特定背景下考慮行為與法益侵害的關系,才能明確行為的意義。更為重要的是,將特定的行為手段本身作為禁止對象,意味著只要在彼時彼地可能發生侵害結果的行為,即使在此時此地不可能發生侵害結果,國民也不得實施,這顯然極大地限制了國民的自由。
3.周文指出:
對交通規則有足夠注意者駕車撞死他人的情形,從法益侵害說的角度看,具體的行為(駕車撞人)現實地導致他人生命權喪失這一后果發生,即便不存在行為的無價值,行為人也應當受到處罰。但是,從行為規范違反說的角度看,只要行為人按照交通規則的要求駕駛,即使發生再重的法益侵害后果,行為人也并未違反行為規范,行為的無價值不存在,對行為人也不能進行刑罰處罰。(第946頁)
這種表述多少有些模棱兩可,委實讓反駁者左右為難。
其一,筆者想追問的是,“對交通規則有足夠注意者駕車撞死他人的情形”,客觀上是否違反了交通規則,主觀上有沒有過失?如果都得出肯定結論,結果無價值論者才會主張行為人應當受到處罰。如果其中之一是否定的,結果無價值論者就不會主張行為人應當受到處罰。順便指出的是,只要行為人違反交通規則致人死亡,即使主觀上沒有過失,也因為侵害了法益而存在結果無價值,只是沒有責任而已。
其二,在行為人遵守交通規則駕駛車輛的情況下,致人死亡的結果就不能歸屬于行為人的駕駛行為,不能認定該行為造成了法益侵害結果。這不是因為缺乏行為無價值,而是因為缺乏結果無價值,所以并不違法。換言之,并不是任何法益侵害結果都表明結果無價值;只有能夠歸屬于行為人的行為的法益侵害結果,才是結果無價值中的結果。
其三,交通規則都是為了防止傷亡等事故而制定的。例如,之所以有禁止超速駕駛、禁止闖紅燈、禁止逆向行駛等交通規則,就是因為這些行為可能產生法益侵害結果。換言之,違反交通規則的行為,都是有造成傷亡結果的危險行為,這不是行為無價值的根據。
(二)關于“不經濟”
在本部分,周文通過一個案例,批判了結果無價值論。但是,不得不說的是,周文誤解或者曲解了結果無價值論。周文指出:
A參加旅行社,在導游C帶領游客到某旅游商店購物時,將價值2萬元的古玩偷偷放入B的背包中(A試圖在B回到旅館后,再從同住一室的B的背包中偷取該財物),不知情的B背著背包外出時被店員查獲,按照結果無價值論,B有盜竊的違法行為,具有違法性,只是由于其在當時沒有故意而否定其責任。(第947頁)
對此,有以下幾點值得說明:
其一,違法性是具體的,而不是抽象的。具有盜竊罪的違法性的行為,并不具有殺人罪的違法性。倘若認為,A將古玩放入B的背包時,A的盜竊行為已經既遂,任何結果無價值論者都不說B的行為具有盜竊罪的違法性;如若認為,A將古玩放入B的背包時,A的盜竊行為并未既遂,結果無價值論者會認為,B的行為屬于類型化的掩飾、隱瞞犯罪所得的客觀行為,因而具有掩飾、隱瞞犯罪所得罪的違法性,只是因為沒有責任而不成立該罪。但周文對兩種不同犯罪的違法性不加區別,一概用“違法性”說明,恐怕不合適。
其二,應當說,在違法性階段所要解決的是行為是否具有違法性的問題,在有責性階段所要回答的是是否具有責任的問題,而不是一個籠統地解決有無可罰性的問題。周文聲稱“說B的行為違法,沒有任何實際意義”。事實上,周文只是考慮了B是否可罰的問題,而忽視了被害人在刑法上的權利主體地位。換言之,肯定B的行為具有盜竊罪(A盜竊未遂時)或者掩飾、隱瞞犯罪所得罪(A盜竊既遂時)的違法性是具有意義的。亦即,只有肯定B的行為違法,才能肯定被害人(包括店員)有權查獲、索回古玩。假如像周文那樣,認為B的行為是合法的,那么,當被害人發現古玩在B背包中時,反而不能向B查獲、索回,這顯然不合適。因為只要肯定B的行為是合法的,任何人都無權向B索要古玩。
其三,周文所主張的經濟做法是,故意、過失等主觀要素都在違法性階段一起判斷。但是,事實表明,從客觀到主觀、從違法到責任的判斷,才是最經濟、最合理的。
周文指出:
如果不考慮一般人主觀上避免結果發生的可能性,對因果關系的限定就是難以進行的,司法資源的浪費在所難免。結果無價值論者試圖借助于法益概念來限定處罰范圍的初衷也必然落空,那種認為堅持法益侵害說就能夠保障人權,實現個人主義和自由主義的主張,就是似是而非的說法。(第947頁)
可是,周文的說法讓人難以理解。“一般人主觀上避免結果發生的可能性”是指什么?如果是故意、過失,那么,為什么要用故意、過失限定因果關系?行為與結果之間是否存在因果關系,是不可能通過一般人主觀上避免結果發生的可能性判斷的。如果是期待可能性,那么,為什么要用期待可能性限定因果關系?德日的三階層體系及其行為無價值論者,也不是用一般人主觀上避免結果發生的可能性限定因果關系。
周文還指出:“德日的階層式犯罪成立要件理論也是深入司法官員的人心的,也是具有實踐理性的,不是停留在紙面上的、圖好看的東西。如果采用這種判決形式,違法性是否能夠先于有責性被排除就是比較重要的。”(第947頁)可是,這段話并不說明誰經濟、誰妥當。結果無價值論沒有也不可能在違法性之前判斷有責性。在德國、日本,行為無價值論者與結果無價值論者基本上都采取階層式犯罪成立要件理論,區別在于故意、過失是違法要素還是責任要素。德國近些年來將故意、過失作為違法要素,但這種做法基本上導致違法性的判斷成為可罰性的判斷,從而使德國學者認為,“德國刑法體系的最新發展又失去了區分不法與罪責所產生的好處”。〔5〕(德)許逎曼:“區分不法與罪責的功能”,載許玉秀、陳志輝編:《不移不惑獻身法與正義——許迺曼教授刑事法論文選輯》,臺北春風煦日論壇2006年版,頁419。
其實,所謂經濟與不經濟的判斷,也是值得進一步討論的。按照周文的觀點,在違法性階段判斷故意、過失就是經濟的,等到責任階段才判斷故意、過失就是不經濟的。可是,不管在哪個階段,都是需要判斷的,何來經濟與不經濟之分。再者,德日的三階層體系是對認定所有犯罪路徑的歸納,其中的違法性階層完全是為少數存在違法阻卻事由的案件而設立的。三階層是認定犯罪的順序,而不是出罪的順序。當一個三歲小孩將另一兒童推入水池溺死時,司法機關不會仔細判斷構成要件符合性與違法性,而會直接以缺乏責任為由而不立案。
周文指出:
在刑法只處罰某些犯罪的故意犯(例如故意毀壞財物罪),不處罰過失行為(過失毀壞財物罪)的場合,依據行為無價值論很容易否認該過失行為的違法性。但是,按照結果無價值論會先認定過失毀壞財物行為具有違法性,再否定其有責性。問題是過失毀壞財物行為本身就不是刑法要類型化地加以處罰的行為,即刑法對過失毀壞財物行為本身就能夠容忍,說它具有刑法意義上的違法性既沒有依據,也沒有意義,同時造成判斷上的不經濟,無罪結論的形成也太晚。(第948頁)
顯然,周文在判斷行為的違法性時,只是將違法性與可罰性聯系起來,將國民當作被動的客體,而不考慮國民(尤其是被害人)在刑法上的權利主體地位。一個可能造成法益侵害結果的行為,即使行為人沒有故意、過失等責任要素,國民也是可以制止、阻止或者防衛的。例如,即使狩獵者甲根本不可能預見到前方是人而事實上向人開槍時,其他國民都可以阻止甲的行為。同樣,即使乙過失毀壞他人財物,國民也是可以阻止其行為的。顯然,要肯定國民有權制止、阻止或者防衛某種行為,就必須肯定該行為是違法的。按照行為無價值論的邏輯,由于甲不具有過失、乙不具有故意,所以,其行為并不違法,而是合法行為。可是,這種觀點難以回答這樣的問題:國民為什么有權阻止合法行為?哪些合法行為是國民有權阻止的,哪些合法行為是國民無權阻止的?
周文還說:
如果將結果無價值論認為過失毀壞財物也具有違法性的觀點貫徹到底,會得出見死不救、通奸、同性戀、單純吸毒等行為都具有刑事違法性的不合理結論。而刑法對類似行為原本就沒有類型化地加以禁止的意思,認定其具有違法性與刑法的最后手段性相悖。
(第948頁)
在本文看來,這種說法明顯違反事實。如所周知,通奸、同性戀、單純吸毒等行為的非罪化,完全是法益侵害說(結果無價值論)的功勞。正如行為無價值論者所言:“結果無價值論的功績,在于明確了違法判斷的內容及違法要素的范圍,必須由該刑罰法規所預定的規制目的、保護目的予以限定。”〔6〕(日)井田良:《犯罪論の現在と目的的行為論》,成文堂1995年版,頁147。由于刑法的目的是保護法益,故刑法將違反該目的的事態作為禁止的對象,違法性的本質就是侵犯法益;通奸、同性戀、單純吸毒等行為沒有侵害法益,當然不能由刑法禁止。至于見死不救是否成立犯罪,與行為無價值論、結果無價值論沒有直接關系。德國刑法規定了見死不救罪,可結果無價值論在德國并不是通說;日本刑法沒有規定見死不救罪,可結果無價值論在日本基本上是通說。
(三)關于“不清晰”
周文指出:“法益概念的含義從來都不清楚。”(第948頁)倘若說這是結果無價值論的缺陷,那么,也難以解釋周文“行為無價值論的法益觀”的標題。換言之,如果說結果無價值論的法益概念不清楚,行為無價值論的法益概念也不會清楚。
周文提出的第一個出路是:“充分認識到某些所謂的法益,實際上是規范關系、規范秩序,從而將法益保護和規范維護有機統一起來,將對法益的解釋轉化為對規范關系的解釋。”(第948頁)可是,當法益概念說不清楚時,將它和規范維護統一起來,就更說不清楚。況且,將法益的解釋轉化為規范關系的解釋,就不需要法益概念了。此外,周文所稱的規范關系,又何嘗不是法益。例如,環境犯罪的法益就是人類生存環境,比規范關系容易理解。
周文提出了的第二個出路是:“充分考慮法益與行為的關系……對犯罪的判斷,在將法益侵害后果作為評價對象時,行為的種類與手段,以及行為人的主觀目的、動機等意思要素,也應當考慮在內,才較為妥當,思考才不會出差錯。”(第949頁)然而,行為的種類與手段,以及行為人的主觀目的、動機等意思要素,并不是使法益概念更清晰的要素,而是表明行為是否符合構成要件或者責任要件的要素。相反,一個犯罪的成立需要什么樣的行為,則是由法益決定的。例如,故意殺人罪與過失致人死亡罪的保護法益是生命,因而要求行為具有足以致人死亡的緊迫危險(后者進一步要求造成死亡結果)。故意毀壞財物罪的保護法益是財產,因而要求行為人實施使他人財物的價值減少或者喪失的行為。由此看來,不是行為的種類使法益清晰,而是法益限定行為的種類與性質。
(四)關于“不自洽”
1.周文指出:“純粹的法益侵害說不能貫徹到底。”“如果堅持徹底的法益侵害說,對不能犯,尤其是在對象不能的場合,只能得出明顯不合理的無罪結論,這就是‘舊客觀說’的立場。”(第949頁)如前所述,對舊客觀說的修正,并不是對結果無價值論的修正,舊客觀說并不是結果無價值論的全部,也不是結果無價值論的核心內容。對舊客觀說進行修正,也不存在與結果無價值論的矛盾,更不是所謂結果無價值論轉向了行為無價值論。
周文指出:
對于某種行為是否有必要進行處罰,要看行為是否違反行為規范,從而可能被其他人效仿,并對規范的有效性形成沖擊。一個舉槍殺人的行為,一定是具有違法性的行為,只是在碰巧被害人剛剛死亡的場合,法益實害沒有發生。但是,這樣的行為如果換一個時間、地點“重演”,很難說結果不會發生,因而法益危險仍然存在。因此,將極度危險的“殺害”行為類型化地評價為殺人行為,并給予處罰,有助于提示行為本身的不值一提,有助于重構被破壞的規范,因而類似行為只能成立未遂犯。(第949頁)
但是,這一觀點存在兩大疑問。其一,在此時、此地的行為,為什么要放在彼時、彼地去判斷有無法益危險?既然在此時、此地針對特定的死人開槍,不可能導致活人死亡,就應當否認其違法性。為了不讓他人效仿而認定該行為成立未遂犯,顯然是將行為人當作預防犯罪的工具了。其二,根據周文的觀點,在某種行為在此時、此地不可能發生法益侵害結果時,只要在彼時、彼地能發生法益侵害結果,也必須宣告這種行為的違法性。于是,國民只能實施在任何時候都不可能導致法益侵害結果的行為,這明顯限制了國民的自由,因而不可取。
2.周文指出:“將刑法目的定位于法益保護,也可能不當地擴大違法處罰范圍。”(第949頁)可是,從上述不能犯的論述以及眾所周知的偶然防衛的處理可以看出,結果無價值論明顯限制了違法處罰范圍,何以不當擴大違法處罰范圍。周文指出:“某些有客觀法益損害的行為,按照法益保護說可能被認定為犯罪行為,但按照規范違反說顯然不能對其以犯罪加以處理。”(第950頁)但是,從周文轉述的雅科布斯(Jakobs)教授所舉之例來看,并不能證明他的觀點。誠然,與行為無價值論將故意、過失納入違法要素相比,結果無價值論因為將故意、過失作為責任要素,可能對違法行為認定較為寬泛。但是這并不意味著法益保護說的處罰范圍寬泛。結果無價值論只是從違法性角度說明哪些行為是刑法所禁止的,是國民可以阻止、制止的。但是,成立犯罪還需要責任要素。換言之,結果無價值論并沒有將責任要素納入違法要素。正確的表述應當是,“某些有客觀法益損害的行為,按照法益保護說可能被認定為違法行為”,而不是直接被認定為犯罪行為。反之,行為無價值論則將故意、過失這樣的心理要素歸入違法要素,導致違法幾乎等同于犯罪。〔7〕行為無價值論者指出:“責任不是為處罰提供根據的要素,只是單純限定處罰的要素。違法判斷,只能是確定處罰對象的判斷(因此而明確為什么處罰某行為)。打個比喻,違法是犯罪論的發動機部分。責任,因為只是單純限定處罰的要素,所以它只是剎車。”((日)井田良:《刑法總論の理論構造》,成文堂2005年版,頁1~2。)由于僅憑違法性確定處罰對象,所以,故意、過失必須成為違法要素。處罰根據完全由違法性決定,而不是由違法性與有責性共同決定。然而,為犯罪提供根據的要素與限制犯罪成立的要素并不是對立的。如同構成要件既為違法性提供根據,也限制了處罰范圍一樣,責任并不只是限制犯罪的成立,同樣為犯罪的成立提供非難的根據。(參見張明楷:“行為無價值論的疑問”,《中國社會科學》2009年第1期,頁109以下。)況且,認為違法提供處罰根據、責任僅限制處罰范圍的觀點,只是一種理論設定,并沒有實質根據。這是行為無價值論的缺陷所在。行為無價值論不能因為其將違法與犯罪相等同,〔8〕根據行為無價值論的觀點,故意、過失是違法要素,責任要素只剩下責任能力、違法性認識的可能性與期待可能性,可是,在絕大多數案件中,行為人都具有責任能力、違法性認識的可能性與期待可能性。于是,只要行為具有違法性,就基本上成立犯罪。正如行為無價值論者所言:“具有了違法性,肯定不能‘表明’具有了罪責。盡管如此,通常情況下承擔罪責并不需要特殊理由,因為,只要沒有例外情況,個人為自己的行為負責是不言而喻的。”“因此,很容易理解,在罪責這一階層上為什么考慮的不是積極的前提,而是排除或者免除罪責的消極條件。”((德)岡特·施特拉騰韋特、洛塔爾·庫倫:《刑法總論I——犯罪論》,楊萌譯,法律出版社2006年版,頁85。)然而,一種只需要消極判斷的責任概念,降低了責任主義的地位(責任不再是犯罪論體系的支柱),而且容易導致整體性地認定犯罪。就認為結果無價值論將違法與犯罪相等同。周文還指出:
根據行為規范違反說,犯罪就應該如此界定:實施某一行為,侵害他人權利,根據社會中存在的規范關聯性,認為是造成了損害的行為。換言之,違法性意味著行為通過規范違反造成法益侵害。這樣的違法性概念,不是要否定法益的重要性,而是強調刑法只有在行為對法益的侵害或者威脅達到了違反行為規范的程度時才能實施懲罰。(第950頁)
人們很難理解,其中的規范違反究竟指什么?如果說規范違反是指行為符合構成要件,那么,結果無價值論完全贊成。因為刑法對法益的保護,也必然受罪刑法定原則的制約,不符合構成要件的行為,就不是刑法所禁止的行為,當然沒有刑法上的違法性。可是,這與規范違反沒有關系。如果說規范違反是構成要件符合性之外的內容,則意味著符合構成要件的行為侵害了法益還不具有違法性,而必須介入規范違反這一中間要素才具有違法性,則有自相矛盾之嫌。因為在符合構成要件與法益侵害之外另要求規范違反,必然導致將維護規范效力作為刑法目的。然而,即使承認刑法具有行為規制機能,也應當否認刑法的目的與任務是維護規范效力。因為行為規制機能基本上只是法益保護機能的反射效果,對規范的維護本身不可能成為刑法的目的。國家是為了保護法益才制定規范,禁止的方法是將法益侵犯行為類型化,并規定相應的法定刑。這種規定方式自然地產生了行為規制效果。況且,行為規制與法益保護并非并列關系;國家不可能為了單純限制國民的自由而規制國民的行為。更為重要的是,規范違反說認為,譴責犯罪人是為了維護規范,只有規范的存在與否才是重要的,這有將人當作工具之嫌。
(五)關于“不準確”
周文指出:
僅僅利用法益標準來衡量所有犯罪,有時難以奏效。對很多妨害社會管理秩序的犯罪,用法益保護說來解釋刑法的規范目的,可能就存在難題。例如,各種妨害社會風化、影響社會善良風俗的犯罪,都是出于維護社會關系的考慮才在刑法上加以規定的。這些犯罪的本質是對社會規范關系的違反。但是,法益保護說對此就必須解釋為:這些犯罪侵害了社會法益,所以,必須受到處罰。但對于社會法益的具體內容,大多以社會純樸風尚、善良風俗搪塞。由此,必然將法益概念抽象化、精神化、空洞化,令人無從把握。而社會善良風俗、社會純樸風尚,實際上就是國民的規范意識、價值理念、道德觀念、規范關系的外化。所以,刑法規定這些犯罪,與其說是保護抽象的、高度精神化的法益,不如說是保護規范關系。(第950頁)
這一說法值得商榷。其一,周文原本就承認刑法的任務是保護法益,在此卻認為刑法的目的是保護規范關系。這凸顯出周文的矛盾。其二,人們應當追問的是,刑法為什么要保護規范關系?規范關系的實際內容是什么?在本文看來,倘若認為法益概念抽象化、精神化、空洞化,那么,規范關系概念必然是有過之而無不及。其三,社會善良風俗、社會純樸風尚究竟是法益,還是規范關系,恐怕只是用語不同而已。其四,法益作為保護客體,一方面與行為對象有所區別,另一方面也是現實的存在。
在此,法益不需具有必要的物的具體現實性,財產所提供的物的使用權,或者通過強制禁止所保護的意志活動自由,都不是有形有體的對象,但是它們確實是經驗現實的組成部分。另外,基本權利和人權,像人格的自由發展、表達自由或者信仰自由,都是法益。對這些權利的克扣會導致社會生活中很現實的損害。同樣,國家制度,像司法機構或者貨幣體系或者其他的公眾法益,雖然不是有形有體的對象,但是它確實是生活所必要的現實,對它的損害會長遠地危害社會的效能和公民的生活。〔9〕(德)克勞斯·羅克信:“刑法的任務不是法益保護嗎?”,樊文譯,載陳興良主編:《刑事法評論》第19卷,北京大學出版社2007年版,頁151。
所以,將經驗現實的法益視為抽象化、精神化、空洞化的東西予以排斥并不合適。
周文還指出:
按照法益保護說,對法益的抽象危險也是有必要加以懲罰的。但抽象危險犯立法的大量增加,很難說其具有合理性;同時,刑法規定抽象危險犯,已經不是在保護通常意義上所說的法益。……我們完全可以說在抽象危險的情況下,刑法實際上是在保護一種相當抽象的社會規范關系,而不是在保護法益。……抽象危險犯在我國近年來的立法中,有不斷增加的趨勢。這說明行為無價值論不僅僅符合中國的司法實務現狀,其與立法上的抉擇也相契合。”(第950-951頁)
這段話不無疑問。其一,結果無價值論并沒有主張對所有的抽象危險行為都加以懲罰。在某種意義上說,增設抽象危險犯是法益保護的前移。但是,這種前移必須具有充分的根據。道理很簡單:如果盲目前移,那些距離侵害結果發生很遠的行為,也會被刑法所禁止,國民就沒有行動自由可言。我們顯然不能因為疏于教育的父母可能導致子女殺人,就將疏于教育規定為犯罪。德國學者羅克信教授對德國刑法第316條(酒后駕駛罪)、第265條(保險詐騙罪)的分析,也說明了這一點。根據德國刑法第316條與第265條的規定,“如果根本沒有發生任何事故,在喝了酒的狀態下駕車(酒后駕車)也要受到處罰。另外,為了過后作為被盜之物而申報保險,某人把自己投保過的東西予以藏匿或者丟棄,那么,他就會面臨由于既遂的保險濫用的刑事可罰性。”
兩個規定無疑服務于法益保護:第一個服務于交通中身體、生命和物的價值的保護,第二個保護保險公司的財產。這些規定的問題在于,這些被納入犯罪的行為距離真正的法益損害還很遙遠。在這一點上,從法益保護的理念所得出的結論只能是,對于這種可罰如此重大的前移,需要有一個特別的根據來說明:對于法益的有效保護,這種前移為什么是必要的。第一種情況提供了這種根據(因為喝了酒的駕車者不能在完全正常的程度上控制自己的行為,以至于任何時候都可能發生事故),但是第二種情況沒有提供這種根據(因為藏匿或丟棄自己財產的人,還總是可以支配的是:在此之后他是以詐騙的意圖去提出保險理賠還是不去申報理賠)。〔10〕同上注,頁159。
同樣,結果無價值論并不意味著要將離發生實害很遠的危險行為都規定為犯罪,只有對那些離發生實害距離很近,而且發生實害的概率較高的危險行為,才能實行犯罪化。其二,抽象危險犯中的危險,本來就是指對法益的危險,規定抽象的危險犯顯然是為了提前保護法益,怎么能說“在抽象危險的情況下,刑法實際上是在保護一種相當抽象的社會規范關系,而不是在保護法益”呢?其中的“相當抽象的社會規范關系”又是指什么呢?為什么刑法不可以保護抽象的法益,卻可以保護相當抽象的規范關系呢?這是需要周文回答的問題。其三,如果說抽象危險犯的大量增加意味著結果無價值論的不合理,那么,為什么按行為無價值論解釋就合理了呢?
(六)關于“不及時”
周文指出:
如果刑法不發揮其積極作用,只在等到有法益侵害或者危險事實的發生才去實施消極救濟,日常生活就無法進行。在有的情況下,用法益侵害說來懲罰犯罪,明顯具有“馬后炮”的味道。例如,對環境犯罪,一旦造成后果就難以挽回。如果也按照法益侵害說進行處理,就會不顧及人類的生活及其質量。(第951頁)
其一,刑法對犯罪的預防有兩個途徑:一方面,刑法的頒布本身,就是對法益的一種許諾性的保護,因而是對犯罪的一種預防。例如,刑法規定故意殺人罪及其法定刑,就意味著要保護人的生命,這一規定本身就能預防很多故意殺人行為。另一方面,在犯罪發生之后,通過對犯罪的懲罰以實現預防犯罪的目的。刑法對某個犯罪的處罰,并不是消極救濟該犯罪已經侵害的法益,而是保護類似法益不被其他行為侵害。沒有后者,前者也會落空。顯然不能認為后者只是“馬后炮”。其二,環境犯罪的保護法益是環境本身,對環境的破壞本身就是對法益的侵害,因此,不存在周文所稱的結果無價值論不顧及人類的生活及其質量的問題。相反,正是因為對環境的破壞會危及人類的生活及其質量,所以,結果無價值論認為環境本身就是法益。
周文指出:“僅僅從法益侵害角度看問題,不僅僅對新型的行政犯的懲罰顯得沒有意義,對幾乎所有的犯罪的解釋力也都有限。例如,一個殺人行為,在被害人死亡的場合,具體法益已然受到侵害,此時,再討論對當前的、特定的法益的保護,已經沒有實際意義。”(第951頁)可是,如前所述,在乙已經被甲殺害的場合,對甲的處罰當然不是為了保護乙的生命,而是為了保護其他人的生命。按照規范違反說的觀點,在乙已經被甲殺害的場合,對甲的處罰可以保護被甲破壞的規范。其實,規范是不可能被破壞的,也不需要所謂的修復。規范一經制度化,在其存續期間,只存在是否有人違反規范的問題。只要規范沒有被廢止,規范就是有效的,對犯罪人的懲罰不可能是為了保護規范本身。所謂維護規范效力,也不過是“違法必究”的另一種表述而已。但是,之所以“違法必究”,也是因為違法的行為侵害了法益,所以,維護規范效力只是一種表面現象,真正的目的仍然是保護法益。即使按照行為無價值論的觀點,在乙已經被甲殺害的場合,也要處罰甲。如果說甲的行為已經破壞了規范,那么,規范曾經被破壞的事實也是無法彌補的。在這一點上,行為無價值論與結果無價值論沒有任何差別。
三、關于“法益的從屬性和獨立性”
在本部分,周文介紹了行為無價值論如何看待法益概念的兩種主張。
第一是所謂法益侵害從屬于規范違反的主張(雅科布斯教授的觀點)。亦即,“刑法保護法益,只是現象,通過對侵害法益的行為進行懲罰,從而證明規范的有效,以促進國民認同和尊重規范,形成對法律的忠誠,防止規范網絡被再次沖破,才是問題的實質。”(第952頁)在筆者看來,這種觀點可謂本末倒置。雅科布斯教授雖然認為刑法的目的是保護規范的有效性,但是,他“有意回避規范內容的合法性或者不法性的任何命題”,“導致法學家給立法者提供恣意的專斷”,“他建議放棄‘過時的’規定,最后可還是(回歸到了)這里所提出的法益保護理念”。〔11〕克勞斯·羅克信,見前注〔9〕,頁164~165。
第二是周文所贊成的法益與行為相互獨立(行為和結果相互獨立)的觀點。問題在于,在什么意義上,行為和結果相互獨立?其一,如果說在構成要件要素上,行為與結果相互獨立,則是無可爭議的。因為任何構成要件都有對行為的描述,既遂犯罪都有實害結果,未遂犯都有危險結果。結果無價值論者不會在構成要件要素的意義上否認行為的獨立意義,也不能認為行為屬于結果的一部分。在這個意義上說,行為與結果當然相互獨立、同等重要。換言之,行為具有定型的意義,亦即,只有符合構成要件的行為造成了對法益的侵害或者威脅,該行為才是違法行為。這是罪刑法定原則的要求,行為無價值論與結果無價值論在此問題不會存在分歧。其二,如果說行為具有構成要件符合性與侵害法益之外的其他獨立意義,結果無價值論則不贊成。在結果無價值論看來,行為的實質意義在于它侵害或者威脅法益,是結果發生的原因。行為無價值論者強調行為具有獨立于結果之外的意義,無非是說行為本身具有違反倫理、缺乏社會的相當性、違反規范之類的意義。周文是在最后一個意義上而言的。其實,行為違反規范的意義,最多只是說明了行為的形式違法性。可是,一個符合構成要件且侵害或者威脅了刑法所保護的法益的行為,當然具備了形式違法性。然而,應當明確的是,規范違反說與法益侵害說是在實質的違法性層面展開的爭論。將形式違法性納入實質違法性中討論,無益于問題的解決。倘若行為無價值論認為,行為違反規范是指違反刑法之外的規范,則大有商榷的余地。這是因為,一個符合了刑法所規定的構成要件且侵害或者威脅法益的行為,一定是違法的,而不會以違反刑法以外的規范為前提。否則,就意味著刑法完全從屬于其他法律,而不具有獨立性,這是早已被否認的觀點。
周文反復強調的是,在結果發生之后,刑法沒有辦法防止該結果的發生,因此,應當通過禁止行為來防止結果的發生。于是,需要充分發揮刑法的行為規范的機能。其實,結果無價值論也并不否認刑法規范是行為規范,也知道只有通過約束行為才能約束結果。換言之,結果無價值論并非不講規則。一方面,在通常情況下,遵守規則就意味著保護法益,所以,在這種場合,結果無價值論必然也主張遵守規則。但結果無價值論主張遵守規則,是因為遵守規則才能保護法益,而不是為了遵守規則而遵守規則。另一方面,結果無價值論還有一個簡單的、基本的規則(指導),并且要將這種簡單的、基本的規則貫徹到具體境遇中。結果無價值論反對用事先確定的“規則”來校正人們在例外情況下的行為,強調人們行動境遇的當下特殊性,以當下特殊的具體境遇中對法益的保護作為行為的基本規則,所以,就特殊的具體境遇而言,無需人為地事先設定“規則”這個中介。對于具體的特殊境遇下的行為選擇來說,普遍性的規則既無必要,也不可能。在具體的實際生活中,尤其是在沖突的境遇中,在與刑法相關聯的意義上,人們只需要問“我的行為雖然符合構成要件,但能否最有效地保護法益”即可,而不需要問“我的行為雖然符合構成要件,但我實施這一行為是否符合既定的規則,是否屬于規則允許的例外”?不難看出,結果無價值論在遇到沖突時有其獨特的魅力,亦即,它既具有簡便性,也具有靈活性。概言之,結果無價值論提供了一個基本的行為標準:不能侵害或者威脅法益。這個基本的行為標準,比行為無價值提供的不得違反規范的行為標準,更為直接、更為有效。
周文認為:“如果承認通過特定的行為方式、手段,進而造成法益損害才具有違法性,那么,就完全可以認為行為和結果在刑法中處于同等重要的地位,只有同時肯定行為無價值和結果無價值,才能得出違法的結論。”(第953頁)其實,通過特定的行為方式、手段,進而造成法益損害,只是意味著符合構成要件的行為造成的法益侵害才具有違法性,這一點,結果無價值論從未否認。但是,周文將行為的構成要件符合性當作行為無價值,這顯然不合適。因為在德日的三階層體系中,正當防衛的殺人也是符合故意殺人罪構成要件的行為,但是,不可能認為正當防衛具有行為無價值。同樣,在蘇聯和我國的四要件體系中,正當防衛也不可能具有行為無價值。此外,承認通過構成要件的行為造成法益侵害才具有違法性,是否表明行為和結果在刑法中處于同等重要的地位,取決于如何看待這里的“同等重要”。從構成要件要素的角度來說,任何一個要素都是同等重要的,因為缺少任何一個要素都不可能成立犯罪。但是,從實質的違法性的角度來說,行為與結果就不是同等重要的。因為刑法的目的不是禁止外表不適當的行為,而是禁止造成或者足以造成法益侵害的行為。換言之,某種行為是否被禁止,取決于該行為是否造成或者足以造成法益侵害結果。在此意義上說,結果(包括危險)比行為重要得多。
周文認為:
按照行為和結果相互獨立的觀點,對既遂犯和未遂犯的處罰就可以得出正確的結論:既遂犯實際造成法益侵害,公眾能夠直接感知這種后果,從而產生強烈的處罰渴求。如果放縱既遂犯,等于國家發出允許法益侵害發生的明確信號,可能導致人們更多地模仿類似行為,從而造成更多的法益侵害。但是,由于未遂犯畢竟沒有造成實害,公眾對沒有造成特定結果的未遂犯的否定意識較低。因此,對未遂犯和既遂犯的處罰當然應該不同。(第953頁)
其實,按照結果無價值論的觀點,對既遂犯和未遂犯的處罰也是理所當然的不同。這是不言自明的,也得到各國刑事立法的認同。倒是按照行為無價值論的觀點,未遂犯與既遂犯的處罰不應當有區別,因為違法的實質是對行為規范的違反,而未遂犯與既遂犯都是對行為規范的違反;一個行為的違法性是在行為當時就可以確定的,是在著手時就已經形成的。正如規范違反說的主張者雅科布斯教授所言,未遂與既遂意味著以同樣的方式“對規范的效應的完全侵害”。〔12〕Günther Jakobs,Strafrecht Allgemeiner Teil,2.Aufl.,Walter de Gruyter 1993,S.711.但是,將違法視為對行為規范的違反,是不可能反映違法程度的。因為任何犯罪行為對規范的違反程度是一樣的,不能說故意殺人罪100%地違反了規范或者違反了規范的全部,而盜竊罪只是60%地違反了規范或者違反了規范的60%。人們通常所稱的違法程度不同,并不是指對規范的違反程度不同,而是實質的違法程度不同,即侵害的法益不同,或者對相同法益的侵害程度不同。
四、關于“行為無價值論和結果無價值論在法益概念運用上的具體差異”
(一)關于法益保護內容上的差異
周文指出:“純粹的結果無價值論認為,刑法保護當下的、具體的法益。”(第954頁)雖然周文對此沒有具體解釋,故難以理解“當下的、具體的法益”指什么,但聯系周文所稱的“行為無價值論則主張:刑法保護未來的、其他的、一般人的法益”。(第954頁)則大體可以明白上述表述的含義。
如前所述,對于行為已經侵害的法益,刑法不可能保護(只是在某種場合可以挽救),這是常識。結果無價值論不可能認為,刑法僅保護已被侵害的法益。例如,甲殺害乙后,刑法不可能再保護乙的生命。但是,刑法作為一種規范,當然地對人們的行為起指導、制約作用。所以,一方面,在當下的具體法益還沒有受到侵害時,刑法就在保護當下的具體的法益。這是不容否認的。相對于法益主體而言,這種保護是許諾性的;相對于其他人而言,這種保護是通過刑法的禁止規范體現出來的。周文完全否認這一點,這與周文強調刑法對公民行為的規制是自相矛盾的。另一方面,在當下的具體法益受到侵害后,刑法通過懲罰侵害法益的犯罪行為來預防犯罪,保護其他的、一般人的法益不受到侵害。這一點,結果無價值論并不會否認。因為結果無價值論者從來不否認刑罰的目的是預防犯罪。在本文看來,周文所提出的結果無價值論與行為無價值論在法益保護內容上的差異,是并不存在的。
周文指出:
按照行為無價值論的法益觀,未遂犯和不能犯的區別就是:某種舉動、行事方式對未來是不是有危險?如果在具體個案中,結果沒有發生,但是沒有發生的原因是這個行為人所無法掌控的,將其作為未遂犯處理,一般是妥當的。因為類似行為,如果換一個時間、地點實施,結果十之八九會發生,或者誰也無法保證其不發生,行為的危險性是顯而易見的。對危險的判斷,其實是在對未來作預測。對類似在未來可能輕易造成實害的行為如果不處罰,后果將是災難性的。如果僅僅因為當下的、具體的法益侵害沒有發生,就草率認定某種行為是不能犯,那么,其他人都可以學習類似行為,規范效力必然受沖擊,規范破壞的局面就會形成,社會就會變得很危險,“未來的”法益保護就會變得很困難。(第954-955頁)
這段話清楚地表明了行為無價值論將人當作工具的觀點。其一,行為無價值論的邏輯是,某行為雖然在此時、此地不可能侵害法益,可是,如果其他人在彼時、彼地實施該行為,則可能侵害法益,所以,為了防止其他人效仿,就必須將該行為當作犯罪處理。亦即,為了防止法益侵害,必須將某些沒有侵害法益的行為當作犯罪處罰。按照結果無價值論的觀點,為了防止法益侵害行為,也只能將侵害法益的行為當作犯罪處理;不能為了防止將來的法益侵害,而將現在并沒有造成法益侵害的行為當作犯罪處理。其二,周文說:“對危險的判斷,其實是在對未來作預測。”這意味著,某種行為有沒有法益侵害的危險,是指將來由其他人在他時、他地時實施該行為時有沒有危險。可是,將哪些他人、何時的他時、何地的他地拿來作為判斷資料呢?結局恐怕是沒有判斷標準了。其三,行為無價值論者擔心,當甲以殺人故意向一分鐘之前已經死亡的人開槍時,如果不處罰甲,其他人就會模仿。但是,這沒有模仿的可能。因為其他人知道,只有向死人開槍才不構成故意殺人罪。倘若一個人為了逃避刑事責任,而想方設法在一個人死后一分鐘向其開槍,也不存在對生命的侵害,當然不能以故意殺人罪論處。所以,對不能犯宣告無罪時,不可能出現有人以未遂犯的行為模仿不能犯的行為。再如,刑事判決宣布偶然防衛不違法,并不會帶來消極效果。這是因為,刑事判決宣布偶然防衛不違法,既保護了偶然防衛者的法益,也不會導致有人在故意殺人時期待自己的行為產生偶然防衛的效果。亦即,當X偶然防衛致人死亡但被法院宣告無罪時,其他人是無法模仿偶然防衛的。倘若真的有人因為偶然防衛不違法,就長時期跟蹤自己的仇人,打算乘仇人殺人時將仇人殺死,則他的行為已經是有防衛意識的正當防衛了,更加不違法。概言之,在刑事司法上宣布偶然防衛不違法,不可能起到鼓勵人們實施偶然防衛的作用。
(二)關于方法論上的差異
周文指出:“純粹結果無價值論認為,對法益是否受侵害,應該進行個別評價;并從整體事實中抽取并不重要的事實進行評價。但是,行為無價值論則傾向于主張對法益是否受侵害進行整體判斷,且不能從總體事實中抽取不重要的事實進行判斷。”(第955頁)
其實,周文所稱的并不重要的事實,剛好是最重要的事實。以周文所舉之例為例。在行為人A對B實施殺害行為的場合,即便行為手段是用槍射殺,但只要被害人B此前已經死亡的,A的客觀行為就不是剝奪被害人生命的行為。周文指出:結果無價值論的觀點是,
剝奪生命的殺人行為以存在生命為前提,既然被害人已經死亡,不再具有生命,針對被害人的行為就不可能成為剝奪生命的行為。但是,這種個別判斷的方法論,行為無價值論難以接受。因為對一個行為是否屬于實行行為,應在行為當時進行判斷。犯罪是行為這一命題意味著犯罪是“實行行為時”的行為。其實,站在行為的時點判斷行為,更能夠保持判斷的客觀性。(第955頁)
可是,故意殺人罪的對象是人,人是活體而不是尸體。既然B已經死亡,就只是尸體,而不是活人。既然沒有活人,就缺乏行為對象。“殺人”這一詞,包含了對象。如果沒有人,也就沒有殺人,沒有殺人的實行行為。而有沒有人,只能根據行為時的具體情形做出判斷。在殺人罪中,對方是生是死是一個重要問題,但周文卻認為并不重要,這是本文難以贊成的。在周文看來,只要一個從外表上看屬于故意殺人的行為,即使射擊的是尸體,也要認定為故意殺人罪。按照這種邏輯,一個外表上屬于故意殺人的行為,即使射擊的只是野獸,也要認定為故意殺人罪。這其實走向了主觀主義的立場。
周文舉的另一例子是:
甲為殺害乙,偷偷對乙開槍,子彈從乙眼前飛過,打死了當時也想殺害乙的丙,客觀上救了乙一命。堅持純粹結果無價值論的學者會認為甲的偶然防衛行為無罪。但自相矛盾的是:采用結果無價值論的學者同時會得出甲對乙而言,具有違法性的結論:因為在開槍殺人的場合,子彈離誰越近,行為對誰就越危險。甲發射的子彈離乙的身體很近,乙有死亡危險,因而甲存在違法性。(第955頁)
在本文看來,結果無價值論的觀點沒有任何矛盾。其一,甲開槍射擊,保護了乙的生命,這是對乙的生命的保護,不成立對乙的犯罪。其二,即使開槍行為對乙的生命有危險,但與客觀上保護了乙的生命相比,法益的衡量也使甲的行為不具有違法性。其三,周文的設定不合理。既然甲射擊的子彈打死了丙,就不能說子彈離乙的身體反而更近。顯而易見的是,既然子彈打死了丙,就表明子彈離乙的身體遠。換言之,即使在行為的當時,甲的行為造成丙死亡的危險大于乙死亡的危險,法益衡量的結果當然是甲的行為沒有違法性。其四,周文顯然是因為“甲為殺害乙”的主觀故意而認定其行為違法。事實上,在現實案件中,并不是先考察行為人的主觀故意,而是先考察客觀事實。當查明丙正在殺害乙,查明甲將正在殺人的丙殺死時,不可能再過問甲當時是否具有殺人故意。其五,甲的行為導致誰死亡,死者當時是否在實施不法侵害行為,這些都是非常重要的事實,而不是不重要的事實。
周文還指出:
基于侵害法益的意思,行為有造成未遂的法益危險(而不是結果無價值論意義上的既遂危險)時,應該處罰。對基于殺意的偶然防衛行為,雖然不存在故意殺人既遂的結果無價值,但是存在殺人未遂的結果無價值(有槍殺無辜者的危險性),對其就應該得出成立故意殺人未遂的結論,不能阻卻違法性。(第955頁)
筆者并不完全反對這段話的前半部分(因為有造成未遂的法益危險時,完全可能成立預備犯)。但是,不能由前半部分推導出后半部分,前半部分更不能證明后半部分的合理性。在偶然防衛的場合,槍殺無辜者的危險與客觀上保護了無辜者的生命相比(如果沒有槍殺無辜者的危險,就不可能保護無辜者的生命),這種危險就必須允許。況且,即使行為不是偶然防衛而是有防衛意識的正當防衛(射殺不法侵害者)時,無辜者的生命同樣存在危險,防衛人也完全能夠認識到這種危險,但同樣不能認定為未遂犯。
(三)關于重視實害還是危險上的差異
周文指出:
結果無價值論在法益實害和法益危險這兩者之間,為了保證所謂的判斷標準明確性、客觀性,通常會更重視實害(既遂結果),而對未遂犯的具體危險,即便并不忽視,也只是從“作為結果的危險”的角度解釋未遂犯的處罰根據。……行為無價值論重視未遂意義上的法益危險,至少將未遂的危險與既遂結果同視,并且從“行為危險”的角度解釋未遂犯的處罰根據。(第955-956頁)
在本文看來,這種歸納并不妥當。其一,結果無價值論所稱的結果,包括具體的危險,而不是僅指實害結果,否則結果無價值論不僅不能解釋未遂犯與中止犯的處罰根據,而且結果無價值論本身也沒有存在的余地。在此意義上說,結果無價值論更重視危險結果。其二,是重視實害還是重視危險,既取決于案件的具體情況,也取決于刑法的規定。在殺人未遂時,結果無價值論當然重視危險結果;在殺人既遂時,結果無價值論就重視實害結果。在刑法處罰危險犯時,結果無價值論重視的是危險結果;在刑法不處罰未遂犯只處罰既遂犯時,結果無價值論便只重視實害結果。其三,行為無價值論也不可能將未遂的危險與既遂結果等同看待,否則不可能解釋未遂犯的處罰為什么輕于既遂犯。其四,僅從行為危險的角度解釋未遂犯的處罰根據,必然導致未遂犯的處罰范圍過于寬泛,也不能說明未遂犯的處罰輕于既遂犯的根據。
其實,如前所述,行為無價值論重視的并不是犯罪行為本身對法益侵害的危險,而是“如果不處罰此行為人的此行為,其他人模仿此行為可能產生的危險”。于是,行為無價值論將他人將來實施此行為可能造成的危險,當作處罰此行為人的此行為的根據。由此可以清楚地看出,不將報應作為限定刑罰的正當化根據,必然導致將行為人作為預防他人犯罪的工具。
(四)關于法益是否與特定構成要件、犯罪形態有關問題上的差異
周文指出:
行為無價值論強調行為與法益侵害的關聯性,從其思維邏輯出發,能夠對構成要件的特定性、犯罪形態的特定性進行界定,將法益和構成要件、犯罪形態連續起來。結果無價值論弱化構成要件的價值,可能籠統地得出因為存在損害,所以具有結果無價值論的結論,至于是什么具體犯罪的結果無價值,在所不論,因此會得出故意殺人、過失致人死亡、故意傷害致死的違法性相同的觀點。(第956頁)
其一,法益侵害討論的是違法性的問題,認為結果無價值論弱化構成要件的價值的說法,恐怕是對結果無價值論的嚴重歪曲。其二,結果無價值論只是認為故意殺人、故意傷害致死與過失致人死亡的違法性相同,因為三者侵害的法益完全相同,而不會認為故意殺人與盜竊的違法性相同。相反,根據行為無價值論的思維邏輯,任何犯罪都是對行為規范的違反,因而任何具體犯罪的行為無價值都是完全相同的,因而違法性是相同的。
在此有必要對周文所舉的假想防衛略作說明。結果無價值者并不主張致人死亡的假想防衛成立故意殺人罪。但可以肯定的是,假想防衛是違法的。致人死亡的假想防衛不成立故意殺人罪,并不是缺乏所謂故意殺人罪的行為無價值,也不是因為缺乏故意殺人罪的結果無價值,只是缺乏殺人的故意。此外,假想防衛也可能是意外事件,但不能因此認為,假想防衛的行為就是合法的。否則,就意味著知情的第三者不能阻止、制止、防止假想防衛行為,這顯然不妥當。
周文還指出:
法益概念還和犯罪形態有關。對于偶然防衛,因為“防衛人”殺死的也是一個罪犯,該結果法律并不反對,可以認定其不具有故意殺人罪既遂的結果無價值,但有未遂的結果無價值;如果同時考慮到“防衛人”具有犯罪意思,沒有防衛意思,有未遂的行為無價值,因此,不能阻卻違法。因此,脫離特定犯罪形態、犯罪階段,也難以討論法益概念和結果無價值論。(第957頁)
在本文看法,這種說法也不成立:其一,既然法律并不反對偶然防衛的結果,就不能認為偶然防衛存在未遂的結果無價值。其二,將防衛人有犯罪意識和無防衛意識,作為未遂犯的行為無價值的根據,充分說明行為無價值論不過是心情無價值而已,與主觀主義只有一紙之隔。其三,根據這種觀點,法律對一個行為造成的好結果是不反對的,但仍然要反對這種行為本身,這也是難以令人贊同的。其四,如果像行為無價值論那樣認為偶然防衛是違法行為,就意味著任何人都可以阻止偶然防衛。然而,如果阻止偶然防衛,就意味著犧牲無辜者的法益,這是明顯不當的。只有像肯定偶然防衛是合法的,才能說明為什么不能阻止偶然防衛,從而保護無辜者的法益。
正如周文所說:“結果無價值論則站在個人主義的立場,強調對國家權力的制約。”(第957頁)在本文看來,這正是當今的中國所需要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