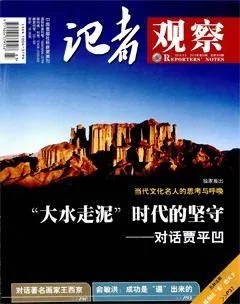“大水走泥”時代的堅守
賈平凹是中國文壇的領軍人物,被譽為“鬼才”。他是我國當代文壇屈指可數的文學大家和文學奇才,是一位當代中國具有叛逆性、富有創造精神、有著廣泛影響的具有世界意義的作家,也是當代中國可以進入中國和世界文學史冊的為數不多的著名文學家之一。前不久,賈平凹歷時4年創作的60萬字新作《古爐》正式出版。面對世事浮華,他始終堅守寫作,他所思所寫的,仍是當今中國的“大多數人”。
近年來,他以每三至四年創作一部長篇小說的速度,陸續完成了《懷念狼》《秦腔》《高興》等作品,不但每部作品都取得較好的市場反響,《秦腔》還于2008年獲得了第七屆茅盾文學獎,正是這部作品把賈平凹推上了文學創作的巔峰。在《秦腔》的授獎辭中這樣寫道一
賈平凹的寫作,既傳統又現代,既寫實又高遠,語言樸拙、憨厚,內心卻波瀾萬丈。他的《秦腔》,以精微的敘事,綿密的細節,成功地仿寫了一種日常生活的本真狀態,并對變化中的鄉土中國所面臨的矛盾、迷茫,做了充滿赤子情懷的記述和解讀。他筆下的喧囂,藏著哀傷,熱鬧的背后,是一片寂寥,或許,堅固的東西都煙消云散之后,我們所面對的只能是巨大的沉默。《秦腔》這聲喟嘆,是當代小說寫作的一記重音,也是這個大時代的生動寫照。
面對紛至沓來的祝福,賈平凹的獲獎感言既獨特又發自肺腑一
第七屆茅盾文學獎能授予我,我感到無比的榮幸!
當獲獎的消息傳來,我說了四個字:天空晴朗!那天的天氣真的很好,心情也好,給屋子里的佛像燒了香,給父母遺像前燒了香,我就去街上吃了一頓羊肉泡饃。
在我的寫作中,《秦腔》是我最想寫的一部書,也是我最費心血的一部書。當年動筆寫這本書時,我不知道要寫的這本書將會是什么命運,但我在家鄉的山上和在我父親的墳頭發誓,我要以此書為故鄉的過去立一塊紀念的碑子。現在,《秦腔》受到肯定,我為我欣慰,也為故鄉欣慰。感謝文學之神的光顧!感謝評委會的厚愛!
獲獎在創作之路上是過河遇到了橋,是口渴遇到了泉,路是遠的,還要往前走。有幸生在中國,有幸中國巨大的變革,現實給我提供了文字的想象,作為一個作家,我會更加努力,將根植于大地上敏感而憂患的心生出翅膀飛翔,能夠再寫出滿意的作品。
記者:文學創作要有精品意識,這是一個常提常新的話題。您每隔三四年就有一部作品問世,并在不斷求變、求新、求精品。請談—下您如何看待作家的精品意識。
賈平凹:作家的精品意識,說到底還是要出好作品。強調要有精品,有精品就代表了一切。這就像我們現在說中國就想起長城,說古時候的小說就想到《紅樓夢》《三國演義》等古典名著。
文藝精品創作要有占領制高點的觀念,起碼要做兩方面工作,一是普及,二是抓重點作品。比如支持文藝創作的資金,只能用來做普及工作。精品不能事先來確定,誰也不知道創作的一定會是精品,只能有成果以后形成一種效應,因此,創作精品不能急功近利。
現在,我們需要寫倫理,寫出人情之美;需要關注國家、民族、人生、命運。這方面我們的作家還寫得不夠好,不夠豐滿。但是,我們要努力達到這個目標。或許—時完不成,但要時刻心向往之,將眼光放大到宇宙,追問人性的、精神的東西。
我認為,大家大作可以起到引導和提供國家綜合文化素質的作用,益于培養公眾道德情操、凈化人格修養、提高文化知識、提升閱讀水準,這些就是作家的時代使命。
記者:您前面談到,寫作要有精品意識,怎樣才能寫出好的作品?
賈平凹:在文學創作中最關鍵的是抓人,這是社會轉型時期的大時代決定的,要產生大的作品,就一定要關注社會和現實。現在文壇上一直關注現實、研究現實的作品還不太多。沒有大作品就是因為理想不足、境界不足。我認為,史詩是一個時代的境遇,也是作家本人的境遇,作家深入生活后,在生活中有體味,這體味又建立在崇高的向往中,個體生活的感受應該和社會大的境遇一致。
我們所處的這個時代,精神是豐富甚至混沌的,這需要我們的目光必須健全,要有自己的信念,堅信有愛、有溫暖、有光明,而不要筆寫偏鋒,只寫黑暗的、丑惡的。要寫出冷漠中的溫暖,堅硬中的柔軟,毀滅中的希望,身處污泥盼有蓮花,心在地獄向往天堂。人不單在物質中活著,更需要活在精神中。精神永遠在天空中星云中江河中大地中,照耀著我們,人類才生生不息。
所以,作家要關注時代關注社會,人的理想要大,成功的作家的思想要想大問題,要有偉大的胸襟。此外,還要在專業上豐富自己,要豐富自己的筆墨。這是作家修養問題。這兩點正是目前我們的作家缺乏的東西,只要具備了這些條件,好的作品就可能問世。
記者:在現今中國文壇,許多和您同時代的作家,在達到一定創作高度后都不再專注于寫作。但您卻是一個例外,仍然保持著旺盛的創作力,并不斷尋求突破,這種現象非常難能可貴,您可以談談這方面的情況嗎?
賈平凹:我們生活在一個“大水走泥”的年代,這個時代是劇變的,價值觀混亂,秩序在離析,規矩在破壞。這樣的年代,混沌而偉大,它為文學提供了豐富的素材和想象的空間。
我認為,作家是社會的觀察者,永遠要觀察這個國家和民族前進的步伐和身影,永遠要敘述這個社會的倫理和生活,更要真實地面對現實和自己的內心,盡一個從事作家職業的中國人在這個大時代里的責任和活著的意義。我是一個普通作家,越發要努力寫作,不敢懈怠和虛妄。
更何況,每個人的情況有所不同,有的耐性強,適合馬拉松;有的擅長沖刺,適合百米。作家一定要有沖動的勁頭,保持自己的寫作狀態,有鮮活的生活積累,在藝術上一直有突破,同時保持好奇心和不服輸的勁頭,強迫自己時常有變化。
舉個例子,我認識一個人,他說自己發現了長壽的秘訣,就是永遠覺得有干不完的事情。這個農民從60歲開始每年訂計劃,訂到了120歲,連120歲那年1月、2月干什么都有詳細計劃。寫作也一樣,只要有宏大的目標放在那兒,人的寫作壽命就會延長。
記者:您的作品一部一部接連問世,普遍得到社會認可。您心目中的好作品是什么樣的?有沒有個大致的標準?
賈平凹:好作品可以是多樣的,我個人覺得如果一個作品出來,不會寫小說的人讀了產生出他也能寫的念頭,而會寫小說的人讀了,又產生這樣的小說他寫不了的念頭,那么這個作品就好了。
記者:您把自己的創作分為幾個階段?您覺得從哪部作品開始,對自己的寫作風格比較自信了?
賈平凹:我在創作中一直追求變化。從30歲寫完《浮躁》之后,便開始不滿意那種寫作方法,覺得那是上世紀50年代以后常用的寫作方法。后來寫《廢都》,也總想著變化,但這些變化都不是劇變,而是慢慢地變。當時經常覺得有一些想法想去實施,但各方面的能力還達不到,于是一直在嘗試。基本上是從《廢都》開始,一直在做這種實驗,到了《秦腔》,再到《古爐》。但還是任何東西寫完以后都覺得應該寫得更好。
記者:您的《商州初錄》《浮躁》《高老莊》《秦腔》等作品,無一不是深入農村后完成的。《秦腔》獲茅盾文學獎,是對您深入生活拒絕浮躁的肯定,請談談《秦腔》的寫作。
賈平凹:茅盾文學獎增加了我寫作的自信和力量,但寫作的目的并不是獲獎,文學的路還長著呢。我寫《秦腔》時,父親去世了,母親還在世。我母親沒文化,但她給我講了很多家族和村子里的事情,這些都成了我寫作的素材。
我對自己的家鄉和生活在那里的鄉親們,一直懷有深厚的感情。雖然在城市里生活了30多年,但是我對自己的定位還是農民。我的本性依舊是農民,如烏雞一樣,是烏在了骨頭里的。所以要用憂郁的目光觀察農村,體味農民的生活。我要用文字給故鄉立碑。
我的《秦腔》中有家鄉生活的點點滴滴,有我自己的影子,也有我的家族印跡。這部書寫的是我的老家,我家族的事情,有刻骨銘心的記憶,是和生命有關的寫作。
近年我寫了不少農村題材的作品,《商州初錄》《浮躁》《高老莊》,這些作品中有我對陜南商州家鄉的真摯情感。我感激著故鄉的水土,我要用文字給故鄉立一個碑,寫作是我生命的另—種形態。在《秦腔》之前,我的《浮躁》《高老莊》《懷念狼》都入圍過茅盾文學獎但沒有評上。《秦腔》獲獎對于我當然是好事,但寫作的目的并不是要獲獎,創作之路遙遠,它只是走渴了,遇到了一眼山泉,過河時遇到了橋,你還得繼續往前走。
《秦腔》我寫了兩年多的時間,其中四易其稿,除了第四次是在原作的基礎上修改,其余三次都是重新展開寫的。我一直用筆寫作,光是抄寫這三遍一百多萬字的作品,就是一件體力活。
記者:談到您和您的作品,不能不提到《廢都》。在沉寂了17年后,您的《廢都》與《浮躁》《秦腔》一起打包為“賈平凹三部曲”,由作家出版社出版發行。能談談《廢都》嗎?
賈平凹:《廢都》基本是上世紀末的那個時候,寫知識分子一些心境的,寫的是一種精神狀態。在當時寫出來,一般人不愿意承認那個東西,誰也不承認,就包括知識分子,他也不承認,是我我也不承認,精神狀態不好的時候,你也不愿意承認那些東西。實際上過一段時間以后,你冷靜下來,就是那么回事情。大家當時都對性的描寫有爭議,關注那方面的事情,引起了爭論。當時寫的還是有些早了,但是文學作品,對社會的感知,對人生的感知,我覺得一定是要具有預見性、前瞻性的那些東西。
我自己的體會是,在我二三十歲的時候,很愛寫作,那時見到什么都有感覺,見到什么都想寫。現在50多歲,回過頭來一看,再遇到年輕時遇到的那些事情,也許還有沖動,但一想也沒什么意思,就不寫了。我一生一直在受爭議,從我一開始寫作就受批評。特別是在我30多歲的時候,是最沒有顧忌的,關鍵是有時寫作我就不管那些東西了,我怎么想就怎么寫,《廢都》就是在這種狀態下產生的。
《廢都》現在能再版,首先說明了社會的進步、社會環境的寬松和文壇關系的回暖。這些年來,社會價值觀已經漸漸發生了改變,人們對文學的認知度提高了,對文學的評價也不僅僅像上世紀90年代初那樣,道德評價、政治評價占主流,而是回到文學本身。
記者:前不久,您的又一部長篇《古爐》出版,能談一談這部小說的寫作嗎?
賈平凹:寫長篇是慢活,既要保持寫作狀態又要把握住節奏。我雜事很多,而在寫《古爐》過程中除過一些必須參與的會議、活動和家事外,我盡量拒絕一些可去可不去的場合,拒絕一些可干可不干的事。這些年里,六七次出國機會我都謝絕了,一些必須去的大活動和會議都帶著稿子,晚上書寫。在西安的日子,每早8點前必須到書房里,寫到中午11點,11點到12點接待來訪人,中午睡一覺,起來寫到下午5點,5點到6點又待客,基本生活規律就是這樣。有時寫順了就特別愉快。寫不順有各種原因,有時就不知道怎么個寫法了,有時故事不知道怎么延續。寫的時候要沒有感覺,作品肯定就沒意思。要是哪天寫得特別有味道,就特來勁。靈感來了嘛,就很愉快,一般一天能改好5000字,特別順當就能寫到8000字。有時就兩三千字,太忙就放下。3年左右短的文章都沒有寫。
每個人創作的習慣不—樣,年輕時寫散文、寫中篇,我一般寫一遍再抄寫一遍就完了。但現在不一樣了,理出一個大概的脈絡,然后會在—個筆記本上打草稿,然后再改一遍,然后再生稿子背面寫一遍,然后再定稿,《古爐》就是在這樣的過程中寫出來的,前后加起來寫了兩百多萬字。這部書用去了三百多支簽名筆。但寫完《古爐》,并沒有被掏空的感覺,還有別的東西等著寫呀,作家就是靠這個吃飯的。
記者:《古爐》的寫作,似乎延續了《秦腔》的寫法,重整體,重細節,以實寫虛,混沌而來,蒼茫而去,在當今文壇上風格別樹一幟,這種寫法是怎么形成的?
賈平凹:這種寫法可能更適合于我吧。我一直寫的是當代生活,行文上又想盡力有中國氣派,這兩方面結合起來其實很難,如國畫很難表現現代生活一樣。這需要作者必須熟悉生活,掌握生活細節,講究節奏,把味道寫足。
散文可以這樣寫,但六七十萬字的長篇寫下來氣息綿長就不容易做到。這套寫法從《廢都》之后就開始了,但那時僅是試驗,過渡到《高老莊》,再過渡到《秦腔》《高興》,直到《古爐》。
人常說“文如其人”,其實只有寫到一定程度了才可能文如其人,又常說“得心應手”,即便心里想到的未必能應了手。《古爐》在構思時是艱難的,寫作時常有一種快感。年輕時寫東西,有激情,銳力外向一些,年齡大了,就可能沉淀了些,想寫的都是在現實生活中真正有了個人生命體會的東西,就不講究技法、起承轉合,只想著家常話,只想著樸素了。古人講的幾個階段,“看山是山看水是水,看山不是山看水不是水,看山還是山看水還是水”,琢磨琢磨,真是這樣,可這樣也真難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