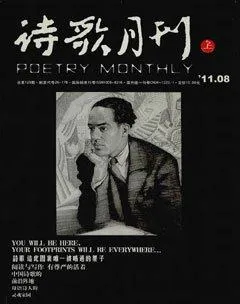懲罰(組詩)
懲罰
二十年多來,他一直不停地寫啊,寫,
他從中得到快樂,同時也感到
深深的失落:生不逢時啊,
詩歌不能讓他出名賺錢,而且耽誤仕途,
更無法藉此博取心儀女子的芳心。
想到這里,靈感瞬間被激活了,
于是他又投入了緊張的造句分行。
現在詩人已不再年輕,當然還不算太老。
他以嫻熟的技巧、超常的毅力
繼續消耗剩余的激情與才華。
他把寫詩當作對時間最嚴厲的懲罰。
心理咨詢
然后,年輕漂亮的心理咨詢師打開筆記本,
努力讓自己平靜下來;她的對面
坐著一個年齡相仿、素不相識的女子,兩人中間
隔著茶杯,桌面上的靜物:
一盆鮮花、一本臺歷。
每次接待來訪者,她總是這樣,
屏息靜聽、輕聲細語,并認真記錄在案。
從不使用簡單的肯定句或者否定句。
但這時,她的手微顫著;
她對自己提出了一連串無法回答的疑問。
有時候悲傷也像甲流一樣會傳染,
當它帶著一股淡淡的花香。
她從一張憔悴的臉上理解了
另一個人的痛苦與無奈:誰在流淚?
誰能讓一顆柔軟的心依然快樂,當它小心翼翼
卸下了黃金盔甲,而永無傷害?
而她經歷了這場未曾經歷過的危情。
哭喪
哭喪婆穿素衣,纏小腳,
這時她開始高一聲、低一聲地哭。
沒有眼淚的哭,更像婺劇里的唱腔。
不唱給生者,只對死者傾訴。
第一次哭喪眼淚就流光了——
她癱坐在那兒,雙手有節奏地拍打著
剛剛合蓋的木棺;靈臺燭光搖曳,
她不停地哭,哭她自己。
那一年,她兒子因病早逝。
村里的長壽老人死去。那是喜喪。
最悲傷的人,是靜靜地躺在
棺槨中的死者;被哭喪婆深深打動的人,
是那個頭戴鴨舌帽的民俗學專家。
刻有名字的陶瓷碗
春節回老家,我又捧起了這口
舊陶瓷碗:碗沿有幾處小缺損,
碗底刻有祖父的名字。那黑色字跡
顯然不太工整,但依然清晰——
說得不錯,藝術之美源于生活之真——
盛飯的時候,我讀到它;吃完飯,
我又讀到它。祖父已離世多年,
記得當年,他拿起小鐵錘、細鑿子
在碗底一筆一劃刻下自己的名字,
像一個小心謹慎的民間藝人;
然后涂上墨汁著色,用抹布把碗擦干。
那時,我面黃肌瘦還是個懵懂少年。
兔年寫下的第一首詩
除夕夜,我面對電腦寫一首詩,
但是爆竹聲鋪天蓋地,擾亂了我的思路。
我被迫中斷寫作,暫時給這首詩
留一截兔子尾巴。不想看春晚,
書也看不進去,那就翻讀手機短信,
順便簡單回復。都是一些異口同聲的祝詞,
都是一些熱情洋溢的客套。
是的,生活照舊,看你如何翻新。
現在我44歲,再過一分鐘,我就45歲了。
再過二十年,我還能讀詩、寫詩嗎?
還會有人記得我的詩嗎?
——誰知道,管它呢。
我發現樓道那盞聲控感應燈出故障了,
它遲遲不肯熄滅,在喧鬧和狂歡平息之后;
這只天生蠢才的大傻眼。
在綠緣花木場
南方的春天一概濕氣偏重,以致于
給我的憂郁增加了水分與重量
最高的是天上的陰云,最低的
是地上的枯葉,我與樹
并立,保持適當的審美距離
春天還在繼續蔓延:從合歡、含笑、喜樹
三角楓、六月雪、八角刺,一直鋪展到每一片樹葉
并且投下冬天殘存的灰影
如果春天可以縮小,就縮小到一只鮮花盆景
讓蜜蜂在季節的案頭陷入迷失
在綠緣花木場,我看到,最堅硬的是鐵樹
最虛弱的是風,潮濕的風
吹進我空蕩蕩的體內
不可避免地,被我瘦瘦地擋了一下
我整了整衣角,像一棵患上風濕性關節炎的香樟
裹緊自己的年輪
一個內在的人
他習慣于低著頭走路,躺下來思考。
當他推開老百姓藥房的玻璃門,一個人
回到擁擠的大街,你猜那手里拎的是什么?
他近乎抽象,而那移動的背影
是具象的:冷風中,淺灰色的風衣
緊裹著一顆孤獨的心。
他習慣于以旁觀者身份介入現世生活。
夾在街頭鬧劇現場的人群中間
努力使自己保持中立。
他想:與其在公園里籌備感情投資項目,
不如在市中心規劃一座清冷的寺廟。
他想到的總是比看到的多。
他能做什么?最好做自己的忠實保鏢。
別叫他表態,他寧可成為感情豐富的大啞巴。
不是不得已,而是不愿意。
臣服于內心與自我。
他出生卑微,時運不濟,其性格
仍然完整:三分自卑,加七分自尊。
他從大街拐進小巷,手里拎著東西。
你看見了他,他也看見了你,
當他轉身。他是他自己,而
你是誰?為何尾隨著他?愛著他?
在古樟樹下
1
我不禁為某種奇異的力量所吸引
它來自于古樟樹那龐大樹冠
粗壯而挺拔的樹干
裸露地面如同龍爪一般的根以及
沿著樹干跋涉在懸崖峭壁與深壑險谷之中
緩緩而上的蟻隊
2
古樟樹沉默著,每一片深綠的葉子
都是自由和獨立的存在
我聽見鳥類在茂密的枝葉叢中婉轉啼叫
仿佛清涼的露珠滴落
仿佛快樂思想者
在沉思的間隙吹響了春天的口哨
3
小鳥在空中筑巢,松鼠在枝頭跳躍
樹葉微微轉動,遺漏點點光斑
我相信,任何事物的內心都是愉悅的,且不可言說
包括這棵返老還童的古樟樹
盡管它主干早已中空
4
坐在古樟樹下,讓我多歇息一會兒
讓我放低姿態默默地注視
一只螞蟻、一株小草、一片在風中
旋轉而下的落葉
獨享那份靜美,讓我得到光陰的恩寵與庇護
讓孤單的影子被巨大的濃蔭吞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