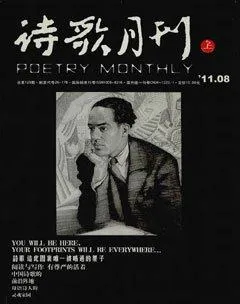許敏:手握青草在宣告的詩人
中國的鄉土詩寫到許敏這個份上,依我看已是相當成熟了:
泥土的心跳藏在螞蟻細微的呼吸里
一條路的韁繩牽出一座村莊
牽出塵世廣闊的牧場
——《吹送2》
許敏,似乎在登高望遠,看到自己的村莊所處的地理位置,還有更廣闊的牧場,也由一條路的韁繩牽引而出。詩人許敏深深地知曉鄉土和一條路的因果關系,從表面上看,有點像人文地理雜志上的解說詞,但是作為一種詩人的自覺,它涉及詩人心靈深處最為靜謐的關于村莊起源的謳歌。
詩壇目前還沒有真正理解從一個地理方位的角度來寫鄉土將意味著什么,我們不僅看到許敏的鄉土詩歌寫得很大氣,大氣還蘊藏著細微,甚至包括螞蟻的心跳。
許敏是位善于寫螞蟻心跳的鄉間詩人智者,他在觀察螞蟻馱著巨大的米粒從灶臺上路過的時刻,似乎是螞蟻的瞳仁在放大,許敏逐漸看到了鄉間景觀里的所有親人,對于鄉間親人的捕捉以及塑像般情態的描寫,這也使詩人成為一個頗為懂得心靈透視的畫人。
風從長城以北吹來
走累了也不肯在許樓村的樹杈上
小歇一會兒外婆邁著小腳
去灶間煮雞蛋謹慎地取出花瓷大碗
往里面加一勺黑乎乎的紅糖
母親已經不那么驚慌了
這是她的第三次生育
——《1976年的大雪》
陰雨天。火柴皮濕了。
母親擦了兩根,沒擦著
就心疼得不忍去擦第三根了……
她去鄰居家引火,攥緊一把柴禾
又從柴堆里抽出一把,以作酬謝。
看著母親匆匆的背影
轉過墻角,那么低矮
像一朵由淚水構成的暗黑的火焰。
——《簡單的一天》
最為感人的是許敏的外婆在灶臺前忙碌的身影,外婆邁著小腳去灶間煮雞蛋,謹慎地取出花瓷大碗,往里面加一勺黑乎乎的紅糖,許敏的童年是在紅糖尚很金貴的年代度過的,他的目光自然也離不開灶臺,灶臺依舊,后來換成了母親的神態,許敏敘述道,母親擦了兩根火柴,都沒有點著柴禾,便舍不得再擦第三根,她于是去鄰居家借火,順便扯一把柴禾作為對鄰居的酬謝。許敏母親的節儉和寬厚自然已經歷歷在目,但從詩的取向來看,這個關于母親借火素材的深意卻沒有被敏銳地表現,素材挖掘當在母親借火的過程中,而不是在美好素材后面加上議論的絮語。這一位母親到鄰居家不是借火柴,而是到鄰居家灶臺里引火,“引火”也想到了酬謝,一個中國鄉間母親的心靈思索暫時還沒有有力地展現出來,但許敏的詩已接近禪機。
許敏鄉土詩歌感人至深的奧秘的確尚未得到明確揭示,我讀他的詩,也絕不輕易放過他的詩歌字里行間任何閃光,因為他的語言在各處閃光,如同蟋蟀在各處蹦跳,有時語言的閃光蒙上了口語的懈怠,但我仍然不把它放過。
格外地要說一下,當讀到許敏的《夜曲》里這么一句:“三間茅草屋,有了一些松動”,心便被揪緊了,在另外一首《燕子又回來了》,許敏寫道:
牧牛,拔草,除蟲,擔糞,然后寫下炊煙
然后松動——松果樣墜落
這兩處出現的“松動”,可謂是詩意在無意間迸發的精品,“松動”,有時代表著茅屋可能倒塌,有時卻代表著緊張勞動后,更為緊張地松果般墜落,許敏在暗示著對于既往景觀的一種總結,“松動”一詞鬼使神差地用上,關鍵是,當發現了茅屋和牧牛生活在咔咔作響時,真正的松動、闡發其實則剛剛開始,是的,許敏當加固業已松動的既往生活。
許敏鄉土詩歌語言的精美和時而滑過的恰如其分的“口語”,準確,實際上不用我多說,讀者即可享受到它的好處,并感受詩意盛宴,問題是,許敏拋棄了心靈的傲慢之后,他長久地沉浸在鄉村的景觀中,他可能要面臨著什么,另外,許敏的詩從客觀上,他究竟向詩壇貢獻了什么?
多年前,文學界曾有過《白鹿原》、《平凡的世界》那類關于世代鄉村的小說,鄉村在滄桑變化中給人造成了心靈矛盾和渴求至今仍沒有答案,“鄉間”是一個哲學命題,是一個非有大智慧才可涉入的近在咫尺的、欲說還休的永恒話題。
鄉村變遷的時尚主題在許敏情愫中,并沒有表現出過分的焦躁和不安,他先是在合肥郊區父親的糧站工作過了些時日,后來他當上了警察,派出所就在一座“公廁”的旁邊,這個農村青年當時并不是在戲弄派出所,而是表達良好的平凡心態,這就是警察也融于鄉間,在中國,任何新鮮職業都將染上農村的土氣和方言,鄉間,它將融化一切,合肥的鄉間甚至比許敏所鐘情的白雪和黑夜都更加廣闊,鄉間令黑夜置于鄉間,而不是包圍著它。
許敏的詩與鄉土水乳交融般的契合,讓許敏的詩歌少走了不少彎路,避免了流行的浮躁,這幾乎是土里土氣訂下了許敏詩歌心路歷程的終身。
詩歌貴在沉浸,沉浸中看到的合肥鄉間的山水圖,許敏是這樣描寫的:
像驅逐盲人眼中持久的白霧和黑夜,
大地剛剛側身,壓扁的乳房——山巒
有寂靜之美,湖水與之并排躺下。
——《孤島》
中國文化的奧秘在合肥山水間被許敏無意揭示著,中國山水圖,最講究令我們夢回的合肥鄉間在整個圖畫里它究竟在什么位置,鄉間是怎么形成。但是,往往形勢是這樣,中國山水景觀令人感到親切的描畫并不多見,在離我們最近的鄉土之外,如果繼續透視,我們親切的山水河流,并不能流得很遠,特別是文人畫,把親切的山水畫成了陌生的山水,令人感到這是孤獨的山水。同樣,在詩歌中,我們尚沒有讀到真正地面向鄉間的鄉土詩歌,因為鄉間到底是陌生的,還是親切的呢?鄉間到底有多大,它的疆域在哪里?它是無限還是有限?
許敏,至少在思考這些問題。講到許敏對于鄉土詩歌的確有貢獻,我是有把握的。
暮色依舊,燕子又回來了
銜著濕泥,沿著燈火的方向回家
野地里,你多次拾到腐朽的棺木
那是大地的胃液尚未將逝者的亡靈消化
——《燕子又回來了》
這就是許敏對于亡靈的貢獻,他將生者與死者連為一體,我相信這絕不是偶然的,順便也說一下,拾到了棺木,怎樣精確地表達,可能將預示著詩歌經典的誕生,但許敏確與經典詩歌擦肩而過。不要輕率地進入大地的胃液當中,不要輕易讓棺木腐朽,讓棺木進入虛空,那是文人的情感,農民不是這樣想問題的,棺木實則就是一種建筑,后人看到朽木,是后人看到了本不該看到的形態,棺木沒有腐朽,它在大地的胃液中繼續形成宏偉的建筑,鄉間也就是中國人永恒的殿堂,我們當依從許敏的思路,我們當活在鄉間的宏偉墳墓,而不是消亡,變得無影無蹤。
鄉土詩歌寫作寫到靈魂出竅的時候,這將帶有人文地理的特征,許敏肯定有這么一個體會。許敏早期所接觸的外國詩,那些帶有銅質的地理方位般的詩歌取向,也深深地感染著他,外國詩為什么能標出鄉間與周圍景觀的關系呢?這不是單純的因果關系,不是單純的顯示大氣磅礴而為,這是因為,在基督教的世界,鄉間之外的景觀是庇護鄉村的,因此在基督教世界里,鄉村再廣闊,詩人均不感到陌生。咱們中國的情況略有不同,中國的鄉村走不了十里,我們就感到陌生,如同方言,我們走不了十里,就語言全變。許敏心情大致也會在陌生和親切之間徘徊。
誠懇地說,一條路牽引出廣闊的牧場,是詩人心靈所愛所至,許敏沒有刻意地去指責大路對于鄉間的陌生感,這非常珍貴地指示出詩人鄉間疆域的寬闊和無限,但我們的確也不放棄這里面的哲思。
我記得,汪曾祺小說曾經寫過,在日本鬼子轟炸重慶大學的“間隙”,有男女學生偷著跑回校舍打開水,并趁機談戀愛,汪曾祺小說無意地告知了好像日本人的敵機在呵護青年學生的浪漫生活。滄桑巨變對于合肥鄉村的侵蝕,卻讓許敏的詩在時光的“間隙”中顯得更加欣欣向榮。
還有一位小姑娘來到井邊打水,裝滿水桶的水清澈照人,剛剛在井臺上放了一會,便有牽牛花爬過來,爬到水桶上喝水,并在此生根,這個美一點的例證,與嚴峻的現實道理,異曲同工,后者因為美,我們忘卻了真實的嚴峻。牽牛花準備生根的地方,恰恰是小姑娘準備拎桶就走,扯去花朵的“間隙”,而牽牛花全然不知。
還有許敏的詩也寫到:
蟲聲,細柔了下來。被月光碰碎之前,
它們是锃亮的黃銅、絢爛的絲織品,
是一群穿花裙子的小姑娘擠在槐樹下躲雨。
——《憶桂花》
如同牽牛花一般的寓意,這個“躲雨”的鏡像,在一群小姑娘全然不覺地完成。趁著蟲聲未被月光碰碎之前。許敏的詩雖說詩意承接尚不十分精確,但他深曉,一個“碰碎之前”,足見其詩意有其匠心,當然,也可能這是筆意和朦朧的深邃所致。
這樣看來,許敏的詩已經概括著中國鄉土詩發展至今的全部成就和全部疑點和難點。中國鄉土詩和許敏的詩,其情感的真摯和語言狀景的透徹早已不成問題。許敏和許多鄉土詩人一樣也面臨著他們家鄉究竟有多大的遁世挑戰和詰問。
有一句解說詞,我記不清什么時候聽到的了,但仍記得:“當洪水將鳥蛋沖向下游,這些鳥蛋將開始獨立地生活了。”許敏的詩也如同奇異的鳥蛋,被洪水沖到下游才會真正開始詩歌的獨立寫作。
往往好的句子,我們想拼命思考,它到底好在何處,因為一般情形是這樣,生命只有真正誕生,才會走向獨立,生命尚在孵化,怎么就被沖走了呢?我們現在的思維習慣是,我們能很快地發現生命的悲劇,因為我們的家鄉疆域過于狹小。
我們欣喜地認識到,許敏的鄉土疆域正逐漸地擴展,他從一個個碎片似的美輪美奐中脫穎而出。他說,他越來越感到合肥民俗里有很多人生的秘密,它們是民間耐讀的精妙部分。
在中國,詩人能說出這樣的關于民俗的感悟是很不容易的,譬如我,至今對合肥民俗知之甚少。詩人由碎片似鏡像的觀察和回憶,走向融入合肥民俗的日常人情世故中。這是一個值得珍視、稱道的巨大轉變。我相信,許敏的確率先實踐著一種詩性的大轉變,心靈中的家鄉疆域在許敏平和真誠的道白中,他的心靈將變成無限。因為合肥的民俗在與其他民俗的共融中是否能獨占鰲頭,還有待許敏使之能夠生花。
風一次次地把目光,刮到樹上,碰出聲響
村莊,鳥巢一樣。樹頂的星群,像一個內心
緊抱信仰的人開始平靜下來。那些白日里
穿越林梢的麻雀,斑鳩,灰喜鵲,白頭翁
它們都到哪里去歇息,它們把夜晚交給了螢火蟲
一粒,兩粒,三粒……有著這么美而易親近的距離
仿佛漂亮的卵石露出水面,所有的燈火都黯淡下去
而我是村莊唯一的孩子,杉樹一樣舉著自己
手握青草,持續地高燒,把夜晚看成是一垛堆高的
白雪
——《獻詩》
這不是傲慢,也不是鄉間孩子的偏見,這是許敏為中國新詩活著而選擇的道路,我預祝許敏成功。
(梁小斌:朦朧詩派代表詩人之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