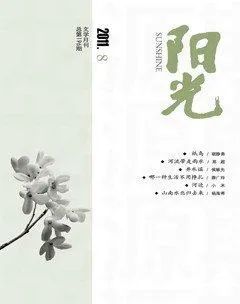紙鳥
到底是國慶喜氣多。那一隊花車剛過去,這又過來一溜,打頭的都是黑亮的加長勞斯萊斯,車前那碩大的紅雙喜字和纏繞車身的多色鮮花洋溢著濃濃的婚慶氣息。一些行人饒有興味地駐足而望。
衛家姝兀自走自己的路,她只是不經意地瞥瞥那花車,心卻像被什么小細蟲給輕輕蜇了一下。她也曾坐過這樣一輛引人注目的花車。一晃,十年了。湮沒在十年時光里的瑣屑的家事公事,是沒法細數的,如同秋季那漫天的黃葉不可細數一樣,索性讓它們飄散在記憶的泥潭。
人長著雙眼睛,從來都是往前看的。身后的事只有胡思亂想。她在宜城熬日子的時候,恨不得自己長雙翅膀,想飛哪里就飛哪里。不想來到北京,依然是要熬日子。如果說有什么不同,以前是一潭死水,現在這潭水在泛了短暫的漣漪之后,開始有結薄冰的跡象。至少在宜城,她衣食無憂,她本有屬于自己的小窩。在京城,她猶如無根的浮萍,飄來浮去的。家里人都希望她不要在外飄。昨天哥哥還特意打來電話,告訴她宜城日報社打算創辦晚報的事,她要是想回去,正好是個機會。
她是無論如何都不愿回日報社的。五年前社里人事大變動,賞識她的老社長退了,她最不喜歡的孫某當了一把手,在所謂的“競聘”中,她從文藝副刊的副主編淪為一個可有可無的小編輯,竟讓她干些寄送之類的雜事。原先她當副主編的時候,儼然也是個人物。求她發稿件的作者很多,她常被人衛老師長衛老師短地客客氣氣地叫著,時不時有人給她送東西,請吃飯。她在市日報社里說話多少也有分量,就算她在社長和總編跟前發點兒小牢騷,社長和總編也還能買她的賬。突然間什么都不是了。她有種繁花落盡的蕭條感,又極大的忿忿不平。好歹她是中文系科班出身,還在有名雜志上發表過好幾個中篇小說、若干散文和隨筆。在小小的宜城,她算得上一個小有名氣的才女。她這棵本來長得很蔥茂的果樹,落在這個旮旯地,開不了花也結不了果,遲早會枯萎的。
逃離的念頭自然而起。娘家人都勸她慎重,畢竟而立之年了,出外闖什么闖啊?該弄個孩子出來。她不免有點兒猶豫,跟黃千葉商量,黃千葉不置可否。男人那甕里死鱉的樣子刺激了她本已脆弱的神經,她索性狠了心。
那個沒有風日的秋暮,她獨自登上北上的列車,從此踏入深不可測的京都河流。
奔走了兩三周,她總算跟一個叫《今日風》的娛樂雜志扯上了關系。
《今日風》雜志外表花哨,實質上內瓤空洞,尤其愛揪明星們的小辮子,給明星繡點花邊新聞,傳播傳播緋聞。《今日風》主要就是靠這些在社會上賺了點名氣。有時候衛家姝翻翻雜志,看到自己采寫的那些東西,感覺自己真是無聊。要說賺錢,在這里賺得也不多,還時常受氣。
剛進雜志社那陣,衛家姝背著包,挎著個攝像機,到處追訪那些光彩照人的明星,委實是件新鮮的事。時間長了,她對明星也漸漸沒了興趣,明星頭上的光環也就成了鐵環。就她采訪過的那些明星,沒有一個不故作姿態,不喜歡別人吹捧的。z尤其如此。
z是近幾年活躍在影視歌舞臺上的三棲明星。這位明星像轉動的陀螺一樣繁忙,而且緋聞不斷。衛家姝受命對其進行采訪,追尋她追了兩三周,也沒找到她。下半月版《今日風》的“今日主星”欄目敲定要上她,老板催命鬼一樣向衛家姝催要稿子。
衛家姝好不容易打聽到z正在西雙版納休閑,火速趕到那兒,找到z下榻的賓館。人家連面都不露一下,只讓長頭發經紀先生出來傳個話,說近期不接受任何媒體采訪。長頭發還黑著臉斥責衛家姝:你們這幫無聊的娛記,成天不干正經事,凈想著造一些無中生有的破事,壞人家的名譽!沒等衛家姝開腔辯解,長頭發一轉屁股,眨眼間就沒影了。
沒辦法,衛家姝只好打電話向老板征詢。老板語氣強硬,你不能自己想辦法?衛家姝終究想不出什么辦法來,只得悻悻而歸。
見衛家姝無功而返,老板十分惱火:你,怎么回事?!下半月的版樣早已排出來了,就缺你這篇稿子,今明兩天你必須交上來!衛家姝說,采訪不成,沒法寫,我拿什么交呢?老板擲地有聲,就是編,你也得給我編出來!衛家姝說,我要是編不出來呢?
老板冷笑,你是個大才女,怎么會編不出來呢?順手將桌上的《京都時報》《京都晚報》(上面都有衛家姝寫的豆腐塊)往衛家姝面前一扔,說你編的東西滿天飛,你成天忙著干私活,連自己來這里干什么都沒搞清楚!
衛家姝的臉繃了繃,我已經盡力了!
老板恨恨地說,盡力?你什么時候盡力過?還沒干幾天,就想著要給自己轉正加薪。工資少發一點兒,就上門來討說法。采訪任務沒完成,你還覺得很有理是不是?你這種人我們沒法再遷就了!你不想干現在就給我走人!
衛家姝怔了怔,旋即也橫眉擲了一句:走人就走人!在你這里我也受夠了!然后就昂首挺胸地走了出去。
回到編輯室,她將自己的辦公桌收拾了一下,屬于她的東西不多,一個手袋就能裝得下。也才剛剛月初,不存在薪水扯皮的問題。
她強作鎮靜地跟自己的同行作了簡短的告別,將小皮包往身上一挎,拎起手袋,離開了那個待了近兩年的地方。
穿過長長的過道,坐電梯下到底層,出寫字樓大廳,正午的陽光白得有點兒耀眼。衛家姝說不出自己是怎樣的心情。她下意識地轉過身,朝這個三十六層的高檔寫字樓看了兩眼,腦子里驀然閃現出幾天前自己做的兇夢。
她夢見自己站在寫字樓的頂上,像一片樹葉飄落下來。她落到地上時,冷冰冰的混凝土路面上出現了一些殷紅的大蝴蝶。她似乎還夢見黃千葉驚惶地跑過來,黃千葉手里舉著的白紙牌掉落下來,那紙牌上寫著一行鮮紅的大字:老婆,外面的世界很精彩也很無奈。還是跟我回家吧。
她本是一個心高氣傲的人,現在只感覺自己如同一只紙鳥,想飛卻飛不了。當初她來京時,父親就說她將女人經念歪了。放著穩定的工作不要,放著清閑的日子不過,放著自己的老公不管,像紙鳥一樣飄飛,飄飛到最后,只會成骨架子的。
眼前的一切都被淚擋了視線,衛家姝掏紙巾狠命地揩了揩眼。
回到租住地沒多會兒,家里的電話就來了。母親嘆氣說,家姝呀,你還是回來吧。你看你跟黃千葉兩個人,夫妻不像夫妻,時間長了,么樣行呃?
你曉不曉得?這小子快管不住自己的褲襠了!父親語氣忿忿的。
衛家姝像是挨了一記悶棍,說不出話來。
父親提了聲調:你在聽嗎?我問你,你到底還要不要這個家?!
衛家姝聲音發著顫,我以后再打電話,掛了啊?
那之后接連兩天,她賴在床上,反復爬梳自己的生活。這兩年她在京城混,臘月底才回家過個年,平素都是打打電話。讓黃千葉為她獨守空房,不對外搞開放,很難啊!這個市長的秘書,向來在場面上迎來送往的。她長期不在他身邊,他搞什么樣的逢迎,那還用說嗎?唉,認了,不認又能怎么樣呢?
三個月后,黃千葉正式提出離婚。衛家姝很配合地答應黃千葉的要求,請假回了趟宜城,跟黃千葉一起將離婚手續辦了。雙方家長的干涉不起任何作用。沒有孩子拖累,財產對半分割,他們的婚離得相當干脆。
倆人從當初辦結婚證的地方換了離婚證,同了一段必須要同的路,到十字路頭,該分手了。衛家姝低頭看了一眼自己的腳尖,捋了捋額前被風吹亂的發絲,準備邁步先走。黃千葉從褲兜里抽出一只手來,他原本是想跟衛家姝握一握手的,不知怎么的,他的手很不自然地朝自己的臉上抹去。他自嘲地笑了一下,低聲說,家姝,對不起。
衛家姝盯著黃千葉那張并不生動的國字臉,冷冷回敬:到這個份兒上,提這個還有什么意思?她轉過身,疾步走了。再不走,她怕管不住自己的淚腺。她不想再看見黃千葉,不想看見他還穿著當年結婚時穿的西裝和皮鞋,西裝領子都有了褶皺,皮鞋上也有了劃痕,這些東西都是當年自己在商場幫他挑的。她覺得黃千葉真是虛偽,他故意在向自己顯擺他的歉疚,他歉疚什么?歉疚拋棄自己?這年頭,男女散伙談不上誰拋棄誰的問題。衛家姝心中清楚,這個婚現在不離,將來也是要離的。現在黃千葉先提出離婚,比將來自己提出來要好,省得別人胡亂猜疑,以為她在外面的花花世界中混花了腸子。
回到娘家,衛家姝像往常一樣幫父母做做家務,好像什么事也沒有發生。父母長吁短嘆,仿佛離婚的不是女兒而是他們。倒是哥嫂看得開,說離了就離了,有合適的再找一個。
衛家姝在家只待了一天,翌日上午,就動身上北京。她已橫了心要在京城混到底。
不久,她在一家私營圖書公司找了份編輯的工作。同時也籌劃著有朝一日在京城買個房,哪怕小一點兒都沒關系。城區的房子買不起,就買通州那樣的郊區的。沒料到后來房價跟喝酒喝迷糊了的醉漢一樣,向上瞎躥,躥得人心腫大。她不得不更加鉚足勁向前奔。給別人打工的同時,她更是留著心思寫自己的稿子。沒有整塊的時間寫大部頭長文,她就專營豆腐塊。豆腐塊容易發表啊,現在各種報刊雜志幾乎都有她的一席之地。隔三差五也能收到稿酬單,稿酬不多,一般是幾十元到百元不等,衛家姝有些知足,若這樣細水長流下去,也是不差的。
感情方面也是留著心。雖然離婚之初不想再找人,一場急性闌尾炎又讓她改變了想法。那次她一個人在醫院待了一周,看著周圍的病人都有親友照料著,凄涼感油然而生。她現在還沒老,還能自個兒撐著,要是將來老了,撐不動了呢?想喝一口水都得自己弄啊。她想她不但要找人,而且還要終日廝守著。
前前后后也結識過幾個男人,還跟其中的某位有過瓜葛,但最終都不了了之。那些男人,照她的感覺,做情人還可以,一提到做老公的檔次上,都是不夠格的。
最近經人介紹,她又結識了—個叫錢古的男人。
錢古在一家資訊報做“車記”(專門在汽車方面做文章的記者)。據她觀察,這錢古是個好游玩之徒,好浪漫,而且是個抓錢不走的主兒。有錢他盡情消費。錢消費完了,他就跟女人伸手。
少女時期,衛家姝覺得這類男人爽直,也是抱著一種欣賞的眼光去看的。跟著黃千葉在婚姻的城堡中轉了一遭之后,又有過跟幾位男人周旋的經歷,她對男人逐漸提高了警惕。她覺得居家過日子,男人還是實在一點兒好。她三十五歲了,是被納入垃圾股的那一類女人,委實沒有多少資本跟男人玩浪漫。
錢古對衛家姝卻頗有興趣,時不時地打電話約衛家姝出去喝茶。衛家姝總是找借口推脫。錢古不死心,索性找上門來。
錢古跟黃千葉真是出奇地相像。當年黃千葉看中衛家姝,不顧這朵花周圍飛舞著多少蜂蝶,他窮追猛打,將衛家姝追到手方罷休。現在錢古也是,大有糾纏到底的意思。衛家姝心生厭惡,這種淺薄男人是不解女人心的深淺,他將女人看成跟他一樣,寂寞就找伴兒消遣消遣。
他一進門,連該有的客套都免了,欲直奔主題。
衛家姝費力地從錢古懷里掙脫出來,忿忿地打開門,示意錢古離開。錢古牽牽自己的西服衣領,一臉的不以為然,你為什么這樣正經?衛家姝冷冷地盯著他,你為什么這樣不正經?
不正經?錢古訕笑起來,喜歡你啊。
趕走錢古,衛家姝靠門站了許久,目光落在對面墻上的一幅春景圖上,那上面有一朵心形的花,兩只顏色光艷的彩蝶在花上翩翩飛舞。那是前幾天她的一位搞美編的姐兒來玩時隨手畫的,畫得多少有點兒毛糙。衛家姝不大喜歡這幅畫,眼下她卻對花和蝴蝶有些上心。
她無由頭地在客廳里不停地來回走著圈,仿佛丟失了一件重要的物件。在她的腦子里,鬼使神差地盤桓著錢古和黃千葉,只是錢古的影像很快被黃千葉的給覆蓋了。
轉眼,又是一個國慶節,衛家姝跟兩個文友相約著去奧林匹克公園轉轉。在“鳥巢”前熙熙攘攘的人流中,她居然跟黃千葉相撞。
黃千葉目前是一個囡囡的爸爸。爸爸這個身份早在他和衛家姝離婚之前就差不多確定了。當情人告知她懷了他的種,倚在床頭嚶嚶地哭個不停,說一定要生下這個孩子,一定要他負責任。這就容不得他多想,在懷孕的情人與外出闖江湖的老婆之間,他只能選擇情人。
這男人,說來也有點兒奇怪,情人變成老婆,不但原有的那股自由散漫勁兒磨損了,還被調馴得服服帖帖。這個后來的老婆遠遠沒有原配的性情好,動不動就耍小性子,特別是生了孩子之后,更是有了支使男人的法寶。
黃千葉每天一下班,總是第一時間火速往家趕,途中還要忙著日用品的采購。女人坐月子期間黃家老太過來幫忙,幫了三個星期,實在忍受不了新媳婦的脾性,罵兒子眼睛長歪了,好的媳婦不好好攏著,要這么個沒心沒肺的半吊子東西!老太出了怨氣,一抬腳,走了。
隨后黃千葉找了個小保姆,一個十七八歲,模樣清秀的鄉下女孩。女孩做事很上心,讓黃千葉很滿意。黃千葉偶爾給女孩買點兒小禮品,不想引起女人的多疑。女人惟恐黃千葉跟人家小保姆來那么一腿,硬是將女孩給辭掉了。在不到半年的時間里,黃家走馬燈般地換了五六個保姆。后來女人干脆堅持不要保姆,說家里住外人,總別扭。她自己又不愿干家務。黃千葉沒辦法,只得親自動手,洗衣,拖地,做飯,洗碗,家里的活兒幾乎樣樣都要干。他成了名副其實的婦男。常常該干的家務他剛干完,休假在家的女人嬌稱自己累死了,將女兒往他懷里一塞,自己躺到沙發上看電視去了。
黃千葉自然心煩,又不能發作。只要他稍有點兒牢騷,女人粉嫩的臉便如同澆了層辣椒油,怎么了?你以為你這爸爸是好當的!你以為你這個老公是好當的!黃千葉要是再吱聲,那層辣椒油會辣得更厲害:黃千葉,你不要沒有良心,我一個黃花閨女嫁給你這個二鍋頭,已經很虧了!你做點兒家務,帶帶孩子,還屁話連天的!當初你跟我的那些表白,都當屁放了嗎?
女人生了孩子之后身體就逐漸走了樣,原來那小蜂腰肥得跟個蠶秧子似的,她成天變著法子減肥,恨不能把減肥藥當飯吃,也沒見有多大效果。
最讓黃千葉不滿的,是女人帶孩子不太上心。冷不丁孩子就給弄病了,三天兩頭上醫院。黃千葉要是說她兩句,她那火氣就噴上來了,我都煩死了!我愿意孩子病嗎?!你那么會帶孩子,那你帶呀!
黃千葉不免念起前妻衛家姝的諸多好處。還是母親嘮叨得地道,夫妻還是原配的好,什么樣的腳得穿什么樣的鞋。鞋瞎換,怎么都會卡腳!要是自己還是跟衛家姝在一起,就不會是現在這番樣子。如今怎么說都有點兒晚了,畢竟有了個囡囡。對于女兒,黃千葉是極其疼愛的,要是沒這孩子,恐怕離婚的決心他都下了。
大約在跟情人結婚后不久,黃千葉的心里又裝了衛家姝。他上過幾次京城,每次都想著看看前妻,卻又終究沒有勇氣去找她。
這次國慶節單位組織游京城,他將女人孩子也帶上了,沒想到跟衛家姝照上了面。
兩個人相視無言。衛家姝竭力平靜地沖黃千葉笑了笑。黃千葉又激動又尷尬,推推眼鏡,不知該說點兒什么好。
黃千葉!身后傳來尖脆的一聲喊。
黃千葉沖衛家姝抿嘴點頭,轉身走了。
幾步之外,一個棉花團般的女人對賴在地上哼哼唧唧的小女孩發脾氣。黃千葉過去哄孩子。女人還余怒未消,你夠可以的!買瓶水也這么慢!黃千葉沖她瞪了眼,嚷什么?將兜里的一瓶礦泉水掏出來扔給她。女人接了瓶子,揚起臉,說你瞪什么眼!還了不得呢!
衛家姝站在那里看著,她想黃千葉眼光真不行,挑了這么個女人!又想黃千葉這號人,能有人磨磨他也好。她似乎出了口濁氣,心底泛起難言的快意,這快意旋即又被莫名的悵惘所替代。
女友招呼家姝,說上“水立方”那里留個影。衛家姝應了聲,又不由自主地朝黃千葉那邊看了看。黃千葉抱著孩子,走得飛快,像在躲避什么。女人小跑著跟在后面,不時地嚷著,黃千葉,走那么快干什么?又沒有人要吃你!
目送那扭著肥屁股追得急躁的女人,衛家姝嘆口氣,別過臉,甩了甩披肩長發,挺胸束腹,跟女友一起匯入去“水立方”的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