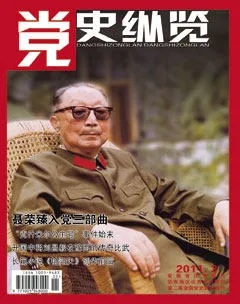長篇小說《艷陽天》創作前后
2011-12-29 00:00:00熊坤靜
黨史縱覽 2011年3期

我國當代著名作家浩然,原名梁金廣,1932年3月25日出生于河北唐山,1946年參加革命,1948年11月加入中國共產黨。從1956年11月在《北京文藝》上發表處女作短篇小說《喜鵲登枝》起,浩然在40多年的寫作生涯中,先后創作出短篇小說集《喜鵲登枝》,長篇小說《艷陽天》、《金光大道》、《蒼生》、《樂土》、《圓夢》等作品,共出版著作70多部,僅在國內發行量就達1000多萬冊,系我國作品發行量最大的作家之一。
浩然在寫作中,經常深入冀東和北京郊區農村體驗生活,由于“浩然總是那樣不厭其煩地深入農村,那樣不厭其煩地寫農民、歌頌農民”,因而有些專家學者稱贊其小說作品“是很形象的中國農村近半個世紀的圖畫”,“寫出了個人和社會的雙向的真實”,“是樸實無華的自傳體,給人絢爛至極、歸于平淡的藝術感受”,“具有史料性和藝術性兩方面的價值”。特別是他的代表作之一、洋洋126萬字的三卷本長篇小說《艷陽天》,情節豐富曲折,結構完整緊湊,人物形象生動,鄉土氣息濃郁,有很強的藝術特色,在國內外頗有影響。德國一位漢學家稱贊《艷陽天》是“描寫中國農民生活的一個絕唱”。在《劍橋中華人民共和國史》中,美國伯克利加利福尼亞大學東方語言學教授西里爾?伯奇以《浩然的小說》為題,對《艷陽天》和《金光大道》給予高度評價:“在講故事的流暢方面沒有誰比得了他。用精心選擇的細節來使人物的一舉一動一顰一笑富于感染力,從庸常瑣屑中搶救出的小插曲也飽含寓意,而象征則既像芟剪枝蔓的斧斤,又像在扣結之處蓄著力量的繩索——一個生動的故事所具有的這一切都似乎行云流水般出自浩然。”1999年,香港《亞洲周刊》評選出“20世紀中文小說100強”,在1949-1976年間的中國內地小說中,僅有浩然的《艷陽天》和王蒙的《組織部新來的年輕人》入選。
浩然在《艷陽天》里,通過京郊東山塢農業生產合作社麥收前后發生的一系列矛盾和沖突,塑造了眾多可信可愛的貧苦農民的形象和真實生動的落后農民的形象,勾勒出農業合作化時期生機盎然的生活畫卷,表達了社會主義永遠是“艷陽天”的堅定信念。因此,我國也有學者將《艷陽天》與柳青的《創業史》相提并論,認為兩者“共同的特征是描寫出了建國初期農村的階級形態以及各形態在時代大潮前的消長關系”,它們都是“描寫農業合作化運動的壯闊歷程,揭示運動過程中紛繁復雜的階級關系的長篇巨著”。
那么,《艷陽天》這部著名小說的創作始末究竟如何呢?
下放昌樂得素材
1956年9月,浩然由《河北日報》社調入北京俄文《友好報》社當記者,不久,他又被該報主管機關中蘇友好協會總會副主任朱光調去當秘書。在工作期間,他創作發表了《喜鵲登枝》等一系列表現農村新人新事的短篇小說,并于1959年10月被吸收為中國作家協會會員,由此步入文壇。由于他是在農村長大的,后來又曾長期工作在基層,在大都市里待久了,難免想念農村,便乘著中央機關下放干部之機,主動向組織上請求下放勞動,獲得批準。這樣,1960年春節剛過,浩然和同事高莽來到了山東濰坊昌樂縣,被分配在離縣城較近的城關公社東村大隊勞動鍛煉。這個400口人的村子原有2名黨員,現在加上浩然,達到了建立黨支部的條件,他即被組織上任命為大隊黨支部書記。
當時適逢三年自然災害時期,東村大隊全體社員每人每天定量只有6兩糧食,所以每日只吃兩頓粥,早一頓,晚一頓,不要說蔬菜和肉類,有時甚至連咸菜也吃不上。為了辦好食堂,保證社員不斷頓,浩然真是絞盡腦汁,煞費苦心。首先,他安排大隊會計、保管員認真清倉查庫,把所有能吃的東西全部儲存起來,同時又安排食堂精打細算,到老壩河打撈一種能吃的水生榨菜,去山坡上挖野菜,做到糧菜摻和,粗細搭配。他還根據所掌握的情況,組織大隊干部走訪貧困戶,做到逐戶安排。在和社員們擔水栽煙、澆地的過程中,他發現大隊南面有200畝地因地勢較高澆不上水,便帶領下放干部和社員們冒著冷颼颼的西北風,每天挖土筑堤,連續苦戰了半個月,修成一條長1公里、從北流泉通到村西頭的引水渠。
浩然的另一項重要工作就是組織帶領大隊小隊干部和社員混合編組,看護莊稼,以防失竊。每逢輪到他值班看護莊稼時,他的內心總是很矛盾:一方面作為大隊支部書記,他要堅決維護集體的利益,不能讓大多數老實本分的社員吃虧;另一方面,他對那些因饑餓至極而小偷小摸者,尤其是那些老者、病者,又懷著深深的同情。于是,當他發現某些社員有偷挖地瓜或者在衣褲里夾帶糧食行為時,往往不是唱歌就是吹口哨,遠遠地把他們嚇跑了事,從不深究。
在東村時,有幾戶人家給浩然留下了深刻的印象。特別是他的第一個房東田守業一家,簡直老實本分得出奇。田守業家住在村邊,離莊稼地很近。他家的東屋外邊就是晾曬、打軋糧食的場院,而且有朝東開著的屋門。如果他想偷一點隊上的糧食充饑,是十分方便的。盡管田守業和他的父親餓得形銷骨立,田守業的兩個孩子也都面黃肌瘦,餓急了常常爬上樹去掠樹葉子吃,但田守業一家人絕不偷拿隊上一穗一粒糧食。浩然見狀實在于心不忍,出于憐憫和同情,他曾在幾個夜晚多次把同去看護莊稼的大隊干部支走以后,故意打開通往場院的大門,然后到外面去串門子;輪到他獨個看護莊稼時,就以去開會為由,有意找田守業父子頂替代崗。然而,面對這一次次“機會”,田守業一家始終不越雷池一步。
東村大隊保管員田敬元是個處處唯唯諾諾、事事小心謹慎的“老好人”,但對庫房卻管得特緊。來找他的,不論是多少人,也不論什么職務,都只能停步在保管室門外,用什么或交什么,都由田敬元親自開門,取出來或送進去;辦完了事,不管取送東西的人走沒走,他都要立即關門上鎖,毫不遲疑。在割麥時節的一天,浩然的鐮刀折了,去找田敬元調換。田敬元打開門,浩然想跟進去,卻被田敬元拉住說:“你就在外邊等,俺麻利地給你找一把來。”
浩然說:“我要親自挑一把刀刃鋒利的。”
田敬元死死地堵在門口,笑瞇瞇地對浩然說:“你別進去,保準給你找把好使的就是了。”
有幾次,浩然到保管室通知田敬元參加隊干部會,隨后與他一道去會場。離開保管室的時候,明明看見他關了門上了鎖,可等到散會后,田敬元偏要繞個大彎子,到保管室再摸摸門究竟上鎖了沒有。浩然嘲笑他說:“你老糊涂,剛剛鎖上的就忘記了嗎?”
田敬元卻說:“小心不為多余,閃失的事兒,多半出在大意上。”
50歲開外的田明先老漢,是另一位下放干部高莽的房東,因此他也成為浩然最熟悉的社員之一。田明先一天到晚耷拉著腦袋走路,平時見了人也從不說笑。
這年麥子收割了以后,浩然日夜守在場院上,看護著那一座座山峰似的麥垛。豈料下了一場暴雨,緊接又是連天陰雨。雨一停,浩然就帶著幾個大隊干部每天早上將麥垛挨個查看了一遍。只要沒有坍倒的,也沒有漏雨的,大家就放心地陸續回家去睡大覺,浩然則留在小屋里,坐著蒲團,把看場人睡的床當桌子,伏在上面寫小說。
有一天早上,照例查完麥垛后,其他大隊干部散去了。浩然坐下來,掏出草稿本子正準備寫作,忽聽到“啪噠、啪噠”的腳步聲由遠而近,隨后門口的光線被擋住了,他抬頭一看,原來是田明先站在那兒。浩然問他:“你有事兒嗎?”
田明先眨巴著眼睛,說聲“沒”,就轉身離去了。
浩然伏在床上,剛寫了幾個字,外面又響起“啪噠、啪噠”的腳步聲,浩然抬頭一看,又是田明先站在門口,于是有些不耐煩地問:“你到底有啥事兒?進來呀!”
田明先連忙倒退著說“不,不”,就從門口消失了。
沒過多久,門口的光亮又暗了下來。浩然猜是古怪的田明先又來了,遂心生反感,頭也沒抬,只顧寫他的小說。不料足足過了一兩分鐘,他既不走開,也不過來,把光線全給擋住了。浩然生氣地抬頭一看,面前除了田明先,還有他的堂兄弟田明金。于是浩然強壓住怒氣,改用和氣的口吻說:“大爺,請進來坐吧。”
田明金看一眼田明先,說:“他有個意見,想給提提,又不敢,一定拉我跟他搭伙來。這回行了吧,你有話就說呀。”見田明先仍是一副戰戰兢兢的樣子不敢開口,田明金就說:“麥子垛可能漏了雨水。”
浩然笑笑說:“就為這個呀?放心吧,我們每天都換個兒地檢查一遍,沒有漏一點雨的。”
田明先忍不住終于開口了:“你們那個檢查法不中呀!我爺在世那會兒,就漏過垛,毀了一場麥子,可凄慘了……”
浩然打斷了他的話:“如今是社會主義!”
田明先竟被激怒了,瞪起眼睛大吼道:“啥主義水火也沒情,你支書想帶著俺們當餓死鬼咋的?啊?”
浩然被質問得目瞪口呆,田明金趕忙勸他說:“梁同志,你聽聽他的,興許有道理。”
于是,浩然繃著臉孔問田明先:“你說說,咋個檢查法才中?”
田明金又幫腔說:“梁同志,你就聽他一回吧,讓他教教你,要不他就絕難死了。”
浩然氣呼呼地站起身,跟著兩位老漢出了場屋,走到汪著水的場院里。按照田明先所說的辦法,浩然將胳膊往麥垛的深處用力插入,然后抓出一把麥穗一瞧,結果發現麥穗濕漉漉的,而且變了顏色。浩然趕緊召集大隊干部和社員,把所有的麥垛都仔細、深入地檢查了一遍,凡是漏雨的,都拆開垛來讓其透風;沒有漏雨的,就動員社員把自家能擋雨的東西都拿出來重復地苫蓋一遍。等到天空放晴了,就突擊晾曬。這樣總算保住了十幾萬斤糧食,使國家得到了公糧,群眾分到了口糧,也讓浩然避免了一次重大的失職錯誤。
這件事使浩然“心靈受到沖擊與震顫,真正將心融入了社會生活,獲得了第一部長篇小說《艷陽天》中許多場景、意境和人物心態的素材”。及至多年以后,他在與《浩然口述自傳》的整理者鄭實談起此事時,還說道:“尤其重要的是,這場親身經歷的驚心動魄的體驗,使得北京郊區那位我熟悉的英雄人物蕭永順GtBL8Hxc+HV5WhoAi1uEmg==有了一個用武的陣地和施展其本領的‘載體’,對這部小說的結構起了決定性的作用。有趣的是,在我身上已經形成這樣一種條件反射,不論走到什么地方,只要一見到麥子有了發黃的顏色,我就想到昌樂,就擔心沒容小麥打軋入倉便陰雨連綿,直到得知準確的收獲完畢的消息之后,才把懸著的心放下。”
三十而立尋突破
浩然在昌樂生活了8個月后,就提前返回北京,調入《紅旗》雜志社工作,負責編輯文藝副刊。工作之余,他更加勤于創作。古人云:“三十而立”,年近30歲的浩然急于想在國內文壇上嶄露頭角,成為一名專業作家,而僅靠他以前寫的那些短篇小說是難以實現這個理想的。他抽空閱讀了蘇聯作家肖洛霍夫的長篇巨著《靜靜的頓河》和我國古典文學名著《紅樓夢》、《三國演義》等大量作品,感到自己已有了駕馭長篇小說的能力,加之在昌樂下放期間的所見所聞總在他腦際縈繞,關于田守業、田敬元和田明先等人的許許多多故事憋在心頭,非寫出來一吐為快不可。
轉眼到了1962年初冬。一天,與浩然熟識的中國青年出版社編輯室副主任蕭也牧敲開了他的家門。在談話中,蕭也牧先是稱贊浩然近幾年來在文學創作上進步很快,然后便把話題轉到了來訪的目的上,說:“我們出版社想給你出個選集,把可以保留的上等品挑出來,印一本,做個小結。我覺得你現在可以寫長篇了,創作出一個代表作。”
浩然說:“我正有這個打算,但覺著沒有把握。”
蕭也牧語氣十分堅定地說:“我認為水到渠成了,要有信心。”
好友的一席話,使浩然毅然下定了創作長篇小說的決心。于是,他把中國青年出版社編輯王主玉調來頂替自己的工作,然后向單位請了創作假,住進了北京西山八大處作家寫作所。他從1962年年底開始動筆創作《艷陽天》第一卷,每天都寫到很晚才休息,餓極了就吃幾塊點心來充饑。萬事開頭難,剛開始他總擔心萬一失敗了怎么辦,還不如乘機多寫些短篇小說。就在他信心不足,老想打退堂鼓的時候,王主玉及時給予他熱情鼓勵,才使浩然振作起精神按原計劃繼續寫下去,寫著寫著就順手了,故事、人物紛至沓來,躍然紙上。
在東村護秋、曬場等場景,都被浩然寫進了《艷陽天》。當寫到社會主義的根子深深扎在農民心里那些情節和細節的時候,浩然很自然地聯想到田敬元,以及與他類似的眾多對集體事業赤膽忠心的老貧農,由此誕生了“馬老四”這一文學形象。
寫了改,改了又寫,如是者三遍過后,浩然才感到滿意。起初,他把《艷陽天》第一卷手稿交給人民文學出版社,但等了很久沒有回音。這時,正趕上《收獲》文學雜志復刊,該刊編輯葉以群到北京來組稿,拿走了《艷陽天》第一卷復寫稿,并很快發表了出來。1964年,《艷陽天》第一卷被人民文學出版社出版發行后,反響很大,浩然每天都會收到很多讀者來信。這年10月,他順利地調入中國作家協會北京分會,終于圓了專業作家之夢。在此前后,浩然一鼓作氣寫出了《艷陽天》第二卷、第三卷,由人民文學出版社于1966年3月出齊。所得稿費1萬元,全被他交了黨費。
“四清”運動開始后,浩然和作家汪曾祺等一道被下派到農村去搞這項工作。期間,汪曾祺曾滿懷信心地要把《艷陽天》改編為現代京劇,但只完成了一半,就因“文化大革命”爆發而中斷了。北京人民藝術劇院還把《艷陽天》改編為話劇,進行了彩排,但后來卻沒有公演。1973年,長春電影制片廠根據這部小說改編拍攝了同名彩色故事影片,于1974年正式上映,受到廣大觀眾的熱烈歡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