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級幕僚”醫改夢
2011-12-29 00:00:00許十文雷順莉
南都周刊 2011年4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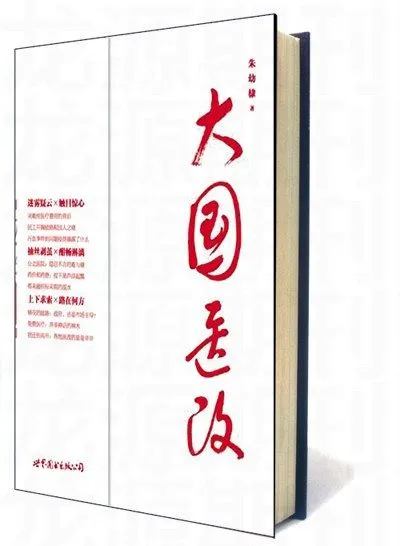

從2001年至今,朱幼棣在國務院研究院社會政策司司長的崗位上呆了十年,被吳曉波形容為“高級幕僚”。過去幾十年從未對現實政策有過公開言論,在61歲這一年,過了退休年齡卻依舊在崗的他,卻因一本抨擊中國醫改徘徊不前的《大國醫改》,顛覆了他多年謹小慎微的官員形象。
作為前新華社中央組組長,如今的國務院研究院社會政策司司長,61歲的朱幼棣終于寫起了政論。過去幾十年,他從來沒有對政策的現實公開發表過任何文字。
朱幼棣曾經寫過關于珠寶鑒定的冊子,也撰過大散文風格的《后望書》,而新近的《大國醫改》,是他的第一本政論式著作,也成就了他“最痛苦”的一段寫作經歷。
在北京,跟很多中央機構的司長一樣,朱幼棣出門沒有公務車搭載。在朱妻眼中,他還是個謙和的人,不抽煙,不喝酒,喜歡鉆研書法、文學地理。
朱曾經感慨道:“中國古代官員多作家、詩人,但現世卻沒有這樣的人。”
“朱幼棣寫政論,我一點都不驚奇。他要寫的話,就會寫出核心觀察來。”他的老朋友,曾一起在新華社共事的財經作家吳曉波說,朱幼棣曾經是個跟在中央領導后面寫行蹤和指示的紅墻記者,也是個“行將絕種的文人官員”。
朱幼棣參加過不少中央政策的調研和內參工作,吳曉波形容他是“高級幕僚”。朱也深諳中國各種各樣的問題,背后少不了具體部門千頭萬緒的利益驅動。“我不想做揭黑類的暢銷報道文學。”這個頂發稀疏的司長,說話的時候,眼鏡下有一雙靜默的眼睛,總是若有所思的樣子—“但我看到的,是最核心的事實。”
譬如,他直接寫道:“有確切的證據表明,藥品從生產文號的報批、流通、定價,進入醫保目錄、藥品集中招標‘采購’,進入醫院,一直到醫生開出處方,幾乎每一項行政審批,每一個環節,都有一些潛規則,都可能滋生腐敗,彌漫著不正之風。”他甚至直言,“怪不得有人稱衛生部長是中國醫院的‘總院長’,或中國‘公立醫院集團’的董事長兼總經理。”
朱幼棣曾想用“十年徘徊”來命名這本書,以表達心中對現實的無奈。復雜、現實而沉重的題材,使這個“核心知情者”,有點筋疲力盡的感覺。
在兩年前出版的《后望書》里,國家發改委副主任解振華為朱幼棣作序。此書中,朱幼棣記錄了很多陳年往事。他走訪、回顧了在大建設中被毀滅的自然和人文地理景點。在記錄三門峽大壩使古城潼關毀滅的歷史時,他站在黃河邊發出感慨,“胸中升起一種蒼涼、無奈的情緒”。
而在寫完《大國醫改》的時候,他又有了另一種強烈的傷感:“比較傷,很受傷。我想是因為我們心憂?但我們是沒法憂的。”
然后他哈哈大笑起來。
切膚之痛
朱幼棣的童年是在浙江黃巖度過的,出生書香世家,長輩不乏有名望的官員。1957年,他8歲的時候,父親突然被打成“右派”,在黃巖城內教書的母親受到牽累,被調到鄉下小學任教,朱幼棣的生活環境從城市換到了農村。“就在那一年,我的想法一下子就變了,人也成熟了起來。”
而后,朱幼棣的父親在勞教農場勞動,母親全身浮腫,得了肝病,醫院的治療手段簡陋至極:每天打一針葡萄糖,但母親竟奇跡般地活過來。朱說,自己也得過急性黃疸肝炎,靠祖父每天兩碗的“茵陳湯”,也得以康復。
從1983年開始,朱幼棣進入新華社,開始其“高級幕僚”的仕途。1995年,朱幼棣任職新華社政治室主任(“中央組組長”),開始跟著領導去外地考察,后來又在山西省辦公廳、國務院扶貧辦任職,從2001年開始擔任國務院研究院社會發展司司長。
在這幾十年間,中國的醫療事業也發生了巨大的變化。朱幼棣年少時,中國農村缺醫少藥,中草藥更多地得到采用,還出現了世界聞名的“赤腳醫生”。從1990年代開始,中國的衛生醫療開始了市場化,新的檢測設備進駐各大醫院,“點名手術”、“特殊護理”等醫療服務被人們廣為討論,藥品廠家紛紛升級換代。
到今天,他形象地描繪,“在中國,(公立醫院)有無須回報的政府投資,有固定資產、運營費用和一定的人員工資補貼等優惠政策,有國有銀行的大量貸款可用于發展。同時,還有種種檢查收費、賣藥暴利,可充分享受市場經濟帶來的好處……怪不得有人稱衛生部長是中國醫院的‘總院長’,或中國‘公立醫院集團’的董事長兼總經理。”
在醫生們開始專注于賺錢的1990年代,朱幼棣對醫改的想法還比較樸素:“我只是覺得窮人因病致貧是很大的問題。醫改能做的,8e0JW7ax/8EG5nu3EWMXyf+s5y2VAhZycsPYAIgCK54=應該是將最窮的人拉一把,這是最應該做的,其他的體制分配也應該這樣做。”
這來源于朱幼棣在扶貧辦—“最多機會見到真實民情的中央機構”—下基層的調研工作。譬如,曾經在新疆,當他看到一個生產隊隊長家里連一件家具都沒有的時候,塞給了生產隊長兩百塊錢,生產隊長變得非常激動—他們從來沒見過面值100元的鈔票,并要把他們唯一的財產—一只羊,宰殺來招待朱幼棣。
“這些人怎么可能看得起病呢?”朱幼棣回憶起來還很感懷,“即使是一年交幾十塊錢的‘新農合(新型農村合作醫療)’,他們都交不起。我們能不能為窮人提供一些免費的藥品?”直到現在,朱還一直在不同的文獻中探討國家基本藥物,“免費藥”的可能性。
朱幼棣甚至還會懷念“赤腳醫生”:“他們的精神和價值取向,即低水平、廣覆蓋、體現醫療衛生的公平性、醫療衛生服務和藥品的可獲得性方面,至今仍有極大的現實意義。”
當今的中國醫療衛生,自然不是他理想中的這個樣子。
世紀之交的中國,醫療改革結束了“大爭論”的時期,確立了產權改革的方向,以及實行醫藥分業等幾項原則,但朱幼棣直言,至今中國依然是“以藥養醫”,這是醫改前進的主要阻力,也是醫德淪喪的核心根源。
他自己就有切膚之痛。2002年,朱的父親住進了一家“有如大型超市”的三甲醫院。治療期間,主治醫生問朱幼棣的妹妹借過車去上課,而醫院每隔一兩天就通知交錢,“否則停藥。”藥是沒有停過,但78歲的老人每天十多個小時的大輸液,心臟不堪重負,出現心衰癥狀,最后掛著針去世,其時病房里卻沒有醫生。
“也許從那時候起,我就下定決心要搞清醫藥和衛生的真相,究竟出了什么問題?”
核心真相
朱幼棣愛寫作。在做記者期間,“從新聞上來講,我是黨員干部楷模,《孔繁森》的主要作者。”他在國務院研究室的主要工作,則是給國務院領導起草講話,起草政府工作報告,等等。不過,在《大國醫改》之前,朱幼棣公開發表的作品里,從來沒有染指過關乎決策層面的現實題材。
朱幼棣認為,醫改的目標其實非常簡單,“讓窮人看得起病,讓有錢人看得好病。寫這個一點也不難,開始動手時,才發現其中的艱苦之處。”書最后取名《大國醫改》,也是因為其中涉及的問題眾多,迂回復雜的緣故。
在朱幼棣筆下,醫改的復雜性,以前所未有的廣度和力度被呈現。這本接近400頁、40萬字的著作,筆觸穿越數十年的政策流變,串聯中央到地方的體制現實,橫跨醫療改革涉及的多個范疇,直揭亂象之后的利益鏈條,邊寫邊議,圈點荒謬,隨處可見犀利的批評,還有,沉重的嘆息。
這不是歸納文獻的工作。2004年,朱幼棣對“國家基本藥物政策”進行調研,隨著調研的深入,他越發體驗醫改面對的強大而頑固的體制阻力—具體涉及部委的各自為政,部門、權力、藥企藥商之間的微妙博弈,林林總總。
朱幼棣本有機會參與醫改的決策過程。2005年,國務院發展研究中心發表報告,提出“醫改基本不成功”的判斷,引起了中國社會的強烈反響。中央政府內部召開會議,準備讓國務院研究室對此進行調研,但后來因為一些原因,醫改新方案稿的主要起草工作,最終交歸衛生部操作。
不過朱幼棣依然有勘測的路徑。
向朱幼棣抱怨的藥企界人士不少,朱甚至發現,一些震驚全國的劣藥事件,從利潤鏈和商品流通的角度,是被各地招標辦、醫院“逼出來”的。在其他部門牽頭的一些相關調研里,他同樣發現了大量的,分布在政策、體制、醫院、醫保等不同領域和層面的,隱秘的事實,在書里,他對此進行了大篇幅地描述。
在參加其他部門組織的相關調研中,朱幼棣也得到了考察的機會。在鐵嶺,他發現當地的私人診所發展得比較好,社區反映也不錯,這證明一些認為國家財政應包攬醫療衛生到社區基層的部委意見站不住腳。“到了沈陽就不行,公立醫院的醫生護士到社區去不但要加班費、夜診費,操作起來還不如社區私人診所那么有效。”他對記者說。
為了分析現狀,朱幼棣還會與一些部委官員討論醫改。他會重新考察一些媒體上廣為報道的案例,指出社會新聞底下被忽略的關鍵鏈條。“有點專業,但我希望能讓老百姓看到。看明白了,那某些機構就沒辦法再忽悠大家了。”
例如,“對藥物從生產到流通,藥物的價格如何層層提升的金字塔,事實上可以了解得非常清楚。”他舉出了具體的數字:“根據醫藥行業的估算,全國醫院在藥品經銷中的獲利,當在1000億元以上。”這個數字與衛生部門官方統計有一半以上的差距。
在書中,有醫藥行業的人士坦言,這差距,一部分作為醫院及各科室的回扣進了小金庫;更多一部分,則是私底下落入了醫院相關負責人的腰包;還有對不上賬的,那是醫藥代表“派發”給醫生的“處方費”。
這些醫療系統的收入,主要由病人買單。朱幼棣手上有一些醫務人員的灰色收入清單,而作為中央的官員,他免不了也要算一下總數。他給醫療系統工作者這一“新興中產階層”算了一下收入。“我國500多萬醫務人員中,少說也有幾十萬人能從處方中拿到好處,一年每人從數千元到數萬元不等。”
精準抨擊
雖說《大國醫改》明顯地踩到了相關利益部門的痛處,但在廟堂江湖走過這么多年,朱幼棣經驗十足。“我寫的全部都是事實,但沒有點名。他們看了很生氣,但又講不出話來。他跳出來罵,不就承認自己有問題嗎?”
朱幼棣反復說:醫改的問題,相關利益部門多年來出了很多論調、方向、概念,把公眾弄得如墮霧里,然而根源上的問題并無得到解決。若體制不改革,醫改就不可能“最終勝利”。
嚴謹是朱幼棣所自豪的一個特質:曾經跟著中央領導采訪、寫稿多年,從來沒有出過錯。他不時用“精準”兩個字來形容自己的下筆追求。
多年積累,了解到一系列亂象,朱幼棣私下里提起來,甚至會輕聲地說一句“他媽的”。但在公開場合少有情緒化的時候。對于各路專家,朱幼棣說自己從來不跟隨他們的觀點。“我跟他們都很熟,但我不聽他們的。”說這話的時候,他孩子般地笑了一下。
—“許多不為世人所知曉的醫療服務中的種種,行業人士沉默,或者遵從了的潛規則。在這一刻,露出了它血色的一角—這也是醫療商業文化中最為陰暗之處,是社會精英和普通民眾都不可能想象的。”類似抨擊,書中有多處著墨。
在私下里,在寫作中,他會直接表達情緒。譬如,他會直接對一些機構人士和專家直接用“豈有此理!”來評價,其中包括認為醫院收費低的廣東中山大學附屬腫瘤醫院院長曾益新,還有建議“高薪養醫”并堅持醫藥不分家的北大教授李玲。在他的筆下,中國的醫改有回歸計劃經濟的跡象,而這種趨勢“為行政尋租、集中收權和擴張行政權力鋪道”。
并非只有他一個官員在感嘆醫改的艱辛。于明德,國家經貿委經濟運行局副局長,看過《大國醫改》后不由得感嘆:“自新醫改方案公布一年多來,以建房子、買設備為代表的增量改革進展較快,而作為醫療資源主體的公立醫院在體制、機制改革進展緩慢,以藥養醫的局面依然故我。”
朱幼棣覺得,他更希望看到“集體的努力,去促成每一項關乎社會民生的國家政策”。幾年以來,他也通過國務院研究室等渠道,將相關的研讀報告遞送到中央高層。
不過,朱幼棣從來不覺得“高級幕僚”的角色有多重要。“你不能保證每篇(報告)都有效果,你寫十個有一個有效果就行。你的工作就是這個而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