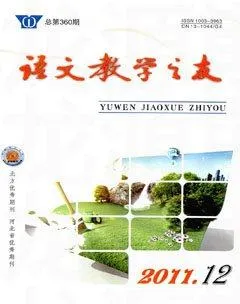“我”非我
人教版語文七年級下冊《教師教學用書》在《社戲》的“課文研討”第一段有這樣一句話:“《社戲》全文原有前后兩個部分,課文節選自后一部分,描寫作者幼時一段看社戲的往事,表現對童年美好生活的回憶和留戀的心情。”對此表述,筆者不敢茍同,竊以為不妥。
按照《教師教學用書》的說法,《社戲》中的主人公“我”——迅哥兒就是魯迅本人。在教學實際中,不僅七年級學生普遍存在這樣一種錯誤的認識,就連一些名師也有類似的錯誤解讀:“魯迅先生小時候也特別喜歡到外婆家去,在他41歲時仍能清晰地回憶起這段往事,并忍不住寫下了一篇帶有自傳色彩的小說,這就是我們今天要學習的《社戲》。”(《中學語文教學參考·初中版》2011年第2期,梁立娟《相見不如懷念——《社戲》文本解讀與教學設計》)
之所以會出現如此的遺憾和窘境,不排除《教師教學用書》在其中所起的誤導作用。其實,《社戲》中的迅哥兒并非魯迅本人,理由如下:
一、《社戲》的體裁是小說
《社戲》是魯迅1922年寫的一篇短篇小說。作品以少年時代的生活經歷為依據,用第一人稱寫“我”十一二歲時在平橋村夜航到趙莊看社戲的一段生活經歷。作品刻畫了一群農家少年的形象,表現了勞動人民淳樸、善良、友愛、無私的美好品德,展示了農村自由天地中充滿詩情畫意的兒童生活畫卷,表達了作者對勞動人民的深厚感情和對美好自由生活的向往。
作者之所以用第一人稱,是為了達到親切、真實、可信的表達效果。而作家自覺或不自覺地結合自己的一些生活閱歷創作小說,也是可以理解的。關于這一點,江蘇教育出版社《初中語文學習評價手冊》2010年12月第9版第56頁中有明確的陳述:“魯迅在童年時代,曾隨母親在農村居住過,間或和許多農民親近。短篇小說《社戲》寫于1922年10月,作品采用回憶的形式,用第一人稱寫就,但不是作者的自傳,閱讀時不能把‘我’看成是魯迅。”
根據小說的常識,只有自傳體小說中的“我”才是作者本人,如人教版語文教材七年級下冊后面的名著導讀《童年》中的阿廖沙就是作者高爾基。既然《社戲》不是自傳體小說,又何來“我”是魯迅一說呢?至于文中出現的“魯鎮”、“平橋村”、“趙莊”等地名,我們也不能想當然地對號入座了。
《社戲》選自《吶喊》,而非《朝花夕拾》。《朝花夕拾》是魯迅所寫的唯一一部回憶散文集,原名《舊事重提》,作者說這些文章都是“從記憶中抄出來”的“回憶文”,它收錄了魯迅1926年所作的10篇回憶散文。人教版初中語文教材中的《從百草園到三味書屋》描寫了魯迅自己童年生活的乏味,《藤野先生》則深情地回憶了最使自己感激的日本教師,這兩篇中的“我”皆為魯迅本人。反之,收錄在《吶喊》中的《社戲》因為是非自傳體小說,而小說又是允許虛構的,因而《社戲》中的迅哥兒并非魯迅本人就是情理之中的事了。
二、創作的風格較另類
與收錄在《吶喊》中的《狂人日記》《阿Q正傳》《故鄉》等直接揭露社會黑暗、指斥冷漠現實的同期作品相比,充滿詩情畫意、描繪美好生活的《社戲》的創作風格多少顯得有些另類,給人一種格格不入之感。
究其原因,這與魯迅先生的“故鄉情結”有著千絲萬縷的聯系。魯迅的故鄉紹興,自然景色秀麗,歷來是人文薈萃之地,前人稱其山水之美是“千巖競秀,萬壑爭流,草木蒙籠其上,若云興霞蔚”。“從山陰道上行,使人應接不暇。”(《世說新語·言語》)盡管魯迅18歲就離開故鄉外出求學謀生,而故鄉給予他的又并非全是美好溫馨的回憶,甚至其間還夾雜著些許不幸、苛待和白眼,但生于書香門第、深受儒家重視人倫親情思想影響的魯迅已把對故鄉的眷戀融入自己的血液之中了。在給親人的信中,魯迅深情地寫道:“行人于斜日將墮之時,冥色逼人,回顧滿目非故鄉之人,細聆滿耳皆異鄉之語,一念及家鄉萬里,老親弱弟必時時相語,謂今當至某處矣,此時直覺柔腸欲斷,涕不可抑。”(《集外集拾遺補編·戛劍生雜記》)故鄉的山光水色、一草一木早已植根于魯迅的心田,思鄉的線始終牽動著一生都在“漂泊”的魯迅。每當人生道路上遇到風波與陰霾,從內心深處油然而生的是那“濃的化不開”的“完美故鄉情”。魯迅是在“昏沉的夜”看到了山陰道上“好的故事”(《野草·好的故事》),也是在北京“嚴冬的肅殺”中想起了故鄉早春二月的風箏時節(《野草·風箏》)。小說《社戲》描繪的正是故鄉的那張夢幻圖景,理想中的桃源圣地。
《社戲》中的故鄉山美水美人更美,而同樣以江南農村為背景的《故鄉》帶給我們的只是日漸凋敝、千瘡百孔的現實景象。為什么差異如此之大呢?原因就在于魯迅心中的“雙重故鄉”,一個是《故鄉》中所描繪的現實中的故鄉,另一個是《社戲》中所展現的理想中的故鄉,魯迅又常常用理想中故鄉的完美來關照現實中故鄉的破敗。編人語文教材的小說《故鄉》刪去了開頭的第一部分,這一部分記述了“我”成年后在北京看戲的兩次經歷。那兩次戲都沒看好,從反面折射出了當時社會的混亂、沉悶、世故、污濁,而這正與“我”少年時在平橋村的自然率真生活形成了鮮明的對比。試想一下,魯迅童年生活過的故鄉真的如他筆下那般完美無瑕嗎?非也!
三、人物的稱謂反邏輯
魯迅筆名之多,堪稱我國著名作家之最,在世界著名作家中也是極少見的。由于當時的社會形勢和寫作環境的原因,魯迅在發表自己那些“匕首”和“投槍”式的作品時,必須要不斷地變換名字,所以,魯迅就有了繽紛多彩的筆名。這些筆名不僅成為了中國文壇上一道亮麗的風景,也成為頗有意趣的一種文化現象,引起了現代文學研究者和魯迅作品愛好者的關注。
魯迅原名阿張、周樟壽、豫山、周樹人,1881年9月25日出生于浙江紹興。當時其祖父周福清在京做官,當抱孫的喜訊傳到他那里時,恰巧張之洞來訪,于是其祖父便以所遇為孫取名“阿張”,之后又以同音異義的字取作大名“樟壽”,號“豫山”。
魯迅7歲進私塾就以“豫山”為名。紹興話“豫山”和“雨傘”音近,同學們常以此取笑他,便請祖父改名,后改名豫亭。1892年進“三味書屋”讀書時,改名豫才。
1898年,17歲的魯迅離開了家鄉,來到南京,投奔一個名叫椒生的叔祖,入江南水師學堂。周椒生本人在水師學堂做官,卻對這種洋務學堂極為蔑視,認為本族的后輩不走光宗耀祖的正路,而跑到這里來準備當一名搖旗吶喊的水兵,實在有失“名門”之雅。為了不給九泉之下的祖宗丟臉,他覺得魯迅不宜使用家譜中的名字,遂將“樟壽”的本名改為“樹人”,取“十年樹木,百年樹人”之意。
1907年又因魯迅先生的慈母姓魯,所以取其母姓,又錄“迅行”,取其“迅”字,合二為一,謂之“魯迅”。1918年5月,在錢玄同的介紹下,魯迅在《新青年》第4卷第5號發表了中國現代文學史上第一篇白話文小說《狂人日記》,首次使用筆名“魯迅”。“魯迅”這個廣為人知的筆名,是他發表《狂人日記》時第一次使用的。據魯迅的好友許壽裳先生解析,“魯”是他母親姓氏,我國春秋時期,“周”與“魯”是同姓之國,取“魯”則在于紀念感懷母親養育教誨之恩。“迅”原是他幼時乳名,又含迅捷進取之意,表明他誓與反動腐朽的舊時代徹底決裂,積極進取的鴻鵠之志。在“魯迅”之前,還曾用過“迅行”的筆名。許壽裳曾對此作過解釋:“(一)母親姓魯,(二)周魯是同姓之國,(三)取愚魯而迅速之意。”“迅行”的含意是奮發、勇進并對未來充滿希望。
關于“魯迅”這個筆名的來歷,當年有一位日本文人曾經當面問過魯迅。這位日本文人想,“魯”是山東省,“迅”有疾馳和激勵人之意,于是,他就問魯迅:“先生是浙江人吧?為何起‘魯迅’?”魯迅說:“這是俄國人名,此名很不錯,故取之。”魯迅還說,“魯迅”這個筆名取自屠格涅夫的《羅亭》。
還有人發現了第三種解釋。認為“迅”字,古義為狼。出處見《爾雅·釋獸》:“狼子絕有力者日迅。”照這樣注解引申出來,“魯迅”是指狼的一個勇敢有力的兒子。持此一說的是歷史學家侯外廬。他說,魯迅是封建社會的叛逆者,他的小說代表作《狂人日記》就是抨擊封建社會“吃人”制度的,他取用這兩個字為名,正是鮮明表示他甘以“狼子”自居,與封建社會制度徹底決裂之心聲。據說侯外廬的這種解釋,曾向魯迅夫人許廣平提起過,許廣平連連稱謝,表示首肯。
“魯”字乃魯迅先生母親的姓,他的小說中常提到的“魯鎮”,就是他母親的娘家所在地;“迅”是他的小名,所以在他的小說里也出現過“迅哥兒”一詞,《社戲》中的六一公公對“我”的稱呼就是一個有力的佐證。按照邏輯推理,魯迅在《社戲》中隨母親歸省平橋村看社戲時的年齡,已在課文第5段有明確提示:“就在我十一二歲時候的這一年,這日期也看看等到了。”1881年出生的魯迅十一二歲時去看社戲與1907年才首次取名“魯迅”在時間上是矛盾的,不吻合的,除非六一公公有未卜先知的特異功能。
綜上所述,《社戲》中的“我”不是魯迅本人這一觀點是成立的。我們在權威的《教師教學用書》面前不應盲目認同,有時還需甄別、辨析,或許你就會發現意想不到的“精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