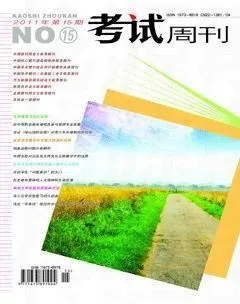“道”與“the Way”
摘 要: 隨著中國(guó)國(guó)力的日益增強(qiáng),世界上掀起一股新的中國(guó)文化熱潮,中國(guó)古典哲學(xué)典籍的價(jià)值也再次被發(fā)覺(jué)。但這些典籍的傳播仍然面臨著語(yǔ)言溝通上的障礙。在典籍的翻譯過(guò)程中,學(xué)者們從各種角度出發(fā),采用不同的翻譯理論和翻譯方法進(jìn)行嘗試,力圖找到最佳的翻譯。Arthur Waley翻譯的《道德經(jīng)》頗具影響力,他把“道”翻譯成“the Way”。但是二者的含義有極大的差別。
關(guān)鍵詞: “道” “the Way” 英譯 《道德經(jīng)》
1.引言
老子所著《道德經(jīng)》,雖然只有五千言,卻內(nèi)容廣泛豐富,對(duì)哲學(xué)、歷史、社會(huì)、軍事、政治及修身處事之道均有論述。老子的思想不僅對(duì)中國(guó)人的思維產(chǎn)生了巨大影響,是中國(guó)文化的重要組成部分,而且已經(jīng)成為一種重要的國(guó)際思想,對(duì)西方世界也產(chǎn)生了不可忽略的影響。現(xiàn)在,隨著中國(guó)經(jīng)濟(jì)實(shí)力不斷增強(qiáng)和國(guó)際地位日益攀升,國(guó)際上又掀起了一股研究《道德經(jīng)》的熱潮,《道德經(jīng)》的翻譯熱潮也隨之再次興起。
19世紀(jì)末到20世紀(jì)初,西方世界已經(jīng)出現(xiàn)了250余種《道德經(jīng)》的譯文。到20世紀(jì)60年代,其英譯版本已有40多個(gè)。在《道德經(jīng)》的翻譯歷程中,各個(gè)翻譯家面對(duì)的難題大同小異,他們一開(kāi)始就面臨一個(gè)相同的挑戰(zhàn)——對(duì)于“道”的翻譯。翻譯家們采用了各種各樣的單詞,試圖使目標(biāo)語(yǔ)讀者了解“道”的含義。
近年來(lái),Arthur Waley的英譯版本引起了很多學(xué)者的興趣,紛紛撰文評(píng)論他的得失。在他的譯文中,“道”被譯成了“the Way”。本文通過(guò)對(duì)比《道德經(jīng)》中的“道”和英語(yǔ)“the Way”的意義,討論把“道”翻譯成“the Way”的可行性,進(jìn)而為中國(guó)古典哲學(xué)典籍中文化負(fù)載詞的翻譯提供一定的思路。
2.“道”的哲學(xué)特征
“道”是漢語(yǔ)中一個(gè)極其重要的文化負(fù)載詞,不僅出現(xiàn)在文學(xué)和哲學(xué)典籍中,還頻繁出現(xiàn)在中國(guó)人的日常會(huì)話中。例如:“走正道”、“道喜”、“道歉”、“道謝”、“婦道”、“茶道”、“志同道合”等。“道”這個(gè)詞在老子之前就已經(jīng)被廣泛地使用,其主要意義是指“道路”或“道理”。《左傳》有“天道遠(yuǎn),人道邇”的說(shuō)法,《論語(yǔ)》中有“志于道,據(jù)于德,依于人,游于藝”的表述,都是把遵循的路線視為道,而且主要指的是“人道”。
老子在其《道德經(jīng)》中極大地豐富了“道”的含義,把“道”發(fā)展成為一個(gè)神秘幽昧、深不可測(cè)且極其抽象的哲學(xué)概念。在《道德經(jīng)》81個(gè)章節(jié)中有37章提到了“道”,共出現(xiàn)了74次,是使用頻率最高的一個(gè)詞匯。正如張廷國(guó)所說(shuō):“‘道’是老子哲學(xué)體系的最高范疇,甚至可以說(shuō)老子的整個(gè)哲學(xué)體系都是由‘道’而展開(kāi)的。”
老子的《道德經(jīng)》是一個(gè)充滿爭(zhēng)議的文學(xué)哲學(xué)現(xiàn)象,他以詩(shī)化的語(yǔ)言闡述了自己的哲學(xué)觀點(diǎn)。Zadeh L.A.Fuzzysets發(fā)現(xiàn),人類思維和語(yǔ)言中本來(lái)就存在著“一種其界限不是涇渭分明地確定好的類別”。這種模糊性更是文學(xué)作品的一個(gè)重要現(xiàn)象。老子在其《道德經(jīng)》中也未對(duì)“道”作出明確的解說(shuō),因此后人很難確切地說(shuō)出“道”的含義。筆者只能嘗試歸納一下老子所描述的“道”的特征。
(1)大、久。
老子說(shuō):“有物混成,先天地生。……吾不知其名,強(qiáng)字之曰道,強(qiáng)為之名曰大。”(二十五章)又說(shuō):“……道乃久,沒(méi)身不殆。”(十六章)“大”是指“道”在空間上的無(wú)限性,“久”是指“道”在時(shí)間上的無(wú)限性。
(2)先天地生,是萬(wàn)物的根源。
老子認(rèn)為“道”比“天”更根本,是宇宙萬(wàn)物的根源,是萬(wàn)物存在的根本,甚至是“上帝”和“神”存在的根本。“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萬(wàn)物。”(四十二章)“道”是純存在,是抽象的絕對(duì),是自然界最初的動(dòng)力和創(chuàng)造力。
(3)非有非無(wú)、亦有亦無(wú)。
老子在二十一章中說(shuō):“道之為物,惟恍惟惚。惚兮恍兮,其中有象;恍兮惚兮,其中有物。”又在十四章中提到:“繩繩不可名,復(fù)歸于無(wú)物。是謂無(wú)狀之狀,無(wú)物之象,是謂惚恍。迎之不見(jiàn)其首,隨之不見(jiàn)其后。”由此可見(jiàn),老子的“道”作為一種超越了萬(wàn)物的“物”而存在,是一種其中有象,其中有物,卻又是無(wú)狀之狀、無(wú)物之物的物質(zhì)性實(shí)體。
(4)不能被感知,不可言。
《道德經(jīng)》開(kāi)篇第一章就提出:“道可道,非常道。”可言之道都不是“常道”,“常道”是不可言說(shuō)的。人類有限的語(yǔ)言并不能全面描述宇宙的本體和規(guī)律,但人類卻只能借助語(yǔ)言去“道”出那個(gè)“不可道”之本體,老子的五千言似乎也只是“勉強(qiáng)而言之”。
3.“the Way”的宗教含義
Arthur Waley是20世紀(jì)英國(guó)最著名的漢學(xué)家和文學(xué)翻譯家,其譯文語(yǔ)言簡(jiǎn)潔流暢。他在翻譯《道德經(jīng)》時(shí)提出,哲學(xué)文本的翻譯重在思想內(nèi)涵的傳遞。Arthur Waley志在進(jìn)行的是一次“史學(xué)性的翻譯”,使讀者能夠發(fā)現(xiàn)《道德經(jīng)》作者的本意。但是,Arthur Waley卻沒(méi)能完全擺脫前人的影響,因?yàn)椤皌he Way”這一表述承載者濃厚的基督教文化氣息。要探討“the Way”的含義,就要首先明了基督教中唯一的真神——上帝——是怎樣的存在。
筆者選取了《圣經(jīng)》中三處經(jīng)文來(lái)描述上帝的特征:
In the beginning was the Word,and the Word was with God,and the Word was God,太初有言(邏各斯),語(yǔ)言與神同在,語(yǔ)言就是神。(約韓福音,1:1)
Jesus said to him,I am the way and the reality and the life;no one comes to the Father except through Me.耶穌說(shuō),我就是道路、真理、生命;若不藉著我,沒(méi)有人能到父那里去。(約韓福音,1:1)(基督教中的上帝具有三個(gè)位格:圣父、圣子和圣靈。)
God said to Moses:“I AM WHO I AM.”我是自由永有。(出埃及記,3:14)
由此可見(jiàn),基督教中的上帝是語(yǔ)言;是道路、真理、生命;是超越時(shí)間與空間限制的存在。“the Way”是通往上帝天國(guó)之門的“道路與方法”,是上帝的特征之一。筆者在Google中鍵入“the Way”,在出現(xiàn)的結(jié)果中,除了日常對(duì)話意義,如“方式”、“方法”或“道路”之外,該表達(dá)多具有宗教意義,指神之道;另有部分表達(dá)指人的精神修養(yǎng)之道,指人之道。
4.異化還是歸化
《道德經(jīng)》中的“道”關(guān)乎天道、地道、人道和王道,“the Way”顯然不能傳達(dá)如此豐富的含義。相反,將“道”譯為“the Way”很容易誤導(dǎo)初識(shí)《道德經(jīng)》的英語(yǔ)讀者,使其將“道”與“上帝”聯(lián)系起來(lái),誤以為《道德經(jīng)》是神存在的佐證。這顯然背離了老子的本意。因?yàn)椤暗馈钡恼軐W(xué)意義主要在“殺神”。老子明確地說(shuō)過(guò),“吾不知誰(shuí)之子,象帝之先”(四章),“以道蒞天下,其鬼不神”(六十章)。老子以“道”否定了天地、鬼神的權(quán)威。因此很多中國(guó)學(xué)者更樂(lè)意將“道”譯成“Tao”,使西方讀者一開(kāi)始就把“道”和“上帝”區(qū)分開(kāi)。
但是Arthur Waley把“道”譯成“the Way”也有充分的理由。Heidegger在《存在與時(shí)間》一書(shū)中指出:任何理解和解釋都依賴于理解者和解釋者的前理解。他在書(shū)中寫(xiě)到:“把某某東西作為某某東西加以解釋,這在本質(zhì)上是通過(guò)先有、先見(jiàn)和先把握來(lái)起作用的。解釋從來(lái)就不是對(duì)某個(gè)先行給定的東西所作的無(wú)前提的把握。……任何解釋一開(kāi)始就必須有這種先入之見(jiàn),……”翻譯的過(guò)程是理解和闡釋的過(guò)程,是“語(yǔ)際間的闡釋”。Arthur Waley的翻譯一方面使“道”這個(gè)傳統(tǒng)的中國(guó)哲學(xué)概念對(duì)于英語(yǔ)讀者更具親和力;另一方面也向我們展示了西方讀者在嘗試?yán)斫狻暗馈睍r(shí)特有的思維模式。
在翻譯中國(guó)古典哲學(xué)典籍的文化負(fù)載詞時(shí),我們會(huì)遇到很多類似的問(wèn)題。到底是歸化還是異化呢?筆者認(rèn)為,當(dāng)今的西方讀者已經(jīng)日趨成熟,他們對(duì)于外來(lái)文化的態(tài)度更寬容。《牛津英語(yǔ)大詞典》收錄日語(yǔ)“御宅族(おたく,otaku)”和漢語(yǔ)“嗲(dia)”就是很好的證明。同時(shí),借助網(wǎng)絡(luò)和各種媒體,西方讀者比以前任何時(shí)候都更了解中國(guó)傳統(tǒng)文化。當(dāng)代的西方讀者已經(jīng)做好了更多的準(zhǔn)備工作,去嘗試?yán)斫夂徒邮苤袊?guó)文化。在這種背景下,將“道”譯為“Tao”,雖然看似根本沒(méi)有翻譯,毫無(wú)意義,其實(shí)卻有助于他們理解“道”的真正含義。這一悖論也體現(xiàn)在《道德經(jīng)》中——說(shuō)“道”不可言,不正是有所言,可以言嗎。正如莊子所說(shuō):“既已為一矣,且得有言乎?既已謂之一矣,且得無(wú)言乎?”
綜上所述,筆者認(rèn)為,文化負(fù)載詞的翻譯應(yīng)該考慮目標(biāo)語(yǔ)讀者的接受能力。只要目標(biāo)語(yǔ)讀者有相應(yīng)的接受力,就不應(yīng)借助目標(biāo)語(yǔ)中意義相近的詞翻譯中國(guó)古典哲學(xué)典籍中文化負(fù)載詞,而是可以通過(guò)音譯的方法使目標(biāo)語(yǔ)的讀者一開(kāi)始就意識(shí)到其特殊性,并借助文本語(yǔ)境感化讀者,使其“轉(zhuǎn)化為讀經(jīng)者的生命”。
5.結(jié)語(yǔ)
Gadamer認(rèn)為藝術(shù)作品只有在被表現(xiàn)、被理解和被解釋的時(shí)候,才具有意義,藝術(shù)作品的再現(xiàn)是藝術(shù)作品本身得以繼續(xù)存在的方式,因此藝術(shù)作品的真理性既不孤立地存在于作品上,也不孤立地存在于作為審美意識(shí)的主體上,藝術(shù)的真理和意義只存在于以后對(duì)它的理解與解釋的無(wú)限過(guò)程中。翻譯過(guò)程是一個(gè)開(kāi)放性的語(yǔ)際對(duì)話和文化碰撞、融合的活動(dòng)。中外學(xué)者、翻譯家對(duì)于“道”及其他文化負(fù)載詞的一次次的爭(zhēng)論與探討將賦予他們?nèi)碌慕忉尯屯⒌纳Γ瞧淅^續(xù)存在的基礎(chǔ),也是中國(guó)文化得以傳播的方式之一。在翻譯過(guò)程中,我們要以準(zhǔn)確、全面地傳達(dá)這類詞語(yǔ)的文化負(fù)載為根本。
參考文獻(xiàn):
[1]付正玲.翻譯中的模糊語(yǔ)言——《道德經(jīng)》第一章的英譯分析[J].西南農(nóng)業(yè)大學(xué)學(xué)報(bào)(社會(huì)科學(xué)版),2009,(2):168-172.
[2]漢斯—格奧爾格·伽達(dá)默爾.真理與方法[M].上海:上海譯文出版社,2004,(7).
[3]張廷國(guó).“道”與“邏各斯”:中西哲學(xué)對(duì)話的可能性[J].中國(guó)社會(huì)科學(xué),2004,(1).
[4]祝揚(yáng).《道德經(jīng)》第一章兩種翻譯版本的對(duì)比賞析[J].大學(xué)英語(yǔ),2008,(9):28-31.
[5]Arthur Waley.Tao Te Ching[M].北京:外語(yǔ)教學(xué)與研究出版社,2003,(1).
[6]Robert,Eno.Towards a history of confucian classical studies[J].Early China,1992,(17).
[7]Zadeh,L.A.Fuzzysets.Information and control[J].1965,(8):338-353.
本文受山東科技大學(xué)“春蕾計(jì)劃”項(xiàng)目資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