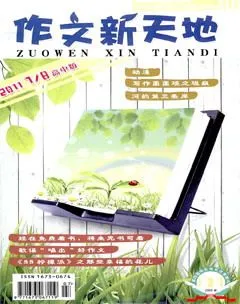文學的紀律(節(jié)選)
其實足為文學藝術(shù)前途之患的,不是任何十足的不懂文學藝術(shù)的階級,而是潛伏在文學藝術(shù)以內(nèi)的而態(tài)度又不嚴重的人。
近代文明特出的一種產(chǎn)物,名叫T.B.M.,就是英文“倦了的商人”的縮寫,他的特點是一天做了八小時的工作,筋疲力倦,余下來的時間所須要的是一點娛樂,是靠在沙發(fā)上口銜雪茄讀一本新出的愛情小說,或是踱到戲園去看一出連唱帶做的音樂喜劇。把文學藝術(shù)當做消遣品,便是一個不嚴重的態(tài)度。社會上這種不嚴重的態(tài)度一天比一天激進,從事文藝的人便有心無心地受了絕大的踏入岐途的引誘。近代的文學批評家說,文學要適應潮流,初不問這個潮流是屬于什么樣的質(zhì)地。其實文學的創(chuàng)作,或?qū)挿盒┱f,一切的文學作品,不是走在潮流前面,就是走在潮流后面,無所謂適應不適應。T.B.M.所須要的文學,是不含深刻意義的文字,同時就有人引了“游戲?qū)W說”(Play Theory)來做理論上的根據(jù)。他們說,文學的創(chuàng)作本來就不過是人類游戲的本能的表現(xiàn)。游戲的結(jié)晶,拿來做飯后的消遣,誰云不宜?這樣推論下去,文學作品能與人以最大之消遣,便為有最大之價值。換言之,文學的價值要純視銷數(shù)多少以為斷。文學的標準定在群眾的胃口。T.B.M.還不過是社會上對文學缺乏嚴重性的人的一種。然而他卻可以代表一般群眾對于文學的態(tài)度。求急功近利的創(chuàng)作家,也便隨著走上不嚴重的路。這也便是經(jīng)濟學上所謂之供求相應的道理。偉大的文學者,必先不為群眾的胃口所囿,超出時代的喧豗,然后才能產(chǎn)生冷靜的審慎的嚴重的作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