淺談柳宗元山水詩意象組合的認知特點
2011-12-29 00:00:00羅小芳
時代文學·上半月 2011年6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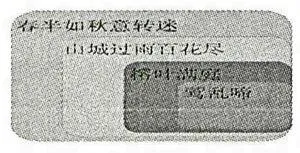
摘要:本文從認知詩學的角度,立足于意象圖式理論和圖形背景分離原則,對柳宗元山水詩的意象組合進行了比較分析。認為柳宗元永州時期山水詩的意象組合多為路徑圖式與容器圖式的結合,柳州山水詩則偏于容器圖式;柳州山水詩中,意象圖形與背景的情感基調一致,強烈直接,而永州時期則不然。這與柳子不同時期心態有別有關。
關鍵詞:圖形;背景;柳宗元;詩歌;意境
傳統詩學中,人們對古典詩歌的研究多從歷史文化的角度出發。認知詩學的發展則為古詩的欣賞開辟了新的視角[1]。
認知語言學是“以人們對世界的經驗和對世界進行感知和概念化的方法來研究語言的新興語言學科”[2]。20世紀末,英國諾丁漢大學的Stockwell成功地將認知語言學應用于文學評論當中,認知詩學迅速興起。作為一種新的文學作品解讀工具,認知詩學有助于我們從詩歌意象認知功能的角度,進一步把握詩歌意境的認知美,從而深入領略詩歌的主旨和內涵。
一
古詩中存在大量意象。意象可以理解為“客觀物體和它們所表達的情感體驗的總和”[3],要求做到“搜求于象,心入于境,神會于物”(王昌齡《詩格》)。意象圖式則是一種認知結構,是與人類經驗相關聯的具體意象的組織形態,“是為了把空間結構映射到概念結構從而對感知經驗的凝縮的再描述”[4]。1980年,Langacker&Lakoff在《我們賴以生存的隱喻》一書中,首次將“意象”和“圖式”這兩個概念結合成為“意象圖式”。圖式既與感知有關,也與想象有關,這與古詩中所蘊含的豐富意象有著某種天然的契合,因而被認知詩學恰到好處地用于文學作品的解讀。
以柳宗元的詩句為例。“崩云下漓水,劈箭上潯江”(《答劉連州邦字》)以 “上”、“下”兩個動詞,點明了由湘江而漓水而潯江的行船過程,路線清晰,位移明確;再飾以“崩云”、“劈箭”之喻,這個具體的空間結構便負載著水翻浪崩的艱難之慨與急切之情,客觀之“象”和主觀之“意”結合在一起,是為意象。其空間組合的結構如下:
湘江——漓水——潯江
(源點) → (路徑)→(目標)
這樣的意象圖式,我們稱之為路徑圖式。Johnson(1987)在他的《The Body in TheMind》一書中列舉了20多個重要的意象圖式類型。據此考察柳宗元的山水詩,我們認為,柳宗元永州時期山水詩的意象組合多為路徑圖式與容器圖式,柳州山水詩則偏于容器圖式。如永州所寫《構法華寺西亭》:
竄身楚南極,山水窮險艱。步登最高寺,蕭散任疏頑。
西垂下斗絕,欲似窺人寰。反如在幽谷,榛翳不可攀。
命童恣披翦,葺宇橫斷山。割如判清濁,飄若升云間。
遠岫攢眾頂,澄江抱清灣。夕照臨軒墮,棲鳥當我還。
菡萏溢嘉色,筼筜遺清斑。神舒屏羈鎖,志適忘幽孱。
棄逐久枯槁,迨今始開顏。賞心難久留,離念來相關。
北望間親愛,南瞻雜夷蠻。置之勿復道,且寄須臾閑。
詩歌首先表明身處竄謫,“竄身楚南極”,由長安而永州。山頂俯瞰、幽谷仰視、斷崖建亭,作者的活動線路非常清晰。遠眺之后,作者鄉愁頓起,思緒拋向北方親友,又因身困南蠻而作無奈之嘆。詩歌中的意象群皆按此線性流向進行組合,大致呈現出 “遭貶而心情壓抑—出游以求解脫—陶醉美景而暫悅—勾起鄉愁—強自寬解而其實未能”的文本結構特點,其中貫穿著時間的流逝、空間的移動,鮮明地體現著源點-路徑-目標的位置變化。這樣的意象認知結構,就是柳宗元永州山水詩常用的路徑圖式。
在這個路徑圖式中,還鑲嵌著容器圖式。
據人類經驗的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