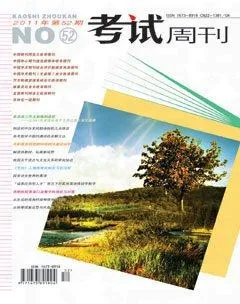“改土歸流”對納西族尚武精神影響的研究
摘 要: 在清朝雍正元年以前涉及納西族的文字中,都把納西民族記載成尚武好勇的民族精神,但是雍正元年改土歸流之后的一些史料中記載納西人“性柔弱”、“生性懦弱”等。本文通過“改土歸流”對納西族社會的影響,來探析“改土歸流”對納西族尚武精神的影響,認為“改土歸流”使納西族民族的尚武精神從感性階段發展到了理性階段。
關鍵詞: 納西族 尚武精神 “改土歸流” 發展
納西族源于河徨地區的古羌人,從有關史籍記載中看,納西族的尚勇好武與古羌人的民風有一脈相承的關系。但是以清朝雍正元年麗江“改土歸流”為分界點,之前的納西族文字和漢文獻納西族人記載成尚武的民族,之后的漢文獻把納西族人記載成性格懦弱的民族。民族精神,從哲學意義上說,它是指民族的意識、思維活動和一般的合乎理性的心理狀態。從文化意義上說,它具有共同文化、共同歷史背景、共同心理素質的穩定的人類群體,在長期的生產和生活實踐中形成的文化結晶。民族精神是民族賴以生存和發展的精神支柱,具有整體性、認同性、穩定性、凝聚性、延續性和先進性的特征。民族精神的核心是愛國主義,具有社會性、歷史性、階級性、層次性的特征。民族精神的靈魂是民族凝聚力,具有團結力、向心力、親和力、支撐力和協調力的特征。[1]所以我們對清朝雍正元年麗江“改土歸流”之后把納西民族記載為“性柔弱”、“生性懦弱”等提出質疑,并從“改土歸流”對納西族社會各方面的影響,來探討“改土歸流”之后納西人尚武的民族精神有了質的發展。
一、順應歷史發展的麗江改土歸流
改土歸流是封建社會統治階級為了鞏固自己的統治地位,對邊疆少數民族實行的一項改革。西南的改土歸流,開始于明代,完成于清代,雍正年間為其高潮。明代的土司制度已經相當完備,從政治、軍事、經濟、文化、思想各方面把土司納入國家統一制度,使之日益明顯地具有流官化的傾向,成為中央王朝對少數民族地區進行統治的有力工具。土司制度實際上是土官制度的最高階段和最后階段,是由土官走向流官的橋梁。土司制度越嚴密,它與流官制度的差異就越小,最后終究要為流官制度所取代。因此,土司制度的極盛之時,也就是改土歸流到來之日。由此觀之,土司制度是改土歸流的前奏。改土歸流,或稱改土設流,就是廢除土官、土酋,改設流官管理。它意味著,中央集權最后戰勝地方分權,地主經濟沖破土司割據的藩籬而獲得發展,意味著封建文化滲進閉塞落后的死角。從這個意義上講,改土歸流是一場社會變革,是對落后地區迅速封建化的有力推動,是順乎歷史潮流的措施,具有進步意義。誠如魏源《雍正西南夷改流記》所說:“小變則小革,大變則大革;小革則小治,大革則大治。后笑先眺,安知非福?……一時之創夷,百世之話熙。”事實證明,未嘗不是如此。[2]元、明兩朝至清朝雍正元年的四百七十年間,麗江由木氏土司世襲統治。如上所述,到了清朝初期,木氏土司已經發展到了極盛時期。雍正元年(1723年),木氏土司向清王朝“自請改流”,麗江實行改土歸流,降木氏土司為土通判,改革也較為順利,木氏土司的“自清改流”在一定程度可以說是順應了歷史發展,同時也為邊疆民族地區的政治穩定和中國“大一統”的形成作出了自己特殊的貢獻。納西族的中國認同從政治上層發展到民眾是清代雍正元年(1723年)改土歸流之后逐漸完成的。清代對納西族地區的改土歸流極大地促進了納西族中國認同的發展進程,使納西族的中國認同從政治上層發展到民眾。這一段歷史說明邊疆少數民族對中華文化的認同與對中華國家的認同是相互促進的;邊疆少數民族群體與主流社會的政治、經濟、文化聯系的強弱地位決定影響著其中國認同的強弱。[3]
二、改土歸流導致納西族人尚武精神民族發展
改土歸流在政治上廢除土司的統治,打破土司分散割據的局面;經濟上在土司地區實行科田納糧,變通土司征稅為中央王朝直接向土民征收糧賦,以增加經濟收入;軍事上解除土司的武裝、收繳土司的武器,以防止地方勢力的威脅,加強對地方直接的軍事控制。[4]改土歸流以委任的流官代替世襲的土官,客觀上有利于在全國范圍內實現政權體制的統一。改土歸流消除了土司政權的割據狀態,結束了土司對中央政權“時叛時服”和土司間長期無休止仇殺的混亂局面,而且對未改流的土司也具有強大的震撼力和威懾力,為清朝后期對尚未改流土司的改流掃清了障礙。這次大規模的改土歸流不但在政治經濟上有利于納西族地區的發展,而且在文化上對納西族人民產生了極其深遠的影響。
(一)社會穩定,中國認同感上升。
麗江地處滇西北,緊鄰滇西北藏區,為滇藏交通要沖,戰略地位重要。在木氏土司統治時期,麗江土知府木氏土司為了鞏固自己的統治地位和發展自己的勢力,極為重視軍事發展。
《麗江木氏宦譜》記載,自始祖葉古年以來,“中間歷唐五代宋元,為公為侯為將帥者,蟬嫣煌霎無間于朝之易代,何可謂不盛,然率以武功顯也”,著力渲染歷代土司的顯赫武功。宋仁宗至和中(公元1054—1055年),木氏祖先牟西牟磋“更立摩姿治大酋長,段氏雖盛,亦莫能有”。可知當時木氏已靠武力發展和鞏固了自己的勢力。納西族在歷史上曾有過全民皆兵的制度,《太祖實錄》卷二五五載:“洪武三十年……十一月……改云南鶴慶、麗江二府為軍民府。時西平侯沐春奏:二府地屬遠方,州縣人民多義兵土軍,聚則為兵,散則為民。”元代和明代幾百年間,木氏土司征戰頻繁,勢力遠達中甸、維西、德欽,以及四川的巴塘、里塘一帶,也曾遠征,達到雅魯藏布江流域,直到現在,西藏腹地還留有不少納西戍兵所建碉堡的遺跡。在明末清初時期木氏尚能調動“雄兵十萬”,由此可見歷史上的納西族的軍事力量是相當強大的。但是到了雍正元年,麗江木氏土司處于衰落階段,再加上西南少數民族多數地區都完成了改土歸流,西南少數民族地區戰事減少,改土歸流的完成給西南少數民族地區帶來了相對穩定的局面。
在此以前納西族社會對中國的認同感只是停留在政治層面上,改土歸流結束后,上升到了民眾層面。隨著中國認同感的大眾化,納西族人認可了周邊的眾多少數民族,也認可了漢族,在軍事訓練中體現出來的尚武精神也得到了提升,之前軍事之中的尚武精神局限于保衛納西族家園,發展納西族社會勢力。但是隨著中國認同感的提升,尚武精神體現出了一些中國的民族精神元素,不再僅僅局限納西族群體。
(二)改土歸流前后對納西族尚武性格記載差異研究。
改土歸流之前的史書對納西族的記載多處使用了“少不如意,鳴缸鼓相仇殺。”“附險立寨,少不如意,相攻殺,此其故俗也。”“勇善厲騎射,挾短刀,少不如意,嗚正鼓相仇殺,婦女投物和解,乃罷。”等文字,多數研究者認為這就是納西族尚武民族精神的記載。在清王朝以前,統治階級一律奉行的是漢民族傳統“夷夏觀”,“內中華,外夷狄”的傳統民族觀的限制,把少數民族稱為“蠻”、“夷”、“胡虜”,信奉的是“自古帝王臨御天下,中國居內以制夷狄,夷狄居外以奉中國,未聞以夷狄居中國治天下者也”[5]的民族隔離觀念。所以我們認為史書上對于納西族性格的記載可能與實際情況有所差異,歷史上納西族民族性格可能有以下兩種情況,其一,尚武但不至于像史書記載的“少不如意,相攻殺”;其二,由于當時納西族社會除了統治階層接受教育,多數納西族人不曾接受教育,尚武精神可能含有一定的野蠻性。
改土歸流之后記載麗江納西族的漢文獻中,不再有“相攻殺”、“相仇殺”的文字敘述,取而代之的是“性柔弱”、“生性懦弱”,我們認為這與清王朝推行的把儒家“夷夏之辨”、“以夏變夷”的傳統觀念上升為“華夷一體”、“中外一家”的新的民族觀有關,此時不再視少數民族為“蠻”、“夷”、“胡虜”,對少數民族的史書記載與以前的王朝有不同點也在情理之中,但是把納西族性格記載為“性柔弱”、“生性懦弱”與納西族人實際情況可能有差異的,因為清朝統治者是滿族,同樣也是少數民族,它提升了儒家“夷夏之辨”、“以夏變夷”的傳統觀念,但是作為統治者對“華夷一體”、“中外一家”的觀點,不可能完全贊同,在記載其他少數民族的資料中,把其他少數民族體現得懦弱一些,自然也在情理之中。
三、教育的大眾化使納西族人開始文武并舉
無論是史書記載有偏見,還是納西族人尚武精神中具有野蠻因素,受教育能使人開化,是不可否認的。麗江納西族木氏土司的統治在云南西北地區經歷了300多年的歷史,以及納西族人全民皆兵的記載,說明了納西族人歷來就是尚武的民族。
木氏土司極力學習漢文化,木氏家族的子弟想盡一切辦法學習漢文化,創造出大量的詩作,形成納西族文學史上的一個創作高峰,但在麗江納西族地區采取的卻是一種愚民政策,對文化學習進行壟斷,壓制老百姓學習漢文化,唯恐老百姓明天下理而反之。直至改土歸流后,納西族民間的教育狀況才有所改變,納西族的作家文學才從木氏土司的深宅大院走入中下層人民中,漢文化也才得以在納西族民間廣泛傳播,涌現了一大批中下層出身的作家。
清朝實施改土歸流之后,大肆強迫納西族人接受儒家文化。康熙三十九年(1700年),建立了麗江府學,從此,受教育的就不僅是土司家族了。雍正元年改土歸流后,麗江教育事業有了進一步的發展,到光緒年間,已有三個書院,義學三十一館。從改土歸流到清末一百八十年間,有許多人登科及第,不少文人的詩文有較高的造詣。清末民初,廢科舉,倡新學,麗江知識界不少知時識勢的人適應新時代潮流,積極主張學習科學,建立新學,于是在光緒三十一年(1905年),建立了麗江府中學堂(后來改為云南省立第六師范,不久又改為云南省立第三中學),還建立了麗江府高等小學堂。改土歸流使納西族地區教育面向大眾,“禮教”逐漸地把納西族從過去強悍的民情風尚中納入封建王朝的倫常道統之下,納西族人也把外顯的尚武精神融合到了文武并舉的發展階段。
四、結語
改土歸流使麗江納西族人認同中國感上升了,教育走向了群眾,也使納西族尚武精神從感性走向了理性化之路。相關納西族的文獻記載納西族人性格是否有誤差有待于研究者繼續探討,但是可以肯定納西族是尚武的民族,納西族沒有尚武的民族精神就不會有木氏土司的輝煌,也不會有麗江在1997年大地震之后的迅速重建。
參考文獻:
[1]謝本書,宋光淑,湯明珠.民族精神問題三論[J].云南民族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2004,(5):49.
[2]史繼忠.略論土司制度的演變[J].貴州文史叢刊,1986,(04):9.
[3]周俊華.歷史上納西族中國認同的發展歷程及其啟示[J].云南社會科學,2007,(2):98.
[4]王鐘翰.中國民族史[M].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94.
[5]明太祖實錄(卷26).中央史語所校印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