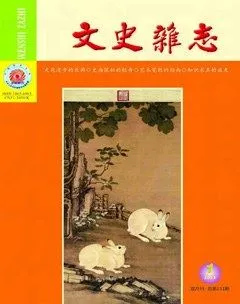峨眉圣鐘:銘刻晉商五百年的記憶
地處巴蜀大地之上的峨眉山,其魅力不僅僅因為它是佛教名山。一串五百年前出現在峨眉山下的山西商人的商旅足跡,亦令人為之欽佩和驚嘆!
一、鐘聲入耳覺清心
在峨眉山麓報國寺門前不遠處的鳳凰堡臺,有一處“圣積晚鐘”亭,亭內有一座通高2.6米,腹徑2.1米,唇厚0.2米,重達25000斤的青銅大鐘懸吊于中央,巍峨高聳。這座“圣積晚鐘”鐘趺十二葉,形狀如蓮瓣,每瓣之上分別鑄刻有“子丑寅卯辰巳午未申酉戌亥”十二地支,象征時空的周而復始,故又名“蓮花鐘”、“八卦鐘”。據該鐘鐘體銘文記載:鐘為明嘉靖四十三年(1564)鑄造,次年運至峨眉山虹溪橋打磨鑿字,明隆慶元年(1567)懸于圣積寺老寶樓中。其素有“巴蜀鐘王”之譽。
清代詩人譚鐘岳曾不辭辛苦慕名來到峨眉山,對這里的山川、里程、寺觀、方位、村舍、林泉勝跡、奇珍妙景均詳加考正,查閱典籍,廣征史料,櫛風沐雨,踏險涉幽,積三年之勞瘁,繪圖64幅,詠詩46首,并提出峨眉山“景之佳絕者有十”的精辟之見。“圣積晚鐘”即為十景之一。譚鐘岳還特意為其賦詩道:
晚鐘何處一聲聲?古寺猶傳圣積名。
縱說仙凡殊品格,也應如兒覺清心。
詩中提到的圣積寺,原為進入峨眉山的第一大寺,環境幽古。寺外有古黃桷樹二株,需數人才能合抱。從這首《圣積晚鐘》詩,可看出該景觀絕妙之處:不在古寺猶傳圣積名,而在鐘聲入耳覺清心。
在這尊大銅鐘之上,布滿密密麻麻的文字,讓人眼花繚亂。鐘體表面的上半部,在鐘體1/5處,是一周突起的鑄字(陽文);在此之下,即占鐘體4/5的面積上,則鑿刻陰文漢字,鐘體內外如同“蠶豆”大小的文字,鑿刻自公元281年到1555年前后1270多年間曾經資助峨眉山佛教發展的帝王、文武官員、豪商巨賈、善男信女和鑄造此鐘的僧俗名諱以及《阿含經》和鐘銘佛偈。在這多達6萬余言的字里行間,有這樣一段獨特的銘文:
山西平陽府蒲州山陰王府儀賓姬紹明朱氏施銅五百斤、紋銀五十兩;臨汾縣信士徐正志己丑年六月父徐鉞謝氏謝爵楊氏謝祿張氏喬氏謝道郭氏□□□施錫五十斤、米三石;蒲州信商張世科溫氏溫梧溫一元施銀三十兩□□□;平陽府蒲州信商郝九思詹氏男郝鼎郝溢施銅六百斤、米六石;臨汾縣東陽廂亢真亢得雨亢國用郭氏施銀□□□十二月十一日子時男亢正湖庚申年施銀五十兩,長治縣信商孟朝卿丙戊年四月二十五丑時劉氏妙賢夫婦庚寅五月初九亥時父孟庫甲寅四月二十八日界定法應施銅三百斤、紋銀三十兩,信士李重丙子年二月毛氏夫婦施銅二百斤、紋銀三十兩、錫五十斤、米三石□□□。
這段五百年前的銘文向我們傳遞出的一個信息是:銅鐘之上,諸如張三李四王氏數萬人的布施者大都沒有冠以地名,而且布施的金額也很少;唯獨山西商人包括長治商人能占據一塊“堂而皇之”地方,顯見晉省商人的“財大氣粗”。
二、晉商殷富甲天下
最早去蜀地的山西人,是戰國時治理都江堰水患的解州李冰父子。李冰時任蜀郡守。解州李氏后裔族譜中有“始祖李冰赴蜀治水”的記載。之后,歷代便有人往來于蜀、晉之間。明萬歷《四川鹽法志》說:“川中民貧,稱鹽商者,多為山陜之民”。清康熙《四川總志》記載:“人民鮮少,貢賦無多,間有商賈往來,俱隸籍秦晉。”《成都史話》寫道:“山西人在成都開設的票號,著名的有日升昌、蔚豐長、蔚豐厚、蔚長厚、協同慶等,專營銀錢匯兌、存放款,在省內外商業中財力雄厚。”《成都城坊古跡考》也記:“山西票號清初時已設立22家,分布在商業異常繁華的春熙、暑襪、中市等多條街巷。”這只是晉商經營票號商人的情況,當然還有晉商中的鐵貨商、皮貨商、絲綢商、糧商、鹽商在四川大地的生意同樣做得紅紅火火。
明朝人李夢陽在其《空同集》這樣寫道:“為商者,嘗西至洮隴,逾張掖、敦煌,窮玉塞,歷金城,已轉而入巴蜀。沿長江、下吳越,已又涉汾晉。”明嘉靖《宜府鎮志》寫道:“大市中賈店鱗比,各有名稱,潞州綢鋪、澤州帕鋪、臨清布鋪、絨綿鋪、雜貨鋪,各行交易鋪沿長四五里許,賈皆爭居之。”這些來自山西的同鄉商人們從明朝開始,為“迎神庥、聯嘉會、襄義舉、篤鄉情”,在巴蜀大地上廣泛營建自己的同鄉會館,僅僅是晉商建立的會館就達十處之多,如成都古中市街皮貨商的“山西會館”,重慶靠近太平門碼頭的販運絲綢商的集散地“山西會館”和九龍坡區走馬鎮上的“晉商關帝廟”,敘永縣城內的鹽店街鹽商的“山西會館”等等。
王學梅先生在《四川會館》記曰:“明清商業和市場的發展實質上與長途貿易發展密不可分,以致形成著名的十大行商商幫,為山西、徽州、陜西、福建、廣東、江右等。”“四川敘永縣城內的鹽店街,由山西、陜西鹽商集巨資,拆除原關帝廟重建。”在如此眾多的晉商旅居巴蜀經營商業的歷史軌跡中,自然包括有“圣積晚鐘”上所銘刻的“蒲州山陰王府,臨汾縣信士徐正志、徐鉞謝氏謝爵楊氏,蒲州信商張世科、溫氏,平陽府蒲州信商郝九思、詹氏,臨汾縣東陽廂亢真、亢得雨郭氏,長治縣信商孟朝卿夫婦、信士李重毛氏”等。尤其是亢真、亢得雨、亢國用的山西亢氏家族,當時大名鼎鼎,巨富天下。清初《康熙南巡秘記》寫道:“亢百萬,晉商魁首,家臨汾,宅茅連云,苑如世家。”《清裨類鈔》載記:“山西富室,多以經商起家,亢氏號稱數千萬兩,實為最巨。”清人馬國翰的《竹如意》也稱:“山西亢氏,家巨富,倉庚多至數千,人以百千呼之。”
當年,銘刻在銅鐘之上的旅川山西商人,能拿出如此巨額資財積善功德,他們是鹽商,還是絲綢商?潞州長治縣的“孟朝卿夫婦、李重毛氏”是鐵貨商,票號商,還是皮貨商?五百年前的晉商到底有多富有?明萬歷朝工部左侍郎沈思孝在其《晉錄》一文中其實已有了回答:“彼時海內殷富,平陽、潞、澤豪商甲天下,非數十萬不稱富。”這就是晉商的富有,潞商的富有。沒有數十萬的白銀,你就不要稱自己富有,這就是明萬歷朝“富有”的標準。
五百年來,響亮、渾重、悠揚,遠播環宇的銅鐘“龍吟”之聲,聲聲不息地傳頌著峨眉山的神奇,傳頌著綿延不斷的巴蜀歷史人文,也傳頌著曾經出入“天府之國”的“晉商”的富有、虔敬和誠信。
作者單位:《紅色太行》編輯部(長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