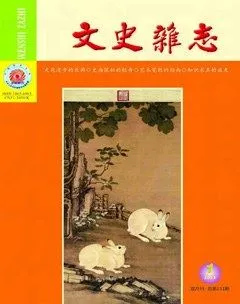名人與口吃
口吃,是一種習(xí)慣性的言語缺陷,指說話字音重復(fù)或詞句中斷,故又稱“重言”或“結(jié)巴”。如戰(zhàn)國的韓非,漢代的司馬相如、李廣、周昌、魯恭王劉馀、揚雄,魏晉南北朝的魏明帝曹叡、鄧艾、孔覬、焦度、崔慰祖、盧柔,隋唐五代十國的盧楚、陸羽、孫晟,宋遼金元的崔公度、陳繹曾、家安國。近現(xiàn)代名人王國維、劉師培、柳亞子以及南社諸人、馮友蘭、顧頡剛、陳登恪、王蕓生、蕭乾等都患有口吃。
王國維(1877—1927),字靜安(庵),又字伯隅,號觀堂、永觀等,浙江海寧人。王國維是近代中國享有國際盛譽的杰出學(xué)者,被學(xué)界共推為學(xué)術(shù)巨擘,世人推允為國學(xué)大師。1911年11月,王國維隨同羅振玉(1866—1940)旅居日本京都,直至1916年2月才返歸故國。
那時,日本學(xué)者梅原末冶常常出入羅振玉家。他回憶說:“羅先生家里人多得簡直不可思議,其中有一位其貌不揚,說話口吃,看起來倒是讀書人的樣子。他好像非常專心地寫著什么,這人就是王先生。”內(nèi)藤乾吉也回憶道:“那時我上小學(xué),羅振玉先生和王先生常到我家來,因我是小孩子,所以沒接待他們。我的房間在客廳旁邊,經(jīng)常能聽到他們的談話聲。我記得有時我從隔扇之間窺視,那時,羅先生清瘦如鶴,相比之下王先生色黑,用日語說話,可是不善談吐,而且口吃。”神田喜一郎說:“王先生會一點日語,有時當(dāng)羅先生的翻譯,可是不太流暢而且口吃,不太好懂的。羅福萇當(dāng)翻譯的話就非常好懂。”他們所講的“王先生”就是王國維。[1]
畢樹棠曾經(jīng)參加了清華國學(xué)研究院1925年秋的聚餐,并且見到了時任研究院導(dǎo)師的王國維。他撰寫回憶文章也提到王國維“講話不利落,似乎還有點口吃”。商承祚(1902—1991) 曾經(jīng)問學(xué)于羅振玉和王國維。他在晚年的回憶文章中說:“王為浙江海寧人,談吐時滿口鄉(xiāng)音,聞?wù)叨嗖灰锥忠虿婚L于口才,言時期期艾艾,與其文筆,判若兩人”[2]。不過,王國維的受業(yè)弟子如劉盼遂、吳其昌等的回憶文章卻未言及先生的“口吃”。他們能隨堂記錄王國維的講課內(nèi)容,這說明王國維用國語講課完全能達(dá)意。
劉師培(1884—1919),字申叔,江蘇儀征人。劉師培是著述甚豐、英年早逝的天才學(xué)者。王森然在《近代二十家評傳》一書中講他:“為人雖短視口吃,而敏捷過諸父。一目輒十行下,記誦久而弗渝”。1917年秋,劉師培應(yīng)蔡元培之邀,任北京大學(xué)文科教授,兼任文科研究所國文門指導(dǎo)教師。他因為口吃,又有肺病,課堂講授效果并不好;但靠編講義彌補,還是受到學(xué)生的歡迎。蔡元培在《劉君申叔事略》一文中,對此亦多所肯定:“君(指劉師培)是時病瘵已深,不能高聲講演,然所編講義,元元本本,甚為學(xué)生所歡迎。”
柳亞子(1887—1958),原名慰高,改棄疾,字亞子,江蘇吳江人。柳亞子是著名的愛國詩人、南明史家,南社創(chuàng)始人之一,曾任中央文史研究館副館長 (1951.7—1958.6)。同為南社社友的鄭逸梅(1895—1992)回憶說:“柳亞子的口吃,的確是很嚴(yán)重的,越是急,越是說不出話來。所以他寧可寫長長的文章,卻怕作短短的講話”[3]。在南社成立大會上,柳亞子、朱梁任因詞學(xué)見解不同,以至與龐樹柏、蔡哲夫爭論起來。柳亞子、朱梁任兩人都有口吃的毛病,自然在爭論中落于下風(fēng)。柳亞子氣得大哭,罵對方欺人太甚。龐樹柏連忙道歉,這才算了事。這件事情,見于柳亞子的《南社紀(jì)略》。說來也湊巧,南社中竟然有多人患口吃,如黃摩西、楊伯謙、姚勇忱等。柳亞子對此也不忌諱,他在悼念姚勇忱的詩中,就有“口吃憐同病,名高竟殺生”之句。
馮友蘭(1895—1990),字芝生,河南唐河人,現(xiàn)代新儒家代表人物之一,“新理學(xué)”的創(chuàng)立者。鄭朝宗在《馮友蘭芝生先生》一文中,回憶了他在清華大學(xué)初次見馮友蘭的情形:
這一次的見面,芝生先生所給我的印象是一個具有儉樸、靜穆、和藹等德性的學(xué)者的印象。但同時我也發(fā)現(xiàn)了一件極不愉快的事,那就是芝生先生口吃得很厲害。有幾次,他因為想說的話說不出來,把臉急得通紅。那種狼狽的情形,很使我們這班無涵養(yǎng)、無顧慮的青年人想哄笑出來。我常想:像芝生先生那樣的嚴(yán)肅端正的人,會有這樣的可憎惡的毛病,真是太不合適。因此,便也時常想到《論語》上的一節(jié):“伯牛有疾,子問之,自牖執(zhí)其手,曰:‘亡之命矣夫!斯人也而有斯疾也!斯人也而有斯疾也!’”像芝生先生那樣的有威儀的人,而會有這樣的“不漂亮”的口吃,真要教我們敬愛他的人大呼:“斯人也而有斯疾也?斯人也而有斯疾也?”了。
葉公超每次遇見馮友蘭,很喜歡拿馮友蘭的口吃打趣,往往誑稱自己又忘記了馮家的門牌號碼。馮友蘭信以為真,必告之“二二二二……二號”,七八個“二”乃止。馮友蘭上課時點名,念到顧頡剛之名時,或“咕唧咕唧”半天而念不出“剛”字;念墨索里尼時,亦必“摸索摸索摸索”許久。這些事情,見于其門生程靖宇《馮友蘭結(jié)結(jié)巴巴》一文。
顧頡剛(1893—1980),江蘇蘇州人,我國現(xiàn)代著名的歷史學(xué)家、民俗學(xué)家。他也有口吃的毛病,再加上濃重的蘇州口音,上課時一般同學(xué)都不易聽懂。因此,顧頡剛便揚長避短,在北京大學(xué)和燕京大學(xué)等校上課時,很少侃侃而談;除了發(fā)給學(xué)生大量資料外,大部分時間都在寫板書。錢穆說:“(顧)頡剛長于文,而拙于口語,下筆千言,汩汩不休,對賓客則訥訥如不能吐一辭。聞其在講臺亦唯多寫黑板。”他的板書內(nèi)容是精心準(zhǔn)備的讀書心得,往往很有見解,對學(xué)生很有啟發(fā)。所以時間一久,大家也自然認(rèn)可了他這種獨特的教學(xué)方法,覺得貨真價實,別具一格。
1923年5月,顧頡剛發(fā)表《與錢玄同先生論古史書》(后收入《古史辨》第一冊),認(rèn)為三皇五帝等古史系統(tǒng)是到漢代才“層累地造成的”。他在對禹作考證時,曾以《說文解字》訓(xùn)“禹”為“蟲”作根據(jù),提出禹是“蜥蜴之類”的“蟲”的推斷。這一推斷被戲稱為“大禹是一條蟲”。此論一出,隨聲附議者不少,但也有人嗤之以鼻。1935年,魯迅創(chuàng)作小說《故事新編·理水》,里面講到一幫學(xué)者爭論“大禹治水”的問題。魯迅抓住顧頡剛說話口吃等缺陷,作了如下描寫:
“這這些些都是費話”,又一個學(xué)者吃吃的說,立刻把鼻尖脹得通紅。“你們是受了謠言的騙的。其實并沒有所謂禹,‘禹’是一條蟲,蟲蟲會治水的嗎?我看鯀也沒有的,‘鯀’是一條魚,魚魚會治水水水的嗎?”他說到這里,把兩腳一蹬,顯得非常用勁。
陳登恪(1897—1974),字彥上,江西義寧(今修水縣)人,著名古典文學(xué)研究專家。詩人陳三立第八子,史學(xué)大家陳寅恪之弟。其好友李璜回憶,陳登恪“談?wù)摃r略有口吃之病,然頗多風(fēng)趣,形容細(xì)致,令人解頤”[4]。
王蕓生(1901—1980),天津靜海人,我國老一輩新聞工作者,著名愛國人士,曾任《大公報》總編輯、社長,第一屆全國政協(xié)委員,第二、三、四、五屆全國政協(xié)常務(wù)委員,第一、二、三、四、五屆全國人民代表大會代表,中華全國新聞工作者協(xié)會副主席。唐振常的回憶文章說:“蕓老談話,略顯口吃。每議論時事人物,掌故連篇,妙語如珠,道出他精辟的看法,娓娓而談,聽者心領(lǐng)神會,不覺忘倦,不感到他的口吃。”[5]
蕭乾(1910—1999),蒙古族,原名蕭炳乾,北京人,名記者、作家和杰出的文學(xué)翻譯家,曾任中央文史研究館館長(1989.4—1999.2)。他在《我愛新聞工作》一文中,直言不諱地說:“我在沒有做記者前,是個結(jié)巴,記者工作迫使我改了這個毛病。”
注釋:
[1][日]神田喜一郎等:《追想王靜安先生》。陳平原、王楓編,《追憶王國維》,中國廣播電視出版社,1997年,第387,388,389頁。
[2]商承祚:《關(guān)于王國維先生之死》,《晉陽學(xué)刊》1983年第3期。轉(zhuǎn)引自《追憶王國維》第269頁。
[3]鄭逸梅:《南社叢談》。《鄭逸梅選集》第一卷,黑龍江人民出版社,1991年,第11頁。
[4]李璜:《憶陳寅恪登恪昆仲》,《大成》第49期,1977年12月。轉(zhuǎn)引自《追憶陳寅恪》,北京:社會科學(xué)文獻(xiàn)出版社,1999年,第13頁。
[5]唐振常:《王蕓老十年祭》,《川上集》,三聯(lián)書店,1966年,第348頁。
作者:四川大學(xué)古籍整理所(成都)教授、
歷史學(xué)博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