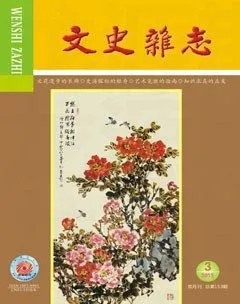《論語》“義”字考釋
在孔子學說中,雖然“仁”與“禮”具有核心范疇的地位,但是“義”在其思想學說中,也同樣具有不可忽略的地位。在《論語》中,孔子對“仁與義”、“禮與義”以及“義與利”都作了解釋。由此我們可以看出,“義”在孔子學說中的真實內涵及其意義。
程頤認為,孔子在《論語》中,說仁的時候,并沒有“仁義”并提;只有到了孟子時,方才“仁義”并提。[1]事實確實如此。盡管如此,孔子《論語》中“義”,已經被賦予了新的內涵,在孔子學說中的地位同樣不可漠視。
大家知道,在孔子的學說中,仁和禮是兩個不可分割的內容,是體和用的關系,仁為體,禮為用。相對而言,仁側重從人的內心來講人的道德品質與人格理想,而禮側重從外在的人的角度來講約束人的行為規定和最終社會理想,兩者表里如一,是一而二,二而一的關系。而“仁”與“禮”糅合之后的產物便是“義”,可以說,“義”是對過于理想的“仁”和過于現實的“禮”的一種折中;雖然“義”早于禮,是禮制興起的源頭之一,但在此時已被孔子賦予了新的意涵。
“義”主要有以下含義:1.義為儀。《說文》:“義者,己之威儀也。”《尚書大傳》“尚考太室之義,唐為虞賓”,鄭玄注曰:“義,當為儀;儀,禮儀也。”2.適宜、適當。《釋名·釋言語》:“義,宜也。裁制事物使合宜也。”3.道德原則的總稱。《孟子·公孫丑上》:“其為氣也,配義與道。”趙歧注曰:“義謂仁義,所以立德之本也。”4.有利、利益。《墨子·經說下》:“義,利也。”由此可以看出,“義”從祭祀禮儀之威儀的本義,被引申為合宜、有利等倫理道德的意義;而孔子所言的“義”,其實便是通過個體的自覺來約束自己的行為,使之合乎禮制。“義”成為一種行為規范和道德、價值的原則和標準。
可以說,“義”作為孔子仁學、禮學相互糅合的產物,仁與禮合一的具體體現,它既有仁的內在道德思想的規定性,又有外在禮儀的規定性。《禮記·禮運》說:“禮也者,義之實也。……義者,藝之分、仁之節也,……仁者,禮之本也,……為禮不本于義,猶根而弗種也。”《禮記》乃孔門后學所為,他們對義與仁、義與禮關系的解釋,其實便是對孔子思想所作的最好注腳。
義在《論語》中有很多記載,如:
子曰:君子之于天下也,無適也,無莫也,義與之比。(《里仁》)
不仕無義,長幼之節,不可廢也,君臣之義,如之何其廢之?……君子之仕也,行其義也,道之不行,已知之矣。(《微子》)
君子喻于義,小人喻于利。(《里仁》)
君子義以為上。君子有勇而無義為亂,小人有勇無義為盜。(《陽貨》)
君子義以為質,禮以行之,孫以出之,信以成之。君子哉!(《衛靈公》)
子曰:“德之不修,學之不講,聞義不能徙,不善不能改,是吾憂也。”(《述而》)
由上我們可以看出,“義”不僅被作為人們客觀行為的合理價值要求,也被作為主觀道德修養的基本準則。經統計,在《論語》一書中,幾乎都是將“義”作為道德價值判斷的標準。行為是否合“義”,是孔子衡量一個人是否符合社會政治、倫理道德規范的道德準則。他認為君子應當“義以為上”、“義以為質”,從人的內在的道德修養來說,“義”被看成是僅次于作為最高道德標準“仁”的道德價值范疇。在《論語》中,孔子將之作為道德人格典范的“君子”所具有的基本品質。
在孔子看來,“義”的最高境界,便是“中”;行為合乎時宜是中,故孔子時、中連言,講“君子而時中也”(《禮記·中庸》)。時中,究其極,就是中。孔子講“無可無不可”(《論語·微子》)和“過猶不及”(《論語·先進》),都是中之確解。孟子以權喻中(《孟子·離婁上》),最為明通。后來子思作《中庸》,在此基礎上,創中和概念,這是對“禮之用,和為貴”思想的最好詮釋。馮友蘭先生也說:“儒家所謂‘義’有似乎儒家所謂‘中’,辦一件事,將其辦到恰到好處,就是‘中’。”[2]孔子78d0e1461dd349c235bd7fab85d915f1說:“中庸之為德也,其至矣乎!民鮮久矣。”(《論語·雍也》)盡管《論語》中“中庸”僅此一見,使我們對其內涵不得其詳,但是從孔子溢于言表的贊美中可知“中庸”乃至高道德品質,而這便是“義”的最高境界。而中庸之德在孔子看來只有君子、圣人方可達到。
由于在孔子的時代,雖然禮樂大壞,但總的來看,禮制依舊在社會生活中扮演著重要的角色,發揮著巨大的作用。故維護和興復禮制,依舊是孔子全力以赴要做的事情。雖然孔子提出了“義”這個貫注著仁與禮相互規定的道德價值標準,相對于“仁”來說,它更容易得到實踐,但他依舊將希望寄托于通過內在“仁”來完成對“禮”的踐履。所以孔子在《論語》中還是較少地提到了“義”,更不要說是“仁義”并提。有人統計在《論語》中,孔子提到“義”共21章23次,遠遠低于提到禮和仁(109次)的次數。[3]如果說被孔子賦予新內涵的“義”,還不太適用于孔子那個禮制還健在的時代,那么到了孟子禮壞樂崩、人人多言“利”的時代,具有折中“仁”與“禮”的“義”,就開始顯現出它的適應性和價值來。
在孟子學說中,已將“仁義”并提,由此看出孟子將“義”提升到與“仁”一樣的地位,使二者共同成為評判人的道德行為的價值標準,且為人的內在道德品質。如當前賢告子說“仁,內也,非外也;義,外也,非內也”(《孟子·告子上》)時,孟子便予以反對,認為“義”和“仁”一樣,都是人生來所固有的道德品質,所謂“仁義禮智,非由外鑠我也,我固有之也”(同上)。后來宋明理學家們對“義”的闡發,皆由此而來。
孔子對“義”的高揚,其實是對傳統社會禮制和道德倫理的認同和肯定,希望通過糅合改造的方式,來發掘傳統文化“仁”、“禮”的魅力,使之在新的社會狀態下,發揮應有的作用。對于義利之間,他認可個人追求私利的行為,但反對為了追求私利而破壞社會和群體利益的行為,即漠視公共的“義”。他說:“不義而富且貴,于我如浮云。”(《論語·述而》)后來孟子強化了孔子的這一思想。他對梁惠王專言私利的行為,批評說:“王何必曰利?亦有仁義而已矣”(《孟子·梁惠王上》)。這些都反映了孔孟主張義利進行辯證的統一,而不是執其一端,不顧其余;反映了孟子在義利觀上,秉承了孔子所言的“中庸”思想。
注釋:
[1]參見《程氏遺書》卷四,中華書局1981年版,第74頁。
[2]馮友蘭:《中國哲學之精神》,中國青年出版社2005年版,第15頁。
[3]參見閻合作:《<論語>說》,河南人民出版社2006年版,第196頁
作者:北京師范大學歷史學院講師,博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