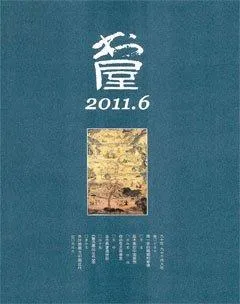鮮為人知的李莊才女——游壽
抗戰期間,四川南溪縣一個叫李莊的偏僻小鎮聚集了一批著名的文化教育機構,如中研院史語所、中央博物院、中國營造學社、同濟大學等,后來這里被稱為“抗戰時期中國四大文化中心之一”。李莊的一大批文化精英中,有三名才華出眾的女性頗為引人注目,她們是營造學社的林徽因、中央博物院的曾昭燏和史語所的游壽。如今,林徽因和曾昭燏(清代重臣曾國藩二弟曾國潢的重孫女,時任中央博物院籌備處總干事,新中國成立后出任南京博物院院長)的名字與事跡較為人熟悉,而游壽則鮮為人知。
游壽字介眉、戒微,1906年出生于福建霞浦縣一書香世家。其高祖游光繹為清乾隆己酉進士,乃林則徐的老師;曾祖游大琛為清道光丙戌進士,是林則徐的同學;父親游學誠,清光緒辛卯舉人,后創辦女子高等小學,親任校長。游壽從這所小學畢業,十四歲考入福建女子師范,得到老師鄧儀中(鄧拓之父)的指點和賞識。父親逝世后,她繼任父親創辦的女子高等小學校長之職。游壽二十歲時已被譽為“閩東四才女”之一,和同是福建籍的冰心、林徽因、廬隱三位遐邇聞名的才女齊名。1929年具有厚實國學根底的游壽考入南京中央大學中國文學系,與同年考人的曾昭燏一起成為胡小石教授的女弟子。大學畢業,她到廈門集美師范任國文教員,1934年8月考入金陵大學文科研究所,再度師從胡小石教授攻讀碩士學位,從事金文、古文字音韻研究,先后完成了《先秦神道設教觀》、《先秦金石甲骨文獻資料研究》等論文。這一期間,在研究金文、古文字學的同時,游壽在胡小石指導下鉆研書畫藝術,其高超的水平為書畫界公認。因胡小石的恩師李瑞清是清末碑學書派代表人物、一代書畫家巨擘,而游壽天資聰穎,書法又深得導師胡小石的真傳,遂成為這一書派第三代的一位代表人物。
游壽的同窗好友曾昭燏赴英國倫敦大學學成回國后,1942年受李濟聘請到李莊中央博物院籌備處任總干事。游壽與曾昭燏情誼深厚,由于曾的盛情邀請,時在四川江津四川女子師范學院中文系任講師的游壽于這年1O月來到李莊,加盟中博院籌備處。游壽參與了中博院在李莊和重慶兩地舉辦“史前石器及周代銅器展覽”的工作,一年后經李濟與傅斯年協商,游壽于1943年8月21日由中博院轉入史語所。在當時專業人員流失的背景下,調游壽去史語所,本是為了人才配置上的一種補缺和救急,游壽也愿意去這樣的機構潛心學術研究,遂改名游戒微。始料未及的是,她踏入史語所,就與所長傅斯年發生沖突,之后厄運連連,不得翻身。
如今不少涉及史語所的文章、著述中,對傅斯年的功績都稱贊有加,或許出于為尊者、賢者諱的緣故,很少提及傅的缺點和錯誤,這是不全面的,盡管和傅的巨大貢獻相比,他的缺點和錯誤是次要的。傅斯年創建史語所,付出了極其艱辛的勞動,他培養和提攜了一批優秀的青年人才,這些都是事實,但他脾氣暴躁,作風霸道,身上的霸氣和才氣可謂并駕齊驅,史語所的人對他敬之愛之畏之,私下里稱他“傅老虎”,他把史語所當做自己家中的“一畝三分地”,唯我獨尊,黨同伐異,容不得不同觀點、學派,傷害了一些好人。游壽不幸便是撞上槍口的一個。性格狷介、脾氣暴躁的傅斯年在學術上存有嚴重的門派之見,向來看不起儒林中沒留過洋的本土派。游壽師從胡小石,走的正是金陵“舊學”之路,在傅眼中這條學術研究之路恰恰是歧途。游壽到史語所后,傅斯年分配她去圖書室管理圖書,并嚴令其老老實實閉門讀書,三年之內不許寫作或發表文章。據說這是傅斯年對初進史語所的青年學者定下的土規矩,決不允許越雷池一步。更有甚之,好像要有意羞辱游壽一樣,原先的圖書管理員那廉君比游壽小三歲,只是中學畢業,無論資歷、學歷、才氣都無法與游壽相比,但此人長期擔任傅斯年的行政助理即秘書一職,傅斯年有意對游壽降格使用,將她排名在那廉君之后。那廉君本人還有點自知之明,感到這樣做不妥,于8月21日致信傅斯年:“聞本所本年度第二次所務會議報告事項中‘借調中博院游壽女士為圖書管理員’一案有‘名次在那君之后’一語,竊以為未便,乞收回此意。”但傅斯年不理會,堅持表示游壽新來所里工作,其名次必須往后排,且只許老老實實閉門讀三年書,不準擅自著書立說。雖說論資排輩是史語所的慣例,但這樣對待游壽,傅斯年暴露出一種私心,未免有失公允。游壽個性剛烈,才高氣傲,哪里接受得了傅斯年這種“教父”式的訓誡,一股叛逆精神在她心中萌生、涌動。一方面她青燈黃卷,坐擁書城,認真管書讀書,另一方面她突破傅斯年設下的禁區,暗暗下功夫寫作,準備向傅斯年叫板。只半年左右,她便完成了《金文策命文辭賞賜儀物》、《漢魏隋唐金石文獻論叢》等學術論文,還寫出了《書苑鏤錦》、《山茶花賦》、《山居志序》等文采斐然的散文。其實早在來史語所之前,游壽就完成了學術價值相當高的《李德裕年譜》等論著,她涉獵的領域廣博,除金石考證外,在經學、文學研究方面也有較深的造詣,其水平足可和史語所一些權威大腕媲美。然而此時她身處困境,遭人冷眼,心情頗為悲涼。一天,她大筆勁書“海嘯樓”三字,既展現胡門弟子出色的書法藝術,也寫出了自己心中那股壓抑已久的山呼海嘯般的情感。須知,游壽青年學生時代就灑脫不羈,極具個性,她在中央大學學習時,有一位講樂府通論的教授叫王易,字曉湘,博學而訥于言詞,學生多以聽其課為苦事,善謔的游壽便擬《敕勒歌》之體嘲道:“中山院,層樓高。四壁如籠,烏鵲難逃。心慌慌,意忙忙,抬頭又見王曉湘。”聞者無不大笑,游壽口無遮攔之性格由此可見一斑。而這種性格在史語所這塊地盤必然會和傅斯年的風格發生碰撞,其遭受厄運也就在所難免了。
1944年6月,由于房屋糾紛一事(史語所地處李莊板栗坳,房屋緊缺,不少人為之困擾),人微言輕的游壽不得已而采取“粘揭帖”(貼小字報)的激烈舉動。在史語所這是前所未有之事。6月21日,史語所致函游壽:“前日見揭帖,深感悚異,執事如以為不可,一言即決,何至出此類揭帖。今既如此,只有與王君對換房屋,并無他法,即希照辦。”可見此種越軌做法引起傅斯年的吃驚與惱怒程度,也更加重了游壽心中的郁悶情緒。
由于游壽桀驁不馴,不斷反擊,時間一長,迫使傅斯年不得不正視這位性格剛烈、不讓須眉的女子;同時,也由于游壽的同窗好友曾昭燏的說情(曾昭燏的哥哥曾昭掄和傅是連襟,而且,傅斯年夫人俞大綵的母親曾廣珊是曾國藩的孫女,與曾昭燏的祖上系同一家族),傅斯年準備對游壽網開一面。1945年2月16日他給曾昭燏寫信:“前談游戒微先生事,最終結論仍以前法為妥,即改任為助理研究員,擬在開會時特別申請以第三年論,若兩年內游先生寫成著作,即可討論升副研究員,不待滿四年也。”這一讓步雖是有限度的,但畢竟比先前僵硬的規定要靈活、寬松一些。然而此時游壽已是跨入四十歲的中年女性,老一輩學者在這個年齡段早已成為教授或研究員了,懷才不遇、時不我待的她已不屑于接受傅斯年的這一姍姍來遲的“寬宏大度”,有心沖破樊籬,去實現自己的志向與價值。她作《伐綠萼梅賦》,借無端遭劫的綠萼梅比喻命運對自己的不公:“繽紛未據要路,且非當門。急斧斤以摧枝,雜畚插而鋤根。何藩籬之森固,戕嘉木之天年。恣榛莽之暢茂,任蔓草以袤延。……未是上林紫蒂,春風早沾;翻似丹嶺綺青,王孫卻伐。望東閣兮,彷徨撫余襟兮,哽噎。”1945年2月21日,即在傅斯年給曾昭燏寫信后的第五天,游壽給傅斯年寫了一張假條:“因舊疾復發。又因家鄉淪陷,暫欲赴渝一行,未完工作擬另派人,或準予假,乞請裁奪。”
游壽這次去重慶待了四個月,其間曾到中央大學國文研究所短暫工作,至該年7月中旬才回到李莊。為此傅斯年等人對她感到不滿,有所責備。8月25日,對此種責難顯然不服氣的游壽再次致信傅斯年:“年來受閑氣蓋平生未有,常恐冒瀆神聽。然以防微杜漸,聊試一鳴,君子不欲高上人,固不與所中舊人尋仇。”傅斯年回信表示:“一切照前約之辦法,您以舊名義未作研究,部分之管理事項可不擔任,一切均交張政烺先生接收。移交之事,乞速辦。”這樣,游壽總算可以名正言順地脫離圖書室雜務,集中精力搞研究了。
接下來的這些日子,恰逢日本投降,抗戰勝利,各內遷機關紛紛忙于返回南京的準備工作。1946年春節剛過,游壽致書傅斯年:“《冢墓遺文史事叢考》已于(民國)三十年草訖,呈送岑仲勉、陳槊兩研究員,指示之點,亦已改定,極想早日付梓,如何呈交,請核示。”來李莊三年多,此乃游壽感覺最有意義的一件事,她希望早日在史語所的刊物上見到自己的學術成果。
然而世事難料,3月5日,游壽又致信傅斯年:“本所還都計劃已奉命在五月以后,職夏日多病,欲先下渝覓交通機會,至都日既向所中前所派人員報到,并聽其指命,伏懇賜準。”因傅斯年這時忙于北京大學復員接收工作(后出任北大代理校長),游壽此信同時致代理所務工作的董作賓。除了身體原因之外,究竟為了什么事,使游壽放下手中尚未付梓的文稿,匆匆先去重慶?其中隱情他人一時無法得知。半個月后,游壽在重慶再次致信傅斯年:“本所復員在夏天,職每年夏令必病,萬不得已,呈請下渝自覓還都機會。頃抵渝已一周,正極力設法交通工具,倘得先行至京之日,即向所中所派接收人石璋如先生報8457dc8f6d9f7241ee7e991cf33de954bbc0239fbb19e414cda195f64fd2032d到。”傅斯年接到第一封信后,立即明確無誤地致信董作賓:“游竟自行離所,應將其免職。此人不能再留其在所。弟當時找她,大失策。甚對本所不起。”當又接到游壽第二封信時,傅斯年心中的怒火實在無法遏止,于3月27日措辭嚴厲地給游壽回函:“執事未得董先生同意,自作主張,自行離所,應自離李莊之日起,以停止職務論。”四天后,對被就地停職而感到驚詫的游壽即回信:“頃奉手諭,不勝駭愕。職此次離所彥堂先生曾批示‘暫作請假’。職在所中前后四年,自揣無過,倘鈞長以離所還京太早者,亦可即返李莊。”同時,游壽又直言不諱致信董作賓:“此次請示先行歸京經過,不圖先生背后報告,傅所長有停職通知。今且忍耐不言,頃再緘倘以為不得擅行還京者,即重返李莊。”從游壽的信函來看,董作賓一開始曾同意游壽請假去渝,后來面對惱恨不已的傅斯年,董作賓唯恐傅對自己產生不滿,遂改口否認,不愿為此事擔肩胛。游壽認為請假之事既已獲董作賓批準,而董對傅卻“背后報告”,矢口否認,落井下石,導致傅錯誤地將她停職,憤慨之情盡現信中,“今且忍耐不言”,言外之意待重返李莊后再辯明是非。這樣,游壽原本早已得罪傅斯年,復又開罪董作賓,史語所的當家人如何會退讓呢?傅、董聯手對付游壽是必然的了。這樣的結果也是游壽剛烈的性格所鑄成,如果換另一種委婉的方式寫信,暫且低頭,委曲求全,事情結局或許會有所改變,但不愿看風使舵、趨炎附勢的游壽怎么會這樣做呢?于是,事情急轉直下,不可能再有轉機了。
不僅如此,傅斯年一不做、二不休,讓董作賓以史語所名義致函游壽:“所著《冢墓遺文史事叢考》一書,本所不能付印,可由執事自行設法出版;所任別存書庫圖書管理員一職,業經通知停止,此職亦即裁并,應照章發給遣散費三個月。”史語所此時采用石印方法出版學術刊物《六同別錄》,游壽的一篇論文本已編妥付印,但霸氣十足的傅斯年下令將她的文稿從已印出的刊物中撕掉。因刊物封面也印有游壽文章的標題,傅斯年不顧一切又下令將封面全部撕毀,重新排版、印刷、裝訂,務必不留下游壽的一點痕跡。至此,游壽在史語所四年來唯一將發表在所里學術刊物上的文章和署名徹底消失了。游壽在數重打擊下依然一身傲骨,沒有示弱,她義無反顧地與傅斯年和史語所決裂,1946年10月4日她致信傅、董,擲地有聲日:“平生志在為學,豈效區區作駑馬戀棧耶!豈效無賴漢專以告訟為事,即日離渝歸東海。”脫離史語所后,她將名字改回原名游壽。
從此,游壽再也沒有回過李莊那片多情而憂傷的土地。
游壽和傅斯年的這段恩怨糾葛,至今尚有若干細節、過程不甚清晰,需要進一步考證挖掘史料。客觀地看,游壽本人的剛烈性格,我行我素,不善于妥協和周旋,有些事情處理過于簡單莽撞,對矛盾加劇有一定關系,但是從矛盾前后發展的整體脈絡來看,主要責任顯然在于傅斯年。傅的性格暴躁,雙方確實存在性格沖突,但此事不能僅用性格沖突來作解釋。更要害的問題在于傅斯年嚴重的門派之見和專制作風。有些知識分子對外部、對上司極力爭民主、爭自由,頗有美名,但對內部、對下級卻喜歡專制、喜歡獨裁,還偏偏文過飾非,不愿承認。以傅斯年來說,他在國民參政會上曾公開炮轟孔祥熙,導致孔的倒臺;又曾炮轟宋子文,發表檄文《這個樣子的宋子文非走不可》,迫使宋子文辭去行政院長職務,傅斯年被社會上公認為有膽有識的諤諤之士。但他在自己一手創建的史語所內,卻不由自主地唯我獨尊,一言九鼎,聽不得不同意見,不容許出現“諤諤之士”,連游壽這樣一個無權無勢、只是個性較為剛烈、力爭自己進行學術研究權利的女學者也不能寬容對待,這不能不說是一個矛盾。這也許是中國一些知識分子的某種局限吧。只因游壽是本土派學者,學術研究路徑和傅不同,傅斯年便從一開始就對游壽給予不公正待遇,無論工作安置、名次排列,都暴露出了他的私心與陋習。博學多才的游壽進所工作四個年頭,直到被停職,始終只是一個圖書管理員的名分,后來傅斯年雖說有松綁的表示,但為時已晚,冷遇和歧視早就傷透了游壽的心。更不可理喻的是,游壽的論文審讀通過在先,且已編在所里學術刊物《六同別錄》付印,而傅將游停職一事在后,但傅斯年卻心胸狹窄,執拗地下令將游之論文從印畢的刊物中撕去,連印有游壽文章標題和署名的封面也全部銷毀,重新設計、排版、印刷,務必斬草除根,不留絲毫痕跡。這種做法有悖知識分子的道德良心,和傅斯年這樣的大學者身份極不相稱。傅斯年對不受監督的政治權力有相當警惕,為此大聲呼吁民主自由,但他對自己擁有的那一份權力卻失去警覺,說一不二,不容異見,對無權無勢的弱者游壽施以無情打擊,非得將其清除出門,不留一點余地。這種權勢者的嘴臉,人們在政治舞臺上見得很多,在文化教育領域也時有所聞,可惜傅斯年也沒能跳出權力擁有者的某種特定悲劇。
傅斯年雖然給游壽造成一定的傷害,但實事求是說,并沒有影響游壽的未來發展。傅斯年和游壽之間的恩怨是非,說到底還是屬于知識分子之間的個人矛盾和爭執范疇,不可能借助于某一政黨或其他政治組織的威權力量與名義去迫害對方。當時的體制下,傅斯年想做與能做的僅僅是讓游壽離開史語所,他既沒有任何權力對史語所之外的文化學術機構發號施令,也沒有必要和可能繼續鉗制游壽的個人發展。脫離史語所這方是非之地與尷尬處境后,游壽獲得的是廣闊的自由空間。“此處不留爺,自有留爺處”。游壽的恩師胡小石在南京有相當深厚的人脈關系,,她于是通過胡小石進入南京中央圖書館任金石部主任,負責整理接收漢奸機構保存的圖書金石拓片和日軍劫掠的文物,因此有機會接觸到大量珍貴的金石拓片及圖書文物。這一常人難得的機會成就了她在金石考證學問上的拓展和提升,順利完成了《金文武功文獻考證》、《論漢碑》等論文。1947年,游壽轉入中央大學中文系擔任副教授。之后,中國社會經歷了巨大的動蕩和變革。1949年傅斯年帶領史語所跟隨國民黨政權去了臺灣,就任臺灣大學校長,1950年12月20日因受刺激突發腦溢血去世。
1949年后,游壽先在南京大學任教,1951年調入山東會計專科學校,不久又去山東師范學院。1957年她和丈夫一起主動響應黨的號召,來到遙遠的黑龍江省,任教于哈爾濱師范學院中文系,后轉歷史系。多年來,她閉口不提有關史語所的任何話題,以致同事們都不知道她在李莊的那段生涯。“是金子總要發光”,任教之余,她在田野考古中著重研究黑龍江這片黑土地歷史上的鮮卑族文化,1963年發表了具有重要學術價值的論著《拓跋魏文化史稿》。1980年,已近耄耋之年的她系統梳理歷代文獻典籍,提出鮮卑族發源地在大興安嶺的論斷。當地青年考古學者在她的指導下,終于發現了一千五百多年前魏太平真君拓跋燾親自派使者到其祖先所居的“石室”撰刻的“祝文”。她和其他學者通過對“祝文”的破譯,揭開了鮮卑族起源的秘密,成為史學界的一件大事。值得一提的還有,游壽的書法藝術越到老年越為精湛,形成其獨特風格,終于成為我國清末以來碑學書派中第三代最重要的代表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