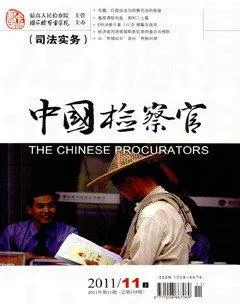瀆職侵權(quán)犯罪處罰輕緩化問題研究
司法實踐中,對瀆職侵權(quán)犯罪案件的判決存在著輕緩化的趨勢,不僅與寬嚴相濟的刑事政策不相符合,而且背離了罪刑法定原則。對此,筆者從實證的角度,針對瀆職侵權(quán)犯罪案件輕緩化問題進行探討并提出矯正對策。
一、從宏觀上看。瀆職侵權(quán)犯罪輕緩化有主觀和客觀層面的原因
(一)對瀆職侵權(quán)犯罪的社會危害性人認識不足
按照理論分類,瀆職侵權(quán)犯罪系明顯的“法定犯罪”。相對于故意殺人、強奸、搶劫等自然犯罪。其社會危害性的嚴重程度不易被社會公眾所認識。因此,嚴懲瀆職侵權(quán)犯罪人的社會呼聲并不像要求懲治其他犯罪那樣強烈。部分公民特別是個別領(lǐng)導干部對瀆職侵權(quán)犯罪案件危害性認識不足。相當多的瀆職侵權(quán)被忽視、被容忍、被“諒解”,甚至有些人對瀆職犯罪行為人抱有同情心理,認為瀆職侵權(quán)行為人是被冤枉的。加之,瀆職侵權(quán)犯罪發(fā)生在執(zhí)行職務(wù)過程中。涉及環(huán)節(jié)較多,責任相對分散,有些部門領(lǐng)導把工作失誤和瀆職犯罪混為一談,認為只要不謀私利,不收取好處,拿錢財,工作上的一點失誤。就不應(yīng)按照犯罪處理。對查辦瀆職犯罪存在抵觸情緒,有的偏袒庇護,法外說情,有的阻礙辦案。
(二)影響瀆職侵權(quán)犯罪輕緩化的立法因素
一是對瀆職侵權(quán)犯罪的入罪標準規(guī)定過高,不利于懲治與預防。人罪標準涉及犯罪圈的大小,其重要功能是威懾作用。在我國刑法中,沒有對瀆職侵權(quán)犯罪的人罪標準予以規(guī)定,由最高人民檢察院以司法解釋的惡性是確定,但是,與其他職務(wù)犯罪相比,瀆職侵權(quán)罪的立案標準偏高。
二是瀆職侵權(quán)犯罪的法定刑偏低。罪行相適應(yīng)原則要求刑罰的輕重應(yīng)當和其社會危害性一致,社會危害性大,刑罰就重,反之則輕。
三是瀆職侵權(quán)犯罪系情節(jié)犯和后果犯,作為犯罪構(gòu)成要件的情節(jié)或者后果缺乏明確性。瀆職侵權(quán)犯罪是情節(jié)犯或者結(jié)果犯,比如,在這一類犯罪的構(gòu)成要件之中,“致使公共財產(chǎn)遭受重大損失”、“情節(jié)特別嚴重”、“情節(jié)嚴重”、“造成嚴重后果”等語意表述比較模糊,缺乏對其描述性或者列舉性的規(guī)定,而現(xiàn)有的立法和司法解釋對這些表述沒有統(tǒng)一的規(guī)定,缺乏可操作性,會導致同一性質(zhì)和情節(jié)的案件,得到不同的處理結(jié)果。
(三)瀆職侵權(quán)犯罪輕緩化存在的司法原因
一方面,在檢察機關(guān)內(nèi)部缺少制約機制。根據(jù)刑事訴訟法的規(guī)定,瀆職侵權(quán)犯罪案件由檢察機關(guān)管轄,從案件初查、立案偵查、偵查終結(jié)到提起公訴等訴訟程序都由檢察機關(guān)依法進行。普遍面臨著“線索發(fā)現(xiàn)難、立案難、查處難、阻力大”的工作壓力;同時,偵查監(jiān)督、公訴部門為了配合瀆職侵權(quán)犯罪偵查部門,往往對證據(jù)認定和法律適用上審查把關(guān)不嚴,導致部分案件質(zhì)量不高。在這種情況下,公訴至法院的案件只要法院作出有罪判決。即達到了辦案效果和司法目的,至于對被告人是否判處實體刑罰,并不十分關(guān)注;對適用緩刑、免刑比例高瀆職侵權(quán)案件一般不主動啟動抗訴權(quán)抗訴率低過低也就在所難免。另一方面,沒有充分認識到瀆職侵權(quán)犯罪的社會危害性,導致對瀆職侵權(quán)犯罪分子從輕處理。法院的自由裁量權(quán)大,對瀆職官員自首或立功法定從輕減輕情節(jié)認定比較寬。而官員往往具有較高的文化水平,對國家政策和法律比較了解,善于玩文字游戲和鉆法律空子。容易表現(xiàn)出有悔罪表現(xiàn),認罪態(tài)度好的假象,法官沒有加以甄別即予以認定。對瀆職侵權(quán)犯罪者的立功、自首從寬認定,再加上法律對緩刑免刑適用條件比較原則,法官有“自由操作的空間”,自然會導致瀆職侵權(quán)犯罪案件緩刑免刑適用率畸高。
二、矯正瀆職侵權(quán)犯罪輕緩化之路徑
2010年12月,中共中央辦公廳、國務(wù)院辦公廳轉(zhuǎn)發(fā)了最高人民檢察院等九部門聯(lián)合制定的《關(guān)于加大懲治和預防瀆職侵權(quán)違法犯罪工作力度的若干意見》,據(jù)此,筆者認為,根據(jù)刑法的規(guī)定。矯正瀆職侵權(quán)犯罪輕緩化現(xiàn)象可以從以下幾個方面施以對策。
第一,完善刑法立法,嚴密懲治瀆職侵權(quán)犯罪的法網(wǎng)。首先。提高瀆職侵權(quán)犯罪的法定刑,增設(shè)資格刑和財產(chǎn)刑,明確構(gòu)成要件。將故意犯罪與過失犯罪的法定刑設(shè)置要加以區(qū)分。罪行相適應(yīng),就是罪重的量刑要重,罪輕的量刑要輕,各個法律條文之間對犯罪量刑要統(tǒng)一平衡,不能罪重的量刑比罪輕的輕,也不能罪輕的量刑比罪重的重。為了解決瀆職罪罪刑失衡問題,立法機關(guān)可以提高瀆職罪的法定刑,具體可以參照貪污賄賂罪的法定刑。以發(fā)揮刑罰的威懾作用。增設(shè)資格刑和財產(chǎn)刑。進一步強化對瀆職者的懲罰力度。法檢兩家盡快出臺司法解釋,對瀆職侵權(quán)犯罪構(gòu)成要件予以明確化。對瀆職侵權(quán)犯罪者在適用緩刑和免于刑事處分設(shè)置限制條件。我國《刑法》第397條將故意形式的濫用職權(quán)罪與過失形式的玩忽職守罪,第398條將故意泄露國家秘密罪與過失泄露國家秘密罪規(guī)定在同一條文中,并規(guī)定相同的法定刑。明顯違背了刑罰配置上的均衡性原則,這必然影響到法律的公正原則。故意罪過比過失犯罪主觀惡性大,因此,建議將故意犯罪與過失犯罪分別予以規(guī)定,并且故意犯罪要比過失犯罪設(shè)置更重的法定刑。其次,瀆職侵權(quán)犯罪分為因公和因私兩類。處以不同刑罰。我國唐律在規(guī)定官吏犯罪時將犯罪分為公私罪兩大類。如《名例律》注云:“公罪,謂緣公事致罪而無私曲者”:“私罪,謂私自犯及對制詐不以實、受請枉法之類。”由于這兩類犯罪的危害不同,故而處刑亦有原則性差別。公罪減輕,私罪從重,犯贓尤重。當前的瀆職侵權(quán)犯罪可以參照古代立法,基于犯罪的原因不同而區(qū)分公罪和私罪,并對因私的瀆職犯罪比因公的瀆職犯罪處較重的刑罰。
第二,充分運用檢察權(quán),加強對瀆職侵權(quán)犯罪的法律監(jiān)督。檢察機關(guān)既是國家的法律機關(guān),又是職務(wù)犯罪的偵查機關(guān)。因此,在查辦瀆職侵權(quán)犯罪的訴訟過程中,檢察機關(guān)肩負著偵查機關(guān)和法律監(jiān)督機關(guān)的雙重職責。一方面,除了依法進行偵查、處理瀆職侵權(quán)犯罪案件之外,還要加強對自身司法活動的法律監(jiān)督。為此,最高人民檢察院印發(fā)的《關(guān)于加強對職務(wù)犯罪案件第一審判決法律監(jiān)督的若干規(guī)定(試行)》,要求檢察機關(guān)對職務(wù)犯罪案件第一審判決實行上下兩級檢察院同步審查的工作機制,這是加強檢察機關(guān)內(nèi)部法律監(jiān)督的重要舉措,對正確運用檢察權(quán)懲治和預防職務(wù)犯罪具有重要意義。同時。正確運用檢察機關(guān)量刑建議權(quán)進行事前監(jiān)督,可有效防止法院量刑權(quán)偏離其合理范圍。檢察院提出量刑建議應(yīng)包括自首、立功、悔罪態(tài)度好等從輕減輕情節(jié);緩刑、免刑的適用,刑期的確定三部分內(nèi)容。因此,檢察院量刑建議沒有涉及緩刑免刑的,法院就不得適用緩刑免刑。法官如果不按量刑建議判,檢察機關(guān)可以作為抗訴的理由進行抗訴。
第三,完善司法機制,形成懲治瀆職侵權(quán)犯罪的合力。首先,建立瀆職侵權(quán)案件人民監(jiān)督員和陪審員制度,保障司法公正。人民監(jiān)督員參與監(jiān)督相對不起訴案件的討論決定,人民陪審員參與審理瀆職侵權(quán)案件。可以起到良好的社會效果、政治效果和法律效果。相對來說。人民監(jiān)督員、陪審員受到社會各種因素的干擾遠遠低于檢察官和法官,他們能從社會公眾的角度出發(fā)考慮瀆職犯罪案件社會上的反映,能夠有效的監(jiān)督與制約司法權(quán)利,有助于加深公民對司法制度的認同。提高公民對法律制度的接受與信任的程度,從而能作出客觀公正的決定。有利于維護法律的尊嚴。其次,在審判環(huán)節(jié)建立緩刑免刑前置聽證制度。對于法院擬判處緩刑和免刑的瀆職侵權(quán)犯罪案件,應(yīng)設(shè)前置聽證制度。沒有經(jīng)過聽證程序,法院不得判處緩刑和免刑。舉行聽證會,通過聽取法學專家、人大代表、政協(xié)委員、人民陪審員、被告人所在單位人員等不同身份的人的意見,可以為法官作出最終判決提供參考意見。從而使法官作出的裁判更加客觀公正。同時,公開聽證接受媒體和社會監(jiān)督,增加了審判透明度,尊重和滿足了社會公眾的知情權(quán),不失為社會監(jiān)督的有效方法。兩
注釋:
[1]王漢斌1997年3月6日在第八屆全國人民代表大會第五次會議上《關(guān)于(中華人民共和國刑法)(修訂案)的說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