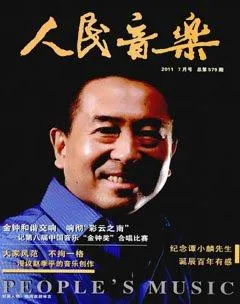區(qū)域音樂研究的方法論基礎(chǔ)——系統(tǒng)論
區(qū)域音樂研究是近年來興起的中國傳統(tǒng)音樂研究面向新對象和運用新方法的研究。從研究對象上來看,區(qū)域音樂研究不再是針對某個樂種、歌種、劇種、舞種的研究,而是一個區(qū)域所有的傳統(tǒng)音樂的綜合性、整體性、系統(tǒng)性的研究;從研究方法上來看,區(qū)域音樂研究采用的不再是單獨的描述、考據(jù)、調(diào)查、比較的研究方法,而是整體性的普查、綜合性的描述、系統(tǒng)性的分析研究方法。區(qū)域音樂研究并非概念形式的翻新,而是中國傳統(tǒng)音樂研究的實際需要;區(qū)域音樂既是中國傳統(tǒng)音樂的一項研究內(nèi)容,也是中國傳統(tǒng)音樂研究的一種方法。
一、區(qū)域音樂研究是具有中國特色的
民族音樂學(xué)研究
20世紀80年代初期,“民族音樂學(xué)”新概念開始在中國民族民間音樂研究領(lǐng)域流行,為當時的民族民間音樂研究注入了新思維、新理念、新方法。以喬建中、苗晶等為代表的一批學(xué)者們,將民族音樂學(xué)的學(xué)科理念和方法與中國傳統(tǒng)音樂的實際結(jié)合起來,著手研究中國傳統(tǒng)音樂呈地域性分布的問題,提出了“民歌色彩區(qū)”和“地理音樂學(xué)”等新概念。
民族音樂學(xué)的研究對象一般是非歐洲主流社會的邊遠地區(qū)、人口稀少的少數(shù)民族、瀕臨消失的文化種群中的傳統(tǒng)音樂,這種音樂往往是自成體系的單個音樂現(xiàn)象或單個音樂品種。用歐洲音樂的話語系統(tǒng)將其描述出來,或者以歐洲音樂作為參照系進行比較性的研究,進而考察這種音樂產(chǎn)生的文化和自然背景,分析這種音樂為何如此的原因及這種音樂本身的社會功能與價值體系。
然而,中國傳統(tǒng)音樂既不是地處邊遠人口稀少的民族音樂,也不是瀕臨消失的文化種群中的民族音樂,中國傳統(tǒng)音樂所在的區(qū)域遼闊,覆蓋的人口眾多;而且,中國傳統(tǒng)音樂的歷史悠久、品種之多,不同音樂品種之間的關(guān)系錯綜復(fù)雜,這是任何一個民族或國家的傳統(tǒng)音樂都無法與之相提并論的。所以,一般用于單一音樂現(xiàn)象或單一音樂品種研究的民族音樂學(xué),當面對中國傳統(tǒng)音樂這個龐大體系時,其學(xué)科理念和研究方法就顯得力不從心和難以駕馭,民族音樂學(xué)在中國也就需要作因地制宜的改造。
1980年以來的三十年,民族音樂學(xué)在中國大致經(jīng)歷了三個階段:
第一階段是學(xué)習(xí)引進階段,這個階段大約從1980至1990的十年間,涌現(xiàn)出了喬建中、王耀華、沈恰、杜亞雄、俞人豪等一大批學(xué)者群體,他們致力于民族音樂學(xué)的宣傳、介紹、引進,并有意識地運用民族音樂學(xué)的學(xué)科理念和研究方法對部分中國傳統(tǒng)音樂品種進行了開拓性的研究。
第二階段是運用提高階段,這個階段大約從1990至2000的十年間,中國藝術(shù)研究院、中央音樂學(xué)院、中國音樂學(xué)院、上海音樂學(xué)院、福建師范大學(xué)等高等院校在民族音樂學(xué)或中國傳統(tǒng)音樂理論等專業(yè)方向的旗號下,培養(yǎng)了一大批碩士、博士研究生,其中許多研究生直接運用民族音樂學(xué)的學(xué)科理念和研究方法,形成了一批豐碩的研究成果。
第三階段是分化發(fā)展階段,這個階段大約從2000年開始,一直持續(xù)至今,這個階段的民族音樂學(xué)研究出現(xiàn)了分化發(fā)展的局面。民族音樂學(xué)的分化大致有三個方向:第一,堅持民族音樂學(xué)原初的研究對象和研究方法,堅持在一定的社會文化、自然地理背景下進行中國傳統(tǒng)音樂的個案研究,堅持民族音樂學(xué)的音樂學(xué)科本位;第二,側(cè)重中國傳統(tǒng)音樂的文化背景研究,學(xué)科歸屬由音樂學(xué)遷移到人類學(xué)或民族學(xué),學(xué)科稱謂也由“民族音樂學(xué)”置換為“音樂人類學(xué)”;第三,基于對民族音樂學(xué)研究的“公式化”傾向和對“音樂人類學(xué)”遠離音樂而去的批評,致力于中國傳統(tǒng)音樂自身的理論體系研究和中國傳統(tǒng)音樂品種的個案研究,放棄“民族音樂學(xué)”和“音樂人類學(xué)”等外來的學(xué)科稱謂,而以“中國傳統(tǒng)音樂研究”或“中國傳統(tǒng)音樂理論研究”為自己的學(xué)科旗幟。
民族音樂學(xué)或音樂人類學(xué)的理論和所采用的分析研究,都沒有脫離16世紀法國哲學(xué)家笛卡爾奠定的理論基礎(chǔ)分析方法,這種分析方法把事物分解成若干部分,抽象出最簡單的因素來,然后再以部分的性質(zhì)去說明復(fù)雜的事物;然而這種分析與研究的方法用于中國傳統(tǒng)音樂的研究實踐時,由于不能如實地說明對象的整體性,不能反映各種音樂現(xiàn)象之間的聯(lián)系和相互作用,它只適應(yīng)認識具體的音樂事項,而不勝任于復(fù)雜的中國傳統(tǒng)音樂研究。將系統(tǒng)論引入中國傳統(tǒng)音樂的研究,則不僅可以彌補笛卡爾的理論基礎(chǔ)分析方法的局限,而且還可以把“民族音樂學(xué)”、“音樂人類學(xué)”、“中國傳統(tǒng)音樂理論研究”等的學(xué)科理念和研究方法整合為中國傳統(tǒng)音樂理論的系統(tǒng)論研究方法,運用了系統(tǒng)論研究方法的區(qū)域音樂研究,是民族音樂學(xué)在中國的延伸與發(fā)展,所以,區(qū)域音樂研究也是具有中國特色的民族音樂學(xué)研究。
二、區(qū)域音樂是需要進行系統(tǒng)性研究的對象
中國傳統(tǒng)音樂的體系龐大,不同區(qū)域的傳統(tǒng)音樂彼此差異性較大,而同一區(qū)域的傳統(tǒng)音樂雖然表]形式、結(jié)構(gòu)方式也有較大的不同,但是都毫無例外地具有某些共性聯(lián)系,這就使得區(qū)域音樂研究具有了必要性和可能性。
其實,中國是世界上最早進行音樂的區(qū)域性劃分和區(qū)域性研究的國度,最晚在春秋時期,中國人就已經(jīng)發(fā)現(xiàn)了音樂的風格和形態(tài)是以地區(qū)性分布呈現(xiàn)的,據(jù)說孔子修訂的第一部詩歌總集《詩經(jīng)》就把160篇地方性民歌分作15個地區(qū),亦即十五國風,“十五國風”也就是當時區(qū)域音樂劃分和研究的成果。隨著社會的發(fā)展和民族的融合,中國的區(qū)域文化發(fā)生了很大的變化,至20世紀初,中國已經(jīng)形成了東部漢族為主的農(nóng)耕文化和西部少數(shù)民族游牧文化兩大部分,就東部漢族為主的農(nóng)耕文化而言,大致可以再分為中原文化、齊魯文化、三秦文化、荊楚文化、江南文化、巴蜀文化、嶺南文化、閩臺文化、東北文化等九個文化區(qū)域。文化區(qū)域的形成既有自然地理方面的原因,也有文化傳統(tǒng)方面的原因,在眾多因素中,生產(chǎn)方式和語言風俗應(yīng)該是兩個具有本質(zhì)意義的原因。
音樂是區(qū)域文化的一個重要組成部分,也是劃分文化區(qū)域的重要依據(jù)之一。一個區(qū)域的音樂與這個區(qū)域的地理環(huán)境、氣候條件、生產(chǎn)方式、生活方式、風俗習(xí)慣、信仰習(xí)慣、文化傳統(tǒng)都有密切的聯(lián)系,而且相互間的關(guān)系錯綜復(fù)雜。
由于中國傳統(tǒng)音樂是一種具有悠久的歷史傳承和高度發(fā)展的音樂,自身的體系完備,品種眾多,即使在同一個文化區(qū)域里,不同體系的音樂和不同形態(tài)的音樂共存一處也是常見的現(xiàn)象,而且不同體系和不同形態(tài)的音樂又有著深度的交融。例如,一般認為民歌是其他民間音樂的基礎(chǔ)形式,民間器樂最初是民歌曲調(diào)的]奏,而后起的說唱、戲曲也是在民歌的基礎(chǔ)上發(fā)展而成的;但是,器樂對民歌的進一步發(fā)展又有支撐的意義,如四川民歌《太陽出來了》的襯詞:“挑起扁擔郎郎才,匡才”及河北民歌《對花》的襯詞“七不龍冬七打七,八不龍冬鏘冬鏘”等都是由鑼鼓經(jīng)改造而成的;許多戲曲的唱段轉(zhuǎn)而成為民歌傳唱事例也都是不勝枚舉的。區(qū)域音樂中,幾乎是同型的音樂結(jié)構(gòu),用于不同場合或不同表]形式時,其稱呼也就發(fā)生了變化;相反,稱呼相同的音樂曲牌,其音樂形態(tài)卻可能完全是兩個不相干的類別。
正是因為區(qū)域音樂復(fù)雜性的特點,傳統(tǒng)的田野調(diào)查、分析研究、比較研究已經(jīng)無法勝任區(qū)域音樂研究的需要,所以,進行區(qū)域音樂研究就必須對研究對象進行明確的界定,對研究方法更要進行仔細的論證。
三、系統(tǒng)論是區(qū)域音樂研究的方法論基礎(chǔ)
“系統(tǒng)”指的是由部分構(gòu)成整體的結(jié)構(gòu)形式。中國古代哲學(xué)中的“天人合一”思想就是把人與自然視為一個大的系統(tǒng)。現(xiàn)在所說的“系統(tǒng)”(System)來源于古希臘語,原義是部分構(gòu)成的整體。“系統(tǒng)”的思想雖然源遠流長,但作為一門科學(xué)的系統(tǒng)論,卻一直到20世紀60年代才逐步確立。一般認為美籍奧地利生物學(xué)家L.V.貝塔朗菲1968年發(fā)表的專著《一般系統(tǒng)理論基礎(chǔ)、發(fā)展和應(yīng)用》是系統(tǒng)論這門學(xué)科誕生的標志。
系統(tǒng)論認為:任何系統(tǒng)都是一個有機的整體,它不是各個部分的機械組合或簡單相加,系統(tǒng)的整體功能是各要素在孤立狀態(tài)下所沒有的新質(zhì),亞里斯多德的名言“整體大于部分之和”是對系統(tǒng)的整體性精妙的解釋;系統(tǒng)論同時還認為,系統(tǒng)中各要素不是孤立地存在著,每個要素在系統(tǒng)中都處于一定的位置上,起著特定的作用,要素之間相互關(guān)聯(lián),構(gòu)成了一個不可分割的整體,如果將要素從系統(tǒng)整體中割離出來,它將失去要素的作用。
系統(tǒng)論出現(xiàn)之前的研究方法,一般是把事物分解成若干部分,再以部分的性質(zhì)去說明復(fù)雜事物的分析方法。這種方法的著[點在局部或要素,它雖然在特定范圍內(nèi)行之有效,但是它不能反映事物之間的聯(lián)系和相互作用,它只適應(yīng)認識較為簡單的事物,而不勝任于對復(fù)雜問題的研究。所以,在規(guī)模巨大、關(guān)系復(fù)雜、參數(shù)眾多的復(fù)雜問題面前,傳統(tǒng)的分析方法難免捉襟見肘,而系統(tǒng)分析方法卻能高屋建瓴,綜觀全局,為分析現(xiàn)代復(fù)雜問題提供了有效的思維方式,也為解決現(xiàn)代社會中的政治、經(jīng)濟、軍事、科學(xué)、文化等方面的復(fù)雜問題提供了方法論的基礎(chǔ)。
中國是世界上最早把音樂作為一個系統(tǒng)看待的國度,如《呂氏春秋·大樂篇》論及音樂本原時說:“音樂之所由來者遠矣;生于度量,本于太一。太一出兩儀,兩儀出陰陽。陰陽變化,一上一下,合而成章。渾渾沌沌,離則復(fù)合,合則復(fù)離,是謂天常。天地車輪,終則復(fù)始,極則復(fù)反,莫不咸當。日月星辰,或疾或徐;日月不同,以盡其行。四時代興,或暑或寒,或短或長,或柔或剛。萬物所出,造于太一,化于陰陽。萌芽始震,凝 以形;形體有處,莫不有聲。聲出于和,和出于適。先王定樂,由此而生。”《樂記》也有類似的記載:“聲成文謂之音”,“比音而樂之,及干戚羽旄謂之樂。”同時,《樂記》對這種綜合性的表]形式有著極力推崇的價值取向,如:“知聲不知音者,禽獸是也,知音不知樂者,眾庶是也,惟君子為能知樂也。”
可見,在中國從傳統(tǒng)思維中,音樂又是一個完整的文化系統(tǒng),是綜合性的表]藝術(shù),而不是一種具體的技藝。中國傳統(tǒng)文化中音樂的整體性和綜合性為上的觀念與西方音樂的“純音樂”為上的觀念相比,具有截然不同的價值觀取向。
鑒于區(qū)域音樂的復(fù)雜性和中國傳統(tǒng)音樂綜合性的情況,系統(tǒng)論的研究方法應(yīng)是其主要的研究方法。
四、區(qū)域音樂研究、民族音樂學(xué)、中國傳統(tǒng)音樂理論研究的比較
“區(qū)域音樂研究”的概念提出以后,關(guān)于中國傳統(tǒng)音樂或者民族音樂的研究至少有三種彼此有一定聯(lián)系但又有各自取向的研究,分別是民族音樂學(xué)研究、中國傳統(tǒng)音樂理論研究、區(qū)域音樂研究。
1.民族音樂學(xué)研究。民族音樂學(xué)研究的對象是在一個特定文化背景下的一個具體的音樂事項;民族音樂學(xué)的學(xué)科理念是文化價值相對論;民族音樂學(xué)的研究是以田野調(diào)查得到的第一手資料為研究的基本材料,運用分析的和比較的方法所進行的研究。
2.中國傳統(tǒng)音樂理論研究。中國傳統(tǒng)音樂理論研究的對象是文獻典籍上記載的或者現(xiàn)實社會中依然存見的具體音樂事項;中國傳統(tǒng)音樂理論研究的學(xué)科理念是“中國音樂中心論”(不是說中國音樂是世界音樂的中心,而是說中國傳統(tǒng)音樂有其自身的理論體系,這個體系應(yīng)是中國音樂的中心,就像歐洲音樂是歐洲音樂的中心而不是世界音樂的中心一樣);中國傳統(tǒng)音樂理論研究是以文獻典籍記載的第二手資料為主,以田野調(diào)查的第一手資料為補充,運用考據(jù)的、田野調(diào)查的和理論分析的方法所進行的研究。
3.區(qū)域音樂研究。區(qū)域音樂的研究對象是一個相對獨立的文化區(qū)域內(nèi)所有的音樂事項;區(qū)域音樂研究的學(xué)科理念是文化多元論,即認為世界文化是由多個源點的文化中心構(gòu)成的,不同的文化源點構(gòu)成了不同的文化中心;區(qū)域音樂研究是既重視文獻記載的音樂事項,又重視現(xiàn)實社會中依然存見的音樂事項,運用系統(tǒng)論的研究方法所進行的研究。
如果說民族音樂學(xué)的公式是:
特定文化背景中的音樂+文化價值相對論+田野調(diào)查+分析研究+比較研究
那么,中國傳統(tǒng)音樂理論研究的公式則是:
文獻記載或現(xiàn)實生活中的音樂+中國音樂中心論+歷史考據(jù)+田野調(diào)查+分析研究
那么,區(qū)域音樂研究的公式則是:
特定區(qū)域文化系統(tǒng)中的音樂+文化多元論+歷史考據(jù)+田野調(diào)查+系統(tǒng)論研究方法
現(xiàn)在,可以為“區(qū)域音樂”和“區(qū)域音樂研究”進行概念性的界定了。
所謂“區(qū)域音樂”指的是:一個相對獨立的文化區(qū)域內(nèi)所有的傳統(tǒng)音樂事項的總和。
所謂“區(qū)域音樂研究”指的是:運用系統(tǒng)論的研究方法,對一個相對獨立的文化區(qū)域內(nèi)所有的傳統(tǒng)音樂事項進行的體系的和自然與人文背景的研究。
由于“區(qū)域音樂研究”具有多項目的綜合性和多學(xué)科的交叉性,往往非個人的研究能力所及,因此,“區(qū)域音樂研究”主要靠一個研究團隊去共同完成,這種集體性的研究,也是過去民族音樂學(xué)研究或中國傳統(tǒng)音樂理論研究都沒有遇到過的。
“區(qū)域音樂研究”的團隊性要求并非一定是有組織的團隊,也可以是松散的學(xué)者群,針對一個特定的區(qū)域音樂,或者是特定區(qū)域音樂的文化背景,或者是特定區(qū)域音樂的自然地理背景所進行的方方面面研究的集合。近年來,有些學(xué)者不斷批評“音樂人類學(xué)”、“儀式音樂”、“民族音樂學(xué)”的研究遠離音樂而去,也有學(xué)者批評“中國傳統(tǒng)音樂理論研究”脫離現(xiàn)實基礎(chǔ)重歸“國粹”之路等等,然而,這些彼此的批評和攻伐,在“區(qū)域音樂研究”的旗幟下全都化解為一體,而且“區(qū)域音樂研究”正好也需要這些方方面面的研究,就某個學(xué)者個體而言,他的研究或許遠離音樂甚至與音樂毫無關(guān)系,他的研究或許完全脫離了現(xiàn)實社會存在,然而,在“區(qū)域音樂研究”的范疇里這些恰好都是它的有機組成部分,“區(qū)域音樂研究”把幾乎分道揚鑣的學(xué)者們又重新召喚在了一起。
田耀農(nóng) 博士,杭州師范大學(xué)音樂學(xué)院院長、教授
(責任編輯 張寧)